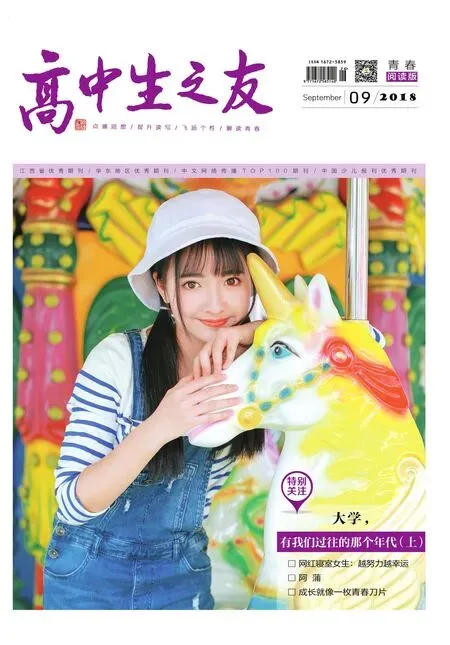创作谈:作家是棵树
○阿 袁

我最初迷恋上写作,是因为写作可以虚构。
世上本来没有贾府,曹雪芹虚构出了一个,里面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的宝玉,有“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的黛玉,还有“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的王熙凤。我一直想不明白“吊梢眉”是什么样子的,想必不好看,曹雪芹不喜欢王熙凤,所以就让她长了三角眼和吊梢眉;而宝玉呢,明明是个男的,却长成中秋之月、春晓之花的样子。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曹雪芹是喜欢女人不喜欢男人的,所以有“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之说,但就凭这个春晓之花的描写,我知道曹雪芹至少是喜欢宝玉的,不过是把他当女人那样来喜欢了。
这真是当作家好玩的地方,类似于上帝造人。一个人,你想让他长什么眉眼,他就长什么眉眼,你想让他有什么性格,他就有什么性格,甚至他的命运,都攥在作家的手心里。我看到宝玉出家去当和尚的时候,真是过瘾。我年轻时特别讨厌薛宝钗,觉得正是她从中作梗,才害得林妹妹和宝哥哥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的,所以曹雪芹让她孤独终老,那是她活该。不过,我那时对曹雪芹还是很有意见的,觉得《红楼梦》的结局没有写好(后来知道错怪了他,其实这是高鹗做下的事)。如果由我来写后四十回,我一定要让宝哥哥最后娶上林妹妹。我第一个写作的愿望,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与其说是想当作家,不如说是想当侠客,有为天下打抱不平的意思。
这种想法当然幼稚,但年少时的我,真是以为当作家就和当上帝差不多。
等到自己真开始写小说了,才知道作家根本不是上帝,左右不了小说里的人物。小说里的人物,其实都有自己的命运,甚至有自己的长相。你不能让黛玉长成面如中秋之月,你也不能让黛玉长三角眼、吊梢眉,她只能楚楚可怜地长着“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所以托尔斯泰在写《安娜·卡列尼娜》时,最后是被安娜牵着鼻子走的。他最初只想写一个上流社会已婚妇女失足的故事,她趣味恶俗、卖弄风情、品行不端;但写着写着,不由自主地把她写成了一个趣味高雅、敢于追求爱情与自我的光辉形象。可以说,不是托尔斯泰写了安娜,而是安娜写了安娜自己。
这似乎有些玄了,但如果一个作家想要创作出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那么,他笔下的人物确实就有自己的方向,人物是不由作家随意虚构的。
所以,作家不是上帝。
那作家是什么呢?
张爱玲在《写什么》里说:“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也就是说,作家是棵树。他的根在哪儿,他就只能写哪儿。这并不像我最初以为的那样。所以福克纳就只写美国南方那一枚邮票大小的地方,张爱玲就只写上海旧式家庭里那些遗老遗少,艾丽丝·门罗呢,写到80多岁,写作几乎终其一生了,可写来写去也只写了加拿大安大略一个叫Wingham的小镇。
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在写作《雪》这部小说时,因为主人公卡在法兰克福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5年,为了真实地描写卡的生活,帕慕克去了法兰克福。在小说里,卡每天清晨从家出发,去市立图书馆,图书馆是卡度过大部分时间的地方。于是,帕慕克亲自体验了这段路程,他穿过车站前的广场,沿着大街,经过土耳其杂货店、肉店。他还去了卡买大衣的百货商场,那件大衣卡穿了许多年,给了卡许多安慰。“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做了很多冗长、看起来不必要的笔记。就像一个初写小说的人,我会为每一处细节而痛苦,会问自己:1980年代的电车真的是这样开过街道的吗?”
这是种子被风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