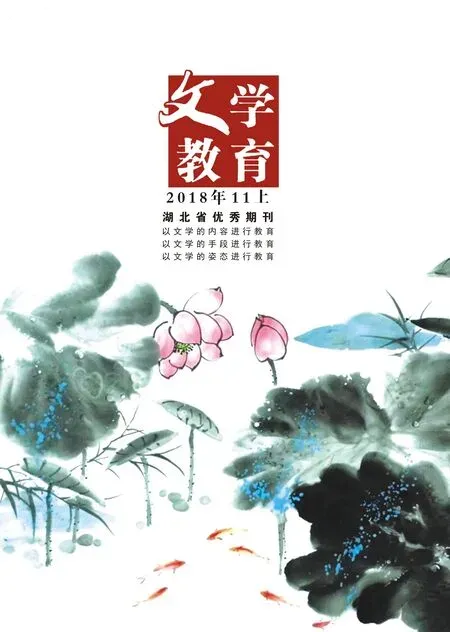当代俄罗斯女作家小说中女性家庭生活的悲剧性解读
曾 佳
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改变了苏联的政治版图的同时,也造就了新的文学格局。新古典主义、后现代主义、新现实主义等各种文学风格异彩纷呈,凸显出多元化倾向。以彼特鲁舍夫斯卡娅、乌利茨卡娅、托尔斯泰娅为代表的俄罗斯女性作家也以自身独特的创作时间改变了女性文学的传统风貌。
19世纪俄罗斯经典文学里,人们熟知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有“俄罗斯的灵魂”之称的达吉扬娜、《战争与和平》里“可爱而富有诗意”的娜塔莎、《大雷雨》里“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的卡捷琳娜等等,隐喻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女神般存在的女性。而托尔斯泰娅轰动一时的小说《野猫精》则描写了人类退化为“野猫精”的荒诞故事,隐喻的是一群性格多变、过度纵欲,充斥着动物本能的女性人物,“她们都是些没文化的傻瓜!除了自己的女人问题,她们什么也不想知道”。嗜吃如命、整日无所事事的中心人物奥莲卡总是对一切食物津津乐道,多自己的烹饪技术夸夸其谈、乐此不疲地炫耀。人性异化的“奥莲卡”们喜欢在“恶”中寻求精神的满足和愉悦。秘密警察头目试图借本尼迪克夺取政权,将俄罗斯文化生活的守护者尼基塔处死。只知道“嘻嘻哈哈寻开心”的奥莲卡“只想多做些漂亮衣服,好在每次去看公开斩首、用车子碾死人或割舌头等热闹时,都能穿着新衣服。”托尔斯泰娅笔下的傻女佣索尼娅(《索尼娅》),家庭女教师舒拉(《亲爱的舒拉》)同样是丑恶、玩世不恭的。她们的命运大多以悲剧结束。
俄罗斯文学传统文学里母亲更一直被塑造为“家的天使”、谦逊恭顺、有着崇高牺牲和奉献精神的圣母形象。但在女作家的艺术世界中,唯美女性的雕像轰然崩塌,活跃着的是要么是一群“把母职变为统治,把母爱化作虐待”,甚至是几乎“丧尽母性”的颠覆传统的恶母形象。母性的“变异”构成了作家小说中家庭悲剧的重要因素。曾获普希金奖,并入围俄语布克奖短名单,在俄罗斯文坛引起强烈反响的小说《夜深时分》中,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塑造了主人公单身母亲安娜·安德里阿诺夫娜。没有固定工作的安娜生活窘困到令人窒息的地步。为了食物、住房,对子女整天无休止地咒骂。在她口中女儿是“免费的妓女”、“白送上门的情人”,女婿则是“畜生”、“下流胚子”。而儿子和女儿眼中的她是“母狗”、“疯子”。她无所顾忌地偷看女儿的日记,还在上面留下恶毒的评语;女儿即将生育时断然拒绝对她的帮助。安娜的母爱得不到子女的理解和回应,因怨生恨,变得畸形。同样,《小格洛兹娜娅》中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里的母亲格洛兹娜娅,她的生活史也是“一部和亲生子女争斗的血泪史”。为了争夺住房与亲生子女大打出手,而撵走了子女的她最后“躺在一平方半米的棺材里,就像被所有人抛弃的精神病人一样,显得寒酸、矮小、凄凉”。此外,在她的多部小说中甚至还出现了现代版的“美狄亚”———以各种理由杀婴的母亲。同名小说《美狄亚》中,母亲因报复丈夫的不忠行为而手刃亲生女儿。《济娜的选择》里失去丈夫的济娜在无力抚养三个孩子的情况下,为保全其他两个孩子,她选择了将刚出世的儿子“送出去”。《婴儿》中的母亲由于无法承受绝望的现实生活,意欲用锥子结果襁褓中嗷嗷待哺幼儿的性命。《婴儿》通篇均用“她”来指称这个残酷无情的母亲,意欲表现的是具有相同行为的无数个“她”。社会规范要求女性在平凡的家庭生活中做一个慈爱的母亲,子女原本是将其与传统社会秩序相连的纽带,母亲杀死自己的孩子,割断或刻意否定了这一自然生成的血缘联系,必然会陷入道德的无序和混乱。而杀死孩子的女性,意味着对未来、对生活已然绝望。这两位作家所描写的如妖魔般的女性、令人惊骇的毫无舐犊之情的母亲回归到了残酷的现实生活,解构了文学童话中传统女性形象模式,使“永恒女性”的神话化为泡沫。
家庭成员关系的扭曲是作家们作品中着力描写的主题。她们洞察了家庭中父母与子女间剧烈的矛盾对峙、夫妻间的背叛和冷漠、老人情感的孤独和无所依托。乌利茨卡娅小说《布罗恩卡》、《索尼奇卡》、《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中的哀怨的主人公都要面对丈夫的背叛和婚变。《夜深时分》中家则成了母亲安娜与子女们的角斗场。安娜年轻时曾与有妇之夫发生婚外情而被报社开除,而面对情感变动不居的女儿追求“幸福”,她以爱为出发点对其横加指责,试图让女儿服从。母亲上演的“家庭式专制主义”激发了儿女们的“反母性”,致使亲情演变成敌我关系。最后她不再被人需要,儿子、女儿、心爱的外孙相继弃她而去,安娜绝望地离开人世。而步入老年却得不到家的慰藉更平添许多悲凉。《魂断蓝桥》中的被丈夫抛弃孑然一身的奥利娅奶奶白天像工蜂一样埋头苦干,晚上便和一群老妇人一起去影院享受精神上的爱情大餐,渴望像电影《魂断蓝桥》主人公那样在蓝桥边遇到自己的爱情,而真实世界却事与愿违,她感觉自己“像准备起飞的擦脚垫:整个世界都把她遗忘了……”。《幸福的晚年》里波林娜和丈夫谢苗每天不断地争吵,吵得“两个人气得浑身颤抖,痛苦不堪”,儿子和媳妇惦记的是父母的遗产,为了得到房子“恨不得把父母都毒死”,她视为生命般的孙子则“懒得与他们打交道”。对晚年生活深深失望的波林娜在听到丈夫久违的一句关怀的话语后竟然“号啕大哭起来”。爱人背叛,亲人反目,家已如同噩梦般支离破碎。作家们摒弃了传统小说的叙事原则,呈现了俄罗斯社会变动时期普遍存在的家庭冲突和重重矛盾,从中我们看到爱情和亲情褪去温馨圣洁的外衣,裸露出变形、绝望和丑陋的内部。
作家们描绘的家庭里丈夫或父亲的角色大多隐匿,或者死了,或者在孩子幼小时就抛弃了妻子、儿女。即便有丈夫,也是依附寄生于女性生活,原本作为家庭秩序的建立者和维护者的男性成为懦弱、自私和贪婪的边缘化存在。失衡的家庭结构,即父权的衰微和男性的不作为象征着“男权”的消解,男性与女性组建的两性社会关系随之陷入混沌状态。我们看到在乌利茨卡娅三部长篇小说《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以及《您忠实的舒里克》中从背叛女性的萨穆伊尔,到开始关注女性但内心并不尊重女性的库科茨基,发展到发自内心爱护女性,甚至性格上也有些“女性化”的舒里克,男性们形象发生了微妙的嬗变,同时印证了当代俄罗斯社会父权文化的衰变。作家们描绘的纯粹的女性世界里,男人们道德堕落、生活腐化,无法让人依靠,感情无处慰藉的女人们在“爱的缺失”中孤独地生活。爱情的“缺失”往往被视为女性恶劣生存环境的根源之一,安娜一家身处逼仄的居所,几乎每天都要绞尽脑汁获取哪怕是一丁点儿食物;以女诗人自居的她会在作完报告后的晚餐时间偷两块夹黄油的面包;女婿睡醒后第一件事是冲进厨房抢最后几颗鸡蛋。可见,男性责任感的“缺席”加重了女性家庭生活的窘迫,使得单亲母亲们独自承担经济压力,面临极度匮乏的物质生活条件,几乎总是在赤贫与饥饿中挣扎,替代欢愉的家庭生活的是无尽的煎熬和磨难。
“悲剧是人的苦难和死亡。这苦难或死亡即使不显出任何无限强大与不可战胜的力量,也已经完全足够我们充满恐怖和同情。”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女性作家都曾聚焦死亡这一主题。“阅读十个女作家的作品,越读越可怕……第一个小说中描写死亡,第二个也是,第三个里面,死去的女主人公正从自己母亲的坟墓里探出身子”。各种死亡的面孔通过不同的手段呈现:自杀、谋杀、意外死亡甚至是不明原因的死亡。各个年龄的人群都弥漫着如影随形的死亡阴影,乌利茨卡娅《欢乐的葬礼》中阿历克面临无可逃避的痛苦而窒息身亡;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约克·阿诺》、《细菌》中青少年酗酒、吸毒选择自杀身亡;《客人》、《来自玛雅人部落的玛雅》和《谢辽沙》等则描写了中老年人的自杀。这些人物在面临生活和心灵危机时都试图用死亡从痛苦和残酷现实的重负中解脱。
女作家们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冷峻地审视女性爱情、家庭日常生活、人际关系中的善恶美丑,将其中最阴暗恐怖、肮脏丑陋的一面赤裸裸地还原和放大。题材多样、风格不同的创作再现了改革时期苏联和俄罗斯民众的生活状况。始终贯穿其创作的核心是女性,而家庭往往成为作家们笔下女性生活悲剧的演绎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