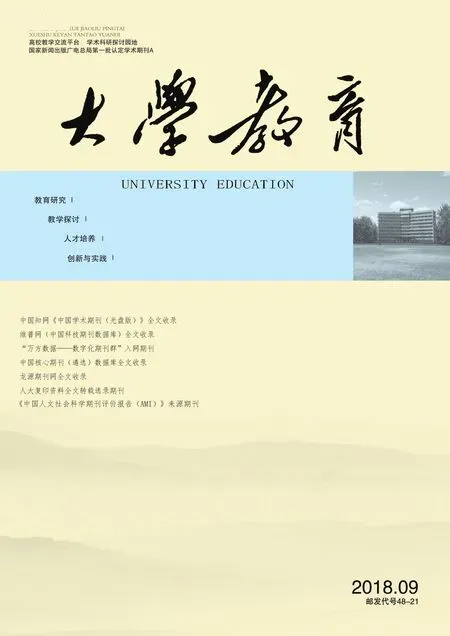论无所不在的悲剧冲突下的人类生活
——以《奥德赛》十一卷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神话故事为基础
(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120)
本研究以《奥德赛》中的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神话故事为话题缘由,引发对当下“人”的生活状态之思考。文章标题或许让人觉得只是一个“噱头”,甚至让人不可接受——生活如此美好,又怎能用悲剧简而概之呢?笔者只是想借此揭露出深藏于我们自己身上那些对于大众而言也许是一闪而过,抑或是不期而遇、如影随形的东西。
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论证笔者的观点,但同时笔者承认这四个方面不可能囊括人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那些具体的悲剧冲突),也承认这四个方面的简单相加绝不可能等于笔者观点的总和。笔者主要从一种宏观的思辨性的角度探讨“无所不在的悲剧冲突下的人类生活”,尝试提供一种思路来审视我们当下的生活。
一、个体与群体的生存
长久以来,人作为一种群居性动物,总是不能切割掉与他人、外界的联系,社会性是人的必然属性。家庭是每个人生活的最小单位,家与我们每个个体是密切相关的。生前的家,死后的冢,说明人从出生之日到死亡之时,都与家息息相关。
首先讨论家于我们个体的含义,要明白“家庭”指代的是什么。我们谈论家庭说得最多的是“血缘亲情”、“血浓于水”,因此大多数家庭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家庭,诸如领养、离异重组家庭。我们能够说血缘关系就牢固可靠吗?一方面我们能看见许多领养、重组家庭的幸福美满;另一方面我们还看见许多夫妻反目成仇的例子,许多老人即使膝下儿女成群,但是赡养老人的责任却像“踢皮球”一样滚来滚去。显然血缘关系并不能使家庭关系更牢固可靠。
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就诞生于希腊人强烈的个体意识产生的基础之上,独立化的公民从传统氏族公社的自然血缘中分裂出来、独立出来,由此“人与人之间那种天然的血缘关系就疏远了,作为血缘亲情的家庭关系也就淡化了”[1]。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提问自己:“就连血缘都不那么牢固了,还有什么是牢不可破的呢?”我们这样思考下去就会发现一个更有趣的现象(事实)——古时常说的“夫妇有别”,意即夫和妻双方的家族是不同的。现在,法律更规定了近亲三代不能结婚——这就表明了至少要结婚共同孕育下一代的两人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那什么才是建立家庭的基础呢?答案是情感。血缘是纵向跨越时间和朝代的,情感则是横向的。这样一看或许可以得出血缘比情感更为重要。你可以不关心你的祖先但是你一定会在意你现在生活的世界——你用情感建立起来的世界,所有对你有意义的事物无不附加上你的情感色彩。所以只能说血缘是其中主要的原因,而情感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除了家之外,人的一生的发展还离不开朋友或恋人。我们可以接着提问:“这样的关系真的是稳固的吗?”爱本身就是一个依靠运气和情绪的产物。对于感情和环境的多变的讨论已有太多大家之作,在此就不细谈了。但是爱情的崇高仍是许多人孜孜以求的。
如果这些关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统统都是脆弱的,只剩下生活在世界上的每个个体是唯一不可被冲击的最小单位。永远都是“我”一个人面对整个世界,即使与你的伴侣、你的孩子朝夕相伴,但他们始终完全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之间隐隐约约存在着一种隔膜感、陌生感。但进一步,就是连“我”自己这样一个独立的个体也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分裂。这种分裂如同精神的消磨,放大了讲是精神死亡——我们或许不担心普通层面的肉体上的死亡,但是必须承认,我们担心死亡是“自我的消亡”(dissolution of myself)。
二、死亡
西西弗斯曾绑架了宙斯派来的死神,致使人间长时间无人死去。不管是被剥夺阳寿(现实意义上的死亡)的他,还是被罚在冥界一直推巨石上山(精神意义上的死亡)的他,一直都在与死神较量。而这可以唤起我们对“死亡”的思考。
死亡是悲剧吗?永生是否又是好事呢?这便是我接下来要说的话题了。死亡无所不在,这是大家都没法否定的事实。但是我们能说它就是悲剧吗?显然不能。一个被疾病折磨的病人希望“安乐死”,一个老人寿终正寝等,你能说他们的离世是悲剧吗?不能。换个角度,如果疾病缠身的人有别的选择,他可能并不会选择死亡。但是疾病就是这样,它摧毁了人们的生活的其他可能性,所以我们说这样死去是悲剧的。笔者不认为一个人死前可以做完他所喜爱的全部事情,所以死亡剥夺了我们可以获得更好生活的可能性,在这一层面上死亡于我们而言无疑是悲剧性的。而且笔者认为死亡的悲剧冲突关键“不仅仅在于指我们周围的人都在死去,更多的是指我们自己可能在任何时候死去”[2]。我们不得不如履薄冰地去与我们这个仅此一次的生命相处。笔者承认每个人都有“试错”的机会,但如果可以,为什么不尽量去避免错误呢?我们想要追求的那么多,又怎么舍得多花一秒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呢?“我们很难知道该以什么样的步调走完一生。人生的整体形态(shape)极为重要。换言之:你人生的‘叙事弧线’(the narrative arc)影响了其总体价值”[3]。假如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死亡,那么你就可以好好地安排你剩余的生活,尽量使得遗憾最小化,但是死亡往往悄然而至,让人措手不及。
人类就是如西西弗斯这般的渺小和脆弱,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东西就会把你推向深渊,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做才能使自己幸免于难。我们面对这些冲突的时候,一种无力感会蔓延全身。人类在这个偌大的世界中始终是脆弱的。这个肉身是脆弱的,人的心灵是脆弱的,人的价值也是脆弱的,而且我们要知道并不是濒临死亡才会让一个人变成这样。正如奥德修斯看见埃阿斯躺在血泊里时雅典娜的回答:“……我想着他,也在想着我本身;因为我看到我们所有活着的人的真实状态——我们是暗淡的空壳、无足轻重的虚影,如此而已。”[4]我们现在的人又何尝不是这种状态呢?
假如我们能像西西弗斯一样绑架死神,获得永生,是否这就是最好的人生状态呢?“长生不死”是个很久远的话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是我们对长辈永远的祝愿。但是永生真正是什么样子的呢?永远到底有多远?永生最大的烦恼——厌倦,可能是我们无法热爱生活的主要原因。所以永生也不是最好的生命形态。甚至我们可以说如果人是不死的那会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人将不再有任何敬畏之心——就连死都不存在,时间又是无穷尽的,人还在乎什么呢?
三、偶然性与必然性
除了死亡之外,我们可以发现蕴含在死亡之下的是死亡的必然性,“不仅是我们每个个人(你、我、他)必将死去,而且更普遍的情况是我们都必然将会死去”[5]。
生活在诸多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交互影响之下的我们深有体会的就是,历史发展是必然的,而生活在历史之中的我们的个人生活则是偶然的。这历史必然性的强大仿佛足以轻视每一个个体的偶然。似乎可以说人类的好生活是偶然的,而悲剧的结局是必然的。
推着石头上山是西西弗斯在冥界唯一的生活,个体的能动性被抹杀在千篇一律的生活之中。他所拥有的生命在命运之前显得如此的孤立无助。渺小的人怎么能撼动历史这棵大树整体的发展呢?似乎西西弗斯就是被碾压在尘土里的脆弱的人类——没有救赎亦看不清未来的方向。
在我们所领会的教育中,历史总是波浪式的前进,螺旋式的上升。每个朝代的史官所记录的鸡毛蒜皮算不上是历史性的著作,而后人在此基础上的凝练和总结的文学创作才更值得阅读。我们把握的总是隐藏在偶然事件中的必然规律,历史中的野史总是被我们当成笑料来看待。让人惊奇的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或那样生活,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印证了中国古人的那句话——“千古无重局”。当下有许多选择,只要你能想到的你都可以去做,仿佛前路一片光明,但真实的情况是,你只能这样做,除此之外你别无选择。
“千古无重局”指的不仅仅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拥有不一样的人生轨迹(生活的多样性),还指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不一样的人生。再往前推,甚至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可能存在的人”,我们会发现每个人都是偶然的,每件事也都是偶然的,除了天灾人祸以外,人类都是自由繁衍的、不受约束的。
就人本身的偶然性来讲,我们在感叹造物主的神奇时也得认识到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你,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历史有历史的脚步,作为个体的我们憾不动大树,每个人都在人海里沉浮,大部分的人最后都消失在历史之中,历史似乎只是寥寥数人的狂欢。就事情的偶然性来讲,不管什么事情,你都会有选择做或者不做,或者直接转身朝向其他事情的权力。这样的不可预知而且完全有可能影响你接下来的一生的事情,你根本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来临。
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与我们个人生活的偶然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我们的生活其实没那么多选择,多的是遗传、环境、无意识的冲动挥之不去的影响,甚至你无时无刻不在当下之中而又无时无刻不活在过去之下。
可以回想一下,你是否在你母亲身上看见了你外婆∕外公的影子,在你妈妈的姐妹身上发现了你妈妈的影子……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血缘对一个人的内在影响是很大的——不仅仅指外表的相似。基因会决定许多事情,你的骨子里就有这种东西,尽管你一直想要去克服,但克服的前提就是承认它对自己的影响真的很大。有人甚至可能会担心“自己最终还是会活成父母的样子”,这实质是在否定父母的生活。
我们会对正在经历痛苦的人安慰说“一切都会过去”,对取得了重大成就的人告诫说“一切都会过去”,但是真的“一切都会过去”吗?显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过去成就了我们的现在,而且过去也将一直影响我们的未来。我们显然不能抛开过去谈未来,我们只会根据自己过往的经历总结出自己的生活经验去走接下来的路,而且他人也会根据你过往的经历来评判你这个人。也就是说离开了过去,谈你本身就会显得毫无意义。过去不仅是过去,它也是将来,过去不断重复发生。可以说在某些层面上我们重复着自己过去的生活,然后又重复着父母的生活(循环的悲剧);从更大的层面上来说,我们常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就连宏观如历史,也是有其必然性的存在,才使我们个人的生活显得不值得一过。更确切地说,“历史叙述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悲剧描述的就是可能发生的事情”[6],前者是我们无法变更的事实,后者可能会重复之前的历史,这种可能在某种层面上则是一种必然。生活的多样性和你当下生活的单一性构成了这样一种反差——你可以拥有别样的生活,但是你却活成了现在的样子。
四、群氓时代
回到我们当代生活,其实一直有一张大网在我们每个人头顶高悬,无一幸免,那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人的迷失。
早在20世纪后半叶,尼尔·波兹曼就当时美国文化中媒体快速发展的现象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中表达了他对其的哀悼。反观当下,这种现象更为突出。比如“明星”这个特定群体。什么是“明星”呢?作为新媒体作用下的产物,其英语定义更为直接——entertainmenters,即供人娱乐的人。他们表面上光鲜亮丽,但其实只是活在各种“人设”之中,就像普罗大众手中的玩偶,任人玩捏。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明星不在于人,更多在于媒体(的宣传)。于我们这些公众而言,“真真假假”可能一生都弄不清楚,你所知道的也只是别人想让你知道的。于是我们就活在对明星的主观臆想和判断之中,为之着迷、为之疯狂。
如果说我们对外界的认知可能有错,那么我们肯定能认识自己,但这句话也不完全正确。我们沉迷于黑镜(black mirror)之中,甚至迷失了自我。真实世界和虚拟的网络世界界线日益模糊,虚拟现实正在消磨我们的感知能力,客户端推送的人们的苦难新闻只是消费的对象,点击率多高,背后的收益就有多高——或许我们可以设想媒体的初衷不是如此,但也正是媒体恪尽职守地保持对苦难的紧张的关注的行为本身,恰恰使得其所能唤醒的人们的同情和理解不断地趋向衰竭。黑镜之下的我们丧失了现实世界的痛感,黑镜之下掩藏着的是我们的偏执、狂躁和冷漠。
科技的发展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实际)距离,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却也拉长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每个人都成了彼此“熟悉的陌生人”。科技拓展了人类“向外看”的能力,可是却使得人愈来愈冷漠,“向内看”的能力极度萎缩,面对种种镜中之像——就像两个镜子对照着形成的镜廊。活在对外界的幻想之中以及迷失了自我的人们,自以为获得了无限真理,但最终只是假象,带有一定程度的自欺欺人和不可避免的自娱自乐。这就是那张大网——伴随着科技而来的娱乐化的大网之下,每个人随地起舞。
五、结语
笔者在构想这个文章的标题以及探讨那些可能只是一闪而过的行为背后蕴含的悲剧性意蕴之时,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柏拉图所说的“有一些伦理处境,像一些在悲剧中所阐发的观点,对人的灵魂过于有害,因此不应该在一个井然有序的城邦里任人讨论”[7]这一道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只是在这世上挣扎求生以获得自己的快乐,不管生活是平凡也好,快乐是短暂和幻想也罢,生活欺骗我但我依然快乐这就足够了。常人的境遇里也用不着此类悲观的术语来描述自己的生活。但需要澄清的是,我们每个人与它的确是息息相关的,甚至越深思越会发现我们每个人与本文论题的关系比我们所知道的更复杂。本文所描述的或许有些片面和极端,但笔者私以为相较于用一种不偏不倚的方法去对待文中的问题并不显得价值更高。我们可以毫无偏见的生活——如果你的视角足够多,那你也可以乐观地生活。本文旨在提供一种可能性,一种思维的角度——理性地思考我们所面临的一切困境,然后才能理所当然地感性生活。
笔者想要探讨的就是“无所不在的悲剧冲突下”的“人类生活”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我想“人类生活”理应是好的人类生活。本文围绕四个维度展开,其背后蕴藏着的是人的自我挣扎——人与自身的冲突,而这种冲突恰恰是我们不能避免的,从出生到死亡。之所以说这些冲突是悲剧性的,是因为其不论哪一个都有可能使我们走向死亡甚至毁灭,不论是精神上的抑或是肉体上的。但好的人类生活就是指人类可以不断反思自己,用理性来指导自己的生活。不论是几千年前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也好,还是今天我们当下的哲人,从未间断过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批判,不怕血淋淋的真相,只怕自己活在幻想之中。
大多数哲学家都赞同“把任何人的痛苦、不幸和死亡都看成是悲剧是肤浅的理解”[8],但是我们也要明确“艺术上的悲剧不等于生活中的悲剧”,本文谈论的就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一个个人们所面临的悲剧性冲突——不是说已经发生了多么不幸的事我们无法挽回,而是说我们可能走入这样的悲剧的境地,强调的是一种可能性,面向任何人、任何时候——不是谈论伟人、名人,而是面向我们自己,一个个渺小而脆弱的个体所发出的声音。
最后回到西西弗斯这里,本文的主旨就像奥德赛的扉页上说的那样,“全书主题不是面对死亡时的勇气,而是面对难局时的知性”[9],并不仅仅是为了大家都能够从容面对死亡,而是让我们在面对人生困境之时,如同西西弗斯面对永恒困境一样,能从容应对人生的喜与悲,以一种哲人的理性思维悲观地看待生活,却又感性地生活在这片充满诗意的大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