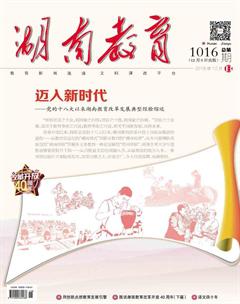那些改革的足迹
刘光成 李雅岚

一部语文教育发展史,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语文教育改革史。从1978年到现在,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走过了40年的艰难路程。正如加拿大教育改革专家迈克·富兰所说:“变革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语文教育改革的40年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回望来路,激越的鼓点萦绕在耳,探索的足迹清晰而深刻。
一、语文教育的“拨乱反正”(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
1978年,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的号角,也揭开了语文教育的新篇章。教育领域经过拨乱反正,恢复了高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蔚然成风,广大语文教师长期被压制着的工作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转化为语文教育改革的巨大动力。这一年由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虽然确定了语文课程“基础工具”的身份,却仍然强调语文课程的重要特点是“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知识教学的辩证统一”“思想政治教育和读写训练辩证统一”,且“思想政治教育”先于“语文知识教学”和“读写训练”。但毕竟这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大纲,语文教育开始摆脱混乱,走上正轨。在随后的1980年,国家对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必须在读写训练过程中进行”的要求。
1977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之后,立即指示恢复中小学教育秩序,重组人民教育出版社,并对新教材作了如下要求: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1978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小学语文教材应运而生,属于“合编本”(综合型)教材。它雖然还没有消除“左”的思想影响,但已从“政治压倒一切”的框框中解放出来,对于稳定局势、拨乱反正、提高语文教学质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198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了重点中学初中《阅读》《写作》分科教材,重点中学高中《文言》《文学》《文化》分阶段分科教材。教材新选入了相当数量品位较高的课文,丰富了教材的“文库”,而且训练的意识比较突出。
1978年3月16日,吕淑湘在《人民日报》著文批评中小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问题,认为学生用“10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叶圣陶、张志公也呼吁,要想使语文教学变少慢差费为多快好省,必须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语文教育界“三老”的文章引起普遍的关注,如何提高语文教学质量一时间成了语文教学改革的核心议题。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各种各样的语文教学改革风起云涌,出现了万马奔腾、百花争艳的喜人态势。李吉林的“情境教学”、于漪的情感教学、丁有宽的“读写结合五步训练”、段力佩的“八字教学法”、钱梦龙的“三主四式导读法”、宁鸿彬的教学卡片与求异思维训练、章熊的语言思维训练、欧阳黛娜的“初中语文能力基本过关”、张孝纯的“大语文”教学、陆继椿的“一课一得,得得相连”教学、魏书生的“语文知识树”教学等,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二、语文教育的“改革探索”(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期)
1985年,党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深化教育改革的新要求。1986年,国家再次颁布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这是新中国建国后首次颁布的“正式”的大纲,大纲第一次从素质教育及培养“四有”公民的高度来强调语文教学的重要意义。其中,《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出,小学语文是基础教育中的一门重要学科,“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有很强的思想性”,要求语文教学要在进行语言文字训练的同时,“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德和爱美的情趣”。《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出,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语文教学要“正确处理好语文训练和思想教育的关系”,“语文训练必须重视思想教育;思想教育必须根据语文的特点,渗透在教学的过程中”。其后,1988年、1992年的教学大纲虽然也强调“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但其位置已经居于“工具性”之后了,这是人们对语文课程“工具”属性的认识深化,这一深化表明语文教育越来越趋向于回归本体。
1986年,国家教委成立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实行教材多样化政策,全国亿万学生一纲一本的“大一统”局面宣告结束。特别是配合20世纪90年代初九年义务教育的全面实施,语文教学界开展了改革语文教材的多向探索,全国各地编写的实验教材恰似山花烂漫,多达三四十种,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委员会审定通过的就是十几种。199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了九年义务教育五年制和六年制小学语文课本各一套。这两套教材指导思想明确,教学要求切合实际,教学内容安排较为合理,课文体系比较严密。同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订了供全国选用的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科书,这套教材最鲜明的特色是“联系生活、培养语文能力”。相较改革开放初期编订的教材,这一时期的语文教材选文篇目大幅减少,力求为学生减负;选文内容也更为理性,一些在过去认为“不讲政治”的篇目,如袁枚《祭妹文》、陶潜《归去来兮》等得以入选,一些描写西方近代科学家、思想家或艺术家的作品,如《画鸡蛋》《月光曲》《伟大的友谊》,以及一些科普文如《蟋蟀的住宅》《麻雀》等也被选入。
这个时期的语文教学已比较注意学生的主体地位,各种旨在让学生掌握学习方法和习惯养成的教学模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尽管具体的步骤和方法不同,但大都重视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如魏书生的“六步课堂教学法”、湖南郑定子当面批改作文的尝试等。这一时期,语文教育界对如何深化和推进语文教学改革进行了深入探讨。1986年11月由《语文学习》等单位发起的“语文教学发展战略研讨会”,对如何取得教改突破的问题统一了思想,并围绕教改提出了一系列研究课题。1987年12月,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围绕“深化教学改革,提高语文教学质量”这一主题召开了第四届年会,进一步明确了“深化”的含义。1990年3月,《中学语文教学》再一次召开座谈会,对语文教学观念革新以及教改范围扩大进行了探讨。再往后,1991年7月,全国语文教学研究会第五届年会又是“深化改革,探索语文教学规律”。
三、语文教育的“讨论反思”(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受世界各国改革大潮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人们的竞争意识、发展意识、未来意识、创造意识、效率意识不断增强,我国中小学教育严重滞后以及应试教育给学生身心所带来的戕害,日渐突出。尽管90年代以来语文教育界的改革探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但是,长久以来形成的一些危害语文教育的社会性问题太严重,人们的不满情绪积蓄得太多,而语文教学质量又不可能立竿见影地提高,于是,一场社会性的“语文教育大讨论”终于爆发了。《北京文学》1997年第11期“世纪观察”栏目刊登了《女儿的作业》《中学语文教学手记》《文学教育的悲哀》三篇文章,拉开了语文教育大讨论的帷幕,讨论一直持续到新世纪。
这次大讨论几乎涉及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各个方面。大体说来,主要是针对学科性质认识分歧,教学观念陈旧,教学内容无所依,课程目标不明确,教材编写问题重重,教学方法僵化,考试制度问题和教师问题。此外还有如语文的性质问题、教学目的和任务问题、教学手段现代化问题、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问题、识字教学问题、听说读写教学问题,以及如何评价改革开放20年来语文教学改革的成败得失等。尽管在讨论过程中不乏偏激论题和尖刻之词,但通过讨论反思,语文教育界对许多重要问题形成了新的更高层次的共识。从一定程度上讲,这次讨论也对2001年正式开始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起到促进作用。人们注意到,2000年由教育部颁发的小学、初中、高中等3个语文教学大纲,对语文课程的特点作了突破性的界定:“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语文教育的“深化改革”(21世纪)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对我国建设面向21世纪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作了全面部署。2001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了“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扎实推进素质教育”的任务。2001年、2003年《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相继颁布,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并提出“语文素养”的新概念,取代过去较为外显的“语文知识与语文能力”。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14年3月30日,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首次提出了“核心素养”的概念。2018年1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正式颁布,新课标立足于我国课程改革现状和国际课程大背景,对高中语文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等多方面做了重新思考。“专题学习”“学科核心素养”“学习任务群”“学业质量标准”等成为高中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关键词。
新世纪之初的课程改革加快了语文教材的编撰,使语文教材迅速从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独大”发展为各地版本教材“群雄并举”。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有了自主选择版本的权利,有的甚至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域,选择使用不同的版本。在国家审定通过的各版教材中,以江苏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语文出版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使用量最大。在“以人为本”精神的引领下,多种版本教材选文注重人性化、科学化、国际化和个性化,选入了许多新篇目,如《钱》《泰坦尼克号》《卧虎藏龙》等,一些传统篇目如《背影》《包身工》《狼牙山五壮士》等被挤出语文课本,这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争论。2016年10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要求对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教材和涉及国家主权、安全以及民族、宗教等内容的教材,实行国家“统一编写、统一审查、统一使用”。2017年9月,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语文、历史、道德与法制等三科教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全国义务教育起始年级统一使用。“统编本”语文教材是对以往“实验版”语文教材的继承与创新,体现了时代价值诉求对语文教科书编订的引领。教材在内容上强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国家主权教育和法治教育等重要内容。所選古诗文数量有所增加,小学129篇(首),初中132篇(首)。还收录了大量革命传统经典篇目,如《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清贫》《吃水不忘挖井人》《朱德的扁担》《开国大典》《回延安》《白杨礼赞》《黄河颂》《回忆我的母亲》等。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以注重人的情感意向、唤起人的自主意识、发挥人的自主学习能力为旨归的主体性教育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广大教师开始自觉地将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转化为教学行为,语文课堂教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鲜局面:教师滔滔不绝的讲解少了,学生琅琅的读书声多了;教师的批评、挑剔少了,课堂上的鼓励、赞扬多了;教师理性化的解析少了,学生个性化的感悟多了;课堂上沉闷的局面少了,学生活泼的场景多了。以学生自主合作为特色的教学模式层出不穷,如山东杜郎口中学的“0+35”模式、山东昌乐二中的“271”模式、沈阳立人学校的“124”模式、江苏灌南新知学校的“自学交流”学习模式等,经多家教育媒体推介后,一时间参观学习者趋之若鹜。注重彰显风格、特色的教学流派精彩纷呈,如王崧舟的诗意语文、孙双金的情智语文、薛法根的智慧语文、窦桂梅的主题语文、王君的青春语文、熊芳芳的生命语文、赵谦翔的绿色语文、黄厚江的本色语文、王开东的深度语文、程少堂的文化语文等。新课程改革不仅催生了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行为,也给语文课堂教学带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与此同时,在教学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追求形式的倾向,这一倾向的主要表现是片面理解,迷信模式,崇尚新名词、新概念,以新为尊,以旧为卑,以致忽视了对语文课程核心功能的思考。语文教学要提倡百花齐放,但不宜模式化,不宜提口号、贴标签。判断一种教学模式、教学流派的价值,不在于它的“新”或“旧”,而在于它是否符合学生学习语文的规律,是否真正能够提高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因此,如何让语文教学回归简单、回归本色、回归理性,如何扎扎实实地提高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是语文教学深化改革面临的新课题。
刘光成,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教育硕士点负责人。兼任全国高考(湖南)语文科评卷核心成员、作文专家组大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