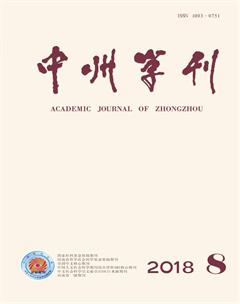明代弘嘉时期中州诗学与“文选学”
王立
摘 要: 弘嘉时期是《文选》在明代流传的一大转关。《文选》诗作为汉魏古诗的审美范例,反映了我国中古诗歌的演进,而以中州文人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复古派恰好以汉魏古诗为宗,便赋予了《文选》诗辨析源流、指导创作等诗学功能,明代“文选学”的文学性也由此凸显。总之,“文选学”、中州传统文化、中州诗学三者阐释共通,加之李梦阳、何景明等文学领袖的激励,弘嘉时期的中州诗坛出现繁盛局面,所阐发的诗学理念既推动了汉魏复古诗学的阐释,又在一定程度上以正统诗学维稳明代诗学。
关键词: 弘嘉时期;中州诗学;“文选学”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8)08-0142-06
明代文人有“借助对前代诗人或诗风的褒贬取舍作为基石,张扬一己的审美倾向” ① ,在前七子复古运动中,因为《文选》诗歌的文献价值和“崇雅黜靡” ② 的文学观符合以汉魏古诗为宗的取向,复古派便将《文选》诗作为创作和诗学阐释的参照,明代侧重于文学性的“文选学”也由此突显。而此时的中州 ③ 诗坛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登上主流文坛,他们对《文选》诗的接受推动“七子派”回归中古审美进程,也对明代的“文选学”和中后期文学复古有重要影响,但在中州文学自宋衰落体认下,这种现象未得充分重视和研究。故本文从地域和诗学的视角出发,探求弘嘉时期中州诗学、明代“文选学”、明代文学复古在文学层面上的互动。
一、渊源有自:弘嘉时期中州文学与“文选学”
弘嘉时期的中州文人对《文选》的重视和诗学阐发是对中古诗歌审美的复归,顺应明代诗学发展趋势,同时,也是在多元质朴的中州文化召唤下维护乡邦文学传统的自觉。他们以高涨的文学热情进行个性化的诗学阐扬,由此形成了繁盛的诗学面貌,在明代诗坛的复古契机中寻得立足之地。
1.中州文学与“文选学”
中州文学属于独立的地域文学空间,以时间为线索,可发现“文选学”与明代中州诗学有跨时空的文化关联。直观来看,《文选》内作家、作品与中州地域有紧密关系,书中选录先秦至梁120多位作家的700多篇詩文,河南籍作家就有20多位,而收录的寓居河南的外地文人也不在少数。中古时期的中州一直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诸多域外文人追慕前来,并以洛阳、许昌等中州重镇为背景进行诗歌创作。具体言之,左思、应贞、潘岳等本土文人和“三曹”“二陆”等域外文人在河洛礼乐和崇情文化的触发下,成为中州文学的创作主体和中古诗歌的代表作家,作品一定程度上受汉魏时期中州文化熏染,中州诗风之盛得到充分反映。此外,中州文学重真尚实的精神可以说是在先秦汉魏时期奠基的,弘嘉时期中州文人自幼浸润其中,以复古挽救诗坛和时局的用意正是本心流露,好古情节和汉魏诗学倾向也源于此,中州文化可看作《文选》与中州诗学结下渊源的内在因素。
在历史的演进中,《文选》的传播也与中州结下不解之缘,作为文学总集,《文选》主要在经济教育发达之地流传,而唐宋时期的中州处于政治、经济中心地位,《文选》以官方意识形态向社会的普及推动了“文选学”在中州的发展。唐代是“选学”大势,以辞章取士的科考制度使《文选》成为举子必读之书,为《文选》作注的李善曾在郑、汴间传授过,宋代亦在开封官方刊刻《文选》。因此,在文化习惯的传承中,中州士人研习《文选》的传统有保持的可能。元代“文选学”势头低落,到了明代,随着推崇汉魏古诗的倾向,“文选学”的价值被重新认识,中州地域内研读《文选》的传统也一直延续,并影响着文人的文艺观。李梦阳、何景明等为宣扬复古汉魏的文学主张,对《文选》重视有加,不仅诗歌创作效仿“选体”,有词、意等借鉴,还多有对《文选》的研究。李梦阳辑《古文选增定》22卷,何景明编纂《古乐府叙例》云:“若《古诗十九首》及他《选》诗,别为编列。” ④ 王廷相亦用“欲骚俪选”称赞何景明的诗作。曾就学于大梁书院的李濂自述与不急举业而好古辞的左国玑、王教、田深甫等同里定立约程,读五经正史并《离骚》《文选》等,相互品评交流心得,也说明了《文选》在当时有着流传的实用需要。这些中州文人深受中州文化熏陶,形成的尚《选》学风、诗风又通过代表文人弥散中州,同时又作用在汉魏诗学复古中。
2.弘嘉时期中州文人群体的生成
“文选学”与中州地域的渊源深厚,潜在的文学关联在明代诗学复古中被激发,成为中州文人的诗学依托之一,要想对这一诗学影响进行研究,首先要明确弘嘉时期中州文人群体的构成。明人结社繁多,作为独特的文学生态现象备受关注,相对于现在公认的文学流派,弘嘉时期中州文人群体的界定有自由度可言,但也要依据流派划分的规范,从文学领袖、成员关系以及一致的文学渊源和观念等方面考量。《中州人物考》言:“弘治人才之盛,中州为最。” ⑤ 《诗薮》亦载:“弘、正间,诗流特众,然皆追逐李、何,士选、继之、升之、近夫,献吉派也;华玉、君采、望之、仲鹖,仲默派也。” ⑥ 描述李梦阳、何景明在弘嘉诗坛的地位,弘嘉时期的中州文人正是在李、何乡贤导夫先路的氛围中渐具群体特征。大致活动年限从弘治七年(1494)李梦阳登科至嘉靖二十三年(1544)王廷相逝世,参与成员有何瑭、田汝耔、左国玑、王尚絅、崔铣、孟洋、王教、戴冠、李濂、曹嘉、高叔嗣、樊鹏等。
弘嘉时期的中州文人群体以同乡和亲友为纽带,伴随着弘治年间中州进士群体的崛起而壮大,在这段活跃期中,可分为京师和中州两个活动地点,也说明了中州文学的影响并不局限在本土。中州文人在李、何的引导下,借助进士及第聚集京师的机遇,重拾诗文唱和传统,形成了在京师的中州文学空间,严嵩《南京大理寺卿孟公墓志铭》云:“时公(孟洋)之内弟何子仲默方有俊名,与其群(郡)李献吉、王子衡、崔子钟、田勤甫及公,日切劘为文章,扬搉风雅,以相振发,酒食会聚,婆娑酣嬉以相乐,时称十才子。” ⑦ 之后,李梦阳回归大梁,间有外地文人拜访,又与妻弟左国玑,外甥曹嘉,李濂,以及王教、郑作等有文学交游活动,形成了在中州的文学活动空间。后李何淡出文坛,中州其他文人或隐居待仕、弃文入道,或著书立说,或兴办教育培育乡人,且后继缺乏文学担当之人,故《诗薮》云:“中原自李、何辈先达,高子业以冲达继之。嗣是作者,虽篇什间存,终非炳赫。” ⑧ 明中叶显名诗坛的中州文人群体遂在嘉靖后期声势渐消。
就弘嘉时期中州诗学的生成而言,信陵君旧走马地、文集雅会的梁园以及河洛文化根基的洛阳城等古遗迹,成为中州文人涵泳性情,凭吊寄托的场域。思想层面兼受儒家、法家、道家等多种学说的影响,具有兼容并包的文化特性,尤其是濡染着醇厚儒家文化底蕴,修身齐家和兼济天下的人生及政治理想已深深嵌入中州文人的精神气质中,集体呈现出爱国忧邦传统和社会责任意识。总之,中州诗学以北方雄浑盛大的文学大传统为根基,形成地域性的诗学小传统,崇尚经世致用,饱含忧患意识,在诗文理论和创作中以现实为参照和回归;追求弘大、浑厚的诗歌气象,又强调真率的流露。
二、明代“文选学”在弘嘉时期的活跃
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中,文人认同《文选》诗的文献价值和“崇雅黜靡” ⑨ 的文学观,“文选学”也由重视文字、音韵、训诂等学术方面转向文学方面的篇章审美解读和效习,包含显性和隐性两种研习轨迹。显性研习指对《文选》选录标准和诗歌的认同,是在创作层面上时效性直承;隐性研习则是立足《文选》汉魏六朝传世文献的地位,在复古文学观的思维结构、审美趣味等方面受《文选》潜移默化的影响。弘嘉时期中州诗学对《文选》的接受属于明代“文选学”的组成部分,对其研究理应从显性和隐性两方面着手。因此,要先考察《文选》的刊刻情况以及《文选》诗相对其他总集、别集独特之处,以便了解“文选学”在弘嘉时期的文学生存空间和中州文人接受《文选》的可能性。
从《文选》刊刻情况 ⑩ 来看,明代前期不过数种,有洪武年间(1368—1398)刘履刊《选诗补注》14卷;宣德九年(1434)陈本深刻《选诗补注》14卷;正统三年(1438)何景春刊《选诗补注》14卷;天顺四年(1460)唐藩刊《选诗补注》14卷;成化二十三年(1487)唐藩朱芝址刊李善注本60卷等,多是官刻本和藩刻本,对《文选补注》的数次刊刻有文学和文本价值的考虑,但更多是因为官方文化意志的导向。《文选补注》共8卷,《四库全书总目》评:“其去取大旨,本于真德秀《文章正宗》,其诠释体例,则悉以朱子《诗集传》为准。” 书中透露出理学意味的诗学趣向,在理学笼罩下的诗坛是易于接受和传播的。弘嘉时期的《文选》刊刻有较大改变,数量增至20余种,出现在嘉靖年间的占据大半,不同于明初以《文选补注》为要,形式也更多样化。有南监修补赣州本60卷、汪谅覆刊六臣注本60卷、晋藩朱知烊刊李善注本60卷等完整的《文选》各家注本;大梁书院刊22卷《文选增定》、王蓥和刘士元刊3卷选诗等诗歌选本以及侯秩刊82卷《广文选》的广续本。除官刻本、藩刻本,以盈利、普及或宣扬文学主张的民间刻本也开始在嘉靖年间出现。此般流布受多重因素影响,总体来说步趋复古思潮的大势,在七子派诗学理念和侧重文学层面的“文选学”倡导下,《文选》的传播途径和地位有了扩展和提升,反过来又助添明代对汉魏六朝诗歌诠释的深度和“文选学”的发展。
在复古汉魏诗歌的背景下,《文选》和后世总集《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保有汉魏六朝诗歌的作用不言而喻。但作为汉魏六朝时期问世的原初诗集,《文选》对明代诗学有着其他选集无可取代的作用,选录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汉魏六朝诗歌创作背景和发展轨迹,并影响着明代对汉魏六朝诗的评判。当时虽有《玉台新咏》与《文选》并列中古文学原初选集,也有“玉台体”的存在,但在明代崇雅宏大和情质并抒的复古取向下,明人对格古调逸的《文选》诗风格推崇有加,并不看重《玉台新咏》撰录的艳歌和绮靡的诗风,在这两种风格的对比中,《文选》保存汉魏高古诗歌的文献价值和重要性日益凸显。从诗歌发展和明代复古的现实背景看,“选体”作为汉魏诗歌范例的地位俨然确立。
明代之前就以“选古”或“选体”指称《文选》的汉魏古体诗,这种传统也将明代前中期诗人对汉魏古诗文本的选择引向《文选》。作为汉魏六朝诗歌渊薮的《文选》,收录有百余位作家的400多篇诗作,涵盖不同时期和多样风格的古体诗,属认可度较高的汉魏诗风代表。后世不仅通过《文选》继承了汉魏文学传统,将《文选》诗作为古体诗标准的意识也通行起来。严羽《沧浪诗话》对明诗学有重要影响,其评“《选》诗时代不同,体制随异,今人例谓五言古诗为选体,非也” ,虽不认同视选体为古诗专称,但透露了这种观念有流传的空间。如《文山集》評诗“诗仿文选体,歌行、律、绝各为一门”,刘克庄亦云:“近世诗学有二:嗜古者宗选,缚律者宗唐。” 将《文选》诗看作学习古诗的对象和门径。关于选诗的风格,《云庄集》云“古诗则兴寄渊邈,词旨超迈,多效选体”,以意象开阔,气势豪迈理解“选体”的风格,也有《金华黄先生文集》云“诗长于古乐府、选体,清婉丽密而不失乎情性之正” ,从清新雅正的角度看待《文选》诗。至明代,五言古体多宗“选体”的传统依旧持续。弘嘉时期,被李梦阳、何景明称赞的袁凯古体诗作就多学《文选》,李梦阳也“自分其五言古作‘《选》古、‘唐古二种” ,效仿《文选》收录的五言古体诗,王世贞《艺苑卮言》中也有“乐《选》律绝”的区分,这种意识无疑会刺激其他复古文人对选体的追捧。同时,李、何等倡导格调说时还将“选体”看作诗歌标准,清人翁方纲言“李、何在前,王、李踵后……因而遂有五言必效仿选体”,且“独至明李、何辈,乃泥执《文选》体以为汉、魏、六朝之格调焉”,虽是抨击之语,也侧面道出李、何等提倡复归古体之时,以《文选》诗为最高典范。
三、弘嘉时期中州文人对《文选》的诗学阐扬
钱志熙先生认为中国古代诗歌史存在对立统一的个体诗学和群体诗学,个体诗学“创造意识、传播愿望都十分突出”,而群体诗学在发展过程中起支配作用。明代弘嘉时期的诗学复古也有个体与群体之分,复古派文人推崇汉魏古诗,可视为群体诗学取向。在个体诗学阐释上,中州文坛双子星李梦阳、何景明的作用尤为突出,分具雄厚、俊逸特征,在复古论争中积极进行诗学探索,也推动诗学复古取向的形成和革新。总体而言,中州文人在明代复古诗坛中彰显了群体诗学特色,沉寂已久的中州文学也因个体诗学的活跃而重焕生机。
1.雄厚气格:李梦阳对《文选》的诗学阐扬
李梦阳幼年由甘肃迁居开封,一生大半在中州度过,既受中州深厚人文底蕴濡染又以雄才负气之姿影响着中州。李梦阳居中州期间遍访遗迹,禹王庙、师旷奏乐之吹台、梁园、阮籍啸台、孙登隐居之苏门山等成为其凭吊往古之地,并留下诗文追思曹刘、阮籍等中古前贤,也作为复古的诗学寄托。同时,中州数千载积累下的古直士风也影响着李梦阳心性和情怀,形成了“秉性直憨,罔谐时俗,摈斥丘壑”的性格特征,不仅导致李梦阳在官场几起几落,也是他复古运动中“格调”和“真情”等诗学阐释的地域影响因素。
李梦阳的诗学观体现着对汉魏古体诗传统的维护,在《缶音序》中说“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认为诗歌发展至唐缺少古体畅顺自发之感,但有其唐诗之调,或影响了李攀龙唐代有其唐古的论断,也可见李梦阳对汉魏古体诗正宗地位的认同。因而,他在诗学实践中对“选体”多有崇尚,由他人评述可窥一二。王世贞《艺苑卮言》称李梦阳作诗“《选》体,建安以至李杜无所不有”,李杜的五言古诗有效仿《文选》的痕迹,可见李梦阳对“选体”创作经验的借鉴,不只拘泥于《文选》元典本身,也将范围扩展至后代诗人的“选体”诗。清人翁方纲言“独至明李、何辈,乃泥执《文选》体以为汉、魏、六朝之格调焉”,明示复古派以《文选》作为汉魏六朝诗歌风貌范例,但泥执于“选体”的意见似不贴切。《文选》选录诗歌是汉魏六朝典范之作,更是明代追溯中古诗歌的重要媒介和首要取法对象,是明代中古诗学阐释的文本参照。且明代复古诗学对中古诗歌格调说的提出和效习,是对逐渐丧失的中国古典诗歌审美理想的重构,诗学中的格调说确实非一家所能概,非一时一代所能专也,但面对明诗坛的靡弊困境和对复古理论依据的需求,李梦阳、何景明等以《文选》诗传达的雅正诗学观为指南,开辟有迹可循的复古路径,满足了明代诗坛的现实需要。因为在李梦阳的文学认知中,中古时期是诗歌演进的关键,其古体传统上承三代遗响,下起近体诗风,有妙不可言的艺术性,“古诗妙在形容之耳,所谓水月镜花,所谓人外之人,言外之言,宋以后则直陈矣”。李梦阳反思宋代以后古诗不兴的原因,认为对汉魏古体诗的推崇是革新明代芜弊诗坛和找寻失落的诗歌传统的一剂良药,但古诗形容之妙属于“心了了而口不能解,卓如跃如,有而无,无而有”,传达出的创作经验和理念太过抽象,李梦阳便从“选体”中揣摩体会,期冀用一种直接具体的诗学阐释,拉近古诗与明诗坛的距离,并从对《文选》的诗学接受出发熔铸其“真情”和“格调”理念。
格调说作为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其内涵也日渐丰富,在明代以复古为导向的诗学中,李梦阳的格调说具有重要地位。他在《潜虬山人记》中说“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概括了诗歌格调说的内涵。当论此说的形成,《文选》中的汉魏古诗是李梦阳诗学复古首选对象,对其中风格、诗法等的领会则是李梦阳格调说的基础。李梦阳向往三代治世升平之音,期望将其带入诗歌创作并改良明诗坛,但三代实去今太远,礼乐和文质谐鸣的创作理想难以完美实现,便退而求其次,选择最接近的汉魏古诗作为师古的方向,在诗歌理论上大力倡导宗汉魏,在对浑沦自然等风格的效习中,推行一条正宗的复古门径。李梦阳在《文选》基础上刊行建安、正始、太康以及东晋时期的代表作家、作品,并在序中有意串为连贯的诗学脉络,他在《刻陆谢诗序》中说“子亦知谢康乐之诗乎?是六朝之冠也,然其始本于陆平原,陆谢二子则又并祖曹子建”,將谢灵运的诗视为六朝之冠,又认为陆机、谢灵运取法曹植的诗歌创作。在对《文选》的深入研习中,李梦阳似寻到架构明代和三代诗歌的津梁,即是借助对汉魏古诗的学习联通古今诗坛,汉魏古诗体现昂扬宏大、梗概多气的气度,能够上溯风雅传统,下接唐人宏大气象,表露出的感人深思、雄浑有力的力量,也与自己在诗坛上的发扬踔厉不谋而合。
真情说和格调说同为李梦阳复古诗学的重要理念之一,在其格古调逸审美理想下,看重受自然和社会感发的真性情,在馆阁诗风和陈庄体流弊下重倡诗歌的抒情和美刺比兴的传统,看重汉魏古诗的本色率真。这由李梦阳对民歌的看重即可管窥一二,《缶音序》云“孔子曰:‘礼失而求诸野。余观江海山泽之民,顾往往知诗,不做秀才语”,李梦阳从儒家诗教出发,不做雕饰之语,认为本色率真的民间作品诗歌的真正属性。他之所以看重民歌,不仅是明文学下移的产物,也因为民歌与汉魏古诗同具真情的特征,如强调:“三代而下,汉魏最近古,向使繁巧崄靡之习诚贵于情质宛洽,而庄诐简侈浮孚意义殊无大高下,汉魏诸子不先为之邪?”汉魏古诗情志融洽,追求浑沦统一的审美倾向是对温柔敦厚儒家诗教的复归,也是情感的自然真实表达,且创作通过比兴手法抒发风人之义。因此,李梦阳对诗歌真情说的重视也就决定了他越过主理的宋诗和独有唐调的唐诗,将汉魏古诗视为最近古的自然纯朴诗风的代表,并以《文选》诗为效仿对象,作为其真情理论阐释的主体。
2.终怜俊逸:何景明对《文选》的诗学阐扬
何景明与李梦阳同为文学复古领袖,在具体诗歌复古与取法、创作风格等方面带有个性表征,也是李、何“尺寸古人”和“舍岸登筏”诗学论争的症结所在,这种差异的形成受社会机遇和思想根源的影响,也有地域性文化的作用。李维桢《彭伯子诗跋》云:“李由北地家大梁,多北方之音,以气骨称雄,何家申阳,近江汉,多南方之音,以才情致胜。”中州文化大传统下又分为若干小文化圈,李梦阳由西北迁入中原,属开封文化圈,而何景明生长于中州南部的信阳属淮南文化圈。信阳山清水秀,是古申国旧地,申国为楚附属国,何景明诗《吾州》云“辽邈吾洲地,名从申伯来”,即表示对信阳地域文化有归属认知,在中州文化和楚文化双重熏染下,何景明在文学思想和复古理论上显示出沉稳俊逸,不同于李梦阳的雄厚气格。
《四库全书总目》云:“何景明序谓‘明初诗人以凯为冠,盖凯古体多学《文选》,近体多学杜甫,与景明颇符,故有此语。”且不论袁凯是否为明初诗坛冠首,何景明如此称赞,表明了对袁凯诗歌艺术的研究和认同,其中就包括古体尚习《文选》的特点。何景明编选《古乐府》“序言”云“若有《古诗十九首》及他《选》诗,别为编列”,在选诗入书时,将《文选》诗做单独编排,标示《文选》诗歌的典范地位,且王廷相以“侵谟匹雅,歙骚俪选”评述何景明的诗歌创作。可见,何景明有意将《文选》应用到他的诗歌的创作和理论方面。
何景明在不断学习中形成特色的诗学观,早期为与李梦阳、陆深共同选校的袁凯《海叟集》作序云:“景明自为举子,历宦十年,日觉所学非是……学歌行近体,有取于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诸人;而古作必从汉魏求之。”表示以汉魏、盛唐佳作为对象的诗法观念。而在正德年间文学复古运动分化时,与杨慎、薛蕙、张含等文人交游,并作《明月篇》序等调整前期想法,博涉初唐和六朝。何景明诗学观的转变赋予其中古诗歌观多重内涵,他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说“诗弱于陶,谢力振之,然古诗之法亦亡于谢”,成为后世文人反复讨论的诗学命题,也是何景明中古诗学观的直观呈现。许学夷就认为何景明未识到陶诗自然率真、浑然天成的文学审美价值,未明诗体至谢灵运演进至律诗的轨迹,也有清代施闰章《重刻〈何大复诗集〉序》云:“至其所谓诗弱于陶,文亡于韩,钱东涧尝力辨其非,盖文人矫枉过当,有为而言也。”认为何论是过当之语,但确是立足于为明七子派文学复古发声。实际上,通过何景明的诗学阐释可看出,以“弱”评判陶诗在慷慨气格上的弱化,是因为何景明认为诗家要旨是柔淡、含蓄以及典厚,陶渊明诗有宁静致远的风格,但淡泊情感上的内敛有度并不等同于汉魏诗歌对情志一合的委婉表述,与何景明在明代诗坛上对醇厚健雅风格的复归并不相符。何景明在《王右丞诗集序》中云:“盖自汉魏后,而风雅浑厚之气罕有存者。”推崇汉魏诗歌续承三代诗风,具有高浑朗健的审美风范,抒发至情人心、世情百态,具有极易产生情感共鸣的普世性,在他看来之后的诗作鲜有表述。“亡于谢”的论断也应顺而生,谢灵运意欲重振诗道,独辟山水意境,大开诗歌声色之门,诗歌直观呈现的骈偶柔弱、有意为之的语词句式,与何景明所倡导的辞断意属、连类比物的古诗不可易的自然之法相违。在何景明看来,诗歌“意象应曰合,意象乖曰离”。如果只看重不饰装缀的语言或者整体流美的意境,诗歌的面貌终会流于空浅俚俗,陶渊明和谢灵运作为魏晋和南朝诗运转关的引领诗人,在气格上与古体诗的背离正是何景明提出诗亡论的出发点。由此可见,在明代诗学复古中,何景明回归到对正宗古体诗效习,在“选体”诗中尊汉魏古体正统体例,诗弱于陶而亡于谢正是在其自觉的中古诗歌辩体观上的生发。
四、结语
弘嘉时期,中州诗坛继明初五大地域诗派,在李梦阳、何景明的带领下崛起于明代文学中,浸润在中州传统文化氛围的文人对《文选》接受,是以正统儒家思想和诗学观对汉魏抒情言志诗歌特质的认同,又是对规矩的正统文学之延续和发扬,与任情自适的吴中诗派,作诗明理的越中诗派,“风雅中坠”的岭南诗派,追求平和的江右诗派有明显不同。论其对《文选》诗进行诗学阐释的动机,当是以情志并抒的诗学理论维稳明诗坛的存在。
中州文人对《文选》编纂的文学观和选录作家、作品典范性表示认同,并从《文选》中汲取诗学养分培植其文学复古主张。复古汉魏诗学由明初朦胧生发至李、何提倡转为成熟理论,后贯穿明中后期诗坛,可以说弘嘉时期的中州诗坛有一定助力。具体理念的阐释为各诗派树立了诗学标杆,也激发了诗坛的繁荣和论争。同时,诗学复古又将《文选》推至社会普遍接受层面,“文选学”的文学性逐渐凸显,有助于明代“文选学”以删注、广续、评点等侧重文学著作的出现。
注释
①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②⑨骆鸿凯:《文选学》,中华书局,2015年,第22、22页。
③中州又称中原,广义上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狭义上专指河南地区,文中明代中州即取后种解释,以《明史·地理志》中河南行政区划分为参照。
④何景明撰,李叔毅等点校:《何大复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94、235、602、序、594、575、594、575页。
⑤孙奇逢:《中州人物考》卷四,广文书局,1977年,第435页。
⑥⑧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63、355頁。
⑦严嵩:《钤山堂集》卷二九,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33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46页。
⑩以下版本刊刻情况据范志新先生《〈文选〉版刻年表》(《〈文选〉版本论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和付琼先生《文选版刻年表补正》(《兰州学刊》2008年第10期)等统计得出。
纪昀等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1711、1477页。
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69页。
文天祥:《文山集》卷一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94页。
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第9册,中华书局,2011年,第4092页。
曾协:《云庄集》原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27页。
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卷三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6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55页。
丁福保辑:《清诗话》之《蠖斋诗话》,中华书局,1963年,第392页。
翁方纲:《复初斋全集》卷八,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4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21、421页。
钱志熙:《从群体诗学到个体诗学——前期诗史发展的一种基本规律》,《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第23页。
李梦阳:《空同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6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62、477、605、605、446、464、477、564页。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之王世贞《艺苑卮言》,中华书局,1983年,第1044页。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一三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一五三,齐鲁书社,1997年,第672页。
施閏章撰,何庆善、杨应芹点校:《施愚山集》第1册,黄山书社,1992年,第62页。
责任编辑:行 健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ongzhou Poetics and Wenxuan Studies in Hongjia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Wang Li
Abstract: Hongjia i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the transmisson of Wenxuan in Ming Dynasty. Wenxuan poems, as the asethetic model of Han and Wei ancient poertry, reflected the evolution of ancient poetry of China. In Hongjia period, the literature renaissance led by the Seven-Scholar School represented by the Zhongzhou literati Li Mengyang and He Jingming happened to regard the ancient poetics of Han and Wei as the root, which gave Wenxuan poetry the poetic functions of clarifying the source and guiding the creation. Therefore, the literariness of Wenxuan Studies became prominent. Wenxuan studies, Zhongzhou traditional culutre and Zhongzhou poetics being in common, plus the inspiration of the literary leaders such as Li Mengyang and He Jingming, made Zhongzhou poetic circles flourish in Hongjia period. The advocated poetic concept to some extent stablised the poetics in Ming Dynasty by orthodox poetics as well as promot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Han and Wei retro poetics.
Key words: Hongjia period; Zhongzhou poetics; Wenxuan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