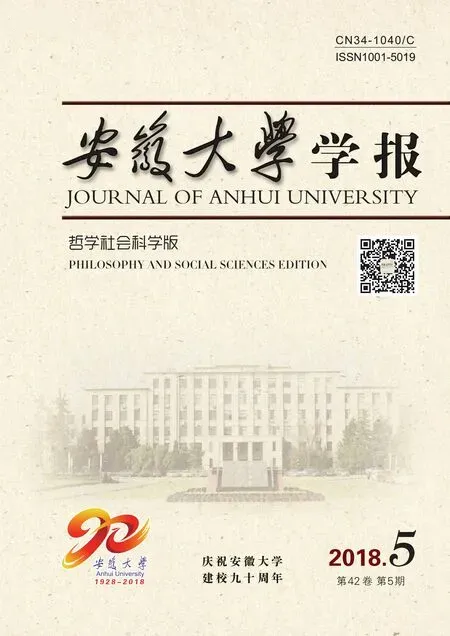吉藏《金刚般若疏》释经方法研究
董 群
对于三论宗实际创始者吉藏(549~623)思想的研究,相比于对禅宗慧能的研究,是极其冷寂的。而在对吉藏的研究中,有一类内容,是对其释经的研究,但此类研究却较少关注吉藏对《金刚经》的疏释,这也是本文选择这一主题的一个原因*释长清曾著有《吉藏〈金刚般若疏〉之初探》一文来讨论这一问题,并提出希望“能唤醒大家对此疏的重视”。参见释长清《吉藏〈金刚般若疏〉之初探》,《正观杂志》2005年第34期。此文作者曾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读博士,其1988年的博士论文为A Study on Chi-tsang’s Erh-ti-i,此后其中英文版本分别获得出版,可参见Shih Changqing, The Two Truths in Chinese Buddhism,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2004;释长清:《吉藏二谛论》,台湾:正观出版社,2007年。。吉藏对于般若类经典的解释,有两部重要的作品,一是对鸠摩罗什译《金刚经》的解释,著有《金刚般若疏》四卷,二是对《大品般若》即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解释,著有《大品经义疏》十卷。
对《金刚经》,吉藏评论非常之高,称其为“三观之虚明,一实之渊致”。依《法华经》的三车论,《金刚经》属于大白牛车层次的经典,“大心始发,方驾此白牛”。他称此经为“正教之洪范”*吉藏:《〈金刚般若经〉序》,《大正藏》第33卷,第84页上。。吉藏此疏,属于“四家大乘师之疏”*此说出自日僧志道的《刻金刚般若经赞述序》(《大正藏》第33卷,第124页下),其余三家为智顗《金刚般若经疏》一卷、智俨《佛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略疏》两卷、窥基《金刚般若经赞述》两卷。其中,智俨注释的是菩提流支译本。对于此经的解释,当然不限于此四家,杨惠南有文《〈金刚经〉的诠释与流传》(《中华佛学学报》2001年第14期)概括了对于鸠摩罗什译本《金刚经》的不同解释。之一,也是四疏中相对较早的。当然在吉藏之前,也有一些解释者,但是吉藏对这些解释并不满意,“释者鲜得其意”*吉藏:《金刚般若疏》卷一,《大正藏》第33卷,第90页下。下引《金刚般若疏》以卷数加页码的形式随文夹注。。这也是吉藏撰写此疏的一个原因。
本文对《金刚般若疏》的考察将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吉藏此疏以十重疏释法为代表的释经方法的考察,二是对于十重结构之前九重的分析,三是通过对十重结构的第十重的分析,考察吉藏对于此经所持的基本观点。
一、由疏文结构体现的释经方法
宗教师对于经典的解释,称为“释经”,其中的方法论等内涵,体现了其“释经学”的观点。关于这一概念,汉译有所谓“诠释学”“解释学”等,英文都是hermeneutics。在西方的学术背景中,这种解释学源自古希腊,盛行于基督教学术圈,又为当代所重视。汉语学术界在西方解释学新思潮的影响下,也兴起对解释学的研究,其热度至今没有消退。
其实,佛教本身就有释经的传统,这个传统构成了佛教的释经学,所以维基百科英文版的hermeneutics词条在谈到解释学的“宗教传统”时,专门列有“佛教诠释学”(Buddhist Hermeneutics)一项,但是具体内容只有几行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学界对已有研究缺乏关注。
在佛教的解释学体系之中,汉传佛教有自己的传统,吉藏的释经,是此传统的典型体现。
在吉藏的释经作品中,对体裁的命名是多元性的,这也体现了其解释方式的特点:有“玄义”“玄论”或“玄意”体,如《三论玄义》《法华玄论》(实为玄论体)、《胜鬘宝窟》(实为玄意体);有“疏”“义疏”体,如本疏和《无量寿经义疏》等;有“游意”体,如《法华游意》。同样是“疏”,方式也有所不同,有的是直接随文疏释,比如《中观论疏》《十二门论疏》《百论疏》等;也有如《金刚般若疏》这样在第一卷就交待整体的结构,即“玄意十重”,从此名称看,这部疏,也是“玄义”体。
从具体的疏文结构来说,《金刚般若疏》有十重结构,“玄意十重:一序说经意,二明部傥多少,三辨开合,四明前后,五辨经宗,六辨经题,七明传译,八明应验,九章段,十正辨文”(卷一,第84页中)。随文疏位于最后一部分的“正辨文”,这也是内容最多的一部分。
这样的十重结构,在吉藏的其他作品中也有采用,如《法华游意》:“《法华玄》,十门分别:一来意门,二宗旨门,三释名题门,四辨教意门,五显密门,六三一门 ,七功用门,八弘经门,九部党门,十缘起门。”*吉藏:《法华游意》,《大正藏》第34卷,第633页下。
除此十重之外,吉藏还有其他的结构类型所体现的解释方法。
有六重解释结构,如《法华玄论》:“玄义有六重:一弘经方法,二大意,三释名,四立宗,五决疑,六随文释义。”*吉藏:《法华玄论》卷一,《大正藏》第34卷,第361页上。又如《观无量寿经义疏》:“六门明义:序王第一,简名第二,辨宗体第三,论因果第四,明净土第五,论缘起第六。”*吉藏:《观无量寿经义疏》,《大正藏》第37卷,第233页下。如《涅槃经游意》:“一大意,二宗旨,三释名,四辨体,五明用,六料简。”*吉藏:《涅槃经游意》,《大正藏》第38卷,第230页中。
有五重解释结构,如《仁王般若经疏》的结构:“第一释经名,第二出经体,第三明经宗,第四辨经用,第五论经相。”他明确说这是模仿智顗的方法:“天台智者于众经中阔明五义,今于此部例亦五门分别。”*吉藏:《仁王般若经疏》卷上(一),《大正藏》第33卷,第314页中。如《胜鬘宝窟》:“玄意有五:一释名题,二叙缘起,三辨宗旨,四明教不同,五论经分齐。”*吉藏:《胜鬘宝窟》,《大正藏》第37卷,第1页下。
有四重解释结构,如《维摩经义疏》:“玄义开为四门:一定浅深,二释名题,三辨宗旨,四论会处。”*吉藏:《维摩经义疏》卷一,《大正藏》第38卷,第908页下。
有三重解释结构,如《净名玄论》:“叙其论意,略为三别:第一名题,第二宗旨,第三叙会处。”*吉藏:《净名玄论》卷一,《大正藏》第38卷,第853页上。如《法华义疏》:“将欲入文,前明三义:一部类不同,二品次差别,三科经分齐。”*吉藏:《法华义疏》卷一,《大正藏》第34卷,第451页上。
也有二重解释结构,比如《三论玄义》:“总序宗要,开为二门:一通序大归,二别释众品。”*吉藏:《三论玄义》,《大正藏》第45卷,第1页上。
从这些看似有别而又大致相近的解释结构来看,此《金刚般若疏》的结构层级,内容是最复杂的。后来的华严宗法藏,也有十重法解释《华严经》。
二、前九重结构之要旨
吉藏对于十重结构之前九重,都做了相对简略的说明,第十重则为重点,有详细的内容,需要另用一节来研究。此处对九重疏释的要旨加以描述性的概括,以显示吉藏《金刚般若疏》的基本内容。
第一,序说经意。这是对此经的意义的大致说明,吉藏解释了如来说此经的因缘,有九大缘由:
其一,此经为习大乘者略说因果法门,“此经为诸大人略说大法”(卷一,第84页中)。“大人”,即是习大乘之人,吉藏引《金刚经》语,是“如来为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鸠摩罗什译:《金刚经》,《大正藏》第8卷,第750页下。。吉藏在此经之序文中说,“大心始发,方驾此白牛”,也说明了此经属于“法华四车”之大白牛车。略说何种大法呢?是因果大法,“佛法无量,略说因果则总摄一切”(卷一,第84页中)。“因”是指什么呢?是指菩萨依般若而生的真实大愿和大行。菩萨的真实大愿指菩萨住般若心,而欲遍度一切众生,令其入无余涅槃,实无所度。菩萨的真实大行指菩萨不住于法,而行布施等一切诸行,实无所行。菩萨以般若心发愿,以般若心修行,这样才能真正成愿、成行。“果”是指什么呢?是指无所得果,即如来实想法身。
其二,为了给一切众生阐明利益功德,“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真实分别利益功德,故说此经”(卷一,第84页中)。这个功德利益,就是让众生产生净信,哪怕是一念净信,都能外受诸佛护念,内生无边功德。
其三,为说明第一义悉檀,“为欲说第一义悉檀,故说是经”(卷一,第84页下)。第一义悉檀指诸法实相。
其四,以大悲心受请而说般若波罗蜜法,“以大悲心受请说法,故说是经”(卷一,第84页下)。如来受请,是为大事,这个大事,就是般若波罗蜜。
其五,为集药治病而说此经,“佛欲集诸法药愈难愈病,故说是经”(卷一,第84页下)。吉藏进一步解释说,众生有两种病,一是身病,即老、病、死,二是心病,即贪、瞋、痴,佛以般若金刚,摧破此两种病。
其六,为增长众生的念佛三昧,“欲增诸菩萨念佛三昧,故说此经”(卷一,第84页下)。吉藏引《金刚经》义说,一般人虽然想念佛,但是不识如来,比如,以色、音、声见如来法身,所以堕入邪见。什么是法身?吉藏认为,应以正法为身。
其七,为显示中道,去除边见,“欲显示中道,拔二边见故说是经”(卷一,第84页下)。吉藏说,此经所说的发三藐三菩提心,就是于法不说断灭相,就是正道之心,不堕入断和常的边见。
其八,为了说异法门、异念处,“欲说异法门异念处故,故说此经”(卷一,第85页上)。什么是异法门?异于一般所说的善门、不善门、记门、无记门,而说非善非不善、非记非无记的中道,异于一般所说常、无常、苦、乐等念处,而说非常、非无常念处。
其九,为了消除众生的深重之障,“欲转众生深重障,故说此经”(卷一,第85页上)。有人认为,般若不是凡夫所行的,这样,就形成了学习般若的深重障碍。吉藏认为,此经强调,从凡夫到十地,都应学般若。总的来说,学习般若,可以断十种障*十障为:一无物相障,二有物相障,三非有似有相障,四谤相障,五一有相障,六异有相障,七实有相障,八异异相障,九如名义相障,十如义名相障。吉藏对此又各有解释。。
第二, 明部傥多少。这一部分,吉藏主要说明般若经的种类,以及有关这一议题的不同说法:
二种般若说,出自《大智度论》,一是共声闻说,二是只为十地大菩萨说。
三种般若说,即《光赞般若》《放光般若》《道行般若》,为上中下三种。吉藏引“旧说”,《光赞般若》在西土本有五百卷,后零落只有十卷,或分为十二卷,是上品般若,《放光般若》为中品,《道行》为下品。《放光》有二十卷,是“古大品”。《道行》为小品。
四种般若说,引长安僧叡的说法:“斯经正文凡有四种,是佛异时适化,广略之说也。其多者云有十万偈,少者六百偈。”*僧叡:《小品经序》,《大正藏》第8卷,第537页上。至于具体哪四种,特别是何为第四种,还有不同看法,吉藏不同意将《金刚经》列为第四种。
五时般若说,吉藏将般若、波若并用,引《仁王经》中的说法,视其分别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金刚般若经》《胜天王问波若经》《光赞波若》《放光般若》和《仁王般若经》。
八部般若说,引菩提流支的观点,第一部十万偈,第二部二万五千偈。此二部犹在外国。第三部有二万二千偈,指《大品般若》。第四部八千偈,即《小品般若》。第五部有四千偈,第六部二千五百偈,此二部亦未传至汉地。第七部有六百偈,即是《文殊师利波若》,第八部三百偈,即是此《金刚波若》。在这里,吉藏引《大智度论》中的观点,不同意菩提流支将《光赞般若》《道行般若》等视为十万偈般若中的一品,而不是单独的一类般若的观点。
对于般若经种类的不同,吉藏总的观点是,对于寿命短、记忆力弱的人类来说,小品般若都读不下去,况且大品?所以,不要局在五时般若,限在八部般若。
第三,辨开合。接着上述诸部般若的议题,那么多部般若,为什么不合为一部呢?吉藏认为,从开合的角度,诸般若开为五时般若,五时般若,不可以合为一部,必须各开五部。这不同于《华严》八会,可以合为一部,因为华严的八会有前后相成的关系,而五时般若之间,没有浅深次第、前后相成的关系。
第四,明前后,即明《摩诃般若》和《金刚般若》的前后。对此,吉藏的看法是,不可以确定说何种经在前,何种经在后,“随宜之言,复何可定其前后?或可一时具说多部,或可一部具经多时”(卷一,第87页下)。这一说法对于后人理解这一问题,有着指导性意义。
第五,辨经宗。对于此经的宗旨,吉藏列出了不同的观点,比如说,无相境为宗,以智慧为宗,等等,吉藏一一责之,而主张“因果为此经正宗”(卷一,第88页中),并引经义加以证明。
第六, 辨经题。在此疏之序中,吉藏有一个总体说明,可以列入这一部分。关于经名,他认为,从梵文译成中土文字的话,经名应当译成“金刚智慧彼岸到经”。他进一步解释说,“金刚”之意,为“无累不摧”,“般若”意为“无境不照”,“波罗蜜”是“永勉彼此”。
在疏文的正文中,吉藏又从五个层次来解释此经名的含义。
其二,释“金刚”。吉藏反对单纯地把金刚看作借世间之喻的说法,“如世间中金刚宝坚而且利,譬于波若体坚用利”(卷一,第88页下)。对这种理解,吉藏不以为然。他认为,般若作为真实法,过一切语言,灭一切观行。如果将金刚作为譬喻的话,金刚就只是譬喻,而不是法了,般若是法而不是譬,这样把法和譬分为了两截。吉藏还有其他一些观点来证明其这一看法。
那么,从譬喻的角度理解金刚,有哪些含义呢?正如他的自设之问:“问曰:汝以金刚喻般若者,此有何义?”(卷一,第89页上)吉藏认为,金刚有无量功德,简略而言,有如下含义:
1)表示“第一”,世间之宝,金刚第一,出世间之宝,般若第一。
2)表示“无法称量”,如同金刚宝,一切世人都不能估价,般若法宝所有所生的功德,一切世人不能称量。
3)表示“无碍”,如果把金刚宝放置在山顶或者平地,都无障碍,般若也是如此无碍。
4)表示“清净映照”,世间金刚宝能够照彻清净,般若也是如此,照实相水,明了清净。
5)表示“不能执持”,世间的金刚宝,只有那罗延天这样的大力士才能执持,般若也是如此,喜欢小法的人,以及执著知见的众生,不能执持。
6)表示“成佛”,世间之人,吞食少量的金刚,就在身体内不朽,般若也是如此,如能了悟般若,就是不朽,必能成佛。
吉藏继续解释了金刚、般若具有的“得安乐”“不定”“无心”或未当有心等含义。尽管如此,吉藏强调般若的不可譬喻性,“般若超绝金刚,非可譬喻”(卷一,第89页中)。在正文的疏释部分,在解释《金刚经》中“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一句时,吉藏又区分了二乘金刚和佛金刚。二乘断惑,也称金刚,此经中讲的金刚,“是佛波若,佛金刚”(卷三,第113页中)。
标定矩阵C即为正映射矩阵G的逆矩阵,由于G一般为非奇异矩阵,不能直接求逆,因而需要利用伪逆矩阵来求解,其求解公式为:
其三,释“般若”。吉藏分别了般若之名和体。对于般若之名,吉藏列出了各种解释,比如说,《大智度论》的两种解释,一是智慧,二是般若甚深极重,智慧轻薄,因此,“不可以轻薄智慧秤量深重般若”(卷一,第89页下)。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地将般若理解为智慧。庄严寺僧旻法师认为,般若有五种含义,智慧只是其中的一种含义,并不是“正翻译”。吉藏又列举了经论中对于智慧的各种解释。他自设宾主而问:经论中为什么不“分明一途”地示人,指示人们什么是般若呢?吉藏指出,圣人并不是不能“一途分明”地示人,而是众生有取著之心,正因为这样,才不能体悟中道佛性,正观般若。如果一途实说了,众生容易执著。所以,不定之说,更显圣人之深意。因此,对于经论中的不同说法,不能“定执经论一文以成一家之义”(卷一,第90页上)。
对于般若之体,吉藏也列出了地论师、成实师和毗昙师三家观点而破之。地论师主张有真修般若和缘修般若两种,前者指第八识,后者指第七识。成实师主张“缘真谛心,忘怀绝相”,吉藏概括说,这是“以此解心为般若体”(卷一,第90页上)。毗昙师主张“缘四谛理无漏慧相是般若体”(卷一,第90页上)。破此三家的观点,吉藏在此处并没有展开。那么,什么是般若呢?这要从悟的角度来理解,般若是假名,吉藏说:“若行人了悟颠倒,豁然悟解,假名般若。”(卷一,第90页上)这个解悟之体,非心非离心。
其四,释“波罗蜜”。吉藏解释了“彼岸到”的基本含义,并特别说明,外国的风俗,大凡一件事做成了,就说“波罗蜜”。如果觉悟了般若,万行周毕,也称为波罗蜜。说到彼岸,吉藏指出,其也只是假名,令人因此而悟入,故不要有此岸、中流和彼岸的分别。所以,在此经的序文中,他说“波罗蜜”是“永勉彼此”。
其五,释“经”,从文和理两个方面论经,“今明文理因缘故为经,因文悟道故,以能表之文为经也”(卷一,第90页中)。
第七,明传译。这一部分主要说明与此经传译相关的议题。
有一种说法,此经本有八卷,如今只有一品*此说法出自《大悲比丘尼本愿经》末。此经只在吉藏的两篇作品中提及。,吉藏否认此说的可靠性。他以此经的三译而反驳八卷说。罗什法师弘始四年在逍遥园中正翻一卷,如果有八卷,他为何不翻译之?菩提流支三藏重译此经,经与论合有三卷,如果有八卷,为什么只解一品?真谛三藏于岭南重翻此经,也没有说有八卷。吉藏还反对此经只有一品说,“此经序、正、流通三分具足,何得止言一品?”(卷一,第90页下)
第八,明应验。持诵此经有何验益?这讲的是其宗教性的功效。总之,吉藏认为“得益不可称记”(卷一,第90页下),广益无量。
第九,释章段。吉藏对于已有的经文解释很不满意,“释者鲜得其意,致使科段烟尘纷秽,遂令般若日月翳而不明”(卷一,第90页下)。这种批评是非常严厉的。他粗列了一些观点,以示其得失。
北方流行菩提流支三藏提出的“开经十二分释”,一序分,二护念付属分,三住分,四修行分,五法身非有为分,六信者分,七格量分,八显性分,九利益分,十断疑分,十一不住道分,十二流通分。吉藏批评其不符合经论,是穿凿之论:“余钻仰累年载,意谓不然。今请问之:此十二分为出般若经文?为是婆薮论释?今所观经论,悉无斯意,盖是人情自穿凿耳。”(卷一,第91页上)吉藏认为,这种“穿凿”的释经方法,妨碍处极多。从吉藏此处的观点看,他主张经释要有经证和祖证,要有“经”的证据和“论”的证据。
也有六章释经法,一序分,二护念付属分,三住分,四修行分,五断疑分,六流通分。吉藏认为此一方法是对十二分法的“学之劣者”,过于与十二分法同,而患更甚。
也有人注此经开为三门,即因缘门、是明般若体门和明功德门*从经初“如是我闻”至“世尊,愿乐欲闻”为因缘门,从“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到“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为是明般若体门,从“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到经末,为明功德门。。吉藏认为,这种解释,“义亦不尽”(卷一,第91页中)。比如说,流通分属于此三门的哪一门?
还有一种三段说,一者序说,二者正说,三者流通说。吉藏认为,这三说释经法,与理无妨,问题是开善智藏之流在使用这种方法时,“不识三说起尽,故复为失”(卷一,第91页下)。他批评成实一系有人不知道三说从哪里起,到哪里尽,用得不当。比如说,把此经之初须菩提问的部分判为序说,从佛答须菩提的部分开始,为正分,吉藏认为,这就错了。一切经,若问若答,都是正,不能以问为序,以答为正。此经的序分,应当是经初途行乞食的部分。须菩提发问开始,就是正了。
在此,吉藏还提出了他的释经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即经文的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部分的互含,“三说无定。虽序说,不妨有正,虽正说,不妨有序。流通亦尔”(卷一,第91页下)。他还对三说的一般性体例作了说明:“序有二者,一通序,二者别序。正文有二,第一周广说,第二周略说。流通有二,一序佛说经究竟,二者明时众欢喜奉行。”(卷一,第91页下)这也可以说是对释经方法论层面的概括。
三、《正辨文》要旨
十重结构之第十重,为正辨文,基本上是随文疏释,也是《金刚般若疏》的重点,其中对序分的内容解释尤其细密。吉藏对于经文本身的解释,包含了诸多重要的观点,此处列出几点略加说明。
第一,三业分经。吉藏把此经的利益,分析为三业利益,他称此为“三业分经”,这似乎是他独有的说法:序分中的佛之“乞食”,是身业利益分,乞食后“入三昧”,是意业利益分,正宗分中的答弟子问,是口业利益分。
第二,通序六事和别序。序分的结构,又区分为通和别。此经自经初“如是我闻”始,为通序。吉藏概括了通序包含的六项内容,即六事:一明所闻之法(如是),二明能闻之人(我闻),三明说教之時(一时),四标说教之主(佛),五明住处(舍卫国),六明同闻众(与大比丘众)。这也是常规的解释。通序的六事,后来也被称为“六成就”,广为运用。为什么要有这六事?吉藏认为,“具足六事义乃圆足”(卷二,第96页中)。
此经自“尔时世尊”开始,为别序。此处,吉藏一如其整体的风格,提出了精细的解释。佛途行入城乞食,利益在家众生,与众生世间利,显如来是应供,是身业益物,令生身久住。佛乞食毕,敷座而坐入三昧中,通利益在家、出家众,与众生出世间利,显如来是施主,以般若法施众生,是意业益物,令法身久住,等等,内容众多。
第三,正宗分两周。自“时长老须菩提”以下,为正宗分。对于这一部分,开善智藏判为序分,称其为“叹请序”,吉藏再次认为“不尔”。北地论师说,此文内容属于十二分中的“护念付属分”,吉藏认为“是亦不然”(卷二,第99页上)。由此可以看出吉藏观点的独特性。由此段开始,经文体现了佛的“口业利益”。
正说分有两周,第一周是为利根人广说般若,第二周是佛为中下根未悟众生略说般若。吉藏认为,这样的区分是“惊乎常听”的。在对正文的疏释中,到第二周的内容时,吉藏也说:“初周为利根人说,钝根未悟,更为后周说也。”(卷三,第118页中)对于两周的区分,吉藏有一些证明辩答,来支撑其观点。须菩提有前问、后问,如来也有前答、后答,这是两周的证据。两周的内容,前周体现“缘”之尽,而后周体现“观”之尽,“前周则净于缘,后周则尽于观”(卷二,第99页中)。“尽”是一个否定词,真正要说明的是无缘无观,“尽缘故无缘,尽观故无观”(卷三,第118页中)。这样的“观”,吉藏勉强用一个名称来概括:“正观”。这种正观,吉藏称为般若、金刚,“强名正观,正观即是般若,即是金刚也”(卷三,第118页中)。“缘净观尽,不缘不观,无所依止,方能悟于般若。”(卷二,第99页下)这叫“缘观俱息”,吉藏认为,此经体现了这一层意思,但并没有正显。至于缘、观之别,吉藏又解释说:“前周尽缘者,正教菩萨无所得发心,破有所得发心,乃至无所得修行,破有所得修行,故是‘尽缘’也。今此章明无有发菩提心人,亦无有修行人,故是‘尽观’也。”(卷三,第118页中)
还有一种区分,就是两会的听众不同。“问:二周说何异?答:前广说,今略说;前为前会众说,后为后会众说。”(卷三,第118页上)
正宗分之初,佛答须菩提之问。吉藏认为,从“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不”一段往下,至 “经竟”,实际上是至《金刚经》“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一句,是断众疑,属于广说般若的第一周。可以理解,这一段文字之上的佛答须菩提之问,是“酬四问”,即对须菩提四个问题的回答,属于略说般若。“前酬四问名为略说般若,后断众疑即是广说。”(卷二,第101页中)
经中的第二周,吉藏认为从“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一段开始,“‘尔时须菩提白佛’下,二周说法中,此是第二”(卷三,第118页上)。此周至经末的四句偈为止。
两周的结构,吉藏认为都有三层:一般若体门,二信受门,三功德门。但第二周的三重结构小异于第一周。
第四,须菩提四问。正宗分开始,是须菩提之问,“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吉藏认为,须菩提此问,实为四问而非三问。如果依罗什法师翻译的经文,一般的理解有三问:“一问菩提心,二问云何应住,三问降伏。”(卷二,第100页下)有人将此三问理解为愿和行,第一问为愿,后两问为行,吉藏不同意这种解释。菩提心之问如果属于愿,那么怎么可能有愿而无行呢?有人解释三问体现了三种空,分别是平等空、实法空和假名空,吉藏也认为不当。须菩提没有涉及三空,佛也没有回答三空的内容。
吉藏认为,这里的须菩提之问有四问:“一问云何发菩提心,二问云何应住,三问云何修行,四问云何降伏。”(卷二,第100页上)其逻辑是:菩萨必须发菩提心,所以,首先问发心。如果依般若发菩提心,则住般若而不颠倒,所以,其次要问住菩提心。只有住立,才能修万行,所以,再次问修行。修无所得行,使有得之心不起,所以最后问降伏。
第五,以“四心”释经文。吉藏引用天亲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之文,“广大第一常,其心不颠倒,利益深心住,此乘功德满”,而概括出四心说:“四心者,一广大心。二者第一心,三者常心,四者不颠倒心。”(卷二,第101页下)他认为,天亲用四心释此经,他也依此。遍度三界六道众生,名为广大心;与众生大涅槃乐,名为第一心;常度众生,诲而不倦,名为常心;虽度众生而不见众生可度,是为菩萨不颠倒心。他认为,此四心不出慈悲和般若,前三心是慈悲心的体现,后一心是般若心的体现。
依此四心,《金刚经》中,“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涉及广大心,“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涉及第一心,“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涉及常心,“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
寿者相,即非菩萨”,涉及颠倒心。而对于两周的判释,其中的一个依据便是:“前周正劝生四心,后周明四心亦息。”(卷二,第99页下)
第六,四句偈。《金刚经》中几次谈到四句偈,比如第一次提到四句偈时这样说:“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胜彼。”*鸠摩罗什译:《金刚经》,《大正藏》第8卷,第749页中。但是,经中并没有具体的四句偈的内容,有的人却要把这四句具体化。吉藏引了这一类的观点,都加以否定,批评他们的解释“得经语,不得经意”(卷三,第108页下)。有的人认为这四句是“雪山偈”,即“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吉藏认为,“是亦不然”,因为这里不涉及别的经。有的人认为,这四句是一个“假名”,不可定有四句定无四句,也不可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四句,这里只是假四句以为偈。吉藏认为,经中并没有这个意思。
吉藏对此四句偈的观点是:“此乃是举少况多之言耳。”(卷三,第109页上)即四句偈只是说明,只要奉持《金刚经》最少的一点内容(以四句表示“少”),就可以有无边的福报,更不用说奉持此经的一章、一品、一部所能获得的福报了。四句并不是具体指哪一个四句,所以,一定要寻找出四句的解释,在吉藏看来,这都是没有了解经意。
第七,四果、十地之通别。《金刚经》中,佛曾问须菩提小乘四果,吉藏自设问答:“何故声闻法中立于四果,菩萨法中开于十地?”(卷三,第109页下)这个提问强调了大小乘果位的区别。
吉藏强调,大小乘之别,只是佛的教化的应机施设,善巧方便,佛法的根本原理本身并无大小之别,“圣人善巧,为欲出处众生,随其根性,故开大小。然至论道门,未曾大小。今作大小者,并是赴根缘故,开大小方便”(卷三,第109页下)。如果进一步分析,四果、十地则有通有别。吉藏认为,从相通的角度而论,四果也可以称四地,十地也可以称十果,大小皆得名“地”,悉得称“果”。但从别的角度,又有果和地的不同。
第八,财施不及法施。《金刚经》中,佛曾设
问:“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尔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鸠摩罗什译:《金刚经》,《大正藏》第8卷,第750页上。对于这一段的解释,吉藏讨论的一个主题是财施和法施的区别,这也体现了他的布施观。其基本观点是:“财施不及法施。”(卷三,第108页中)“财施则劣,法施则胜。”(卷三,第112页中)他举出了十条证据来说明。
其一,法施的时候,布施者多是圣人、智人,而财施的能施者,则不是这样,愚人不能行法施。其二,受法施之人,也必定是智人,愚者和畜生众都不领受智者的法施,而受财施者则不是这样。其三,从得福的角度看,法施能够使布施者和受施者都得福,而财施只有布施者得福,受施者不得福。这是法施的得福胜。其四,法施的时候,布施者和受施者皆有所得,而财施的时候,只有受施者得“五事果”,布施者有失。这五事果具体的内容,吉藏没有说明。其五,财施只有益于众生的肉身,而法施则有益于法身。其六,法施能够断惑,而财施只是降伏悭心。其七,“法施则出有法,财施则是有流。”(卷三,第112页下)这句话大致可以理解为,法施的时候,是有“佛法”布施出去的,而财施的时候,只是有钱财“流出”。其八,从果报的角度看,财施的果报是“有尽”的,也就是有限度的,而法施的果报则是无尽的。其九,从“得”的角度讲,财施的时候,并不是一时得到,而法施的时候,能够一时而得。其十,法施具足四摄,而财施只是四摄中的一摄,即布施摄。
第九,释五眼。《金刚经》中提到五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吉藏说,五眼的含义,“义别须释。今且示数意”(卷四,第120页上),即应当另外再作解释,可见他对此五眼的重视。他在此疏中,先简要表达了观点:
其一,从五人角度看,五人有五眼,“谓人有肉眼,天有天眼,二乘见四谛有慧眼,菩萨照三乘根性说三乘法有法眼,佛有佛眼”(卷四,第120页上)。
其二,从二人的角度看,二人有五眼,二人即因位之人和果位之人,因人和果人,菩萨和佛,“因人四眼,如《仁王经》叹菩萨得四眼五通。果人一眼,即佛有佛眼也”(卷四,第120页上)。
其三,从一人的角度看,这一人即指佛,佛有五眼,“一人具足五眼,即是佛”(卷四,第120页上)。
吉藏强调,五眼的差别在于是否达到“了”的境界,“四眼不了,佛眼具了,故名佛眼”(卷四,第120页上)。
四、结 语
此《金刚般若疏》在吉藏思想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其包含的观点比较丰富,应当有更深入的研究。从结构上讲,此疏从十层展开,在具体的疏释过程中,突出了其中观的立场,中道的方法,以及无所得的境界。一如其固有风格,吉藏在此常常体现“破”的观点,对与此经疏释的相关看法,大多持否定态度。但是,在破的同时,此疏也有所立,不仅正面表达了许多明确的观点,也正面引用了一些高僧的观点。当然,也一如吉藏的固有的风格,此疏疏文比较难读,行文繁杂。
有一个观点,必须在此作一个回应。杨惠南教授在其《〈金刚经〉的诠释与流传》中提到,吉藏否认包括《金刚经》在内的《般若经》为了义经,“但由于《般若经》不曾明说声闻、缘觉也能成佛,因此属于不了义经”*杨惠南:《〈金刚经〉的诠释与流传》,《中华佛学学报》2001年第14期。。理由是吉藏的作品里有这样一段问答:“问:《波若》未明二乘作佛,得是不了教不?答:《波若》明菩萨作佛,此事显了,未得说二乘成佛,约此一边之义,亦得秤为未了”*吉藏:《大品经义疏》,《续藏经》第24册,第209页下。。
吉藏也有“《般若》为浅,《法华》为深”的观点,这只是从二乘方便的角度而言的。“《波若》但明菩萨作佛者,《波若》已明佛乘是实,未明二乘作佛者,未开二乘是方便。约此一义,有劣《法华》,故名《波若》为浅。《法华》即明佛乘是实,复开二乘为权,故《法华》为深也。”*吉藏:《法华玄论》卷三,《大正藏》第34卷,第385页中。
但是,吉藏的这个观点必须全面地看。讲到未明二乘作佛的经典,《华严经》也有类似的观点,“岂可言《华严》未明二乘作佛故,显实亦未足耶?”《般若经》不言二乘成佛,有其缘由:“一切大乘经明道无异,即显实皆同。但《波若》、《净名》之时,二乘根缘未熟,故未得开权,至《法华》时,二乘根缘始熟故,方得开权耳。不可言未开权故亦未显实,《波若》、《净名》辨菩萨无碍之道,究竟无余,《法华》辨菩萨行复何能过此耶?”*吉藏:《法华玄论》卷三,《大正藏》第34卷,第387页上、386页下。吉藏所言的所谓胜劣、浅深,是从某一个方面的比较而论,“《法华》、《波若》互有胜劣。若为声闻人明二乘作佛,则《法华》胜,《波若》为劣。若为菩萨明实惠方便,则《波若》胜,《法华》劣”*吉藏:《法华游意》,《大正藏》第34卷,第646页上。。当然,不能依此“《法华》劣”,而说吉藏判《法华》为不了义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