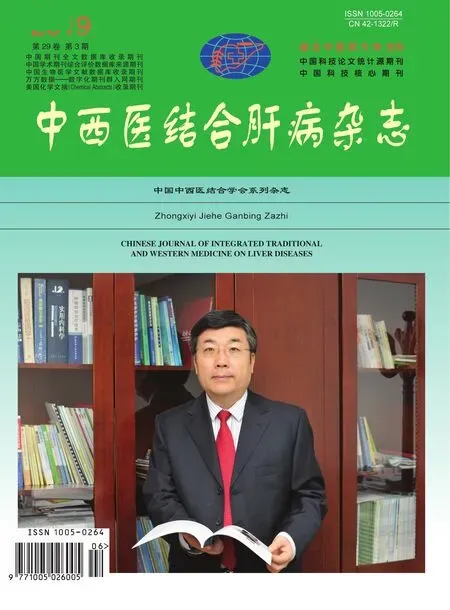中药内服加灌肠治疗肝硬化黄疸1例*
王 燕 赵 瑜 顾宏图△
1.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上海, 201203) 2.上海中医药大学肝病研究所
肝硬化黄疸属中医“黄疸”范畴,《素问·平人气象论》曰:“溺黄赤、安卧者,黄疸,已食如饥者,胃疸……目黄者,曰黄疸。”中医黄疸病是以目黄、身黄、小便黄为主症的一种病症,尤以目睛黄染为主要特征。下面就应用自拟方药口服加灌肠治疗肝硬化黄疸1例,分析如下。
1 病案资料
患者,男,76岁,因“反复乏力5年余,加重伴身目尿黄1周”入院。
有嗜酒史30余年,平均每天饮白酒约半斤。2011 年11月出现腹胀,双下肢水肿,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查PET-CT示: 胸腔、腹腔及盆腔大量积液。患者在肿瘤医院服用中草药保肝及“双克、螺内酯”利尿,症情反复。2012年12月在淮安市楚州医院检查乙肝全套示:HBsAg>250IU/ml、HBsAb(-)、HBeAg 663.472S/CO、HBeAb(-)、HBcAb 11.3S/CO、HBV DNA 1.24×108IU/ml。未进一步治疗。2015年6月自觉腹胀加重,双下肢水肿,在肿瘤医院查 B 超示:1.肝不均质改变(肝硬化可能);2.脾肿大;3.腹腔积液(深度100mm)。至我院肝硬化科就诊,诊断为“混合性(乙肝、酒精性)肝硬化失代偿期”,予利尿、保肝等治疗后病情好转出院。2015 年8 月患者再次出现腹水,下肢水肿,予保肝、抗病毒治疗后病情好转。2016 年下半年患者自行停用恩替卡韦,未再规律治疗。2018年7月27日,患者自觉乏力,伴身目黄染黄尿,遂于淮安市淮安医院查:总胆红素(TBil)305μmol/L、直接胆红素(DBil)213.8μmol/L、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91U/L、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79U/L、白蛋白(Alb)30.1g/L、HBV DNA 2.53×105IU/ml、凝血酶原时间(PT)17.3s。予保肝降酶退黄、抗病毒、抗感染等治疗后,病情好转不明显。
2018年7月31日至我院肝硬化科就诊,查TBil 420.2μmol/L、DBil 270.9μmol/L、IBil 56.3μmol/L、ALT 79U/L、AST 98U/L、γ谷氨酰转肽酶(GGT)120U/L、碱性磷酸酶(ALP)165U/L、球蛋白37.9g/L、白蛋白/球蛋白比值0.93、PT 17.9s、凝血酶原活动度57.0%、血氨64.0umol/L。B超示:1.肝弥漫性病变(肝损样表现);2.腹腔积液。腹部MRI示:1.肝硬化伴再生结节;2.脾肿大;3.门脉高压伴食管下段、胃底静脉曲张;4.腹腔少量积液。再次以“混合性(乙肝、酒精性)肝硬化失代偿期”收治入院。予谷胱甘肽、天晴甘美、多烯磷脂酰胆碱保肝降酶,螺内酯利尿,兰索拉唑抑酸护胃等治疗。8月4日查:TBil 540.5μmol/L、DBil 256.2μmol/L、IBil 284.3μmol/L、ALT 65U/L、AST 128U/L、GGT 336U/L、ALP 218U/L。症见:乏力,伴身目黄染,胃脘部不适,不知饥饱。小便量少、色黄,大便日两次,舌红,舌下脉络曲张,苔黄腻,脉弦。
患者经抗病毒、保肝降酶、利尿治疗后,黄疸仍急剧升高,肝酶持续上升,肝衰竭严重,病势较危。经胡义扬教授会诊后,于8月8日起予中药内服加灌肠,中西医结合治疗。中医辨证属肝胆湿热、血热瘀结,治拟清利肝胆湿热、活血凉血祛瘀,方药如下:茵陈、玉米须各30g,制大黄、白芍、车前子、茜草各15g,焦栀子、连翘、枳壳各9g,甘草6g。三剂,加水煎煮,一剂分三袋,分两次口服,另一袋予灌肠。嘱服药期间忌食生冷辛辣之物,忌烟酒,适寒温,注意休息。
8月10日,患者自觉乏力减轻,查TBil 383.7μmol/L、DBil 184.5μmol/L、IBil 199.2μmol/L、AST 84U/L、GGT 300U/L、ALP 237U/L。当前治疗方案有效,继续前方药口服与灌肠治疗。8月15日,患者黄疸较前明显消退,查TBil 269.4μmol/L、DBil 127.3μmol/L、IBil 142.1μmol/L、AST 58U/L、GGT 276U/L、ALP 236U/L。维持前方药治疗不做加减。8月21日患者乏力不显,黄疸较前明显消退,查TBil 188.4μmol/L、DBil 87.1μmol/L、IBil 101.3μmol/L、PT 15.2s、PTA 76.0%。患者病情好转,应患者要求准予出院,带前方14剂,嘱定期门诊随访。9月7日,患者于淮安市淮安医院门诊查TBil 82.5μmol/L、DBil 78.1μmol/L、AST 49U/L、GGT 107U/L、ALP 172U/L。
2 讨论
肝硬化作为多种肝病的终末阶段,黄疸是其最常见的症状之一。肝硬化时,病变的肝脏细胞功能下降,体内IBil转化为DBil的能力下降,使胆红素滞留血中,血中非结合胆红素升高;另一方面,肝硬化后肝脏微循环障碍,毛细胆管排泄受阻,胆红素难以通过胆道排泄而返流入血,血中胆红素升高,导致黄疸进行性加深和持续不退,高胆红素血症又进一步造成肝细胞损伤,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对大脑和神经系统亦有不可逆转的损害作用[1],为临床顽固难治病症之一。
中药灌肠疗法,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选配中药方剂,将药液经肛门灌注于肠道内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早在《伤寒论》中就有关于中药直肠给药的记载:“大猪胆一枚,泻汁,和少许法醋,以灌谷道内,如一时顷,当大便出宿食恶物,效甚。”《灵枢·本输》云:“肺合大肠”,“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大肠手阴阳之脉络,……下入缺盆,络肺”。肠道吸收津液、药物后,通过经脉上输于肺,而肺朝百脉,主宣发肃降,能够将气血津液沿经脉散布全身,并经肺气作用输注于心脉,将药物输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从而达到整体治疗疾病的作用[2]。现代医学的“肠-肝”轴理论认为肠道与肝脏相互影响[3],也为灌肠疗法治疗肝病提供可行性依据。
中医认为,黄疸多因外感或内生湿邪蕴结于肝胆,肝胆为气枢,为其所遏则疏泄失常,胆汁泛溢,上泛于目,外溢肌肤,下注膀胱而发为黄疸[4]。湿邪又可作为其他致病因素的基础。湿从热化,湿热郁蒸中焦,不得泄越,发为阳黄,身目黄色鲜明;或湿热蕴结化毒,疫毒炽盛,充斥三焦,深入营血,发为急黄,其黄色如金;或从寒化,脾虚寒湿内生,困遏中焦,壅塞肝胆,发为阴黄,黄色晦暗;或饮食不洁、劳倦太过均可导致黄疸的发生。
早在《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治》中记载:“黄家所得,从湿得之”,阐明黄疸的发生与“湿”密切相关,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无湿不作疸”的结论,治疗上更是根据“诸病黄家,但利其小便”提出“化湿邪、利小便”为治疗黄疸病的大法。而“脾色必黄,瘀热以行”,则进一步强调了黄疸的发生与“瘀”的关系,开拓了后世活血化瘀治疗黄疸的新思路。如现代中医肝病专家关幼波先生“治黄必治血,血行黄自却”的治黄要则。
本病案中,患者长期酒湿过度,致肝硬化。湿热蕴结,故见身目尿黄染;脾失健运,失于濡养故乏力,湿邪困遏脾胃,运化失司,故不知饥饱;肝病日久,年迈体虚,湿热疫毒由气及血,瘀阻血分,故舌下脉络曲张。辨证属肝胆湿热、血热瘀结。治以清利肝胆湿热、活血凉血祛瘀。方中以茵陈蒿汤为基础方,行清热利湿退黄之效。加大制大黄用量,保持腑气通畅,既助清湿热,活血通络退黄,又可排出毒素,防止内毒素进入血液。用赤芍、茜草活血凉血,助瘀热消而退黄。车前子利尿通淋、玉米须利水消肿,恰合仲景“诸病黄家,但利其小便”之意。外加白芍养血柔肝,连翘清热解毒,枳壳理气行滞,甘草调和诸药。全方共奏清利肝胆湿热,活血凉血祛瘀之功。《理论骈文》中指出:“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医理药理无二,而法则神奇变换”,本病例采用内服加灌肠疗法相结合,充分发挥了此方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