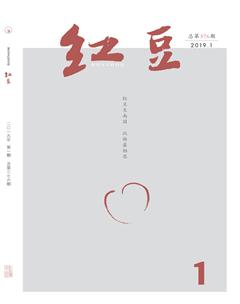静夜九帖
蒋蓝
独一的梅香
绍兴鲁迅纪念馆存放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二树山人写梅歌》。这是鲁迅于清朝光绪丁酉(1897年)即三味书屋读书时期完成的手抄,字迹工整、遒劲,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鲁迅手迹。内容是抄录会稽人童钰(别号二树山人)所撰写的咏梅诗集,看得出鲁迅对梅的倾心。鲁迅后来特请人刻过一枚“只有梅花是知己”的石印,还描述了他心目中的梅花隐喻:“中国真同梅树一样,看它衰老腐朽到不成一个样子,一忽儿挺生一两条新梢,又回复到繁花密缀、绿叶葱茏的景象了。”
他注意到的,在一种清寂的语境里,铁枝横斜的生命造像,两者从未发生龌龊与抵牾,彼此就是为对方而摒弃了昔日的友朋。寂寞如梅,寂寞如黄酒,浓到深处,因为寂寞而自生陶然,因为寂寞而自给自足,因为寂寞而豁然跃升喧嚷的生命。在这样的阅读印象里,我推测,先生的寂寞,必然是一头横卧、斜睨的豹子。
鲁迅在《怎么写》一文里回忆说:“记得还是去年躲在厦门岛上的时候,因为太讨人厌了,终于得到‘敬鬼神而远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白天还有馆员、钉书匠、阅书的学生,夜九时后,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楼里,除我以外,没有别人。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如今,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与之相遇的那一棵老梅树,依然屹立在三味书屋后院的东北角,树龄已超过一百年。
比利时作家马塞尔·德田纳在《处死的狄奥尼索斯》中声称,古罗马时代,人们认为豹子是唯一能散发香气的动物。在我看来,这是暗示了酒神与豹子合二为一的肉身化理由。梅花是豹子的纹身,豹子是一树狂奔的梅花。但在我的感觉里,这分明是远东的香味,是梅花的香味。梅与豹,是木性之精与行动的合二为一。扬雄《法言》说:“圣人虎别,其文炳也。君子豹别,其文蔚也。辩人狸别,其文萃也。狸变则豹,豹变则虎。”圣人老虎是王道之物,孤独的豹子停歇在梅树上,终止了自己的进化。
陆游的《卜算子·咏梅》算是梅香的高音部:“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狂吻马蹄的落梅,其实是想回到豹子身上。
孤寂,是漏斗形的孤寂,是孤独秘密酝酿、聚集、提炼香气的闭关时刻。所以黑色的梅树立在那里,不过是蝉蜕之术。香从孤寂的漏斗下逸走了。所以,只有静处,冷眼旁观时才能闻到;只有安静下来,才能看见。寂寞是一种自适,是一种有所顾忌、有所约束的自适,这里不存在西语里的自由。寂寞不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它对热泪与阳光总是略略反抗一下,它还是会融化,但总比别的事物要缓慢,也是最后收场的。寂寞者与骑墙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寂寞者本身就是一道墙,无须骑,那太费劲了。
世界上真的没有过不去的墙,但是,南墙是寂寞者最后的依靠。南墙不但是弱者自我保护的屏障,更是他可以流尽眼泪的唯一地缘。临到最后关头,绝望总会扶他一把,因为绝望不是均质的,绝望有很多疏忽的漏洞,钻过窄门,他就不至于丧失道义与立场。
世界在变,人就渴望与时俱进,不变的不是孤独者的信念,而是梅花。这与孤独者的未来无关,所以它仍然在南墙内外飘香。孤独的香气,伴孤独者成长,伴孤独者在人生的长路中体验无路时刻,一回头,总会看见梅枝上横卧的豹子。
知道吗?蜀字的三四十种解释里,有一种就是:独一、超拔。
皴法里的哲学
李约瑟在《中科学技术史》中指出:“中国的画家能够对各种地质现象进行这么多的鉴别这一事实本身,充分证明他们具有运用画笔忠实地反映自然的非凡才能……但这里面确实包含有道家那种古老的、经验式的循乎自然的倾向,因此他们所描绘的乃是真实的世界。”在我看来,这其中的筋骨,恰是线描与皴法的互为彰显。
皴法出现在唐代的绘画当中,这等于在线描之外,赋予了山与水的肌肤、纹理。皴法的沟壑开启了中国人平面图像的三维认知,以皴为法的笔墨成为中国山水画演义的美学主脉。皴法主要有披麻皴、荷叶皴、卷云皴等十几种。但是单纯的皴法只能画出山水的皮相,也就是只是展示了山水的细节与阴影变化,但是却无骨,藏匿在皴法更深处的,是人与自然之景合一的心情!一旦缺乏这一追问,即使山水画采用勾线法和皴法,也不能完美再现真实的自然景观。个别大师以一管之笔,拟万物之体,但绝大多数仅处于“画虎—画猫”的循环过程!
山石的阴影部分需用皴法来显出山石的棱角、厚度以及一石獨撑、一石横斜的动态危机,尤其是画家寄托其中的沧桑、孤寂、忧愤、笑傲,等等,通过山石的奇诡得到了无以复加的展现。论者强调尽量避免某些皴法在一张画上的混用,这已经形成一个定式。但是,这并不是皴法的全部。
皴法是山水当中深重的隐喻修辞,或浓或淡之墨,从中不难看出这是画家碾碎自己为墨的踪迹。每一皴法的纸上站立,均是他们身体与心灵的黑暗赋形。
唐代书法家张旭在谈到用笔时说:“孤篷自振,惊沙坐飞,余思而为书,而得奇怪。”“孤篷自振,惊沙坐飞”是传统惯用的诗学隐喻比附,用笔要像一种孤单的飞篷草浑身摇动一样,触动奋起、翻转奔逐;用笔要像受到震动的沙子,自然而然地飞起,奔放纵逸、豪情激荡。张旭绰号张颠,精晓楷法,草书最为知名。这句话的意思是,他看到了上面两种自然现象,领悟到了书法(草书)的用笔,从而使自己的笔势有了新奇的变化,达到了期望的振飞。
但不从皴之浓墨渊薮里展翅者,突兀而起如大漠孤烟,也不是没有。
但在皴法的深谷里徘徊多年的黄宾虹,某天抬头望天,他的眼光从陡然厚重的皴岩皱石上逡巡而过,他说,古人皴法皆无可用!他开始悟出积墨之理:“余观北宋人画,积千百遍而成,如行夜山,昏暗中层层深厚。”“作画不怕积墨千层,怕的是积墨不佳有黑气。只要得法,即使积染千百层,任然墨气淋漓。古人有惜墨如金之说,就是要你作画认真,笔无妄下,不是要你少用墨,世间有美酒,就是要善饮者去尝。中国有墨,就是要书画家尽情去用。”
陈子庄与黄宾虹交往数次,他顿悟出积墨之功,其画作皴无定法、气韵成章。
失眠注解
青春时代的失眠多为空灵性质,在于不知道为什么失眠反而显示出失眠的诗意。
中年时期的失眠多为具体性质,在于知道了为什么失眠而失眠,从而显示出失眠的下坠意义。
老年时节的失眠多为无心性质,因为失眠所以失眠,这就显示出失眠的生命无目的性。也恰恰是在这个阶段,与身体、与诉求无关的冥想,才开始缓慢地将它藏匿的翅膀,变得不再透明。
不再透明的失眠,有些接近于灯笼,接近于皮纸与烛火的关系。旁人窥视到打在粉墙上的影子,就臆想起宋朝空間一间书房的事情。其实呢,粉墙影子的实质并不是失眠,而是没有目的的回忆。只是因为觉得影子好看,所以愿意去回忆。而一个一味通过回忆取暖的人,他的回忆矿藏之所以不会枯竭,在于他走向回忆的矿井时,没有忘记点亮沿途的灯。一如他离开之际,也是不紧不慢地逐一熄灭了灯火,他只把自己的影子交给了黑暗。现在,他在一面镜子里就完成了这一工作。
比如,他越来越喜欢与黑暗相关的场景,旷野、废墟、隧洞、地下室、阁楼、停电时刻,他喜欢黑暗不断增值,但可以收放自如。
他在一种灰色的暧昧穿着里漫漶,甚至旁逸斜出,黑暗的大氅是他倾心的,但太过招摇了,为此他显得扭捏。他说,黑暗中思想的临盆,与阳痿的强度比较近似。后者的难堪与前者的狂喜相互侵略,它们在扳手腕。这种左右互搏的竞赛费力劳神,还是在失眠中两忘比较妥帖。为此,它们在失眠状态下歃血为盟。
他已经习惯在失眠时分写作。他像一个灯罩,被火焰千百次熏黄、烤碎、洞穿,尽管黑夜总是将浑身褴褛的身体予以庇护,可是他已经没有了疼痛,或者不安。对于失眠的写作,与其说他是就着火焰而完成的描红作业,不如说是蘸着黑暗让火焰退却并斩获的场地——就是那么可怜的一块巴掌大的地方,刚好搁下他从硝烟里退下来的思想。他想疗伤。
失眠之书
钱锺书先生说过:“有些人,临睡稍一思想,就会失眠;另有些人,清醒时胡思乱想,就会迷迷糊糊地入睡。”这两种情况并不属于我,临睡之前思考与否并不重要,失眠却是蛮不讲理,夤夜而来。
多年以来,我习惯于把失眠视为一棵树,一棵屹立在荒漠之中孤零零的大树。失眠不是谁轻易就可以造访的,尤其是心宽体胖者或喜欢励志格言的消沉者。因为要来到失眠的畛域,我就必须穿过漫长的偏头痛与重听。我别无选择,我时常来到树下躲避烈日与风暴,失眠反而成为了一个可靠的驿站。我远远看到,树上的鸟儿起起落落,木匠一般在天空弹出墨线,云朵这操起了斧头和锯子。我熟门熟路,来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就看见一派二十年前的大气迎面滚动,一袭狼烟把我簸起来,我必须把体重放在原地,我就随之飞起,像一片金色的枯叶,裹住了一把雪刃,但刀刃的冷光让我浑身褴褛。一个转身,我再次把自己伪装成春情盎然的蝴蝶,翅膀之后是童年的草坪……但是,放在树荫下的肉身不满意了,它在吼,它叫我回来。不要小人得志。不要找不着北。我只好像照顾弟弟那样回来。不快,还是回到我身上。我和身体一起,看着彼此渐渐老去,脸上爬出蚯蚓。
奇怪的是,有一阵子我睡过去了,一早醒来,就发现自己是一个没有完成功课、背起书包就要去上学的孩子,内心忐忑不已。我睁大眼睛,直视天花板,努力回忆,自己似乎应该没有完全睡过去,好像出去遛了一道弯儿。
失眠的确让人头脑昏沉,但昏沉是一种设防空疏的薄弱时刻。平常被理智阻挡在外的籁声,开始让我察觉到一些唯物之神,它们在我失眠的星空闪亮,它们只能照亮失眠的地域。我贪心,促使我带着它们进入梦境,它们就像如水的萤火虫,在窄门熄灭了……
失眠之夜
又是一个失眠之夜。承认失眠并非为了装酷,暗示自己是思想的邻居,随时可以串门儿的熟客。失眠对身体的未来不好,但没有了睡眠,未来又有什么鸟用?!
我非常清楚,我将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下听见一些响动:窗外的冷雨渐渐将箭矢加粗,苦闷的茎,彼此在排斥里撞击。看起来,像绝望的刺猬把浑身的硬刺发射殆尽,它变成了一只荒谬的老鼠。我偶尔听见一个女人的哭声,混合着九眼桥下锦江橡胶坝的跌水,构成了蜀地的夜雾。当然了,这不是主要的,接下来我会听到一些平素听不见的夜阑的挪位摩擦,就像我的上万册藏书里,那些正在尽情啃噬字里行间“神仙”两个字的书虫。它们渐渐变成了脉望,它们逸出了书页,带着发育健全的肢体以及尚未发育经历过极端严寒的灵魂,开始爬出窗棂, 一飞而暝。
现在,我的失眠陷入完全不可辨识的纯黑。
奇妙的是,这个短暂的时刻被窗外更大的雨涂改了。我偏偏看见一袭宝蓝色的旗袍,听见丝绸与身体的摩擦,运动就是在束缚与解放的矛盾里孕生的,因为不紧不慢,进而是带有体温的韵律。
一具斜靠在吧台的身体,头部隐入黑暗,灯光只能从背部缓慢浸入。在腰处渐渐囤积、收缩和跳跃针芒的光,在居中的缝合线周围,定形。开始熔化和大面积密植,将底层的构造浮至表面,向明亮的中心聚集。在针芒上伫立的舞蹈,弧度与椭圆的向心力,把蕴涵的热量甩出来,为向腹部的迂回和猜测做好准备。
经过夜的手指提纯的蓝色,是旗袍的下摆,它又在脚的紧靠下泛出一抹骨色。飘垂的日子突然飞起,作为对重力的抗拒,以不规则的收缩展示缎子的犹豫。光线被褶皱弯曲,改变流向,逐渐渗漏,犹如在金属液体里浸渍……当无边的蓝从光斑深处剥落,就剩下一波一波的起伏,在酒力作用下,成为空气与脉望的姐妹。这是夜晚最柔软、最收敛的部位,可以让身体沉静,像深渊的眼睛直面死亡。而真丝的鸣叫,是一根飞翔的羽毛,正穿越肉体,在我的头骨边缘环绕。
这一宝蓝色的声音与一些徘徊的脉望秘密接头,他们私奔而去……
我在这一间失去声音的房间里,听着心跳,学习热爱自己。
至纯之物
现实中的感觉往往逼真,以至于容易张冠李戴。没被污染过的少年,真纯!总是给人一种想一直保护着他们的纯,不给任何事物或人伤害到而被污染。但这类人单纯。
至纯是一种纯化过程。至纯的事物,指的是从一切美好或不美好当中跃升而起的事理,事理无所谓美好与否,但必然坚忍而素洁。
如果说突然而来的花香,是为了暗示花朵之外、香味隐喻的无垢与无色,那么,有人说花朵简直就是罪孽,似乎成立。
问题在于,一旦抛弃了花,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至纯之物总是又与具体的事体融为一体。
那些黏稠的、浓得化不开的、打不破问不得的、浓郁的、浓艳的、纷繁的事物,均是至纯之物的姐妹。那些捡起影子就忘情的人,他们的特点是肉身阅历发达、智慧欠佳,他们是醇酒、美色的买主,或卖主。为什么买,为什么卖,他们并不知道买卖的平衡与适可而止。
爱那些有伤疤的人,爱那些爱过以后满身伤痕的人。爱那些有伤疤的往事,要学会爱那些残损的。
一个人并非一味单纯就可以旱地拔葱一般,抵达至纯。一个人穿越了这些矫情与风月,提炼最多的是悔意,因为悔意的往返曲折足以使一个人变得谦逊而虔恪,由此才有抵达澄明的可能。
我发现,少数人成功做到了,却让绝大多数步其后尘者比如纸上的诗人,产生了集体性幻觉。
云雾哲学
天上的云朵总是轻而慢,具有神话学色彩。只有置身大海或极高山,当云朵俯下身躯,以匍匐的军团那样冲杀而至时,才会领略到云朵的浓重与坚硬。
这就像我与思想的相遇,多半是在猝不及防的时刻,遭受到它的反手剑与风暴攻击。甚至还没有看清楚思想的容颜,它已经轰然远去了。而留在我身心的伤痛与惊骇,应该就是思想的面目。现在,山巅上的白云突然溢出了墨汁,我确信,它就是思想的再一次君临。
壮美而有力的东西,比如出血的文学,比如一去不复返、毕生不会见面的情人,总是让人在惊骇里学会收敛。
在峨眉山里住久了,我熟悉这里的季候。峨眉山海拔1000米之上是獨立王国,气候不受周围影响,它自给自足,不停地下雨,不息的雾凇与孤月朗照……但是,它的吐纳功夫与别的名山不同之处在于:云与雾可以造型、可以彼此转换,云雾与精灵构成了一种停云,它们并不需要躲避阳光,反而在强光下放荡,渐次妖冶。这里有孤零零的一片一片的冷杉林,因为采取紧紧相拥、密不透风的站位,看上去却是发黑、发蓝色。它们豹子一般呆在坡度陡峭的山肩修身养性,吐纳湿度极大的雨雾,一团团从密林间涌出,就像志怪、传奇的母体一样,于瞬间生成,又在瞬间完美和谢幕。
雾气之中,树与树已经不分彼此,像叔本华所描述散文相互取暖的“刺猬困境”,但各自把针叶调整到可以忍受的长度。因为处于一种迷醉之态,冷杉在夜晚将雾气的浓度调至最黏稠状态,像是从褴褛的爱情里提炼而出的欲火,以体液的方式玉体横陈。我猜想,如果剖开树干,它一定会流出乳白的髓。或者,里面晃动着金瓶梅的叙事腰身。
沉默的杉木不开口而已,一旦开口,就有雷霆之势。这让人联想起海德格尔住在南黑森林里说的话:“那种把思想诉诸语言的努力,则像高耸的杉树对抗的风暴一样。”
唐代最为著名的斫琴家是四川雷氏家族。雷氏造琴传承三代共计9人,造琴活动从开元起到开成止,前后120多年,经历了盛唐、中唐、晚唐3个历史时期。他们所制的琴被人们尊称为雷琴、雷公琴、雷氏琴。《嫏嬛记》引前人之说:“雷威作琴,不必皆桐,遇大风雷中独往峨眉,酣饮著蓑笠入深松中,听其声连绵悠扬者伐之,斫以为琴,妙过于桐。”大雪压树,树枝欲裂,直到发出咔嚓的开裂声,斫琴家由此循声辨音寻木。雷威所作之琴,并不拘泥于梧桐、梓木,而是以“峨眉松”,却比桐木制作的还要好。在传世古琴中,尚未见有松木之作,文献中亦只此一例。根据考证,所谓的“峨眉松”,正是杉木。
奇怪的是,阳光泼不进去的冷杉林,深夜的月光却像登徒子一般,翻越花墙而来,从容插足。并在林间旋转,撒下了一地的珙桐花。
那一夜,我在杉木林里穿行了很远。非常清楚,我听到有一个声音在我身后叫我,猛然回头,一棵树把我拦腰抱住。
诗歌是中性的声音
2016年初,在寒风料峭的成都,我采访了神话学大家叶舒宪先生。席间谈到他早年的一个引起广为议论的“诗从寺说”观点,他说,历经20多年,我至今不改初衷。
王安石根据许慎《说文解字》“寺,廷也,有法度者也。从寸之声”之说,在其《字说》里认为“诗为寺人之言”,进而把寺人之言解为法度之言。叶舒宪认为“寺”上半为“屮一”,下半为“手”,寺是主持祭祀的人。诗、持、寺三字同源,古音同部。也就是说“寺人之言”是指举行各种原始礼仪时使用的祝辞、颂辞与套话。
叶舒宪认为,诗言志当为“诗言寺”,进而释寺人,认为早期无寺庙,故寺当为“阉割之人”主祭祀,故而中国诗多阴柔之美。谈到这里,他对我做了一番阐发。考察古代乃至现在的原始民族,巫祝之人在烟雾缭绕的殿堂里俯仰,与神灵附体,然后代圣立言。他们魂不附体、喃喃自语的声音,并非雄性而昂扬,或者雌性而低回,级别越高的巫祝,发出的声音呈一种中性之声,有点“不男不女”的去性别意味。
我倏然一惊。
联想自己曾经拜谒过的多座宗庙,以及参加过的凉山毕摩大会,我甚至觉得,那些尊贵的发声者,闭目徘徊,旁若无人,进而浑身战栗,声音的确达到了一种“中道”境界。另外,毕生从事这一灵魂二传手的职业,他们的相貌也在发生变化。
记忆里最清晰的一次,是在康区的桑披寺。一早的阳光从天窗涌进来,把一个偌大的经堂铺出一地明媚。地毯上的金莲花在强光下绽开了蓓蕾,呈现一种地涌金莲的幻象。经堂里非常安静,只有檀香在荡漾。远远地,看到一个背影,背影开始发声,我听不懂梵语,但声音分明是从背影下腹热热地蒸腾而上,嗓子开始为之赋形。
在一束光柱中,可以看见气流的跌宕方式,因为灰尘就是最好的标示。背影不断发送而来的声音,在光柱里袅娜,又像金刚杵那样兀立。
高原特有的低氧效应,为听觉带来了一种敏锐。那是一种熟铜的声音,锃亮而柔韧,毫无阻碍,又没有像蝴蝶那样迎风飞起,而是收敛地低飞,然后收拢,把那些没有被照透的地面阴影逐一点亮。黄铜与金色阳光相遇,呈现一种为黄金镀金的庄严,与屏声静气。
我感到诗歌就是这样生成的。我们在《诗经》《楚辞》乃至仓央嘉措的诗里,读到那么多语气词,当代人都视作无益,甚至是一种累赘,目前仅仅成为小学生作文里高频率的使用词。哪里有这么“啊”啊!绝大多数的语气助词都是以韵母为主的开口音发音,比如啊、哎、哦、诶、哟。“兮”字的现代汉语发音与古音完全不同,清代孔广森《诗声类》里说:“《秦誓》‘断断猗,《大学》引作‘断断兮,似兮猗音义相同。猗古读阿,则兮字亦当读阿。”
啊,其实这些语气助词是记录声音把词语托举在空中,它们飘飞的声音,衣袂与空气亲吻的声音,手指与蛇腰缠绕的声音,舌尖寻找红唇的声音……
由于现代汉诗的修辞已经被翻译体完全占领,纸上诗歌是写出来的,古人是吟唱出来的,与其说一些诗人在寻找元写作,不如说是在追忆那种声音。尤其是,那种从头骨中缝灌注的中性之声。
“鱼肚白”的异托邦
近读罗马尼亚诗人卢齐安·布拉加箴言录《神殿的基石》,他对地平线的看法是:“极目远眺,任何地方唯见深渊。”这一峭拔的见解深获我心。
我估计,卢齐安·布拉加看到的地平线,应该是在黎明时分。因为在那个晦暗而希望缓慢的聚集地带,他一定遇到了一种被汉语标举为“鱼肚白”的神秘主义色泽。
但只要仔细打量黎明时分延宕的地平线,就会发现那里麇集着很多颜色,但唯独没有白色——无论是惨白、苍白、润白、淡白,都没有。其实,在阴天雨天时天空的颜色大部分也为鱼肚白,尤其是巴蜀秋冬时节的天气。地平线一如锯齿,山峦跌宕,或者水天茫茫,它们拥有山与水的层次,可以分出不同的重量隐喻。
无论是登临群山之巅,还是置身高楼大厦之上,日出都是一天中最纯洁的时候。我想,西西弗斯也该身披朝霞,推动他的巨石了。
我把注意力收敛一下,注视这个奇妙的“鱼肚白”。
古有“鸡冠红”指称一种如血之红的玉石。而诗人汤国梨1978年在薛家桥的旧作《棹舟》诗“春水鸭头绿,夕阳牛背红。瓜皮渔艇子,摇出小桥东”,“鸭头绿”之外,“牛背红”一词异峰突起,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至于还有象牙白、猪肝紫、乌鸦黑、鹅蛋青、鸭蛋黄、鹦鹉绿、鸦背青、猩猩红之类,不一而足。显然,“鱼肚白”恰恰也属于这类动物色彩学谱系。这些动物应该与古人密接相关,这再一次佐证古代先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命名造句不是虚构的。
清人陈康祺笔记《郎潜纪闻》里,记录明末清初活跃于金陵一带的风雅名士,记了尤侗挽余怀的两句诗:“赢得人呼‘余杜白,夜台同看党人碑。”而在“余杜白”之下,自注一行小字:“鱼肚白,金陵之染料名也。”而诗中的“余杜白”是指明末时期金陵三位诗人,余怀、杜俊、白梦鼐。这分明是用“鱼肚白”的谐音。鱼肚白是明末金陵一带主流的服饰之色。先有染料,然后才有了对三位诗人指称的挪用。
那么,到底谁才是“鱼肚白”一词表指黎明天色的首倡者?
明朝山阴散文大家王思任有名文《小洋》《天姥》传世,《小洋》是难得的描写落日余霞壮美奇观的妙文,几乎囊括了黎明天色的色彩描述:“日益曶,沙滩色如柔蓝懈白,对岸沙则芦花月影,忽忽不可辩识。山俱老瓜皮色。又有七八片碎剪鹅毛霞,俱黄金锦荔,堆出两朵云,居然晶透葡萄紫也。又有夜岚数层斗起,如鱼肚白,穿入出炉银红中,金光煜煜不定。盖是际,天地山川,云霞日彩,烘蒸郁衬,不知开此大染局作何制。意者,妒海蜃,凌阿闪,一漏卿丽之华耶?将亦谓舟中之子,既有荡胸决眦之解,尝试假尔以文章,使观其时变乎?何所遘之奇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看到天空越来越暗,周围近处的沙地变成浅蓝、灰白之色,对岸沙洲全然是芦花月影,一片朦胧。群山也都成了老瓜皮色。而太阳落山的上空,又有七八片像剪碎鹅毛的晚霞,全是黄金锦荔色,逐渐堆出两朵云,竟然是晶透葡萄紫的奇异色彩。山中夜雾层层涌起,如鱼肚白,穿入出炉银红中,金光闪闪。此刻,天地山川、云霞日彩,烘蒸郁衬,像一个大染坊,却不知要染什么。我私下揣度,眼前景色胜过海市蜃楼和佛光妙境,似乎露现祥云的华美。又像是为心胸荡漾、眼眶睁裂的舟中人以心灵之启,上苍赐予的自然文采,使他们观赏景色随时变化的奇妙。为什么我遇到的景象是如此的奇异呢?
需要注意,“鱼肚白”一词出现了。这是不是首次被人使用?不好妄下定论,但王思任似乎是肇始者。
显然王思任是刻意写作这篇文章,目的就是渴望解决大自然色彩的描述。他在文末总结说:“夫人间之色仅得其五,五色互相用,衍至数十而止,焉有不可思议如此其错综幻变者!曩吾称名取类,亦自人间之物而色之耳,心未曾通,目未曾睹,不得不以所睹所通者,达之于口而告之于人;然所谓仿佛图之,又安能仿佛以图其万一也!嗟呼,不观天地之富,岂知人间之贫哉!”
不看到天地富有,怎么知道人间贫乏?!其实,这是指文人想象与词语的贫乏。
我推测,所谓鱼肚白,大概与现在的淡蓝色相近,杂以白底。是微微发蓝的白,并不容易看出蓝色来。电影《卧虎藏龙》里周润发饰演的李慕白所穿的月白长衫,近之。这样的男人一身月白长衫,回头一眼,就足以让知性女人彻底沦陷……
有学者指出,西方色彩词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以比喻修辞和崇高、悲观的美感为主要基调,而中国色彩词的使用以象征修辞和优美性为主要风格。黎明在不同的眼睛里,颜色的确不同。汉语的“鱼肚白”,英语将其称之为rosy-fingereddawn,归入了红色。
西方人与地平线的哲学话题车载斗量,仅举一例:一次笛卡儿坐在自己屋前的台阶上,凝視着落日后昏暗的地平线。一个过路人走近他的身旁,问道:“喂!聪明人,请问,天上有多少颗星星?”他回答道:“蠢人!谁也不能拥抱那无边无际的东西……”
那么,笛卡尔看到的地平线,其实是希望,或者说是乌托邦。犹如詹姆斯·希尔顿写作《消失的地平线》,无论如何,他永远也找不到那个蕴藏着恒在生机与安宁的国度了。他们看不穿的,是汉语味蕾主义的鱼肚白。
但是,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在《日记》里指出了一个奇特现象:“鱼类死后,肚皮向上翻转并浮上水面。这是它们的堕落方式。”这就是说,有些堕落,是以“上升”的形态来完成的。这也许是所有堕落当中最危险、最可怕的一种了。
死鱼们齐齐浮上水面,波光粼粼,被第一道霞光熏染,似乎充满了不可预测的生机。也许,这才是西西弗斯新的一天。
责任编辑 练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