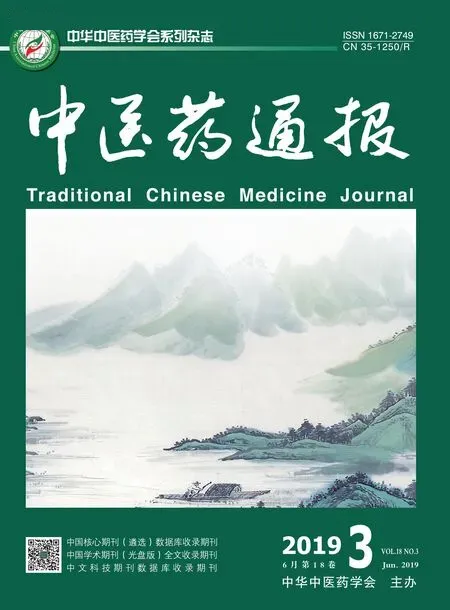论中医学复兴的突破口
● 李致重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遭受到长期的自虐、自残。表现在中医上的自虐与自残,即中医学西医化。这是一百年来“文化对文化的误解,科学对科学的摧残”所造成的传统哲学贫困和近代科学主义泛滥的结果。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终止中医学西医化,实现中医学全面复兴,是我们面临的重要历史使命。这里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一些讨论。
1 复兴中医学要牢牢确立大科学观
当今,全社会时时处处都在讲“科学”二字,但许多人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却讲不清楚、理解模糊。人们头脑里的科学往往只是来自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而不是人类科学的全部。至于作为人类文化核心的哲学,更被人们不自觉地置身于科学的大门之外。虽然偶尔也会听到“哲学是科学的科学”的说法,但是对于哲学这一概念的准确解释至今依然求之不得。最近一段时期,许多人喜欢用文化二字来定位中医,殊不知文化原本是一个内涵极大的概念。大到哲学、科学,小到民俗、风情、餐饮、衣着,举凡一切可以用文字、语言、符号表述的知识,皆在文化这一概念的囊括之中。从概念的逻辑意义上讲,要想准确说明中医学是谁,那就要首先从科学、哲学这两个概念的内涵说起。
科学这一概念,是日本学者在明治维新时期首先提出来的。面对由西方蜂拥而至的门类繁多的近代知识体系,日本学者将日文中故有的“科”与“学”两个汉字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科学这一新词汇,作为表征诸多不同学科的新概念。显而易见,科学这一概念的本意即分科之学。其中的“科”字,即分门别类之谓;其中的“学”字,即系统化的知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面对着由欧洲传来的以近代物理学、化学为带头的种种自然科学或技术知识,科学这一词汇诚可谓应时而来,乃含义清晰的时代性新概念。
哲学这一概念,也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首先出现的。其中的“哲”字,取意于中国古代的“知人则哲”;其中的“学”字,当然是出自于智慧高深的哲人创造的知识。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称之为“爱智慧”。其中的“爱”,指的是学者强烈的求知欲;其中的“智慧”,指的是哲人所揭示的超越于一般知识的学问。可见这与中国早期的“知人则哲”的含义是完全一致的。值得欣慰的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学者既没有将西方传来的近代科学与古希腊、罗马时期智慧高深的哲学相互混淆,也没有将中国历史上的哲学诬之为落后的、封建的而弃之于知识、学问、智慧之外。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在科学与哲学这两个概念的翻译上,有一个至今值得中国人深思的现象。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把日本首创的科学这一概念翻译为“格致之学”。同一时期天主教会的大学者马相伯也将日本首创的哲学这一概念翻译为“格致之学”。当年我们的前辈为什么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与两千年前的哲学统统翻译为“格致之学”呢?这是值得我们仔细推敲、深刻反思的。
《大学》里的“格物致知”,即分门别类地研究事物而获取知识、学问的意思。《大学》那一时代,当然没有来自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所以“格致之学”无疑就是哲学。当年的康有为、梁启超、马相伯没有将哲学与近代的自然科学相互混淆,没有在哲学与近代的自然科学之间厚今薄古或者厚古薄今,或将中国历史上的哲学诬之为落后的、封建的而弃之于知识、学问、智慧之外。
从弗朗西斯·培根关于知识就是科学的意义上讲,哲学与近代自然科学都是知识,所以哲学与近代自然科学也都应当是科学。按照当代辞书、教科书上的普遍说法,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普遍(一般)规律的高度概括;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知识体系。所以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于研究对象上的普遍还是个别,在于知识层次上的高度还是具体。普遍当然大于个别,高度当然位居具体之上。正是因为哲学与科学在研究对象与知识层次上的上述区别,近代常将哲学称之为“科学之母”,或者“科学的科学”。所以笼统地讲,哲学、科学皆是科学;具体地讲,哲学是“科学之母”,是“科学的科学”。
从哲学与近代自然科学各自的分类上讲:人类自古以来的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属于哲学体系的科学;人文学科的历史、文学、美学、法学、军事科学等具体学科当属哲学体系的具体学科。近代自然科学之首的物理学、化学,以及从属于物理学、化学的名目繁多分科之学则属于近代自然科学具体学科。此外这里还需要说明,近代自然科学里的天文学、气象学、物候学、生态学、农学、环境科学等,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哲学的支配。倘若人们将近代物理学、化学基础上的近代自然科学视之为人类知识或科学的全部,那就错了。倘若因为近代物理学、化学基础上的近代自然科学为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物质文明,所以忘记了哲学是“科学之母”“科学的科学”,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值得中国人骄傲的是,《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说,其实是人类科学史上最早、最准确,至今依然是首创性、公理性的科学分类学第一标准。依据《周易》这一公理性标准,哲学是关于万事万物“形而上者谓之道”的带头科学;近代物理学、化学是关于“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带头科学。哲学类的科学成熟于春秋秦汉之际,以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象、现象(包括中医学的证候)为研究对象;近代物理学、化学类的自然科学出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以物质实体的结构与功能(包括西医学的人体结构与生理)为研究对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倘若没有近代物理学、化学为带头的“形而下”的自然科学,就不会有物质、经济的真正繁荣,也将会沦为受人施舍的对象,沦为经济上任人摆布的弱者。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倘若没有“形而上”的哲学,它不仅不会成为真正的精神文明大国,也不会孕育出思维能力缜密、健全的民族与国民,自然更不会成为近代物质繁荣的真正强国。
不论隶属于哲学还是近代物理学、化学为带头的自然科学体系,凡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种种原理,都应当是超时空而存在的。但是必须强调的是,时间的先后历来不是评定哲学、科学之是非的常规标准。倘若以时间的先后为借口把近代物理学、化学及其体系下的各门自然科学视为科学,并以此非议、排斥哲学中的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及其哲学体系下的其它人文与自然学科,无疑是当代典型的文化对文化的误解,科学对科学的摧残。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学科门类的区分首先是以其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区分的。所以应当肯定:将“形而上”的以万事万物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和哲学体系下的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以及其它人文学科、自然科学,与“形而下”的以物质实体结构与功能为研究对象的近代物理学、化学及其体系下的其它自然科学加在一起,才是人类科学的全部。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周易》提出人类科学分类学上“形而上”的哲学、科学,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形而下”的近代自然科学,彼此之间是并存、并重的关系。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将永远不会改变。
基于上述讨论,这里需要着重说明以下两个基本观点。其一,不承认“形而上”哲学、科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我们的科学观就是严重残缺不全的。不承认“形而上”哲学、科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我们的国家、社会就不会实现真正的文明与富强。在全面复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首先应当牢固地确立起大科学观。大科学观的具体表述是:把“形而上者谓之道”的哲学、科学与“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近代自然科学,共同纳入人类科学体系整体范畴,纳入每一个人的科学视野的思想与观念。
其二,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基础理论体系形成于两千多年前,是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孕育下产生的。西医的解剖学、生理学的形成比《黄帝内经》晚了近两千年,是近代物理学、化学的成熟所孕育的结果。中医与哲学一样,研究对象都是事物运动变化的现象(或证候);西医与近代物理、化学一样,研究对象都是物质实体的结构与功能。中医与哲学的研究方法,皆是由综合到演绎的逻辑思维方法;西医与近代物理、化学的研究方法,皆是由分析到归纳的实体实验方法。从《周易》的意义上讲,中医是“形而上”的医学,西医是“形而下”的医学。人们不可能用西医实体实验的方法研究中医“形而上”的证候表现,也不可能用中医逻辑思维的方法研究西医“形而下”的结构与功能。这是由人类科学分类学的规律所决定的,与人们主观的意志或愿望无关。所以当今中医领域流行的中医学西医化,注定是行不通的。
2 不忘历史教训、振奋文化精神
清朝王权专制衰亡以来的一百年,是中国灾难不断和急剧变化的一百年。这一时代的确造就了层出不穷的近代文化精英和权威;这一时代的不少文化精英和权威在传统文化自残的潮流中,也不知不觉地自残了自己。灾难不断和急剧变化的时代,来不及为当时的文化精英和权威留下太多的沉思、历练和自我完善的机会。因此文化精英和权威的文化精神与人格的完善,也在这个时代留下了许多不可弥补的遗憾。
德国著名的思想家、作家、科学家歌德说:“权威,人类没有它就无法生存,可是它所带来的错误竟然跟它所带来的真理一样多。本来应该依次消失的事物,权威居然让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存在下来;对于应当保存的事物,权威却不去保存,而让其湮灭。人类之所以缺少进步,权威应当负主要责任。”
在三千年未有的传统文化大变局的一百多年里,有的精英和权威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混同于王权专制的文化说教,长期非理性地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自虐、自残。有的精英和权威借生物进化论而宣扬了社会进化论的邪说,加剧了近代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卑症。有的精英和权威在推进西方民主、科学上功不可没,但也极力主张“全面反传统,砸烂孔家店”。以上种种,造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空前贫困,形成了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化的近代科学主义思潮。随着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不断泛滥,传统哲学体系里的诸多学科饱受摧残举步维艰,甚至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之灾。中医学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英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罗素说过:“人类唯一的历史教训,就是忘记了历史教训。”当我们平心静气地反思传统文化自残的历史教训时,一百年来引领文化方向、潮流的权威们,首先应当对传统文化的误解和传统科学的摧残负起历史的责任。尤其重要的是,当今所有的人都应当从文化对文化的误解、科学对科学的摧残中认真吸取教训,并把这一历史教训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应当具有的文化精神。
笔者在《医医》一书中,对文化精神是这样表述的:“文化就是文化,只为文化负责,不为功利所使的那么一种彻底的治学态度和学究气。”这种不为功利所左右的“彻底的治学态度和学究气”,研究科学、哲学离不开它,处于兴衰存亡中的中医学更离不开它。
在文化精神中,最重要的是文化人的良心。这种良心就像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说的那样:“良心,就是我们自己意识到内心法庭的存在。”换一个角度讲,文化、科学工作者的“内心法庭”,就是荀子所说的时时监督和推动文化进步的“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在这种监督和推动文化进步的仁心、学心、公心,造就了每一位文化人的“只为文化负责,不为功利所使的那么一种彻底的治学态度和学究气”,养成了那么一种自然而然的风格或习惯。也只有这样,才会展现出不为功利所使地全身心投入文化、科学事业的自觉行动。
笔者在谈到做一个合格的中医人时曾经说:“人乃生灵医因贵,道出岐黄德为基。”生命是天下人生最可贵的,务必敬畏,不得亵渎。医学是人类科学中唯一以济世活人、救死扶伤为宗旨的科学,每一位以敬畏生命为天职的中医人,每时每刻都必须葆有只为中医学负责、不为功利所使的“那么彻底的治学态度和学究气”。
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的经济效益当然十分重要。但是,面对疾病折磨中的生命,医学工作者的仁心、学心、公心则丝毫不容动摇。在中国,质疑中医学西医化的呼声已达半个多世纪,而中医学西医化至今还存在。在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新时代,我们必须得认真反思学术界文化精神。
3 医治传统哲学贫困、清除近代科学主义
近代文化对文化的误解、科学对科学的摧残,反映在当代中医学术与事业上,即传统哲学贫困和近代科学主义泛滥。这里的近代科学主义,即以近代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作为评价一切科学之是非的至上信条或唯一标准的思想观念。当代中医学的西医化,同样是近代科学主义泛滥的结果。
中国的传统哲学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都是在人类第一次文化高峰时期成熟的。两者在文字表达形式上各有不同,但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逻辑思维上,彼此都是相通的。就哲学的体系结构而言,伦理学是哲学的“用”,知识论(也称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哲学的“体”。在哲学的伦理学里,中国的《老子》主要揭示了自然伦理,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学主要揭示了社会伦理,而融入中国哲学的佛学主要揭示了生命伦理。在哲学的知识论里,认识论是关于准确把握事物呈现的现象特征,以认识事物本质的逻辑原则;方法论是关于综合研究事物的现象,经过演绎而揭示事物本质的逻辑思维方法。
一百多年来科学对科学的误解、文化对文化的摧残中,中国传统哲学里的《周易》以及道家、儒家、名家、阴阳家、墨家、法家和佛家等学说,长期被诬为主观唯心主义及客观唯心主义及封建、落后的文化糟粕以致我们上下的三、四代人在哲学观念与伦理上、在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上至今所知甚微,逻辑思维能力甚差。直到今天,当代许多人依然对中国传统哲学停留在唯心、落后的偏见里。由此,在造成传统哲学贫困的同时,也进一步助长了近代科学主义的泛滥。
中医学与自然科学里物候学、生态学、植物学、农学等,与人文科学里的历史、文学、美学、法学、军事学等,都是从现象观察出发以认识其对象本质的学问;都是遵循由综合到演绎的逻辑思维方法而逐步形成并走向成熟的学问。所以这些学科,也都是从属于哲学体系之下的科学。而在传统哲学贫困的当代,中医教育长期以理科的标准招收学生,大学教育里除了少量的古文课程之外,至今没有把中国哲学列入必修的首要课程来安排。这是造成当代中医人知识结构不合理,造成中医学与传统哲学母体之间严重断裂的主要原因。
一百多年来,人们常将物理学、化学为基础的近代自然科学,称之为近代或者现代科学。与此同时,也将近代自然科学派生的诸多技术学科纳入现代科学之中,见怪不怪地统称为“现代科技”。而哲学奠基的人文科学、思维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中的物候学、生态学、中医学等,却被人们普遍地矮化、忽视了。有的人甚至固执、武断地认为“中国自古有技术而无科学”。至今极少有人认识和承认《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以及明清时期的温病学的科学价值与地位。对于两千多年来中医学成功地指导临床辨证论治的事实,对于近代物理学、化学还未问世及近代西医学还未萌芽而中医早已走向成熟的事实,人们几乎无知到丧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念的地步。
当代的中医人最应当自责的是,一百年来为什么未能面对人类科学之林,不能遵照学科定义的逻辑原则为中医学作出定义呢?更令中医人难堪的是,为什么至今依然沉溺于以结晶、瑰宝、伟大宝库、特色、优势、独具、原创性等等自我溢美的形容词之中,来充当中医学的定义而向时代介绍、推销中医学呢?按照学科定义的逻辑原则,在学科定义的定义项里只能使用名词而不允许使用形容词——形容词是无法准确揭示一个学科的本质属性与特点的。如果大到中医的藏象理论、临床四诊、病机学说、治疗法则、方剂结构、中药原理,小到人们常说的一技之长、一条经验、一点体会、一方一药、一针一艾,都可以称之为结晶、特色、优势、独具、原创的瑰宝时,中医学的未来能以这些形容词为根据,制定出可操作的创新与发展战略吗?
中医学至今没有准确的学科定义,其实正是中医领域里文化对文化的误解、科学对科学的摧残的反映,正是中医领域传统哲学贫困和近代科学主义泛滥的结果。
4 总结
基于以上的讨论,在实现中医学复兴的道路上,我们要牢固确立起大科学观,振奋文化精神,医治传统哲学贫困,清除近代科学主义干扰,以中医学的科学定位为依据,把告别中医学西医化作为实现中医学复兴的突破口。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其《国史新论》中指出:“中国民族屡仆屡起,只是这一个传统直到于今,还将赖这一个传统复兴于后。这是人类全体生命、命脉之所在。”他还强调说:“切不可为要学习别人而遗忘了自己,更不可为要学习别人而破灭了自己。”在近代科学主义泛滥的近百年里,钱穆先生颇有远见的宏论,并没有引起国内学术界及中医界的关注。
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沉痛的百年自虐、自残,终于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教师节到学校视察时,明确指出了语文教材中的“去中国化”问题。2015年在《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严肃批评了对待优秀传统文化的“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问题,以及“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问题。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建学立论,建言建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他十分重视中医药学的发展,多次讲到“中医学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2018年的“两会”上进一步提出:“我们既要从精神领域层面去解决对中医药概念的认识问题,还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中医药传承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本文讨论中医学的科学定位,也正是“对中医药概念的认识”上首当其冲的学术问题。
在全面复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面对广受质疑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医学西医化,亟待一场学术思想大讨论。在广开思路、广开言路、广开才路的前提下,动员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文、哲学、科学与中医药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到中医学西医化的总结、反思、讨论、争鸣中来。相信这一场总结、反思、讨论、争鸣,将成为我国告别中医学西医化的真正突破口,成为中医学进入复兴、创新、发展快车道的新起点。
中医学是世界上唯一成熟的可以与现代西医学相媲美的传统医学;中医学的全面复兴将会带来以中西医并重为特征的人类医学的真正革命。中医百年困惑的历史表明,两千年来为中华民族健康事业做出卓著贡献的中医学,一定能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告别西化歧途,迅速迈向复兴,造福世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