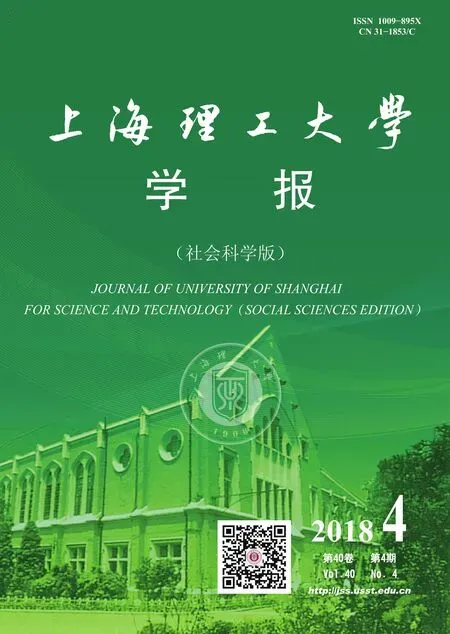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15年(2002—2016)
——基于CNKI 559篇期刊论文的文献统计分析
刘满芸
(长治学院 外语系,长治 046011)
20世纪60、70年代西方轰轰烈烈的女权主义运动激发了70、8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性别平权意识和话语主体意识崛起,加之空间环境下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权力话语等后现代解构理论思潮的盛行,女性译者的“性别”“身份”“主体”及“话语”意识随之觉醒,产生了Sherry Simon,Luise von Flotow,Barbara Godard,Susanne de Lotbiniere-Harwood,Lori Chamberlain,Suzanne Jill Levine以及Gayatry Chakavorty Spivak等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领军人物及其核心力作,影响深远,造就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勃兴。21世纪以来,国内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提出的解构男权话语、颠覆传统忠实、策略性干预源文、打造女性言说方式、在语言中建构女性主体等理论内涵的描述、阐发、实证及其本土化反思如雨后春笋,对性别之于文化的复杂性以及翻译的女性化传统隐喻展开了深刻剖析与消解,对两性翻译角色的“差异平等”、性别场域中的“双性同体”以及社会场域中双性人格的诉求等展开了视角多元、层次立体、持续深入的研究。本文借助CNKI数据库进行高级检索,文献来源设定为“期刊(类别不限)”,文献主题设定为“女性主义+翻译”[注]“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译自同一个英文词汇“feminism”,“女权主义”在早期译介中较为多见,现普遍使用“女性主义”作译名。本文没有将以“女权主义”命名的翻译论文(经中国知网期刊论文检索并人工筛查后,显示有15篇)统计在内。,覆盖区间为2002至2016年[注]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并非在2002年突兀出现,在此之前就有范文美(1999)、王晓元(2000)、廖七一(2000)、许宝强、袁伟(2001)、刘亚儒(2001)等涉猎其中,多以早期的“女权主义”译名呈现,但译界普遍认同把2002年作为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批评范式的正式开端,故本文设此区间。,得出的数据为624篇(检索时间截止于2017年1月16日23时),人工剔除其中的会讯、书讯、征稿通知、期刊总目录以及条件牵强的选项后剩余559篇[注]本文数据统计的几点说明:第一,本文采集到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的单库检索,不能涵盖事实上此类论文的全部,单一库源具有局限性;第二,“精确匹配”下的网络搜索毕竟不同于人工判断,存在一定的含混性,本文对检索出的624篇相关论文做了人工筛选,将涉及到“性别与翻译”“翻译与女性”“女性翻译”等题名的论文统计在内,一些题名(比如“近十年加拿大翻译理论研究评介”)信息不明显、但内容密切相关的论文也统计在内;第三,本文剔除了不涉及翻译问题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类论文;第四,本文未将同期产生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硕博论文并含考察,原因是部分硕博论文作者发表了相关内容的期刊论文,其中的观点、数据与其硕博论文一致,统计在内会有重复之嫌;第五,本文引用的检索数据是网络与人工结合获取的。,采用传统文献计量学中的描述统计分析法,对检索、采集、整理出的相关文献数据进行分类,从现状、主题、视角与方法、存在问题、发展趋势等方面对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做出客观分析与评述。
一、数据统计与分析
(一)数据分布解析
15年间(2002—2016),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论文的刊载总量为559篇,年均发刊37.27篇,其中核心期刊83篇,占总篇数的14.85%。图1数据分布显示: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出现了2003至2008年和2011至2013年两个发展阈值区段。前一区段是国内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引介与阐发期,此间的刊文数量迅速提增,发展张力强劲,究其原因,除了受当时翻译研究的解构思潮影响外,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独特的“性别”内涵、核心期刊隆重推出、名家引介等也是必然因素,比如,2004年《中国翻译》“专栏式”推出的一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论文影响极大,直接推动了此后该研究领域的快速成长与繁荣。2008年以来的年发刊量一直保持在高位区段,年均发刊51.78篇(其中,2013年62篇,为历年最多),核心期刊发刊量与基金支持数量明显高于之前,并且在保持高位发展、稳固持续的同时,于2011至2013年间出现了第二个发展阈值区段,这与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受关注度、影响力以及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密切相关。2013年之后的论文发刊量有所减少,这与社会、经济、文化、尤其是科技发展带来的口译、机器翻译、技术翻译等研究主题的多维延展不无关系,但整体而言,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发展态势良好,持续稳固。
(二)院校与基金分布情况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之所以在国内产生巨大反响并持续生热,还有一些必要的外在条件,例如:作者所在院校的学术研究倾向、基金支持等都保障了该研究领域的发展动力与持续影响,这些都获得了相关数据支撑,见表1。
CNKI授权的局限性可能导致表1数据的不完整性和无法穷尽性,但依然能反映出相关院校单位和基金评审单位的地缘性与学术倾向性。表中数据分布显示:1)论文刊发的数量与各类院校的研究氛围、条件与重视程度以及各级各类基金的扶持力度成正比;2)外语类、师范类和综合类院校较为突出,成果优势明显,但发展阈值点有所不同,比如四川外国语学院的发展阈值点最早,在2002至2004区段,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则在2006至2008区段,整体而言,这些院校的持续性发展态势良好,但系统性、扩展性与实证性研究尚有提升空间;3)湖南省、国家社科等各类基金的扶持加大了本研究领域的人力、物力等资源的投入,保障了研究的质量和数量,显著提升了核心期刊发文的比例,扩大了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发展张力。

图1 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期刊论文年度数量分布(2002—2016)Fig.1 Annual quantitative distribution of papers in feminist translation studies published in China(2002-2016)

作者地缘分布论文篇数基金支持单位次数四川外国语学院16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13上海外国语大学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8中南大学9湖南省教委科研基金5湖南科技大学9四川省教委重点科研基金3广东外语外贸大学8国家留学基金3西北师范大学8北京市优秀人才基金1淮北煤炭师范学院8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基金1湖南第一师范学院8安徽省教育厅科研基金1佳木斯大学8教育部留学人员回国科研基金1湘潭大学7陕西省教委基金1
(三)被引文献分析
某一文献的被引频次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其学术张力和学术价值,也能体现其在某一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译界普遍认为,国内首篇将女性主义批评范式应用于翻译研究的论文诞生于2002年,发表于四川外语学院学报,题名为《重写神话: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1],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结合使“传统的翻译认识论、翻译实践论和翻译方法论之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动摇”[2],因而被认为是“翻译观念和翻译思想上的一场革命”[1],《中国翻译》2004年第4期推出的4篇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论文加速了国内此方面的研究,影响力巨大。直至今日,以上6篇论文的下载与被引频次依然名列前茅,见表2。

表2 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期刊文献后续被引情况(前十)Tab.2 Following-up citation of domestic feminist translation studies(Top 10)
表2数据显示,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主要被引文献多集中于该理论的引介与阐发初期,此间发刊的论文篇数不多,但被引率极高,影响极大。在被引前十的文献中,有9篇属于理论分析文章,被引合计2 077频次,篇均被引230.78次,几乎构成了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石,奠定了作者自身在该研究领域的理论话语地位。比如,被引频次最多的一篇是蒋骁华的《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3],364次被引中有158条期刊论文引证,说明该文献在同类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理论基础性、影响力和导向性。
(四)关键词统计分析
考察关键词的使用频次可以了解某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倾向、研究主题、侧重问题、研究视角与方法等特征。本文利用CNKI提供的EndNote和Refworks软件导出选定的559篇期刊论文的题名、摘要、关键词、作者、机构单位、发表时间等文献记录,结合人工统计确定了15年来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关键词使用情况,见表3。

表3 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关键词使用频次(2002—2016)Tab.3 Frequency of the key words used in domestic
表3数据表明,“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翻译”“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性别”“译者主体性”“翻译策略”“翻译实践”等构成了该研究领域的焦点议题与核心视点,说明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向心性较好。2002至2008年间,女性主义与翻译的结合打开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视阈,这一时期多侧重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背景、内涵和性质的介绍与阐发,性别与语言、忠实与创造等关系被置于研究的突出位置,女性主体性意识开始觉醒,更加注重对新理论的认知与吸收。2009年以来的关键词引用情况出现了突变,即某个(些)关键词的使用频次出现了激增,或者突然出现了一些不曾有过的关键词,数据显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译者主体性”“张爱玲”“局限性”的使用频次均出现了激增,表明这一时段的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实践有较大改观,主体性与理论性研究明显增多,女性译者、女性译作、女性主义翻译批评等实证性与反思性研究进入了新阶段。比如,2008年发表的56篇论文中只有10篇属于女性主义人物、文本个案的实证分析,而2016年CNKI已上传的33篇论文中就有22篇同类型论文。总之,关键词的引频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质性”内涵的丰满与多维实践的扩展,表明本研究真正走向成熟。
二、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分类考察
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主题多样、视角丰富、成果显著,为便于分析与描述,下面按照研究主题将笔者整理出的559篇期刊论文大致分为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译史研究三种类型,见表4。

表4 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主题分布Tab.4 Theme distribution of domesticfeminist translation studies
(一)理论研究
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视角丰富,成果喜人,论文数量占到了总发刊量的近七成,涉及到理论起源(背景)、本质、内涵、意义、启示、引介、解构、建构、述评、影响、接受、伦理、批评、反思、贡献、局限等方方面面,对该理论的研究目标、对象、内容、视角与方法等进行了丰富的阐释,对性别与翻译的结合而引发的认识论、实践论、方法论上的突破不啻为一场革命。女性主义认为,语言是父权制下性别差异建构过程中的操纵工具[2],因此,消解“父权语言”(patriarchal language),批判男性中心,颠覆男权话语,消除男女两性之间的生物性和文化性偏见,正视性别差异,构建两性差异中与男性平等的女性话语主体就成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目标。从研究对象看,多集中在女性译者、女性译作和女性译史等方面。研究的内容多集中在性别平等、女性译者主体性、翻译策略和翻译实践上,一方面,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遵循、借鉴了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的“元话语”,从翻译与性别的隐喻关系背后强大的“父权话语”(patriarchal discourse)特权展开针对译作与原作、译者与作者、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平等诉求,翻译被视为“重写”和“为女性代言”[4],施展的是“干预性”(interventionist)策略,通过“创造性叛逆”体现女性主体性的话语身份。李秀梅、孙佳将其归纳为对传统翻译观的三重解构——重新界定翻译标准、提高译作和译者的地位和进行女性主义翻译的重写[5];另一方面,国内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本地化反思与建构层面有大胆尝试,在肯定其对传统翻译观解构的积极的一面的同时,主张摒弃过于“操纵”和“干预”的“妇占”(womenhandling)意识,倾向于“男性象征秩序与女性书写之间的对话理论”[6],建构一种“可以包容男女性别差异的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双性同体’(或‘雌雄同体’)——来最终消除性别歧视”[7]。双性同体的神话思维体现了男女两性的互补、生理与心理的协调、性别的平等以及人的完整状态[8]。对语言书写、文本意义和译者地位的颠覆性解构显示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强大冲击力,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无限启示。从研究视角与方法看,女性主义视角和性别视角(包括双性视角)为主导,少数论文运用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权力话语、多元系统理论、传统译论、接受美学、功能翻译理论、生态女性主义、元认知心理、历史学、文化学、比较诗学等理论视角进行研究,早期的论文中多使用描述法、文献引用法、文献综合法等方法展开研究,近些年常见实证法、个案分析法、定量与定性法、访谈法、实验法等方法。
(二)实证研究
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实证成果丰富而翔实,展现了缤纷的女性形象谱系,揭示了复杂而深刻的女性构成性。实证方法主要有女性译作的个案分析与对比、女性与男性译者及译作对比、女性作品重译、女性译家访谈、翻译写作实验等方式。西方女性主体性意识指导下的女性主义翻译实践观认为,翻译就是重写,就是写作实验,通过文本干预、语言创造,实现翻译中女性的主体性存在。潘学权、叶小宝归纳了西方女性主义翻译实践的三个阶段:女性借助翻译参与社会文化活动、通过干预性翻译努力消除语言中的性别歧视以及采用身体翻译突出女性体验[9]。Flotow将翻译实践的方式归纳为:加写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增补(supplementing)和劫持(hijacking)等[10-11],劫持主要体现在创造新词和新短语、赋予旧词以新意、施加印刷手段(改变大小写、粗体等)、干预语法性别(将过于阳性的表述改为中性、甚至阴性,比如,重译《圣经》时)、突出女性署名(比如,将translator改为translatress,将author改为auther等)。女性主义翻译实践实质上是一种“写作实践”,是“写作的最高形式”[12],“是让语言为女性说话……让女性在语言中显现”[13]15。
国内女性主义的翻译实践方式除了承袭Flotow提出的三种类型外,更加注重从性别、语言、视角、情感等层面去挖掘女性主义翻译特征,对性别、主体性意识的体现多基于文本实证,相较于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的干预性、操纵性和叛逆性,态度更加隐蔽、温和。一些论文主张摒弃性别翻译意识中的对立与裂痕,而以“双性同体”加以融通,用理性与中和代替极端与偏激,“努力描述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两性角色的独特视界”[14]。从文本个案实证看,国外以英美女性文学作品居多,如:勃朗特姐妹、简·奥斯丁、弗吉尼亚·沃尔夫、赛珍珠、玛格丽特·米切儿、多丽丝·莱辛等名家作品的翻译,也有典籍文本(如《圣经》、《道德经》等)、社会学文本(如《第二性》)和法律文本(如《吕刑》)的个案分析与比较,少数论文还涉及到了儿童文学翻译、口译与翻译教学实践等题材。国内以现当代名家及其译作研究居多,其中张爱玲23篇,朱虹19篇,另有戴乃迭、孔慧仪、冰心、杨必、杨苡、杨绛、林徽因、丁玲、张玲、沈性仁以及茅于美等,也涉及到一些近代以前的女性译者(陈鸿璧、薛绍徽等)、女性译者群体(闽籍群体、民国时期群体等)及其译作研究。
(三)译史研究
国内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翻译史,虽不是盲点,但建树不多,从笔者目前收集到的数据来看,仅有李永红的《寻找“失落”的群体——对我国女性翻译史研究的思考》、吴书芳的《我国女性翻译史研究的缺失与补苴》和包相玲的《对我国女性翻译史研究的梳理与反思》三篇论文,三位作者都意识到我国女性翻译史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都借鉴了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史学观点和史料文献研究方法,李永红强调“从历史与传统中”找寻性别与翻译研究存在和发展的理据,加强对国内不同时期女性作品的发掘、整理与翻译,重视研究女性译者并重新评价她们的价值和历史地位等[15]。吴书芳认为借鉴西方理论应与国情相结合,除了探寻科学的理论支撑与合理的研究方法外,还要重视史料收集和拓展,选用适当的撰写体例[16]。包相玲也认为研究女性翻译史要寻找科学的理论支撑,重视史料收集,使用合理的研究方法[17]。
三、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评述与前瞻
(一)成果与经验
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历经15年,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与实证经验。理论层面主要有:1)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引介、阐发与传播开辟了国内翻译研究的女性主义批评范式;2)在译者主体性研究中开辟了全新的性别视角,女性译者主体性的特点和作用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3)揭开了传统译论中隐匿的性别禁区,对翻译中译作与原作、译者与作者、女性与男性等各种关系的差异性解释揭示了原作、作者、男性的权力身份和地位,为传统译论中“忠实”“对等”“主体性”等涉及到性别、语言本质、翻译伦理等一些问题的认知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4)女性主义翻译关于语言书写、文本意义和译者地位的创造性叛逆丰富了翻译理论的研究视角和实践方法,为扩展译学疆维、丰富翻译内涵带来了深刻启发。实践层面主要有:1)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提倡的干预性策略、翻译写作、翻译实践方式等进行了多层面、多视角的分析、反思与实验,取得了丰富的经验;2)相比西方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中的“干预”“重写”“妇占”等激进的规定性实践方式,国内女性主义翻译实践更倾向于在文本中寻找活生生的女性事实——性别、语言、视角、情感等——来挖掘、发现、呈现翻译中的两性关系,并试图找到新的语言和新的文学形式来对女性现实作出反应,进而树立女性的主体性、差异性及平等意识。突出了描述性实践方式,这是国内在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本地化过程中取得的显著成就;3)为今后的翻译理论、女性主义以及翻译实践方式等的持续性与创新性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存在问题
1.译名纷乱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引介过程中出现了相关理论家及理论概念术语的混乱翻译,译名不统一,甚至同一篇论文中出现了同一个人物的两种译名。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译名不统一的有:Sherry Simon(谢莉/谢利/雪莉/雪梨/希瑞·西蒙/赛蒙/塞蒙等),Luise von Flotow(露易丝/路易斯·冯/梵·弗洛图/福露窦/芙洛图/弗罗托/弗拉德/费拉德等),Barbara Godard(芭芭拉/巴巴拉·戈尔达德/戈达德/格达德/高达特等),Susanne de Lotbiniere-Harwood(苏珊妮/苏珊娜·德·罗特宾尼尔/劳特宾尼尔/洛特比涅尔·哈伍德/哈沃德/哈乌尔德/哈沃特)以及Lori Chamberlain(洛丽/洛利/罗利/罗莉·张伯伦/钱柏琳),等等。概念术语翻译的问题主要有:womanhandling(妇占/粗暴地妇占/妇女操纵/女性驾驭/女性化处理),supplementing(补偿/增补),androgyny(雌雄同体/双性同体),等等。关于译名规范与统一的问题在中外译介史上都频繁出现过,甚至闹出了很大的笑话,应引起注意。就人物名称翻译而言,“零翻译”可以避免译名纷乱的尴尬,也是论文中常见的一种选择;另外,尊重译名的最初使用形式也能避免不必要的混乱;再者,译者应加强译名知识和经验积累,尊重规范性、普遍性和约定俗成性。
2.过犹不及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有其矫枉过正的一面,过于强调译者的“干预”和语言的“操纵”,产生了关于文本失真、翻译本质及翻译伦理等一系列争议,引起了国内译界不少批评,说明理论本身的缺陷值得反思与纠正。另一方面,尽管内心存在本能性的平等与主体意识,但中国女性并没有西方那样深厚的女性主义思想积淀与社会发展条件,没有形成西方那样的女性主义文化气候,对性别平等与女性主体性的反应与主张不像西方女性那样激烈与果敢,大多停留在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阐释和评介层面,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传统使国内女性在语言与翻译平权的道路上总是不愿声张,甚至意志消沉,在理论建树上存在文献重复、方法陈旧、创新乏力等问题,从这一层面讲,国内并没有达到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思想高度。
3.牵强附会
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在文本实证与翻译实践方面积攒了丰富的经验,对文本解读的视角丰富、涉及面广,形成了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特有的话语谱系和特点,但也产生了一些“牵强”现象,比如对非女性主义文本“性别化”和对女性主义文本“性别过度化”施加翻译上的“劫持”和“挪用”,就僭越了文本忠实性的一般伦理,偏离了翻译研究的客观性、严谨性和科学性。在谈到Flotow翻译实践方法时并不统一,有些描述为“加写前言和脚注、增补和劫持”,有些则描述成“加写前言和脚注、增补和挪用”,显示了研究中欠严谨的一面。
(三)发展前景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解构意识交织的产物,它将语言、性别、主体性等置于女性主义审视之下,以差异平等来破除传统译论的二元对立,其核心问题是“性别”问题,性别介入翻译终于打开了对女性而言有些隐隐作痛的历史与现实界面,女性不只存在于“次等”的传统文化隐喻之中,更无时无刻不痛彻于历史长河中繁华的“文本表演”之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要持续发展,性别平等依然会是其基础,这是其理论的灵魂,也依然会将文本中的语言作为其“主体性”存在的土壤,但是否仍以女性主义先辈们激进的“干预”“劫持”“操纵”为手段则值得深思,毕竟这些都是在解构思想生态下演变出的女性主义阐释话语,这意味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本身也是一个破立更新的发展过程。从发展趋势看,今后的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会走向理性与科学性、客观性与多元性,理论体系会更加深入和完善,实证视角与方法会更加广维,女性译史的文献实证研究会持续挖掘并更加系统;相比对性别歧视的“揭示”,会更加注重对性别平等的多样化“建构”,对文本中两性关系的呈现会以“共生”为主导;相比“双性同体”的两性关系构建,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和而不同”的性别平等诉求;也希望未来能出现属于我国自己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著述,能产生像Simon,Flotow和Godard那样掷地有声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代表人物,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世界多元性发展做出贡献。
四、结束语
本文基于CNKI检索出的559篇期刊论文的年度数量趋势、作者地缘分布、基金支持、文献被引、关键词使用、研究主题等相关数据,运用文献计量学中的描述统计方法,对15年来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取得的理论、实践与批评等方面的成就与局限做了文献描述与分析评价,客观呈现了国内此方面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就其未来发展前景给出了前瞻性思考,希望能对今后的相关研究给予启迪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