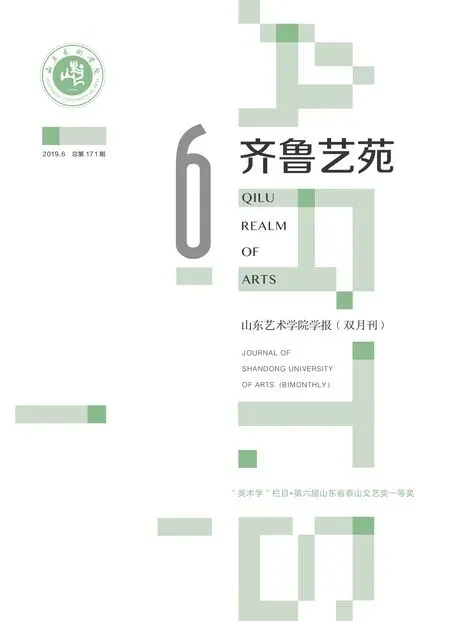清儒陆世仪琴事考述
范晓利
(河南大学艺术理论研究院,河南 开封 475000)
陆世仪是明末清初重要的理学家,学界对其学术之研究往往集中于儒学思想、政治主张和社会活动,若是全面考察陆世仪的学问和人生,他并非仅治儒学,在诗琴书画领域均有卓见,尤其是琴学理论方面。他将古琴艺术作为“六艺”之中“乐”的正统传承,无论顺逆不改芝兰之质,还经常与友人雅集唱和,彰显儒者情怀的同时也为琴坛上“儒派”的形成做出了卓越贡献。正是在多位如陆世仪一样的儒者不经意间的推动下,琴坛之“儒派”虽无意立派,专精古琴演奏的艺术家们亦偶有微词,但是终被琴人认可。
遗憾的是,此事为当代学界同仁忽略良久。考证陆世仪的琴事活动,考察古琴艺术与其人生之渊源,不仅是琴学界的课题,也是对陆世仪儒学思想的有益补充,颇具学术价值。
一、琴书相伴,践行琴学主张
陆世仪认为“六艺”对学子而言,本都应当学习,但是“礼、乐、射、御、书、数”各科在历史发展中或不断变化、或渐渐流失,多数已非本来面目,而且不再具有当初的功用,故而当世学子应当在不耽误“正业”即读书问学的前提下时时留心,争取不错过习“六艺”的机会。学习的方法也不应该脱离实际情况,如忽视当时已发展成熟的骑马射箭之术,执着于“五射”的上古遗法。“乐”早已失传,对此“艺”的学习则应该留心当世能体现“乐”之精神的古琴,并经常操缦弹唱,“乐未便论到精微,只弹琴一事。虽非古调,然亦当稍习,时时操之,使心气和平。”[1](P12)
考陆世仪琴事,留存至今的《桴亭先生诗集》《桴亭先生文集》《陆陈二先生诗钞》《顽潭诗话》是重要文献,诗文集正文中涉及古琴者39篇,可清晰看出16岁至60岁(去世前一年)的陆世仪心态的微妙变化,以及在逆境中对儒家之道的坚守。
陆世仪出身于“五世诸生”之家,祖辈都是普通的读书人,12岁开始跟随父亲陆振吾读书问学,16岁(1626)作《竹庵吟》三首,有“门内琴书陈,门外车马列”之句。此时的他修的是举子业,已经结识盛敬,尚未邂逅陈瑚、寻访江士韶,“太仓四君子”都还是心怀家国、立志济世、意气风发的翩翩少年,因此也有借用司马相如琴挑文君抒发青年男女相思情愫的《秋夜词》。时陆世仪22岁左右,根据其子陆允正所作《行实》:“壬申(1632)季冬(12月),学使者甘公岁使入郡学。”[2](P3)《遵道先生年谱》载“五年(崇祯五年)壬申二十二岁入郡庠”。即,陆世仪当时是郡学的生员。
这一时期他所学知识中是否包括琴学并无翔实文献可证,不过,即便家学中缺乏古琴教育,《竹庵吟》中“琴书”单纯用其象征意义,而入郡学之后,陆世仪接受琴艺教学的可能性就更大了。明代官学和民间书院中都有“乐”科,很多教师通过弦歌的方式把儒家观念融入琴学传教中,如吴归云、虞谦、汪一恒等人曾为《诗经》《论语》诸篇,乃至《大学》《中庸》《孟子》全文谱古琴,陆世仪等人可能少年时代就接触并学习过古琴,至少经历了琴乐熏陶,不然写不出《秋夜词》(1)《秋夜词》:良月满高台,鸣琴发情愫。月华堕清寒,散作琴上露。何当成泪珠,弹向天涯暮。凤凰自相求,莫在临邛住。,也做不到“醉后周郎曲,闲中李贺诗”(2)《读郎元翊诗文杂稿赋赠》:雅道久沦丧,风流复见兹。闭门甘箸作,悬榻待交知。醉后周郎曲,闲中李贺诗。远公今结社,吾意欲相期。。只是诸生把琴艺作为修习儒学的辅助科目,不会专攻弹琴技艺。也正因为如此,陆世仪始终将“琴”与“书”并列,创作《竹庵吟》三十年后亦云“半载琴书清梦隐”,“巾服何逍遥,琴书亦从容”;50岁犹言“江上芳风长绿波,琴囊诗卷一帆过”(3)《送翼微读书澄江,寄示江上诸子》,题目下有“以下庚子”,即1660年,时陆世仪50岁。。他的好朋友陈瑚在家中遭水患无法容身的情况下,“乃携琴书,偕儿徒辈放棹中,流随意所。适潭影空映,荷气袭人,渔歌鸟语之中,琴声书响,络绎间起,彻于田畔。”[3](P33)
陆世仪对习琴的态度见于《思辨录》:“不必十分究心,有亏正业。但当时时留心,遇可学处便学,不至当面放过可也。”[4](P13)他习琴的直接证据是其诗作《月下听姚虞生鼓琴,时予正学琴虞生也》,诗曰:“君不见宣尼昔日师师襄,声音之中见文王。黝然而黑欣而长,精神相遇无何乡”[5](P9)。《韩诗外传》《孔子家语》《淮南子》《史记》都记载了孔子向师襄子学习《文王操》的典故,陆世仪习琴的目的与孔子一脉相承,他学的不仅是技法,更多是琴曲中蕴含的德行和节操。此诗之前《舟中漫赋寄答诸兄》之后,有“以下乙巳”四字,即1665年,时陆世仪55岁,依然不错过学习古琴艺术的机会,还与友人深入讨论乐理(“冬至日,一庵升书,见过出增,释律吕新书示读,兼论乐理,移日始别”[6](P14)),切实践行了自己的琴学主张。
正当陆世仪学问初成时,天下多故烽烟四起,明代朝廷大厦将倾。他虽能习武布阵,但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1643年33岁所作律诗《和圣传湛一亭》中,湛一亭的主人独坐幽亭赏花鸣琴,观物修身,“纵观万物皆生意,静对渊泉识道心”;“水到渠成看道力,崖枯木落见天心”[7](P20),看似悠闲自在,不知人世升沉,但“此中旋转须教猛,不信神州竟陆沈”,显然不能忘世。这一年是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张献忠义武元年,距离明亡一年(1643年)。
明亡之后,陆世仪自述“以不生不死之人,处倏安倏危之地,欲歌不能,欲哭不可(1645年,《感遇诗序》)”[8](P3),可见江山易主对其心理的重创,这种心态的转换在其琴论和涉琴诗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采芝歌》的创作和商山四皓的隐喻意义;其二,《猗兰操》和“幽兰”意象的反复出现。
二、琴操《采芝》,隐喻商山四皓
琴为乐统、琴书相伴是陆世仪一以贯之的琴学主张,并未因朝代更迭而变化,但是他对朱氏王朝的感情非常深厚,入清之后,陆世仪多次辞聘不受,绝不仕清,“筑亭水中居之,罕接宾客,自号曰桴亭”[9](P265),平素仅与陈瑚、盛敬、江士韶等人交游往来。曲《采芝歌》的创作以及歌辞中商山四皓意象的隐喻或许都是这种遗民情结的展现。
根据《桴亭先生诗集》卷四,《采芝歌》创作于庚寅至癸巳,也就是1650至1653年,当时南明小朝廷永历帝朱由榔在位。陆允正《行实》载:“庚寅春,亭畔产灵芝大如盘,高径尺。府君曰:‘孔子见幽谷聚兰,喟然作操。芝非兰俦,当与商山四君子结世外之知而已。’因作《采芝操》,见者咸谓府君仁孝积学所致。”[10](P24)据此可确定《采芝歌》创作于1650年,时陆世仪40岁。
将《采芝歌》的序言与《府君行实》互相参照,可知歌辞的创作过程:1650年的春天,陆家桴亭旁边的草丛中突然长出了一棵品相异常的植物,次子允正发现后将之移栽到盆中,长子允纯识别出这是一株灵芝草,告诉了陆世仪。陆世仪回去一看,果然是灵芝,于是思绪万千。首先想到“土气和”才会长出灵芝来,可自己一介腐儒,自我放逐隐居桴亭,怎么称得上“和”呢?又想到孔子看到在幽谷中生长的丛兰,感叹兰本来应为王者香,但是生不逢时芜没于草丛,于是创作《猗兰操》。芝之为物,虽非兰俦,不过也可以与商山四皓诸位君子比德,结世外之知。于是创作《采芝歌》,聊以表达自己的志向。歌辞如下:
“维彼神芝兮烨烨其光,载兹载荣兮于池之阳。谓兰何为兮不匿其芳,庶草虽繁兮并生奚伤。缅怀商山兮维古之狂。采之疗饥兮以徜以徉,驷马高盖兮非予所望,贫贱肆志兮夫何敢当。”[11](P2)
歌辞中隐藏着两个典故:其一,兰为王者香,众草杂芜亦不掩其香,就如同孔子的德行;其二,灵芝虽不如兰,但是采之也可以充饥,帮助汉惠帝刘盈保住太子之位的商山四皓也值得缅怀。
《采芝歌》中还隐藏着另外一个文本《紫芝歌》,其作者正是商山诸君子,其辞如下:
“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12]
陆世仪三十多岁时曾为贺鹿门翁五十大寿而作琴曲歌辞《鹿门吟》,有应景唱和之意,比较起来,《采芝歌》更能体现他的理想。芝兰都是君子高尚品格的象征,陆世仪也许并不认为自己有朝一日可以达到孔子的境界,他的榜样更加现实,即德行高尚、安于贫困,朝廷需要时还能发挥作用的商山四皓。即使生不成一枝兰花,还可以长成一株灵芝,助人疗饥、补时救世。
怀有这种心态的不仅仅陆世仪一人,江南以“太仓四君子”为首的多位文人都以诗文表达了对商山诸君子的敬仰。《顽潭诗话》之《和青田先生夏日杂兴诗》向辰所和的第二首诗云“芝茁商山堪避世,苔封石室好藏书”;确庵记录的《玩月称觞》组诗也有“商山堪缅想,应续紫芝编”之言。由龚捖记录的《再和陶诗》有“长谣《采芝曲》,共作商山民”之句,《采芝曲》是否就是陆世仪庚寅春所作《采芝歌》呢?
《再和陶诗序》只说作于“八月潮生日”,未标明哪一年。既然组诗名为“再和陶诗”,之前应有“和陶诗”,第一次唱和余兴未消,才有第二次雅集,故两次唱和的时间相隔不会太久。《和陶田舍诗》中“和”的是陶渊明的《癸卯始春怀古田舍诗》,组诗前有陈瑚《总序》,说明此组诗篇由中庵首和,然后与参又和之。每人的诗篇前都有《自序》,其中《与参自序》有“丁亥秋,予以一编谒中庵先生过为延赏,和其中《和陶诗》二章”[13](P36)之语。由此推算,《和陶田舍诗》和《再和陶诗》的创作时间大致应该在1647年的秋天。因此,《采芝曲》很可能还是《紫芝歌》,而非陆世仪所作《采芝歌》。
“太仓四君子”等人对商山诸君子的缅怀,首先是出于对古代隐士的崇敬之情,其次或也隐喻了他们对于南明小朝廷的一丝希望,他们希望能像商山四皓辅佐刘盈一样,扶起新君匡扶社稷。尤其是陆世仪,在清军入关之后南下之时,他依然认为明朝还有希望,于是不顾生死利害,委身致命全力以赴,“上书南都,参与军事,志在抗清复明。”[14](P31)
三、《猗兰》相赠,“幽兰”意象频现
陆世仪中后期的涉琴诗中,《猗兰操》和“幽兰”意象反复出现。如“长歌梁父时摇膝,漫赋猗兰独援琴”,再如:
“兰为王者香,无人生空阿。孔子遇见之,援琴喟然歌。荣落随众草,不得比佳禾。九州岛无定所,逍遥将奈何。”(《感遇诗》)[15](P5)
“草有兰兮木有梅,芳心劲质两无猜。知君近作篱浮想,赠汝猗兰操一回。”(《赠惠甫兰梅》)[16](P15)
《孔子家语·在厄》中孔子曾说:“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谓穷困而改节”[17](P166),芝兰生于杂草丛中,虽生不逢地,却依然散发幽香;君子处在乱世之中,虽生不逢时,却依然坚守节操。因而,芝兰可比德于君子。蔡邕《琴操》载,孔子怀抱治世理想历聘诸侯,但是总也得不到重用,不得已从卫国返回鲁国,途中路过幽隐的山谷,看到兰花与杂草为伍,不由得感叹“世人暗蔽,不知贤者”(4)《琴操》中琴曲《猗兰操》歌辞:“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之子于归,远送于野。何彼苍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无所定处。世人暗蔽,不知贤者。年纪逝迈,一身将老”。,于是创作琴曲《猗兰操(幽兰)》,似有怨愤之情。唐朝韩愈曾依曲作辞,更进一步加强了兰花意象原初的象征意义:“不采而佩,于兰何伤?”
陆世仪心中有江山易主的创伤和生不逢时的忧愤,《采芝歌》的创作和商山四皓的隐喻无疑是一表。不过,他心中装的是儒家之道而非明朝一家之天下,一姓江山之颠覆与儒家文化的代代传承比起来,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陆世仪的好友陈瑚集《顽潭诗话》收录了以“太仓四君子”为首的江南文人的多次雅集唱和,《同人寿鸿逸》组诗的记录者是陆世仪,《鸿逸六十赠言》有“琴尊任意携,花药随时莳”之句。根据其下卷第十组诗《村访》的《序》所记,戊子梅月末日(1648年农历三月的最后一天),桴亭(陆世仪)、寒溪(盛敬)、王生(王育)应确庵(陈瑚)之邀,于薄暮时分抵达蔚村七十二潭之上,
“相见不作寒暄语,各出新着相证剧谈者一日夜,莫逆于心,极性命之幽微,抽经世之鸿绪。鸣琴在右,图史在左。家人具汤饼,佐以芳醴。时醉时醒,或寐或歌。自谓人世之乐,无过我四人今日也。”[18](P40)
与琴人雅集着重展示琴艺、交流艺术感受不同,儒家文人雅集的主题侧重于探讨性命之理交流学术,他们各自的“新着”如下:陈瑚拿出《治纲》《论乐书》《典礼会通》三书,盛敬有《地理》《险要》《乙酉日记新辑》三册,陆世仪出示《思辨录》和《八阵发明》,而王育“不过新诗百首、小文数篇而已”,在儒者眼中,诗文也只是小道。探讨学问的过程中佐以琴乐,赋诗抒情。
第二天一早(《序》尾有“戊子清和月之第一日也”之句,即1648年农历四月的第一天),乘着小船出了西堰进入宋泾,去寻访另一位朋友接侯,读其新着数篇,啜茗而别。然后调转船头去找鼎甫,带他一起返回蔚村继续诗书琴瑟、饮酒畅谈。
戊子年的七月,陈瑚又召集众人聚会,所讨论的作品更多,有《顽潭诗教》《莲社约》《焚草》《过野古集》《典礼会通》《相观录》《蔚洲诗话》《寒潭芳讯》《野古第二册》《印溪草堂集》《晚翠庵近稿》等等,“饭毕即命治舟,携琴尊诗卷子弟,相随入潭中,于时兼葭含风芙蓉浥露。”[19](P39)这次聚会所作诗篇统一命名为《潭上泛月》。
以陆世仪为首的“太仓四君子”,乃至以“太仓四君子”为中心的江南儒生团体经常参与琴事活动。他们在生不逢时的境遇中散发着幽香,也是“猗兰”精神的象征。陆世仪在《论学酬答》之《与张受先生论书出处》一文云:
“士君子处末世,时可为、道可行,则委身致命以赴之,虽死生利害有所不顾。盖天下之所系者大,而吾一身之所系者小。若时不可为、道不可行,则洁身去国、隐居谈道,以淑后学,以惠来兹,虽高爵厚禄有所不顾。盖天下之所系者大,而万世之所系者尤大也。”[20](P10)
因此,陆世仪面对明清之朝代更迭并没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壮烈,虽然认同自己的遗民身份辞不出仕,却在学问上不断精进,著书论述讲学传道,多了一份坚守儒学的隐忍与坚韧。他也没有不食周粟避入深山的决绝,一如既往地关注民生精研水利惠及乡里,因为“士生斯世,不能致君,亦当泽民。盖水火之中,望救正切”。[21](P6)其诗文著作中《猗兰操》和“幽兰”意象的反复出现,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充分说明他心中尽管有幽怨暗恨,面对黎民苍生的苦难境遇,还是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同猗兰,无论顺逆,幽香四溢。
徐世昌编纂的《清儒学案》载:“先生自明亡,无心用世,托诸论述,皆有功于世道人心。尤关怀乡邦利弊、救荒治水,长吏咨而后行。知州白登明,循吏也,浚刘河,为百年之利;巡抚马牛祜浚吴淞、娄江,皆用其规画。”[22](P96)可左证“幽兰”意象和《猗兰操》在诗文中反复出现之深意,即便生不逢时,猗兰也不断幽香;亦可见其知行合一,不脱离社会民生的儒学才是真儒孜孜以求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