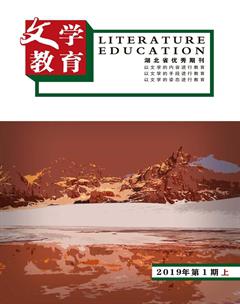论《无名女人》中的“身份”意识和“记忆”与“梦”
内容摘要:学界关于《无名女人》及汤婷婷的解读与研究,主要围绕着女性主义、性别与种族歧视等方面,而对于其中体现的“身份意识”与“记忆”、“梦境”等问题却相对缺乏重视。本文将从弗洛伊德的“身份”与“梦”的理论出发,从而挖掘《无名女人》中潜藏着的“身份”意识、“记忆”与“梦”的独到存在。
关键词:《无名女人》 弗洛伊德 “身份意识” “记忆” “梦”
《无名女人》是华裔女作家汤婷婷《女勇士》的第一章节,也是窥探汤婷婷内心深处关于“身份意識”、“记忆”与“梦境”的重要考察文本。深入考察文本可知,汤婷婷除了展现了“中国人”和“女性”的双重“身份意识”,在书写过程中同时展现了她深层次的童年记忆及独到的“梦”。
一.《无名女人》中的“身份”意识
Peter Straffon & Nicky Hayes的A Studentcs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认为,“身份就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1](P87)弗洛伊德曾用“Identification”的概念来解释人对他人的归属。“身份”一旦被“认同”于某种属性,则其他属性的差异便被确认。钱超英进一步解释“身份”意识在移民及群体中的重要意义:“‘身份概念尤其便于用来考察和研究那些在明显不同的‘文化历史设定的裂缝之间漂移运动的‘主体——移民、‘问题群体、在全球化中经历急剧社会转型的民族——所必然面临的生活重建经验。一个人从原居国移民到另一个国家,或者从乡村迁往城市,所面对的不仅是居住环境、工作、用品和食物的变化等实际问题,而且更是关于‘我曾经是谁、现在是谁、‘我为什么如此生活的问题,他需要有一种令其满意的完整解释,以便接受和平衡转变所带来的风险,使自我和变化着的环境的有效联系得以重建,以免生活意义的失落和虚空。[2](P91)
《无名女人》中的“身份意识”,笔者认为,至少有3层:一.姑姑的姓名以及其作为家族女儿的身份;二.女性在旧时中国两性关系中的身份;三.作者在美时反观自我国人的身份。
第一层是故事层面上的身份确认,即姑姑的名字。从题目《无名女人》中已经看出,书写“无名”是为了证明“有名”。这个“名”不仅仅是姓名的意思,还有的是一个人曾为人的凭证。“无名”就意味着“姑姑”得不到“认同”,所以无法确认有无。要么是带有他传性的真实存在,要么是“幻想”与构筑。姑姑除了不被家族承认,也不被村里承认,“就跟没出生过一样”[3](P66)也就是说,姑姑的身份,被剥夺被消灭了。为了弥补身份缺失,“我”选择了“幻想”。
其次是女性身份在旧中国两性社会关系中的重提和肯定。“我”在母亲的劝慰下,重提了女性在两性社会关系中重要地位。有研究者认为汤婷婷的书写有过分媚俗嫌疑,主要是她对旧中国的某些现象加以歪曲或者丑化。笔者认为,汤婷婷之所以强化某种现象的书写,其实是对女性身份的再肯定。除了直面描写姑姑以外,作者还从侧面展现否定女性身份的现象,“兄弟姐妹们都刚刚成人,他们必须抹去性别的特征,表现出普通的仪态。”[3](P71)
第三则是在美华人反观自我国人的身份。尽管是美籍,但身体总不免流淌着中国人的血,也就是说,浸润着中国文化血统的作者,需要找回这种陌生的熟悉感。笔者认为,作者的异乡书写,实际上是在“寻根”。身在异乡的“我”,不免感慨“作为华裔美国人,当你想了解自身哪些东西属于中国时,你怎分得清哪些是中国特有的,哪些是童年,贫穷,疯狂以及一个家特有的,哪些是你成长过程中给你讲故事的母亲特有的呢?什么是中国传统的东西,什么又是电影里虚构的东西?”[3](P67)
二.《无名女人》中的“记忆”与“梦”
F.W.希尔德布兰特解释“记忆”和“梦”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梦,它的材料都来源于现实,来源于以这个现实为中心的精神生活。......换言之,它必定来自我们已客观地或主观地体验过的事物中。”[4](P6)弗洛伊德进一步阐释两者关系,“所有构成内容的材料均按某种方式来源于体验,它们在梦中再现或被记起——这些至少可以当作不容争辩的事实。”[4](P6)换言之,现实或者记忆由于种种条件的阻碍,无法满足人类所有期盼,对于这种不争的事实,人类不得不接受。当这种矛盾的情感带入到梦境中,则尽情释放,由此拟补了现实或者记忆中的空缺。所以梦境“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它的内容”[4](P79),以至于具备了以下特点“短小和简单”[4](P79)的、“混乱和繁杂的”[4](P79)。
关于《无名女人》中的“记忆”与“梦”,笔者看来,有以下两种解读方式:1.假如姑姑已死是“记忆”,那么作者对姑姑的生平则是“梦”,作者通过想象姑姑的生平传达对姑姑的思念;2.假如童年禁欲是记忆,那么对姑姑生平的想象则是实现生理欲望的释放。对姑姑生平的想象,即“幻想”,属于“梦”的范畴。作者在有意识地“做梦”,而这种有意识地“做梦”是某种程度的理性压制。
如果禁欲是记忆,那么作者在书写姑姑的生平时实际上是生理欲望的释放。笔者认为可以采用倒推的方式对文本进行探讨。所谓“倒推”,即至把文本进行倒置阅读,然后再进行分析。参看以下两段文字:
或许返祖现象多于恐惧,我曾经暗暗地在男孩子的名字后面加上‘兄弟二字,这样一来,不管这些男孩子请不请我跳舞,我已叫他们都中了魔法——他们显得不那么可怕,反而像女孩子一样亲近,一样值得善待。
当然,我也给自己施了魔法——不约会。我本该站起来,挥舞双臂,隔着图书馆大喊:“喂,你!爱我吧。”但是我不知怎样有选择地吸引异性,吸引谁,吸引到怎样的程度。假如我显示出自己美国式的风采,从而使班上那五六个中国男孩爱上我,那么班上的其他人——高加索人、黑人和日本人也都会爱上我。看来还是庄重、可敬的姐妹版的风采更为适宜。[3](P71-72)
以上文字不得不让笔者产生以下疑问,作者基本上是以激情洋溢的状态对姑姑的生平进行了一番尽情的想象与描绘,可是却又在文本后半段用压抑遮蔽的手法展现现实的对立,这种矛盾性如何理解?笔者认为,正是这种“记忆”中的压迫(笔者注:此处“记忆”包含过去时和现在进行時),才导致梦境的张扬跋扈。换言之,主人公通过对姑姑生平的激情想象来满足自我愿望,这个目的直指生理与欲望上的满足与释放。
弗洛伊德将这种梦概括为“感情的梦”,他认为“男性和女性的性欲渴望”和“烦躁心境”的梦是相似的。[4](P82)笔者认为,作者负有激情的对姑姑生平的想象与描绘,也体现着一定程度上的烦躁与焦虑。有如这段姑姑生产的文字描述:
她跑到外面地里,跑得远远的,直到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她把身子紧紧地贴在地上,这再也不是她自己的土地了。她感到临产前的阵痛,还以为是自己受了伤,身子缩成一团。她想:“他们把我伤害得太狠了。太可恨了,就要害死我了。”她用额头和膝盖抵着地,身体抽搐起来,一会儿又放松了。她翻身平躺在地上。天空有如一口黑井,星星一颗颗地熄灭,熄灭,永远熄灭;她的身体。她的全部好像都消失了。她也是一颗星星,黑暗中的一个亮点,没有家,没有伴,永远在寒冷和寂静之中。一种对旷野的恐惧从她心底油然而生,越升越高。越变越大,她没办法控制了:这无边无际的恐惧
上述文字张力十足,姑姑宛如一匹受伤的狼在原野上嚎叫。但是,与《颓败线的颤动》中的受伤的狼不同,姑姑更多的感到外在世界的恐惧而蜷缩,而《颓败线的颤动》中的女人却更多表现对残酷命运的怒号。所以前者体现的除了焦虑,还有恐惧,后者更多的体现愤怒。以至于姑姑后来跑向猪圈,此处作者用“虚无”一词来强调一种无意义——外部世界的冷漠与自我生命的凋零。
三.结语
本文从弗洛伊德的“身份”、“记忆”与“梦”的理论出发,挖掘《无名女人》中潜藏着的“身份”意识、“记忆”与“梦”的独到存在。这种“身份”意识体现在三个层面:一为姑姑的姓名以及其作为家族的女儿的身份;二为女性在旧时中国两性关系中的身份;三为作者在美时反观自我中国人的身份。此外,“记忆”与“梦”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姑姑已死是“记忆”,那么作者对姑姑的生平则是“梦”,即作者通过虚构想象姑姑的生平以达到满足好奇和表达意志的愿望;二是童年禁欲是记忆,那么对姑姑生平的想象则是生理欲望的满足于释放。综上所述,关于心理学与《无名女人》之间的关系,还有更多的可供挖掘的空间。
参考文献
[1]Peter Straffon & Nicky Hayes.A Studentcs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Z]. Edward Arnold, 1988.
[2]钱超英.身份概念与身份意识[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4).
[3]胡上花.华美文学作品集:短篇小说卷[M].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4](奥)弗洛伊德著;张燕云译.梦的释义[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
(作者介绍:黄恩恩,广东科技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