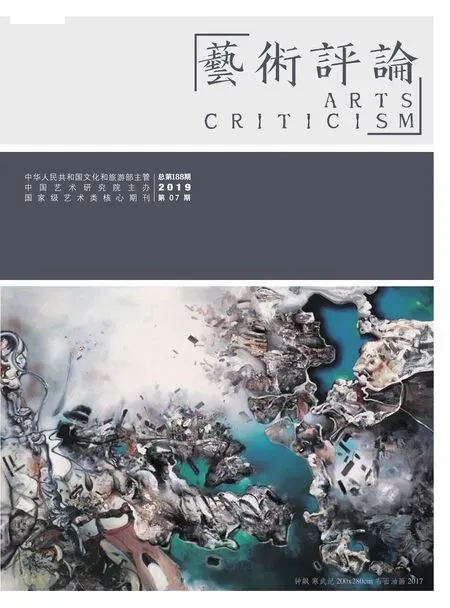公牛、斗牛与米诺陶
——毕加索的“斗牛士”世界
[内容提要]毕加索的一生中曾以公牛、斗牛以及米诺陶为主题创作了大量作品,这既与他的生活经历相关,又反映了他对历史神话与现实生活的解读。通过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艺术手法,毕加索描绘了他对公牛、性与两性之间关系的认知。同时,通过象征和隐喻的艺术符号,毕加索的创作也表达出他对西班牙斗牛士的人格认同。
作为现代艺术的先驱者之一,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的绘画创作中有一个不断出现的图像,即公牛,由这一主题演绎出斗牛的场景以及人身牛头怪米诺陶(Minotaur)的形象,这些图像演变从不同角度诠释着毕加索的艺术世界。
一
公牛在古希腊神话中具有丰富的色彩,如欧罗巴与公牛的典故,讲述了希腊神话中的腓尼基公主欧罗巴,被因爱慕她而化为一头公牛的宙斯带往了另一片大陆,后来成为了这里的女神,以她的名字将这片大陆命名为欧罗巴(Europe)的故事。希腊人经常将公牛献祭给神,在爱奥尼亚和塞萨利——也就是备受地震困扰的地区——举办斗牛是为了向海神表示敬意。欧里庇得斯在他的悲剧《希波吕托斯》中描述了一头牛从海中魔法般地出现,并成为湖镇和地震毁灭英雄的工具。在早期地中海的克里特文明中,斗牛的习俗始终存在。在18世纪,西班牙流行着一句“面包和斗牛”(Pany Toros)的谚语,意思是说只要有面包和斗牛,生活就足够了。在毕加索的故乡——马拉加的角斗场,基于安达卢西亚人的传统,斗牛比赛是周末最重要的娱乐活动,而毕加索恰恰从童年时期就爱上了斗牛这一活动,并时常随着他的父亲前去观看斗牛比赛。毕加索曾在他定义的“完美星期天”中描述道:“上午一大群人聚会,下午观看斗牛表演,夜晚在妓院。”但他指出,他可以没有第一样和最后一样,但离不开斗牛的娱乐生活。
斗牛,在西班牙文化中,是独特的象征符号。斗牛场上发生的一切演变成了一套审美标准。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1914—1984)曾指出西班牙人人生观的形成与斗牛文化关系密切,他认为:“在西班牙,人们的情感教育,是在妓院和斗牛场完成的。多亏了斗牛,一个西班牙人才得以了解自己,明白自己身处何种世界。”由这段言论中,多少可以印证毕加索缘何如此热爱斗牛活动。
斗牛文化,反映了植根于西班牙骨髓中的民族性格。西班牙著名语言学家Luque Duran如是写道:“斗牛的世界里,人物、仪式和场景纷繁,在西语文化里形成了为数众多的隐喻并被运用到其他领域和人类活动当中。从中世纪以来,西语中就存在着很多跟斗牛相关的表达方式。尤其是在文学作品当中。斗牛世界的中心无疑是斗牛场上的角逐。这场由众多参与者和众多场景组成的盛大事件,以高度概括的形式展示了人类和大自然最为崇高和野蛮的方方面面。敌对、挑战、决心、勇气、冒险、欺骗、超越、痛苦与死亡是这一事件根本之要素。无论是在我们的文化或是其他文化中,很难再找到如此完整而又丰富的仪式;而且它有十分强大的生成语言的能力。原型神话、历史传说、宗教仪式和传统、体育活动、电影世界和现代表演等,都可以生成西语中产生隐喻的主要来源,但是没有任何一种能比得上斗牛仪式所具备的完整性、冲击力和启示性。这种几近神圣的斗牛仪式堪比驱使人类活动的原动力,使得人们很容易把它同生活或者其它任何特定的活动联系起来,如人生、爱情、政治、体育等。当然,斗牛的象征能力和潜力远不止于此。”通过毕加索对斗牛主题的艺术表现,恰恰可以看出他的审美情感和身份认同。
在毕加索看来,公牛是世界上最为骄傲和自豪的象征,斗牛则显示了智慧和勇气。毕加索的私人助手萨巴特斯(Jaime Sabartes)曾称毕加索对公牛不吝赞誉之词:“公牛是野蛮而高贵的动物,在任何危险面前,它们从不退缩和屈服,是不可动摇的勇气、力量、威严、痴迷于攻击的化身。任何斗牛表演爱好者的自尊都源自公牛本身和它的力量,同时,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公牛那样勇于尝试的精神。”
但是,毕加索眼中的斗牛显然比其他人看到的竞技行为更多了许多涵义。他曾告诫好友弗雷瑞斯(Frejus)千万不要对斗牛期望太高,因为一切仅止于模仿和游戏,所有的斗牛因素都被精确计算过。毕加索固然有他的理由,他崇尚激情,讨厌陈腐与按部就班的行为方式。在法国,他尽可能不错过尼姆、阿尔勒的每一次斗牛竞技比赛,最终,生活中的所见与所想,成就了他创作中的斗牛主题。
在早年创作的一系列关于斗牛的速写后,1900年,毕加索创作了他的第一幅蚀刻版画,绘画的标题为“左撇子”,描绘了一位骑马斗牛士。此后,毕加索搬到法国,当先后尝试了立体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风格后,他又一次回到了曾经熟悉的斗牛主题。但这一次,他将居于主导地位的公牛和显现出屈服形象的马并置在画面中,从而为绘画增添了新的元素。画面中,既没有斗牛士,也没有手执长矛的助手,但公牛俨然是胜利者。
将公牛与马联系在一起的灵感,首先来自于斗牛的戏剧化现实。在斗牛的竞技表演中,充满着狂暴的愤怒、无畏的勇气与卓越的技巧,同时,这又是一出关于死亡的演出。安达卢西亚裔诗人兼剧作家加西亚 · 洛尔卡(Federico Garcia Lorca,1898—1936)形容道:“西班牙是唯一一个把死亡视为一种自然景观的国家。”在洛尔卡看来,斗牛运动之所以让人疯狂地痴迷,正在于观看者对死亡的视觉凝视,它使得人们从身体和精神双重意义上得到解脱。在决斗场中,斗牛士身着艳丽服装,头脑冷静,勇敢灵活,而牛和马则在这场死亡的对决中成为一对敌人。
毕加索目睹了角斗场上公牛的受伤与死亡,在残忍的暴力和宣泄的本能面前,人们狂欢不已。在1937年创作的《格尔尼卡》中,毕加索以象征的手法表现了公牛与马。而此前,他在很多蚀版画中都描绘了马在遭受攻击后,昂首嘶鸣的暴怒之态。在《格尔尼卡》这幅画中,毕加索将公牛视为黑暗和残忍的力量,将马认同为遭受苦难的人的象征。在创作此画的大量草稿中,毕加索经常表现了公牛、马和飞马,如果将毕加索童年经历的地震与希腊海神的神话相联系,这似乎是他的记忆在现实政治和生活中的一种混乱的投射。

图1 《女斗牛士与伟大的斗牛》 蚀刻版画 1934年
公牛与马,代表着斗牛竞技场上对抗的双方,毕加索却为二者赋予了更多的角色。在蚀刻版画《女斗牛士与伟大的斗牛》(图1)中,毕加索描绘了三个主要形象:颈部插着长矛而狂暴愤怒的公牛、不省人事的女性斗牛士、直立的马。在这幅画中,毕加索表现了一种超现实主义色彩。由女斗牛士袒露的胸怀可以辨认出她是毕加索此时的情人玛丽·泰蕾兹(Marie Therese),她已经从公牛背上掉落;而右侧的马像用连枷打谷似的鼓胀着,代表毕加索困惑无望的妻子奥尔加(Olga Khokhlova)。
可以看到,画面中纠结费解的线条,被毕加索用作表现攻击性的符号,在这种画面的张力中,斗争的主题一目了然,但画家同时表达了:在这样压抑、激动的混乱之中,没有任何一方是胜者。
二
如果说,在斗牛竞技场中的斗牛士象征着男人,公牛则代表着女性。西班牙人认为,男女恋爱如同斗牛,你来我往、针锋相对。能够用勇气与技巧征服公牛的斗牛士将被看作是英雄,怯懦无能者则会遭受嘲笑和奚落。在毕加索的斗牛主题的绘画中,公牛、斗牛士和马,直接反映出毕加索对两性关系的描绘。毕加索的一生中,曾有过两任妻子和众多情人,在他艺术创作生涯的不同阶段,总有一位女性与之密切联系,如粉红色时期的费尔南多·奥利维(Fernande Olivier)、新古典主义时期的奥尔嘉·柯尔克洛娃(Olga Khokhlova)、超现实主义时期的玛丽·泰雷兹·沃尔特、立体主义时期的多拉·玛尔(Dora Maar)等。这些女性是毕加索爱情与艺术创作的对象,也是其艺术风格不断创新和变化的原动力,在毕加索的绘画语言中,他巧妙地将这种两性关系转换为公牛或斗牛主题的艺术符号。

图2 超现实主义杂志《米诺陶》封面设计 1933年

图3 《垂死的米诺陶》蚀刻版画 1933年
1924年,随着超现实主义的来临,毕加索的作品中也开始出现对神话原型的追溯,其中,最重要的图像符号即牛头人身怪米诺陶,他以现代性手法和观念创造性地演绎了这一古典主义神话。在古希腊神话中,米诺陶由克里特岛国王弥诺斯之妻帕西法厄与海神波塞冬所派的公牛所生,被弥诺斯终身囚禁在迷宫之中,他把雅典的年轻男女当牺牲品吃掉。1928年,毕加索以拼贴和绘画的方式创作了《牛头人身怪米诺陶》,画中的米诺陶是音乐和艺术创作之神赫尔墨斯的分身,罗马名为墨丘利(Mercury),与1924年俄国上演的芭蕾舞剧《墨丘利》同名。这绝非巧合,而是毕加索有意为之,在此前的《米诺陶之战》中,毕加索就以变形、夸张、移位等艺术手法表现了这一瞎眼牛头人身怪兽。1928年至1936年间,毕加索的作品中不断出现斗牛主题的图像元素。1933年5月,毕加索受委托为超现实主义杂志《米诺陶》创刊号设计封面插图(图2),他以立体主义手法对这一人兽同形的图案进行拼贴,并以木条、锡纸、树叶为之装饰。
牛头人身怪米诺陶,引发了毕加索连续性的创作主题,这些创作似乎毫无关联,仅仅显示出毕加索的形式创造。如1933年一幅《米诺陶》作品中,画面中只描绘了怪物头部的犄角、紧瞪的双眼和凸出的鼻息,由而反映出其野性的特征。但在题为《米诺陶与窗帘后的妇人》的作品中,米诺陶的形象则突然转变为一个驯良的对象,在装饰着花卉图案的窗帘的掩映下,米诺陶安静地怀搂着一位美丽姑娘。1934年的《女斗牛士》中,毕加索描绘了一位裸体女性持剑刺向一头公牛的场景,这似乎喻示着米诺陶与公牛的死亡命运。
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到1935年的《米诺陶之战》系列,毕加索对米诺陶的形象进行了各种想象化的加工,事实上,在很多时候,毕加索将米诺陶视为自己的肖像照,如同奥维德的《变形记》所描述的那样,毕加索通过米诺陶的变形,展现了一种复杂的人性,既渴求欲望,又被各种禁忌所压抑。1943年,毕加索邀请弗朗索瓦斯·吉洛(Fransonie Gilot)前往他的画室欣赏《沃拉尔系列》蚀版画,在题为“米诺陶亲吻熟睡的妇人”这一画面上,米诺陶既是凶猛的存在者,又是温柔的爱人,这显示出他的两面性本质。毕加索对该画解读道:“他在端详着她,试图读懂她的心思。他希望了解她是否因为他是怪物而爱他……很难说他究竟是想唤醒她还是杀死她。”根据这些作品,吉洛曾转述毕加索对两性的观点:“对我们而言,生活即斗牛,一种充满规则的仪式。”在《米诺陶之战》的套色版画中,画面右方是瞪大双眼的半牛半人的怪物米诺陶,它正将右手伸向左面小女孩手中的蜡烛,二者之间,则是撕缠在一起的裸体女斗士和马,画面中性器官暴露无遗,米诺陶的性别则含混不清,这一切都为画面上方的三位观看者所默默注视。显然,作为热爱斗牛表演的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深谙公牛以及米诺陶主题的战争寓意,他视公牛为地中海背景的象征;就米诺陶这个怪物本身而言,它的形象既卑贱又神圣,既纯洁又色情,同时交织着情爱和仇恨。对于巴黎超现实主义者来说,牛头人神怪象征着黑暗、非理性与暴力,是犯罪和残酷的根源。但毕加索却对奥维德的神话叙述进行了艺术转换,他承认牛头怪是潜藏在人类潜意识中的怪兽,不过,他更乐意于将这种形象认同为其祖国西班牙的斗牛士,代表着骄傲、勇猛与力量。正因为此,毕加索创作了属于他自己的崭新的米诺陶神话,他把自己塑造成牛头怪,把他和泰雷兹的两性故事展现在他的艺术舞台上,而非黑暗的迷宫之中,如《垂死的米诺陶》(图3)和《被征服的米诺陶》等作品,米诺陶现身于地中海阳光撒照的斗牛场,而场中的观众都长着玛丽·泰雷兹同样的面孔,由此他表达了对泰雷兹的爱恋。
1934年9月22日至12月31日,毕加索创作了一系列的《盲眼牛头怪》蚀版画(共四幅)。该系列作品中,失明的牛头怪失去了往昔的威风,手持拐杖,仰首嘶鸣,由长着泰蕾兹容貌的年轻女孩牵领着,显得年老孱弱、可怜无助。在这一系列绘画的第一件作品中,小女孩右手捧着花束,其他几幅女孩则怀抱展翅挣扎的和平鸽。
“失明的米诺陶”是毕加索的首创,这一理念源于他在蓝色绘画时期及创作《粗茶淡饮》(1904)的痛苦经历,他一度困扰于失明的恐惧。同时,将米诺陶刻画成“盲目者”,也表现了这一时期他和妻子奥尔加,以及情人玛丽·泰蕾兹之间的复杂关系。1935年7月,毕加索的缪斯女神兼模特玛丽·泰蕾兹怀了他的孩子,奥尔加带着她和毕加索的儿子保罗离开了家,二人分居后却并未离婚,因为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拒绝对此承认。毕加索或可以放弃西班牙国籍解决婚姻问题,但他显然无意于此。最终,当毕加索和玛丽·泰蕾兹的女儿玛雅出生时,毕加索对泰蕾兹的情感已经日渐淡漠。对于该时期陷入财产分割和情感纠纷的毕加索而言,这段时间是相当糟糕的时期。与此同时,这些作品也渗透了画家对20世纪30年代欧洲日益昏暗的政治局势的不满,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并为毕加索1937年描绘战争灾难的不朽壁画《格尔尼卡》奠定了基础。
1936年5月28日,毕加索创作了《穿着阿勒甘服装的米诺陶遗体》的巨幅水彩画,在这幅画中,神情悲戚的长生鸟象征着永生,米诺陶又瞎又瘸,身着五色服装。通过这一作品,毕加索似乎希望表达对前一段生活和绘画的告别。他隐匿在各式米诺陶的形象背后,但又若隐若现。这一时期,毕加索开始在作品中描绘他的新欢——超现实主义摄影师朵拉·玛尔,她以女性米诺陶的形象呈现在画面中,直视着太阳,却代表着死亡。数月后,毕加索与朵拉结婚,他创作了朵拉遭米诺陶强暴的巨幅彩色素描,其象征涵义不言而喻。
从斗牛士到米诺陶,毕加索的画作中不断展现着暴力图像,这是他对两性关系的描绘、历史文化的求同,以及个人人格的体认。可以看到,无论如何乔装,毕加索的面具后,始终是一名艺术的探险家。
在毕加索的大量速写中,可以看到公牛、米诺陶与裸体女性的图像被画在一起,画家甚至赤裸裸地在画中表现男性对性的窥视。对此,毕加索毫不避讳,他认为性是最自然的艺术,是人类生活和艺术创作中最普遍的本质,而艺术并非纯洁高雅的代名词。
毕加索的情妇弗朗索瓦斯·吉洛说,毕加索对待女子形象只有两种办法,或是把她称作为女神,或是当成可怜虫。实际上,“女神”和“地雷”(land Mine)是更为确切的形容。在虚构女斗牛士和米诺陶时,这种譬喻恰如其分,表现了毕加索对两性之间的复杂态度,既追慕爱情,热切渴望爱与性,又时常陷入私人生活的矛盾中。因此,米诺陶便成为了他自我投射、表现情绪的神话符号。

图4 斗牛场景 陶瓷 1959年
三
毕加索的一生都对斗牛主题保持着极大的热情,他的“斗牛”创作广泛涉及素描、版画、雕塑、陶瓷(图4)、海报等艺术门类,其艺术风格也包括立体主义、新古典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20世纪30年代,毕加索更强调于对整个斗牛事件的现实描绘,有时候他描绘的是斗牛场景中的全部参与者,有时候则仅仅描绘一个受伤的斗牛士,或骑马的斗牛士手持他长矛的动作,甚至只是在画面中央绘制公牛的动物形象。

图5 毛笔铜版画 1957年
1959年,巴塞罗那出版的26张凹版腐蚀制版画或许是毕加索最具代表性的“斗牛术”绘画创作,该作受到了毕加索的偶像——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1746—1828)的作品启发,在向古典主义前辈戈雅的致敬中,毕加索重现了西班牙斗牛的仪式感,并巧妙地表现了他的生活冲突。
在参观完阿尔勒的一场斗牛表演之后,毕加索于三小时内在铜版上即兴创作了26幅毛笔画(图5)。这种充满激情而不由自主的创作状态折射出毕加索对斗牛比赛的深刻领悟,他以迅疾的用笔捕捉了斗牛比赛的特征,同时,虽然笔简却激起了观者的充分想象。
通过这些作品,毕加索再现了一场令人愉悦的斗牛表演,他对斗牛过程中不同的搏斗位置都予以概括性的描绘,正像他自己所说的精确计算一样。竞技伊始,角斗场四周布满着观看的人群,人们为斗牛士、愤怒的公牛以及他们的精彩对决而欢呼雀跃。
值得一提的是,毕加索斗牛主题的艺术创作中还融合着他早年喜欢的另一主题,即杂技和马戏表演。当他创作出《斗牛术》时,已年逾75岁,并且再也没有碰触过这些在“二战”前于这一主题作品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存在的、象征主义的符号。这些例证代表着斗牛主题在毕加索版画中的高潮和尾声,尽管他偶尔仍会在其他印刷品上使用这一符号,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964年,但是主题本身继续吸引着毕加索。
在90岁时,毕加索创作了一系列穿着明艳服装的斗牛士和斗牛士半身像,头部用鬓角装饰,顶着奇怪的松软的帽子,像是小丑,诉说着以往人生的悲喜剧。
毕加索曾经对他的朋友布拉萨依(Brassai)说道:“我梦想着将来会有一种‘人的科学’,通过它可以研究我的艺术,并从中发现人类存在的真实状况。通过某一个体的体验,揭示人类的悲欢离合。我要再次重申,我的作品不止是我的生活轨迹,或者印迹,作品就是我的生活。如此说来,作品成了复杂的东西,但同时它却又比你们搞出来的东西简单的多。”在毕加索的艺术世界中,公牛、斗牛与米诺陶的相关主题创作,不仅表现了他的艺术体验,还反映出一种真实的人性和一段直观的人生。
注释:
[1]玛丽·M·盖多.艺术作为自传——毕加索的《格尔尼卡》[J].许春阳译,世界美术,2007(3):86—95.
[2]陈星.“斗牛”文化与西班牙语谚语[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2009(3):165—166.
[3][6]Anita Beloubek-Hammer.Pablo
Picasso
:Women
.Bull
fi
ghts
.Old Masters,Edited by the Kupferstichkabinett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 2011, Gestalten.p107.[4][5]贾永生.斗牛文化在西语中的象征、隐喻和熟语[J].语言学研究,2015(1):171—180.
[7]〔美〕拉塞尔.马丁.毕加索的战争:格尔尼卡的毁灭及扭转乾坤的巨作[M].林立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4.
[8]1933年至1939年,许多欧洲艺术家都深受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包括毕加索在内,杜尚、玛格丽特、恩斯特、米罗、马宋等艺术家都曾为超现实主义杂志《米诺陶》创作过封面和插图。
[9]Stephen Coppel.Picasso
Prints
-the
Vollad
Suite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2012.p165.[10]〔美〕珍妮特·霍布豪斯.毕加索的裸体画[J].封一函译,世界美术,1989(3):20.
[11]〔英〕尼尔.考克斯.毕加索说[M].杨秀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