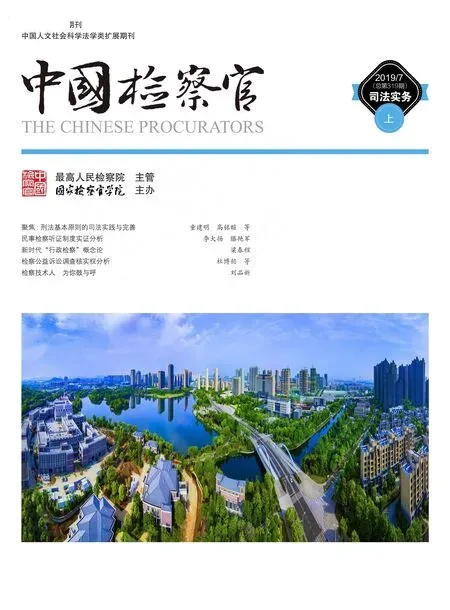刑法基本原则的实现机理:立足于技术和方法的视角
劳东燕(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刑法基本原则在理念层面的确立,已经没有任何疑问。问题在于,我们需要一套技术和方法,把基本原则的理念贯彻到实务适用之中。这实际上涉及到基本原则的实现机理问题。实务方面一直有这样的需求。那么,理论上如何发展与适用这样的技术与方法呢?
首先,就平等保护原则的动态适用问题,应该包括以平等原则来指引和审查个罪在立法论与解释论上的合理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应该考虑用平等保护原则来指导对构成要件的解释。由于平等原则还是一个宪法性原则,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还是个案审判中的法官,虽然无权对法条进行违宪性审查,但负有使相应的解释结论合乎平等原则的义务。就平等保护原则在民营企业权利保障中的适用问题,我之前有所关注。具体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言,从平等保护原则的角度来看,这个罪名无论是在解释论上还是在立法论上可能都存在一些问题。
如果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做扩张解释,就会使民营企业在融资方面处于特别不利的地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从《商业银行法》第79条,也就是修改之后的81条衍生而来,从立法论上就是要保护国有商业银行的利益,保护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的利益。但是在今天,银行并不能完全代表金融产业的利益,严格说来,银行只是金融产业中的一个利益集团。这个罪名的存在,不仅严重妨碍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的解决,也影响到金融创新与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这样一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法由于立足于保护银行集团的部门利益,在立法论上就显得不再合适。尤其是,该规定的存在,导致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融资保护上的不平等。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有必要考虑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法规定做出相应的调整与修改。
同时,从解释论的角度来讲,结合商业银行法的相关规定,应该考虑加一个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比如说以资本运营为目的,添加这样一种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能够跟商业银行法的相关规定是协调起来。为什么这个罪名中用的是存款的概念,而不是用的资金的概念,也表明非法吸收公款存款罪旨在处罚间接融资的行为。现在司法实务中把存款直接解读为资金,会使这个罪名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口袋罪。所以,就非法吸收公款存款罪而言,我倾向于认为,如果眼下立法论上没有办法解决平等保护的问题,至少在解释论上添加上一个构成要件。这样的话,至少民营企业的自我融资行为,即直接融资用于生产经营的行为,就可以做去罪化的处理了。
除平等保护原则之外,我还想讲一下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如何在司法中予以实践化,也涉及一些技术问题。人们往往认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只涉及量刑阶段的问题。这样的理解,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作为基本原则的角色。既然是基本原则,就不可能只影响量刑阶段或只影响处罚,必然也影响定罪阶段,影响刑法适用中的解释问题。在此,其实涉及对罪刑关系的全面理解问题。说到罪刑关系,一个方面当然是说刑本身是由罪生出来的,也就刑由罪生;另一方面,也要考虑说罪本身是受到刑的制约的。这个问题如何来理解呢?我觉得,应该将罪刑相适应原则理解为刑法解释中的一个指导原则。从立法层面来看,法定刑的配置是由什么来决定?立足于刑法理论,势必得出法定刑的配置只能由行为的不法程度来决定的结论。也即,行为的不法程度,其实是由客观上的法益侵害和主观上的不法意识共同来决定。立法层面虽然也会考虑一般预防,但一般预防的因素,只能在行为不法程度所对应的罪责的点之下来进行考虑。这也是责任主义原则的要求使然。
如果法定刑体现的是行为的不法程度,那么,对于构成要件的解释就必须体现与立法所配置的法定刑相适应的不法程度。所以,由此可以推导出一个解释论上的指导原则,也就是法定刑反过来应当决定构成要件的解释。在此,我讲的是法定刑决定构成要件,而不是说宣告刑可以决定构成要件的解释。这也是基于体系解释的要求,有必要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与体系解释之间建立起内在的关联。接下来,我讲一些实例,并不是要专门批评司法实务,只是想指出司法解释的有些规定或者实务中的做法,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来看,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个例子是生产销售假药罪中对加重情节的解释。司法解释中有关加重情节的成立,其中一种情形,是根据生产销售的金额来认定的。但是结合法条的相关规定,从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加重构成来看,其中的“其他严重情节”是与“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相并列,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与“致人死亡”相并列。这意味着,从罪刑相适应的要求出发,对“其他严重情节”的理解,必须与“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不法程度相当,而对“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理解,则应当与“致人死亡”的不法程度相当。然而,现行司法解释直接根据销售金额来决定加重法定刑的适用,这就会导致出现这样的问题:销售未经批准进口但是有真实药效的药品,是否仅因销售金额的提升,就可以认定为存在“其他严重情节”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实务中出现的相关案件,只要销售金额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数额,都直接适用加重法定刑。但这样的判决结论合适与否,值得斟酌。在药品具有真实药效的情况下,很难认为,单是销售金额的提升,就足以使行为达到与“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与“致人死亡”相当的不法程度。做这样的理解,难以使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加重构成,与故意伤害致人重伤与故意杀人罪的法条相协调。基于此,我倾向于认为,对于司法解释中适用加重法定刑的数额规定,需要做限定性的解释。也就是说,加重法定刑的适用,要求药品本身具有对人体健康的危险。在此前提下,如果销售金额有增加,在实质上可达到跟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与致人死亡相当的不法程度。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持枪抢劫中枪支如何解释的问题。抢劫罪加重构成中最不具争议的就是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由于持枪抢劫是与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相并列的不法类型,对枪支的界定,显然不能采取行政法上的枪支标准;否则,便难以使持枪抢劫与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形在不法程度上相当。因而,对于其中的枪支,有必要限制解释为具有类型性地引起重伤或死亡危险的枪形物。刚才喻海松处长在发言中提到,为什么对刑法中的枪支要采取不同于行政法上的枪支的标准,相应的正当性根据在哪里?在我看来,正当性根据就来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将该原则作为指导原则贯彻到持枪抢劫的解释当中,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三个例子是绑架杀人未遂的情形,即绑架过程中实施杀人的行为,但未能得逞的情形,能不能适用总则中有关犯罪未遂的规定?这其实涉及绑架杀人的行为结构问题。不难发现,绑架杀人其实是一种非典型的结合犯的行为结构,也就是说,绑架罪再加上杀人罪等于加重的绑架罪。既然如此,如果后罪未遂,则显然应认定为加重绑架罪的未遂,应当适用总则中未遂的从轻减轻的规定。这也是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
除此之外,比如,司法实务中一般都不认为说同种数罪可以并罚。实际上,就同种数罪而言,之所以通常不并罚,是因为我国立法规定或者司法解释经常存在累积性计算的规定,据此就已经把相应的不法评价进去了。但这不意味着,同种数罪在规范上就不能并罚。如果说有一个行为人,分别捅伤十个人,每个人都达到轻伤的程度,在这种情形之下,能进行数罪并罚吗?答案是肯定的。现行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规定,没有将捅伤多人的情形规定在内,只有通过实行并罚,才能得出合理的量刑结论。这意味着,在实施同种数行为的情形下,如果不并罚无法实现罪刑相适应,就应当考虑对同种数罪实行并罚。
当然,承认法定刑反过来会制约构成要件的解释的同时,必须强调,解释结论应当同时处于罪刑规范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的形式上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不能做过度实质性的解释。解释结论只有处于实质处罚必要性与形式的文义可能性的交集的范围之内,才可能具有合理性。这样得出的解释结论,才既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又符合罪刑法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