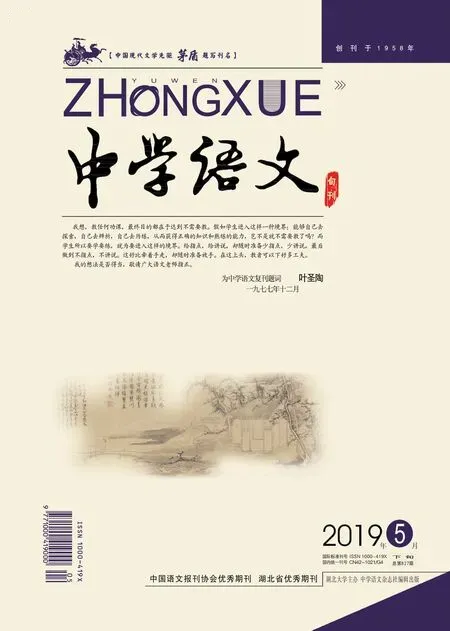关于新版语文课程标准及教材的断想
张 波
一、新的课标、教材,要有真的“新”东西、新的“真”东西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明确提出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其中较为亮眼的是“语文学习任务群”。此版内容是由教育部组织专家编制而成。
研读新课程标准,笔者认为,其思想的顶层设计是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由此推演,学生的核心素养则应该是“立德树人”中的“德”,以“德”为魂,则能“修身”,有德方能“成己”“达人”,方能服务于社会。在所有学科中,语文学科尤能促成学生顺利地养成这个“魂”,而这“魂”是由语言、思维、审美与文化四位一体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内容濡染渐塑,而其核心素养则需要通过学生践履“语文学习任务群”来淬炼养成的。学习任务群则以自主、合作、探究为主要学习方式,凸显了学生学习语文的根本途径。
比较新旧课程标准,两者的主要学习方式是完全一致的,即自主、合作、探究;而两种标准下编制的教材体系,一个是学习任务群,一个是单元体系,相似度也较高。虽然“学习任务群”的篇目可能更利于比较鉴别,更利于训练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透视视角。但是篇目的作者何以养成其独特的视野,作者何以成就其经典,这倒是我们读者、求学者很少关注、更少探究的地方。在这一点上,新旧课程似乎没有迥异之处。而恰恰这一点,似乎对学生的成长、成才更具有启发性。因此,新课标要“真”、要“新”,新教材体系也应与之相匹配。
因此,笔者惶恐,两者主要学习方式相同,新旧教材体系的组篇相似,只是“学习任务群”内篇目内容要求以自主合作探究方式来学习,这样比较能够强化训练学生的思维,但似乎与单元体系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即两者在思维深度、广度、密度上也不见明显的区分度。
二、学生有所敬畏尊崇——哲学思想该重视的问题
哲学能训练人的思维深度,也能拓展思维的广度密度。因此,哲学的启智功能不该被忽视。西方许多国家的高中生甚至是八九年级学生就开始学习哲学了。如“尼采挂在楼上——楼上的学生(注:九年级)已经学习哲学了”(《流浪人,你若到斯巴……》)。中国古代教育中,一直要求学生从小学习“五经”(其中《周易》就是玄妙哲学),“童而习之”;我国古代有无数的人文经典,其中许多经典就是作者青少年时期的奇思妙想。反观当代,中学生几乎不知哲学为何物,在现代教育训导下,学生虽勤奋却多只知追分数、求名校,拜金逐物,崇尚享受,如此人生“规划”之路极其简明。当代学子们其心多无禁忌,更少敬畏尊崇,最为关键的是缺少哲学思想“童而习之”的体悟。而哲人的视野、哲学的玄思,是需要长期体悟、渐进的。
当然,肯定有人会说,我们高中语文教材上也有古代哲学家的文章啊。比如《庄子·秋水》,可编者、教师从中所要传授给学生的是一个狂妄自大、知错就改、谦虚好学的河伯形象,此种认知容易导致学生以为《秋水(节选)》就是庄子《秋水》本来想要表达的思想。这是阉割了道家广博的思想,更是粗暴地曲解了原文意蕴。一代代学生就这样失去了“自主、合作、探究”博大精深的道家思想的契机,错过了领略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机会,更无缘于世界上无数的文化经典。为此,笔者不能理解编者为什么断章取义地推荐学生学习这个片段,更不理解他们是如何认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的。作为教师的我们,认识到编者有对人类的优秀思想、优秀作品生杀予夺的权力。几千年来,文史哲是不分家的,现在为了分数,学生学习的多是干瘪的知识碎片。为了考试,为了升学,编者的解读可能就是得分的指南针;为了分数,为了名校,本该崇尚真理的教师带着学生们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样的人文教育现状,会造就出什么样的人才?
三、编著者的眼界与使命
教材编者应该是某领域的大家。正如教材“五经”曾在几千历史中的作用一样,教材是关系着国家命运、民族未来的一件大事,甚至影响着社会的思想走向。因此,编制教材要有扎实的起点,更要有顶层设计。中国几千年的编制教材历史中,笔者陋见:叶圣陶编写的小学教材,起点好;孔子编著的教材,顶层趋向性高远。之所以认为叶圣陶的好,是因为教材内容的起点设定在让幼小的学生从做好人开始来开启人生,“正其心,诚其意,修其身”,亲爱其亲,而不是一味地充斥着空洞的道德说教。之所以认为孔子的好,是因为其教材,既有顶层设计,更有实践体悟;既有全面发展,也有因材施教;既有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又有适时的“启”与“发”,而不像现在那样灌注各种知识与情感,而极少体悟实践的做法。叶圣陶是著名的作家、教育家、编辑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一个视野开阔的大师级人物,所以其编制的教材考虑深远。孔子更是大师中的大师,所以其编著的教材自然是人类的思想精华。因此,编制教材,是“经国之大事”“不朽之盛事”。
常言道:“取法乎上,得其中;取法乎中,得乎下;取法乎下,则无所得矣。”同样,要“学者学乎上”,则期待着“编者编乎上”。孔子曾专程拜访老子三次,聆听他的天道思想,孔子深深觉得老子思想“神龙见首不见尾”。孔子晚年学《易》,韦编三绝,并进而成功借鉴老子之思,悟通了他的儒家顶层思想,从而构建了儒家思想体系。
因此,编制与课程标准相匹配的教材,需要具有全球眼光,集萃世界先进教育理念与经典,让我们的青少年据于文化巨人的肩膀之上享用人类文化盛宴,完成“功在未来”的“千秋大业”。但是,取人之长,切不可妄自菲薄,数典忘祖。
四、学习任务群的构建与解读
既然如此,18个“语文学习任务群”的构建,可提供丰富的史料、史识,可以有哲学华章等等。语文的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语文学习任务群”所选篇目不能只是囿于选择文学作品,也该多有下及“饮食男女”,上达历代诸子百家之“玄妙天道”的内容,拓展课程标准附录中所涉及的道儒等家文章,体现的是文化自信、思想自信、教育自信、语文自信,让青年学子们能自信地自主探究出新的思想火花。编者编乎其上,则学者学乎其上。这样,可以让学生在自主探究学习任务群内各种思想观点的“源”与“流”、本体与万物的生成演绎,既可以让学生领悟到高远的奥秘,也可以体察其心弦的颤动,既可归宗为“一”,又可散而生“万物”,宏微结合,小中悟大,大中识小,道器一矣。
当然,有人会说吃鸡蛋,何必看下蛋的鸡呢?仅以文豪苏轼为例。我们中学阶段六年学生学习到的苏轼的许多诗文,有的文中流露出来的道家思想难道能说是一个完整的道家“鸡蛋”吗?充其量只能是《道德经》《庄子》等道家思想“鸡蛋”的一点碎片罢了;同样,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儒家“五经”、中国本土佛家等思想也仅是诸领域中的一些碎片而已。不了解这些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原典,学生便如井底之蛙一样以为天只有井口般大。笔者认为,苏轼最终成为“文学之士”中的“上”者,是与他广博采集各领域的“上”者分不开的。其实,苏轼宗儒家,精通道释纵横家等等思想,他胸怀宇宙之玄妙,口含百家之精华,心悟人世之波澜……可我们只看苏轼的文章,而不知其多种思想的源头之多姿多彩、波澜壮阔……是无法窥见苏轼的其人、其心、其志的。
综上所述,编制与新课程标准相匹配的语文学习任务群,任重而道远,“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选文与解读,不能被各种宗派的思想“遮住望眼”,而应该“透析”各种意识形态的优劣,透视并汲取其中人性的美、人类的智慧、宇宙间的大道,汇集之,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世界性思想。在此基础上编制的教材才能真正引领学生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理解和接受全新的人类性思想,才可能避免因思想的不同、信仰的狭隘而泯灭人性,从而造福于全人类。
——依托《课程标准》的二轮复习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