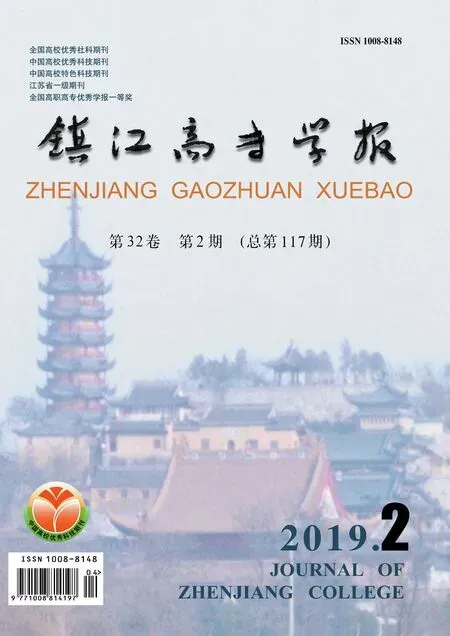意象视域中的民族文化心理建构——评吴恩泽中篇小说《洪荒》
崔 丹,王松锋
(贵州师范大学 a.文学院;b. 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吴恩泽是贵州省松桃县杰出的苗族作家。1980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热乡热土》;1994年出版中篇小说集《洪荒》,获贵州省政府文艺奖二等奖;1998年出版长篇小说《伤寒》,获全国第六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长篇小说奖;2002年出版长篇小说《平民世纪》。
吴恩泽发表处女作《热乡热土》后,创作热情高涨,在梵净山深厚文化底蕴熏陶下,他将梵净山山区的自然环境、风俗人情和民间信仰融入作品,使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
民族传统对一个民族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也就是民族情感、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1]247。苗族历史是一部历经磨难、充满血泪的迁徙史,苗族人民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性格。吴恩泽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他更能深刻理解苗族文化心理。吴恩泽父亲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吴恩泽15岁初中毕业后不得不在偏远的山村当教师谋生,文革时期又因家庭问题被遣送到贫瘠荒凉的山阳溪。在对生命、生存与生活深刻体验的基础上,吴恩泽继承了苗族人民坚韧、勇敢的民族性格。吴恩泽在中篇小说《洪荒》创作中,多次运用具有地域文化色彩的山洞、灵魂、菩萨等意象,将客观事物与主观情感相结合,体现了梵净山山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展示了苗族人民在历史长河中的艰辛奋斗历程,凸显了梵净山山区人民的民族文化心理。
1 山、山洞意象
原始初民时期,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类既要与自然抗争,抵御自然灾害以求生存,又要依赖于自然的恩赐来维持生命的延续。自然以其不可知性,让原始人类对其产生敬畏心。梵净山被称为“天下众名岳之宗”,一直是当地居民崇拜的神山、圣山,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其在宗教艺术、民俗风情、社会文化等方面具有浓郁的原始性色彩。吴恩泽在《荒谷情魔》《苦力》《苍凉山谷》等小说创作中以梵净山为背景,建构了具有神秘色彩的“梵净山乡土世界”。
在《洪荒》创作中,高山、崖石、万丈深渊、溶洞等意象的描写使小说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革命者笃和顺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召为偷出两人遗体予以安葬而被追杀,召把笃夫妇的头颅偷出来之后安置在溶洞中,并留妻子风独自住在飞天凤的山洞。山洞对于风和召来说,不仅是一种表示自然的符号化语言的能指,即山洞的封闭性可满足人们遮挡烈日风寒的需求,还是具有“家”和“未来”的所指,蕴含着风和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冀和憧憬。能指和所指构成了山洞的概念符号,使得山洞既具有大自然的“寒”,又具有人性的“暖”,成为一种“两面性的心理实体”。
自古以来,山洞在众多文人笔下被赋予一种神秘意义。《山海经》里,西王母居住在昆仑山的石洞之中;《聊斋志异》中有对查牙山洞的描写;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描述了山洞后隐藏的世外桃源;《西游记》中妖魔鬼怪大都居住在山洞之中;在金庸、古龙等作家创作的武侠小说中,山洞更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象征符号,人物命运往往在山洞中发生重要转折。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指出:“石洞可能是大地母亲子宫的象征,成为转变和再生可以出现的神秘地方。”[2]277风在山洞中生下苦,并用牙齿咬断孩子的脐带,用舌头慢慢舔去孩子眼睑上的血,这种具有原始初民色彩的生育方式显示出原始生命力的旺盛,体现了苗族人民的山洞崇拜。在吴恩泽的《苍凉山谷》中,风水先生把蛤蟆寨的人丁兴旺归功于石壁上被后人称为“根”(地方方言,意为男性生殖器)的岩柱。在苗族鼓社石窟里至今安放着供奉祖妣“央公”“央婆”兄妹的裸体木雕像及泥塑的生殖器,两旁还放着一对酒糟桶,桶内放着象征繁殖人类的酒糟[3]509。
《洪荒》中人物命运的变化都离不开飞天凤。飞天凤危峰兀立,沟谷深邃,山川、草木、大地、虫鱼等呈现出的原始生态使其具有一种天然的神秘性。自然的神秘使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具有传奇、灵异色彩,飞天凤背后似乎有一种无形的神秘力量在冥冥之中操控着每一个人的命运。不管是风还是召,最后都回归飞天凤。召经历了“离去—归来—再离去—再归来”的过程,最后被埋在飞天凤绝顶。风生母的灵魂曾告诫她,不能离开这座山头,否则会后悔莫及,离开了飞天凤的风经历了丧子之痛,最后在召的坟前飞下了万丈深渊。飞天凤似乎早已预示到风和召的悲剧命运,只有在这里才能庇护他们躲避外部世界的混乱纷杂。风生母灵魂的出现有两种可能:其一,风生母灵魂是飞天凤的幻化,因为它无法直接告知风和召即将面临的悲剧命运,所以通过神力幻化成风生母的灵魂;其二,飞天凤是风生母灵魂的归宿,灵魂的出现体现了母亲对子女的牵挂与保护。山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自然符号,而是一种“神灵之物”。无论是山洞崇拜还是大山崇拜,归根结底都体现了苗族人民对自然的崇拜与敬畏、对大自然无私恩赐的感激。
2 灵魂意象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4]24除文学作品外,巫术信仰也渗透到民族文化心理层面,逐渐演变为民族风俗。苗族是一个信仰鬼神的民族,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限制了苗族先民的思维能力发展,他们认为万物有灵,大自然中不能解释的万事万物都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神秘色彩,这为苗族鬼魂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信仰奠定了基础。“宗教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5]68这种超自然力的原始宗教赋予苗族文化心理一种神秘色彩。
巫风巫俗的盛行是苗族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具有神秘难测的意蕴。神秘是人对世界之莫测的感知,预言和预兆正是这种神秘的自我呈现。从生母的预言开始,风就在冥冥之中踏上属于自己的命运之途。为了拯救召及其部队,风不得已违背生母告诫离开飞天凤,在逃离途中,儿子苦不幸死去。在苦死去后,这种神秘延续到了风的身上,在夜深时,她飞升的灵魂会驾着毫无知觉的肉体梦游而见到生母和苦,在苦的棺木要入土时,宏看到了风的魂魄扑在苦的棺木上,急忙念咒把风的魂魄打回到其肉身之上。不管是风还是其生母,都在灵魂的操纵下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除此部作品外,《苍凉山谷》中风水先生的预测、巴岩阿爸的巫师身份以及萝芙看到荒坟里的幽灵向她招手等都极具神秘色彩。长篇小说《伤寒》中也有对巫术的描写,万从美想要知道久苇是否还活着,就找巫婆作法占卜,巫婆借用一碗清水看到了久苇的魂魄,判定了久苇的死亡,这种巫文化增强了小说的地域文化色彩。苗族有鬼魂崇拜,苗族人民认为人死之后肉体消失,但灵魂依然存在,他们将祖先崇拜与灵魂崇拜相结合,认为具有极高威信的先祖魂灵会庇佑子孙后代,由此产生一系列的崇拜仪式。吴恩泽在小说内部结构中融入民间的原始宗教信仰,大大增强了小说的神秘性。风在召要报杀子之仇时留下蓉,似乎已经预料到自己和召的命运,随后便在铁索仍在、四壁完好的房间里飘然而去,在召被行刑前使召安然离去,免受了刀剐之苦。对于风最后的结局,据说在清晨第一缕晨曦沐照在召的坟头时,她跳下了万丈深渊。随着风的消失,故事也结束了。关于预言、梦境、灵魂、死亡等疑点,小说没有任何交待。在文本里,我们只看到结果,产生结果的原因却无法解释。这种断裂使这些人物具有了宿命的神秘意味,人物故事成了无解之谜,留待读者们作出自己的解读。
3 色彩意象
在《洪荒》中,吴恩泽以红色为主体、黑色为辅助,组成了小说的色彩基调。红色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色彩能指,而是随着小说环境的演变,成为一个动态的所指,它既是生命、力量的代表,又是鲜血、死亡的隐喻,它既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也带来了悲惨和痛苦。黑色既是压抑、悲伤的表示,又是神秘、严肃的隐喻。因此,在解读色彩意象时,其所具有的象征与隐喻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度的。
对于黑色,莎士比亚有过形象的描述,“黑色是地狱的象征,是地牢之色,是黑夜的衣裳”[6]。在小说中,黑色具有灵异、神秘色彩,同时意味着恐怖与阴谋。召在黑夜中看到了几十具血肉模糊的断头尸体,黑色是恐怖、罪恶、死亡的象征。黑暗与白昼相对,白昼带来光明,而黑夜是阴谋的怂恿者,肆无忌惮地造成了大量的流血和死亡。在《荒谷情魔》中,吴恩泽以荒凉而又阴森恐怖的黑森林为背景,描写了野花和花子王在封建族法压制下殉情的悲剧。
作为小说的主色调,红色是生命力和希望的隐喻,与太阳意象具有同质性特征。小说中对于太阳的描写并不是简单的客观对象叙述,而是渗入了作者的主观情感,在故事情节建构、人物情感表达以及深化文本内涵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太阳意象与红色意象都围绕山峰描画,如“山顶处出现了一抹长长的红色”“绝顶沐上红色”“太阳红山时分”“山顶一片艳红”等。从时间上看,都是以清晨为主;从太阳位置上看,都是以上升为主;从山峰位置上看,都是以顶端为主。3个方面要素促成了象征希望与力量的主体的构成。小说中写道:“东边天上开始微露曙光,山顶上出现了长长的一抹红色,紧接着孩子的第一声‘呱呱’的哭声随着朝阳的升起而响起……苦是大家的太阳。”[7]8太阳给予大地光芒与热量,促进万物生长,是生命和力量的代表。美好寓意的“太阳”与“苦”联接,暗示了希望与苦难并存。苗族是一个古老而又苦难的民族,从炎黄时代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苗族人民遭受战争迫害而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经历数次大迁徙,寻找安居之所。但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苗族人民并没有放弃希望,而是以顽强的精神为支撑,完成了充满血泪的迁徙史。苦不仅是召及其十七个的“根”的延续,更是民族希望的传承,小说中红色意象贯穿始终,作品把苦在太阳初升时降生作为开始,虽然苦在战争中不幸死去,但是希望并没有消失,最后小说以蓉在清晨中生下孩子结束,这种巧妙的情节安排显示出作者的独具匠心。
红色既是鲜血的象征,又是人性温情的表现,还是个人理想与民族精神的隐喻,三者相互交融构成了红色多义性特征。笃和顺为革命牺牲;风为了召的军队能够逃脱闻的突袭,违背生母的告诫而牺牲了自己的孩子苦;崇为了民族大义而不得已杀了召……救命之恩、血缘亲情、兄弟义气与民族苦难相交织,小说在虚构的故事情节中,实现了革命历史的个人化叙写。召的恩人笃和顺被闻背叛而牺牲,他认为复仇是自己作为人所应该具有的良知与正义,即使以自己的性命作为交换也理所应当。这些流血与牺牲不仅体现苗族人民在历史长河中的艰辛历程,而且也蕴含着人们对天下太平、安居乐业生活的期冀,表现了苗族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召组建自己的军队之后渴望等到那支叫作“红军”的队伍,红色的表层意义指代红军,是革命的象征,其深层意义指向召自身所具有的火热的激情、超凡的能力、勃勃的雄心,以及想要救民族于水火之中的迫切愿望。召具有个人色彩的复仇最终转化为民族集体化的复仇。召、笃、顺、宏、苦、风等都以死亡而告终,但这个苦难深重、坚韧不拔的民族并没有失去希望,最后崇给召送来了中国远征军首站告捷的消息,梵净山敢死团令敌人闻风丧胆,蓉和召的儿子也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流血与死亡并没有压垮这个民族,苦难、悲壮而又伟大的苗族人民以顽强的意志、虔诚的信仰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并凭借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
4 菩萨意象
梵净山作为武陵山脉的主峰,自古就被佛家辟为“弥勒道场”,是受众人崇拜的佛家净土。梵净山的寺庙依据佛教宇宙图谱构建,以红云金顶为中心,“象征现世佛释迦的须弥山和未来佛弥勒的兜率宫日月双明、净土梵天,以四大皇寺四十八座觉庵呈群星拱卫状,象征接引无量信众山顶朝谒”[8]45。在《洪荒》中,多次出现观音菩萨的形象,它主要指佛教文化的观音菩萨和人性化的观音菩萨。
4.1 佛教文化中的观音菩萨
在佛教术语中,“观”有看之意,是指用智慧来观察,如观心就是内观自己的心性,“音”即声也,所以“观音菩萨”意指能够看到民间疾苦、听到民间祈求的菩萨,当众生遇到苦难时,观音菩萨会挽救众生于水火之中。作家在小说中对观音菩萨意象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寺庙建筑,其二为民众心理信仰,也可以说寺庙建筑是民众对佛教文化心理信仰的体现,两者相辅相成。绝顶观音殿在人们心中具有极高的神圣性,它见证了召和风历经劫难的婚礼,也是风唯一能够寻求心灵解脱之地。现实的苦难生活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心理恐惧,风认为是自己害死了儿子苦,在菩萨面前虔诚忏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心灵的安宁。人们将宗教作为心灵归宿,希望能够得到心灵的平衡,虽然宗教的解脱方式是虚幻的,但是其心理基础却是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人们对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的信仰体现了人们对现实世界苦难的痛恨与无奈以及对光明世界的追寻。
4.2 人性化的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普遍被认为是女性,用以歌颂与赞美女性的善良与无私。《洪荒》中不仅有佛教文化中的观音菩萨,还有人性化的观音菩萨。在召临死之前,他看到了观音菩萨,那就是风。风在召及其兄弟们面临生命危险时,不顾生母灵魂的劝诫,带他们逃出生天,苦的死亡使她承受着巨大的伤痛,风在冥冥之中知道自己的命运之后,留下蓉陪伴召并为召传宗接代,自己消失了。但是她似乎又无处不在,见证着这个世界上人们的苦难。风的慈悲、善良、无私与观音菩萨具有同质性特征。吴恩泽在创作中对于女性群体较为关注,刻画了一系列女性形象,如《苦力》中慈眉善目、温柔体贴的荒嫂,《005病房》中刀子嘴豆腐心、心地善良的小杨,《花家院》中春阳嫂子。“春阳”寓意春天的阳光,这是春阳嫂子牺牲自己、为别人着想的隐喻。这些都是人性化的观音菩萨,她们代表着生活在梵净山山区的纯洁、善良与崇高的人民。
吴恩泽在梵净山的生活土壤和文化土壤熏陶和滋养下成长,民族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意识通过各种形式对他的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使他自觉从本民族的精神与心理出发观察事物、感受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吴恩泽能把创作聚焦于少数民族文化,通过意象建构苗族人民的民族文化心理,这在当时颇具创新性和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