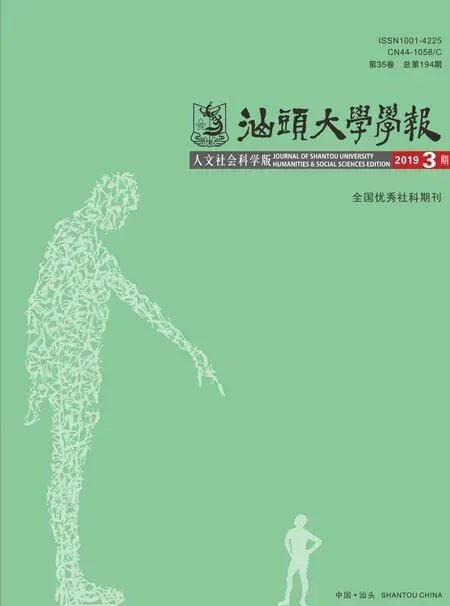中国古典诗学的“以食喻诗”批评策略
叶汝骏
(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台湾 台北 11605)
一、前 言
在中国古典诗学中,批评家们常常运用多样化的批评策略或方法来传达特定的诗学理念。譬如张伯伟先生曾归纳出三种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精神的方法,包括“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以意逆志’法,受学术传统影响的‘推源溯流’法,以及受庄禅思想影响的‘意象批评法’”[1]8。其中他将“意象批评法”解释为:“以具体的意象,表达抽象的理念,以揭示作者的风格所在。其思维方式上的特点是直观,其外在表现上的特点是意象。”[1]198本文所要讨论的“以食喻诗”,初看似与此若合符节,然细究之,从属于“以食喻诗”的“以味喻诗”(详后文),以及古典诗学批评史上著名的“以禅喻诗”,之中的“味”与“禅”,却并非是“具体的意象”,而是“抽象的理念”。由此看来,“以食喻诗”及“以禅喻诗”俱与“意象批评法”扞格,亦不能归入张氏所归纳的余二者。笔者以为,这里不妨用“取象比类”的说法更为合适。所谓“取象比类”,张岱年先生解释为“把形象相似、情境相关的事物,通过比喻、象征、联想、推类等方法,使之成为可以理喻的东西”[2]83。循此以理解,将“以食喻诗”及“以禅喻诗”等纳入“取象比类”的研究方法,则将不存在扞格之情形。
诗学理论是抽象思维的产物,往往不易索解。“取象比类”作为一种重要的诗学批评策略,它能调动人们的既有经验,或藉助人们熟识的事物,将深奥、抽象的诗学理论化为明白、可感的具体内容,从而有效帮助人们对于诗学理论的理解。“取象比类”在中国古典诗学批评中极为常见,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以禅喻诗”。除此以外,古代批评家还通过其他事物、概念的类比来推演诗理,如宋人有“以剧喻诗”者,《王直方诗话》载:“欧阳公作《归田乐》四首,只作二篇,余令圣俞续之。及圣俞续成,欧阳公一简谢之云:正如杂剧人,上名下韵不来,须副末接续尔。”[3]90又黄庭坚云:“作诗正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方是出场。”[3]14他们都通过宋杂剧艺术方法的类比来阐述特定的诗歌理念。明人又有“以书喻诗”者,此即以书法之理来类比诗歌之理,如王世贞评李攀龙云:“于鳞拟古乐府,无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与古乐府并看,看则似临摹帖耳。”[4]351谢榛《四溟诗话》亦言:“学诗者当如临字之法,若子美‘日出篱东水’,则曰‘月堕竹西峰’;若‘云生舍北泥’,则曰‘云起屋西山’。久而入悟,不假临矣。”[5]46再如清人又有“以棋喻诗”者,《随园诗话》卷十二载:“吴冠山先生言:‘散体文如围棋,易学而难工;骈体文如象棋,难学而易工。’余谓古诗如象棋,近体如围棋。”[6]第九册449袁枚在吴冠山“以棋喻文”的观点上,又进一步“以棋喻诗”。然而,以上除“以禅喻诗”外的种种批评策略,在古典诗学中应用的实例并不多见,也未能形成一种传统。
不过,仍有一种批评策略堪与“以禅喻诗”并提,其在具体诗学批评实践中所呈现出的复杂性及对中国古代文论产生的影响,可以说甚至超过了“以禅喻诗”,此即“以食喻诗”。所谓“以食喻诗”,是指通过饮食的譬喻等来推演出特定诗学理念的批评方法或策略。需说明的是,此处的“喻”并非限于“譬喻”一种,而是如前引张岱年先生所言的“比喻、象征、联想、推类”诸种,如此表述方能与批评史的实际相合。“以食喻诗”的批评方法或策略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陆机《文赋》所言的“遗味”、刘勰《文心雕龙》提出的“繁采寡情,味之必厌”、锺嵘在《诗品》中标举的“滋味”等,皆可视为“以食喻诗”的早期观点。后来,“以食喻诗”批评方法所蕴含的一些审美观念,如“味”等,更是沉淀为中国古典诗学批评的核心理论,而“味”也被古代批评家用以指称代表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作品中最为核心、最为本质的特征,即成为了文学性或诗性的一种代名词,这种影响是“以禅喻诗”等其他批评策略所未能达到的。再者,若将视野放大至世界文学,由于东、西方的古典文学分别是以诗歌和戏剧为主体,在东方衍生出了“以食喻诗”的传统,而在西方也出现了不少“以食喻剧”的言论,如英国批评家威廉·赫斯列特(william Hazlitt)在《英国的喜剧作家》中以调味的盐譬喻富于修辞色彩的戏剧语言——“隽语”:“隽语是调味的盐,而不是食品本身。”[7]下卷40从这种差异来看,“以食喻诗”也突出体现了东方文学批评的特点。
尽管“以食喻诗”的批评策略源远流长、特点鲜明,然综观学界的相关研究,大抵仍呈现出以下几点待完善之处。其一,学界对饮食与诗歌的关系较多关注,饮食诗的研究较为兴盛①近年来学界饮食诗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如孔祥贤:《陆游饮食诗选注》(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年版);曹逸梅:《中唐至宋代诗歌中的南食书写与士人心态》,《文学遗产》,2016年第6期;周斌:《唐代文人宦游视域下的岭南饮食题材诗歌文化表达》,《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刘丽:《宋代饮食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至于饮食与诗学阐释之间的微妙关系,特别是饮食何以能成为一种诗学批评策略之原因的揭示,相关研究则对此涉足较少。其二,亦是最突出的一点,即学界在研究中常将“以食喻诗”与“以味喻诗”混同、纠缠在一起,而未能分辨两者的逻辑层次及其微妙关系,且“以味喻诗”往往最终成为了论述的主体,以至掩盖甚至消解了“以食喻诗”的其他批评路径,尤其是古代诗论中极为丰富的具象化的“以食喻诗”,其特征与价值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揭示,而“味”则成为了人们探讨的主要对象②学界对于“以食喻诗”批评策略的研究,往往集成于对“味”的探讨之中。近年来的相关代表性成果如陈应鸾:《“诗味”论之成因试探》,《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张庆民:《中国古典诗学诗味论探微》,《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杨子江:《“诗味论”的蕴涵与嬗变》,《北方论丛》,2001年第2期;李知:《诗味论中的解释学思想》,《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王秀臣:《“诗味论”溯源》,《社会科学辑刊》,2014年第2期。。其三,相较饮食与诗歌关系研究之繁荣,学界对于饮食与诗学关系之研究本已落寞,且多为宏观的研究,在个案研究方面仍未有专文进行阐发,多集成于相关诗人或学人的研究中,非但零碎而不成体系,且多未能从“以食喻诗”整体的批评传统的视角下对其进行观照。缘此,笔者拟就这一论题作初步的阐发。以期能在“以禅喻诗”之外,再从中国古典诗学批评中钩稽出并构建起“以食喻诗”这一渊源有自、承传有序、体系严密的批评策略,并以此一种视角展现古代诗学批评家的独特理路与创造性思维,从而对当代的诗学批评产生有益的启迪。
二、从苏轼到袁枚
历代运用“以食喻诗”批评方法的学人不计其数①据笔者初步检索,曾发表过“诗味”方面言论的批评家有钟嵘、司空图、欧阳修、梅尧臣、黄庭坚、苏轼、陆游、杨万里、方回、郝经、范德机、杨载、揭傒斯、谢榛、李贽、朱承爵、陆时雍、胡震亨、沈德潜、黄子云、袁枚、吴乔、梅曾亮、朱庭珍、贺贻孙、翁方纲、李重华、乔亿、刘熙载等。。从时代来看,通观历朝“以食喻诗”的批评实践,则未有如宋代和清代之盛者。这大抵是与此二朝的批评家多身兼诗人与学者的双重身份有关,且他们还往往精通饮食之理,长于思辨的批评家们常常创造性地借用饮食来譬喻诗理。从个人来看,正如严羽可视为“以禅喻诗”批评策略的集大成者,这里不妨推举苏轼和袁枚为“以食喻诗”批评策略的集大成者。苏轼和袁枚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身兼诗人、学者、美食家的多重身份,集中亦写作有不少的饮食诗,各自又有食谱类的著述传世,如东坡的《煮鱼法》、袁枚的《随园食单》等。此外,二人皆发表过丰富多样的“以食喻诗”的言论,他们共同将这种批评策略演绎到了极致。
(一)巧于取譬——苏轼“以食喻诗”的批评实践
宋人好为“以食喻诗”。如北宋梅尧臣《依韵和晏相公》诗云:“苦辞未圆熟,刺口剧菱芡。”[8]368他以菱芡的刺口之感来形容未圆熟的苦辞。又如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五载晏殊选诗之轶事:“公风骨清羸,不喜肉食,尤嫌肥羶。每读韦应物诗,爱之曰:‘全没些脂腻气。’故公于文章尤负赏识,集梁《文选》以后迄于唐别为集,选五卷,而诗之选尤精。凡格调猥俗而脂腻者,皆不载也。”[9]47晏殊用“全没些脂腻气”譬喻韦应物等人清俊古雅的诗风。南宋人也发表了许多“以食喻诗”的言论。如杨万里《和李天麟二首·其一》云:“学诗须透脱,信手自孤高……可口端何似,霜螯略带糟。”[10]199霜螯指秋天的蟹,糟是未清带滓的酒,饮酒品蟹乃美妙无穷的享受,杨万里在这里将“透脱”的诗歌比作可口的霜螯与糟酒。又如其于《颐庵诗稿序》中云:“至于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10]3332这里的“荼”指的是茶,诗亦如茶,初尝虽苦而回味愈甘,与北宋人常说的橄榄型诗味类似。
然宋代运用具象化“以食喻诗”的批评方法最为频繁、娴熟和精妙者,当推苏轼。苏轼不仅是位诗人、学者,同时也是一位美食家。其集中诸如《豆粥》《猪肉颂》等饮食诗歌极多,此外他还写有《煮鱼法》《书煮鱼羹》等食谱类著述,相传著名美食“东坡肉”的创制也与其有关。苏轼在《菜羹赋·叙》中亦自云:“东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称家之有无。水陆之味,贫不能致,煮蔓菁、芦菔、荠而食之。其法不用酰酱,而有自然之味,盖易具而常享。”[11]第一册56可见其对饮食烹饪之道有着独到的见解。
熟参饮食之理的苏轼,在诗学批评中也常常能够自如运用“以食喻诗”的批评策略。如其《读孟郊诗二首·其一》云:“夜读孟郊诗……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又似煮蟛(虫越),竟日嚼空螯。”又《其二》云:“有如黄河鱼,出膏以自煮。”[11]第十一册153-154苏轼在诗中用特定的饮食来类比阅读孟郊诗歌的感受。又如其在《评韩柳诗》中谈到:“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中边者,百无一二也。”[11]第九册237这里的“膏”“甜”“甘”“苦”等都是借食物的情状来类比韩柳之诗。又《评杜默诗》云:“吾观杜默豪气,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饱后所发者也。”[11]第九册315苏轼讥讽杜默之诗不过是喝了私酿劣质之酒、吃了瘴死的牛肉之后的狂怪之作。《书黄鲁直诗后二首·其二》评黄庭坚云:“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11]第九册278苏轼在这里并非讥刺,而是在赞赏黄鲁直的诗文,宋人王楙《野客丛书》卷七对此解释道:“诗文比之‘蝤蛑江瑶柱’,岂不谓佳?至言发风动气,不可多食者,谓其言有味,或不免讥评时病,使人动不平之气。乃所以深美之,非讥之也。”[12]76又如苏轼在《凫绎先生诗集序》中推赏颜太初的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11]第二册9,此言其诗文内容充实,有的放矢,如五谷般可以疗饥。再如《石林诗话》卷中载:“近世僧学诗者极多,皆无超然自得之气,往往反拾掇摹效士大夫所残弃。又自作一种僧体,格律尤凡俗,世谓之酸馅气。子瞻有《赠惠通诗》云:‘语带烟霞从古少,气含蔬笋到公无。’尝语人曰:‘愿解蔬笋语否?为无酸馅气也。’闻者无不皆笑。”[13]135苏轼以“蔬笋语”和“酸馅气”类比惠通之诗与其它一些凡俗诗僧作品气格的不同。苏轼这种具象化“以食喻诗”的说辞还有不少,这有效地帮助了人们对其诗歌理念的理解,一些观点(如“枯澹”说)甚至还具备了经典性的意义。
(二)诗食互喻——袁枚“以食喻诗”的批评实践
相较苏轼等宋人,清代的袁枚又将“以食喻诗”的批评策略推进到了新的境界,其“以食喻诗”的批评实践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袁枚首次明确提出了“以食喻诗”的专名。宋人好为“以食喻诗”,但“以食喻诗”这一说法却是由清代的袁枚才正式提出来的,《随园诗话》有云:“孙兴公说曹辅佐:‘如白地光明锦,裁为负版裤,虽边幅颇阔,而全乏剪裁。’宋诗话云:‘郭功甫如二十四味大排筵席,非不华侈,而求其适口者少矣。’一以衣喻文,一以食喻诗,作者俱当录之座右。”[6]第九册446袁枚在这里拈出了宋人郭祥正(字功甫)的批评策略为“以食喻诗”,为这种批评策略确定了专名。
2.袁枚的“以食喻诗”亦以譬喻精当、恰切、巧妙著称。如《随园诗话》云:“味甜自悦口,然甜过则令人呕;味苦自螫口,然微苦恰耐人思。要知甘而能鲜,则不俗矣;苦能回甘,则不厌矣。凡作诗献公卿者,颂扬不如规讽。余有句云:‘厌香焚皂荚,苦腻慕蒿芹。’”[6]第八册251袁枚在这里认为献公卿之诗不应过“甜”,即不应过分谀诵;而应“微苦”,即有所规讽,如此则能“回甘”而使人不厌。又如:“《乡党》云:‘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则不食之矣。’能诗者,其勿为三日后之祭肉乎!”[6]第八册200袁枚在此处通过祭祀之肉过三日的典实,表明了作诗要出新意、去陈言的观点。再如:“凡菱笋、鱼虾,从水中采得,过半个时辰,则色味俱变;其为菱笋、鱼虾之形质,依然尚在,而其天则已失矣。谚云:‘死蛟龙,不若活老鼠。’可悟作诗文之旨。然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作者难,知者尤难。”[6]第十册616袁枚在这里则通过食材的力求新鲜,譬喻作诗文要鲜活、灵动,充满生命力。除《随园诗话》,袁枚在《陶怡云诗序》中也运用了“以食喻诗”的批评策略:“伊尹论百味之本,以水为始。夫水,天下之至无味者也。何以治味者取以为先?盖其清洌然,其淡的然,然后可以调甘毳,加群珍,引之于至鲜,而不病其唐腐。诗之道亦然,性情者源也,词藻者流也。源之不清,流将焉附,迷途乘骥,愈速愈远。此古人所以有清才之重也。”[6]第七册632他通过阐释水之味为“百味之本”的道理,引出了诗人应该首先做到性情的纯正,然后才可以为诗的道理。此外,袁枚还曾模仿托名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①目前学术界倾向于《二十四诗品》为后人托名司空图而作。参见陈尚君、汪涌豪:《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收于傅璇琮、许逸民主编《中国古籍研究》(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39-74页。写了《续诗品》三十二首,其中《澄滓》云:“描诗者多,作诗者少。其故云何?渣滓不少。糟去酒清,肉去洎馈,宁可不吟,不可附会。”[6]第二册455此处借饮食的处理方法说明作诗应当去“渣滓”,即不要刻意模仿、掉书袋,要发挥性灵,自出新意。综合这些观点来看,“以食喻诗”也成为了袁枚阐释其标举的诗学观念——“性灵说”的一种重要批评策略。
3.袁枚真正超越苏轼之处,在于其做到了诗食互喻。作为一位诗人和学者,袁枚能纯熟地运用“以食喻诗”的批评方法来建构自我的诗学体系;作为一位美食家,袁枚还能通过“以诗喻食”来阐明自身对饮食之道的独到理解。譬如其在《随园食单·戒单》中谈到:“唐诗最佳,而五言八韵之试帖,名家不选,何也?以其落套故也。诗尚如此,食亦宜然。今官场之菜,名号有十六碟、八簋、四点心之称,有满汉席之称,有八小吃之称,有十大菜之称,种种俗名皆恶厨陋习。只可用之于新亲上门,上司入境,以此敷衍;配上椅披桌裙,插屏香案,三揖百拜方称。若家居欢宴,文酒开筵,安可用此恶套哉?必须盘碗参差,整散杂进,方有名贵之气象。余家寿筵婚席,动至五六桌者,传唤外厨,亦不免落套,然训练之卒,范我驰驱者,其味亦终竟不同。”[6]第十五册13袁枚在这里通过阐述历代选家多选唐诗而惟独不选唐代试诗的现象,表达了饮食烹饪应该力戒俗套的观念。袁枚诗食互喻,既能“以食喻诗”,也能“以诗喻食”,可谓真正做到了诗理与食理的会通。
三、“以食喻诗”批评策略的主要形态
苏轼和袁枚可谓“以食喻诗”批评策略的集大成者,从二人以及历代大量的具体批评实践来看,“以食喻诗”批评策略演化出了多种不同的批评形态,如正喻式的“以食喻诗”、反喻式的“以食喻诗”“以食别诗”“以食衡诗”等。这些批评形态按逻辑层次的不同又可划分为两层:首先从“喻”的性质来看,正喻式和反喻式的“以食喻诗”为第一层级;再从“喻”的功用来看,正喻式或反喻式的“以食喻诗”又可细分出“以食别诗”“以食衡诗”等情形。
(一)正喻式与反喻式的“以食喻诗”
正喻式的“以食喻诗”是一种最为常见的批评策略,亦即正面、直观地以饮食的若干特性来譬喻诗歌。例如宋人好以橄榄喻诗,欧阳修《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诗云:“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14]75其称赏梅尧臣的诗歌如食橄榄,初食苦涩难嘬,久而真味愈出,令人回味无穷,这是正面的譬喻。这种橄榄型的诗味其实可视作整个宋诗的特点。宋人也以橄榄喻诗者甚多,它如黄庭坚《谢王子予送橄榄》诗云:“方怀味谏轩中果,忽见盒盘橄榄来。想共余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其又自注云:“戎州蔡次律家,轩外有余甘,余名之曰味谏。”[15]278江西诗派二十五法嗣之一的谢薖在《读吕居仁诗》中写到:“浅诗如蜜甜,中边本无二。好诗初无奇,把玩久弥丽。有如庵摩勒,苦尽得甘味。”[16]15764黄庭坚所说的“余甘”“味谏”,谢薖所谓的“庵摩勒”,都是橄榄的别称,可见宋人欣赏和追求的是如橄榄般愈嚼愈有味的诗歌审美类型。另外,缪钺先生曾对唐宋诗之别作了一个精妙的比喻:“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17]31即说明唐诗所呈现出的是一种荔枝型的诗味,而宋诗则是橄榄型的诗味。若结合另一逻辑层级来看,此为一种“以食别诗”的情形,统合起来可称为正喻式的“以食别诗”。再如清代道光年间的京师古文领袖梅曾亮在《太乙舟山房文集叙》中谈到:“见其人而知其心,人之真者也。见其文而知其人,文之真者也。人有缓急刚柔之性,而其文有阴阳动静之殊。譬之查、梨、橘、柚,味不同而各符其名,肖其物。”[18]121梅曾亮通过阐述各种水果性味虽不同而能符其名、肖其物,譬喻作诗文应当求“真”的观点,这也是一种正喻式的“以食别诗”。
在“以食喻诗”的若干种批评形态中,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现象,即饮食中的一些珍馐美味往往不用于正面譬喻优秀的诗歌,相反,它们常用以譬喻劣诗、俗诗,这种饮食与诗歌之间呈现出的反差、错位的审美譬喻,可称之为反喻式的“以食喻诗”。譬如前引《读近人诗》中所用的“蟹螯蛤柱”,陆游就这种异常鲜美的海味譬喻为雕琢艰险的近人诗歌。姚勉也有类似观点,其于《汪古淡诗集序》中谈到:“诗……有道味,有世味。世味今而甘,道味古而淡。今而甘不若古而淡者之味之悠长也。食大羹饮元酒端冕而听琴瑟,虽不如烹龙炰凤之可口,俳忧郑卫之适耳,而饫则厌久则倦矣。淡之味则有余而无穷也。为今之人甘,可也;欲为古之人,其淡乎!惟古则淡,惟淡则古。”[19]卷三七姚勉以为,似“烹龙炰凤”之诗,初食虽可口,然饫则厌倦;未如“大羹元酒”之诗,古淡悠长,味之不尽。结合另一逻辑层级来看,这是一种反喻式的“以食衡诗”。又如袁枚《随园诗话》云:“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者也;生吞活剥,不如一蔬一笋矣。牡丹、芍药,花之至富丽者也;剪彩为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6]第八册22熊掌、豹胎这些珍馐需要经过精心的烹煮才有味道,如果生吞活剥来吃,还不如寻常的蔬笋鲜美可口。袁枚通过饮食之理的类比,意在说明作诗要追求清新鲜活,追求原味,反对过多的修饰。
(二)“以食别诗”与“以食衡诗”
所谓“以食别诗”,是指通过饮食风味、口味的不同,来譬喻诗歌风貌的差别。如明代谢榛《四溟诗话》卷三云:“作诗譬如江南诸郡造酒,皆以曲米为料,酿成则醇味如一。善饮者历历尝之曰:‘此南京酒也,此苏州酒也,此镇江酒也,此金华酒也。’其美虽同,尝之各有甄别,何哉?做手不同故尔。”[5]74此处借用酿酒之人及其手法的不同,说明各家诗歌风格的差异。又如黄庭坚《书陶渊明诗后寄王吉老》论及不同境遇下阅读陶诗的感受:“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如决定无所用智。每观此篇,如渴饮水,如欲寐得啜茗,如饥啖汤饼,今人有能同味者乎?但恐嚼不破耳!”[15]1404这也属于“以食别诗”的一种情况。再如清代吴乔《围炉诗话》卷一载:“问曰:‘诗文之界如何?’答曰:‘意岂有二?意同而所以用之者不同,是以诗文体裁有异耳……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文之措词必副乎意,犹饭之不变米形,啖之则饱也。诗之措词不必副乎意,犹酒之变尽米形,饮之则醉也。文为人事之实用……实则安可措词不达,如饭之实用以养生尽年,不可矫揉而为糟也。”[20]479吴乔通过阐释同出于米的饭与酒的差别,譬喻诗与文的“同而不同”,取譬特为新颖,令人印象深刻,这也是“以食别诗”的一种灵活用法。若结合上一逻辑层级来看,这是一种正喻式的“以食别诗”。
所谓“以食衡诗”,即通过饮食质量、品格的高下来衡裁诗歌的高下。“以食衡诗”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以食别诗”,差别在于“以食衡诗”在区分诗歌风貌的同时,还有衡裁优劣高下的意味。如南宋陆游《读近人诗》云:“琢雕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君看大羹玄酒味,蟹螯蛤柱岂同科?”[21]第八册44陆游在这里以“大羹玄酒”喻古人诗歌,又以“蟹螯蛤柱”作为对立面喻近人诗歌,衡量高下之意显见。所谓“大羹”,是指不用五味调和的肉汁。《礼记·乐记》载:“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郑玄注曰:“大羹,肉湆,不调以盐菜。”[22]1528所谓“玄酒”,是祭祀中作为酒使用的清水。又《礼记·礼运》载:“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户。”孔颖达疏曰:“玄酒,谓水也。以其色黑,谓之玄。而太古无酒,此水当酒所用,故谓之玄酒。”[22]1416可见,“大羹”和“玄酒”都是醇淡自然的饮食,多在祭祀等重要仪式中使用,是献给神明的饮食,品格不可谓不高。古人也多以之譬喻古朴自然、醇淡有味的诗文,如《新唐书·文艺传上·骆宾王》载:“韩休之文如大羹玄酒,有典则,薄滋味。”[23]5743再看“蟹螯蛤柱”,它们本是鲜美的海味,古人视其为珍馐美食,如梅尧臣《吴正仲遗蛤蜊》诗有云:“罇前已夺蟹螯味,当时莼羹枉对人。”[8]746陆游将格外鲜美的“蟹螯蛤柱”与醇淡无味的“大羹玄酒”作对比,表达了他其对“雕琢”“奇险”的近人诗歌的否定与对古朴自然的古人诗歌的尊崇。若从实际的味道来说,作为珍馐的“蟹螯蛤柱”自然要胜过无味的“大羹玄酒”,但陆游在这里用了反喻,结合另一逻辑层级来看,这明显是一种反喻式的“以食衡诗”。又如朱熹《答巩仲至书》云:“夫古人之诗,本岂有意于平淡哉?但对今之狂怪雕锼,神头鬼面,则见其平;对今之肥腻腥臊,酸咸苦涩,则见其淡耳。”[24]3037朱熹以“淡”譬喻古人之诗,而用“肥腻腥臊”“酸咸苦涩”喻今人之诗,表达它对平淡诗风的推崇,同时也具有正面的衡裁之意。
四、“以食喻诗”的学理依据
从宋代到清代,从苏轼到袁枚,“以食喻诗”的批评策略广为批评家所使用,可谓已形成了一种批评的风气,甚至沉淀为了一种批评的传统。那么,这种批评策略的学理依据究竟为何?以下试从文化、文学、美学等维度剖析中国古典诗歌与饮食的多维关系,以期为“以食喻诗”的批评策略寻得学理上的依据。
(一)礼乐文化视域下的诗、食关系
形成于上古时期的礼乐文化,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构成礼乐文化的要素或载体方方面面,诗歌和饮食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两种。诗歌自不必多言,孔子曰:“不能诗,于礼谬。”(《礼记·仲尼燕居》)[22]1614又曰:“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记·孔子闲居》)[22]1616孔子在这里将诗与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后来汉儒们又将其改造为一种具有功利主义诗学色彩的儒家诗教观念,《毛诗大序》云:“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22]270这便赋予了诗歌在礼乐文化体系中的至高地位。与诗歌类似,饮食在中国古代礼乐文化体系中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礼记·礼运》甚至将饮食视为“礼”的起源:“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22]1415不过,这里的饮食主要是指祭祀鬼神的饮食。而且“礼”字的本义也与祭祀的饮食有关,王国维在《观堂集林·释礼》中解释道:“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曲若礼,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25]291除了在祭祀中发挥重要作用,饮食还充当着明确等级秩序的重要手段。譬如据《周礼》载,掌帝王饮食的食官之长——“膳夫”,在六官之首的天官序列中排位前列,在膳夫之下又辖上士2人、中士4人、下士8人、府2人、史4人、胥十有2人、徒百有20人等等。除膳夫外,天官系列中涉及到饮食的官员还有内饔、外饔、兽人、渔人、腊人、食医、酒人、盐人等,各自也下辖一套复杂的机构[22]659-679。若按《周礼》的规定,总共有50种食官负责王室的饮食事务,需配备3,794名人员,这充分体现出饮食是明确社会等级秩序的一种重要手段。同时,饮食也发挥着调和社会关系的作用。据《周礼·春官·宗伯》载,五礼之中的“嘉礼”内容有六,其中饮食之礼为“嘉礼”第一,其云:“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22]760意在以饮食敦睦宗族兄弟。《诗经·小雅·棠棣》诗云:“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22]408此亦是在叙写兄弟聚首饮食,共叙手足之情的场景。又如清代宫廷曾举办四次“千叟宴”[26],宴请各地前来为皇帝祝寿的老者,显然这是清廷以饮食为媒介以笼络人心、调和社会关系的一种政治手段。再如古人还以饮食烹饪之道类比治国之道,如《老子》第六十章曰:“治大国若烹小鲜。”[27]244从上可见,饮食在中国古代礼乐文化体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饮食与诗歌,皆是构成传统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或要素,这也是二者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特定的、独有的关系。
(二)饮食诗与作为诗歌题材的饮食
如若抛开礼乐文化的特定背景不谈,诗与食的关系便可用寻常的关系逻辑来推演。从饮食的角度来看,诗歌是表现饮食以及饮食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诗歌中的一些饮食书写往往亦可视作饮食史料的重要来源,同时诗歌作为一种文艺形式,也可以为饮食活动增添情趣。再从诗歌的角度来看,饮食是诗歌的一种重要的描写对象或题材,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此外,饮食活动或食物本身也可以视作一种触发诗思的外在媒介。这里主要讨论与本文密切相关的饮食诗与作为诗歌题材的饮食。中国诗歌中的饮食书写起源甚早,诗、骚之中就有不少例证,如《诗经·豳风·七月》描写的是平民百姓的饮食:“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22]391颂诗中也有不少关于祭祀饮食的书写,不过《诗经》中的饮食书写主要还是集中在“雅”诗之中,更多反映的是贵族阶层的饮食活动。如《小雅·南嘉有鱼》描写贵族的宴饮场景:“南嘉有鱼,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22]419《大雅·行苇》展示了贵族家宴繁复的烹饪技法:“或献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荐,或燔或炙。嘉肴脾臄,或歌或咢。”[22]534楚辞中的饮食书写亦令人叹为观止,最具代表性的是《招魂》:“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麦,挐黄粱些。大苦咸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陈吴羹些。胹鳖炮羔,有柘浆些。鹄酸臇凫,煎鸿鸧些。露鸡臛蠵,厉而不爽些。粔籹蜜饵,有餦餭些。瑶浆蜜勺,实羽觞些。挫糟冻饮,酎清凉些。华酌既陈,有琼浆些。归来反故室,敬而无妨些。”[28]207-209屈原在这里不吝笔墨地描写楚地的祭祀饮食,另外《大招》中也有类似《招魂》的较大篇幅的饮食书写。汉代乐府诗中的饮食书写不多,《十五从军征》是一例:“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烹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29]336诗人通过饮食来表现底层人民的贫窘生活。不过,总体而言,饮食在早期诗歌中主要还是作为一种配合性的内容,而并未完全成为一种独立的审美表现对象,屈原的《橘颂》勉强可算作一个孤证,但该篇对于橘在饮食功用的书写实涉及不多。诗歌中的饮食书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取得了长足进展,饮食本身也在此际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如谢惠连的《咏螺蚌诗》云:“轻羽不高翔,自用弦网罗。纤鳞惑芳饵,故为钓所加。螺蚌非有心,沉迹在泥沙。文无雕饰用,味非鼎俎和。”[29]1197可以说,“饮食诗”这一诗歌门类是在魏晋时期开始确立的,在这以前饮食只能视为一种从属性、配合性的诗歌题材,不能视为真正的饮食诗,确切的说法应是诗歌中的饮食书写。自魏晋以降,饮食诗的创作日渐繁盛,学界对此已有较为成熟的研究,本文不再赘述。
(三)诗与食深层美学追求的共通性
上述两层关系,充其量只能说明诗与食之间存在着复杂而紧密的联系,实际尚未深入到饮食与诗歌原理关系的层面。但以上两方面仍然是极其重要的,饮食与诗歌的频繁互动,正是触发“以食喻诗”批评策略形成与完善的一个必备前提。不过,“以食喻诗”批评策略的出现,根本上仍有赖于诗与食在深层次美学追求上所存在的共通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定语境中,诗与食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深层的共通关系,中国古典诗歌以“中和之美”为终极追求,而“五味调和”则是中国传统饮食的最终奥义。“中和”思想是汉民族一种独特的价值观,该词首见于《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22]1625喜怒哀乐等情感在未抒发之前,是互相牵制和平衡的,呈现出的是“中”的状态;当其从内心抒发而出,“中”的状态被打破了,但这种破坏又是适度的、节制的,总体上仍呈现出一种和谐的状态,此即“和”。随着儒家话语地位的不断强化,“中和”思想开始全面渗透于人们对宇宙自然、人伦社会、文艺创作的认知与实践。其用以指导诗歌创作,强调感情的抒发要不激不厉,节制而有限度,“文”与“质”要达到调和的状态等。尽管“中和”思想首先是作为一种儒家话语存在的,但也内蕴着一些普适性的美学规律,包括“价值判断上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节制、适度原则;矛盾要素的平衡与调和”等[30]。无论是从儒家的还是普世的视角来看,“中和之美”皆可视为中国古典诗歌的终极美学追求。中国传统的饮食亦以追求“五味调和”为终极的目标。被后人奉为烹饪之祖的伊尹,即以“善均五味”著称,《吕氏春秋·本味》篇载有伊尹调和五味之论云:“凡味之本,水最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时疾时徐,灭腥去臊除膻,必以其胜,无失其理。调合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不能喻。”[31]114-115元代太医忽思慧在《饮膳正要》中也说:“五味调和,饮食口嗜,皆不可多也。”[32]79五味的调和,其实质是要求饮食烹调中各种矛盾要素(原料、调味料等)要达到平衡与和谐的状态,各种要素的配比要遵循节制、适度原则,此正如林语堂先生所云:“中国的全部烹调艺术即依仗调和的手法。”[33]第20卷328袁枚在《随园食单·须知单》中也强调了食物的配合与平衡:“凡一物烹成,必需辅佐。要使清者配清,浓者配浓,柔者配柔,刚者配刚,方有和合之妙。”[6]第十五册2可见,“中和”的审美理想是中国传统的诗歌和饮食的一致追求,也就是说,诗歌创作之理和饮食烹调之理在终极的层面上是共通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定语境中,诗与食在深层次美学追求上的共通关系,为“以食喻诗”的批评策略提供了基本的逻辑前提。
五、“以食喻诗”与“以味喻诗”辨析
以往的研究通常用“以味喻诗”来替代“以食喻诗”,或将两者混同起来,然笔者以为个中仍有厘清的空间和区隔的必要。“以食喻诗”的诗学批评策略,实际上存在着两条不同的逻辑理路,包括具象化的“以食喻诗”和抽象化的“以食喻诗”。所谓具象化的“以食喻诗”,是指借助具体饮食本身个别的、非本质的属性与诗歌进行类比,饮食在这里“形”与“神”俱在,是实实在在、有据可依的“以食喻诗”。而抽象化的“以食喻诗”,则是先从饮食中提炼出“味”这一所有食物共同的、本质的抽象概念,从而代替具象的饮食介入相关的诗学批评,故又可名之为“以味喻诗”。刘勰、钟嵘等早期的观点多属于此种。而具象化的“以食喻诗”,则是从唐代才真正开始兴起的,如《文薮·序》有云:“古风诗,编之文末,俾视之粗俊于口也,亦由食鱼遇鲭,持肉偶馔。”[34]8353皮日休在这里借用“鱼”“肉”与“鲭”“馔”等食物,来譬喻编于正文的赋、铭、赞、论等与编于文后的古风诗在风格方面的差异。“以食喻诗”的这两条基本的逻辑理路,前贤多将其混而为一,实际上,二者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兹析为如下五端。
1.“以味喻诗”是抽象化的“以食喻诗”,从名物的逻辑上来看,其为“以食喻诗”的一个子概念。在具象化的“以食喻诗”中,用以譬喻的饮食,其“形”与“神”皆存留其中,这里的“形”即饮食本身,“神”则是与之相关的各种食理。而抽象化的“以食喻诗”,首先是从各种饮食中提炼出一个抽象的概念——“味”,然后以之替代各种具象的饮食从而介入诗学批评的。“味”的概念本就源起于饮食,随后才逐渐介入了审美的领域之中。在纯粹的抽象化的“以食喻诗”中,用以譬喻的饮食的“形”已经完全无迹可寻了,其“神”(即各种食理)则被集成、融合为“味”这一多元复合的抽象概念来使用。如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陶渊明诗,专以味胜。”[35]33又如刘熙载《艺概·诗概》云:“诗能于易处见工,便觉亲切有味。白香山、陆放翁擅场在此。”[36]215在具象或抽象的层面上而言,“以味喻诗”与“以禅喻诗”实有些相像,“禅”与“味”都是抽象的概念,其模式与“以棋喻诗”“以剧喻诗”等具象化的批评路径有所不同。
2.“以味喻诗”皆超过了具象化的“以食喻诗”。尽管从名物的逻辑上来看,“以味喻诗”是“以食喻诗”的一个子概念,但无论从发生演进之先后、内涵外延之宏细、实际影响之大小而言,“以味喻诗”皆超过了具象化的“以食喻诗”,析出“味”的概念应是“以食喻诗”批评策略的终极走向。承认“以味喻诗”是“以食喻诗”是一个子概念,并非是窄化、矮化“以味喻诗”的地位。从批评史的事实来看,抽象化的“以食喻诗”(“以味喻诗”)发生早于具象化的“以食喻诗”,其内涵、外延及实际影响力等,皆非具象化的“以食喻诗”所能对等或匹敌。“味”这一概念的析出,可以说是“以食喻诗”批评策略的终极旨归。形形色色的饮食、林林总总的食理,全部统合为“味”这一终极的概念,并以之作为整个饮食文化的最高代表,强有力地介入诗学批评之中,从而将中国传统饮食和中国传统诗歌的理想追求有机统一起来。“味”,可谓中国传统饮食文化馈赠给传统诗学批评的最佳礼物,其最终蜕变为了中国传统诗学批评的一个核心的概念,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饮食与文艺存在着良性互动的确证和佳例。
3.相较具象化的“以食喻诗”,抽象化的“以食喻诗”(“以味喻诗”)存在着若干超越性。首先,“味”是从全部饮食及整个饮食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审美概念,所以它几乎可以全盘代表整个饮食及饮食文化。这便意味着,“味”的涵盖面、代表性及其效力皆超过了某种特定饮食或某种特定饮食门类。其次,“味”兼具名词和动词的双重词性,这也意味着“味”的概念具备了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属性:作为名词,“味”可视为所有饮食之味的全体,用于诗学批评则代表了诗歌的某种元素或质性;作为动词,“味”有品尝、体会的意思,是一种主观的行为,从接受、品鉴的角度来谈的,如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这里的“味”即是具有主观性意味的品尝、体会的意思。复次,“味”这一概念又存在着若干的子概念。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五味”可以视作“味”的同义词,《尚书·洪范》所言的“五味”指的是咸、苦、酸、辛、甘[22]188。古人或纯以“味”论诗,或据其所需在“五味”中择取一“味”来论诗,这便赋予了以“味”论诗较大的灵活性与自由度。再次,“味”既可以作为一个中性的词看待,代表所有食物之味的全体,同时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具备价值色彩的语词来看待,其代表着理想的、美好的事物。在某种程度上,“味”具备着褒义的色彩,“味”的价值属性与“至味”“美味”等是一致的,求“味”即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内在追求。以上这些超越性皆是具象化的“以食喻诗”所难以达到的。
4.相较具象化的“以食喻诗”,抽象化的“以食喻诗”(“以味喻诗”)也存在着若干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以“味”论诗存在着思维上的二次转换。“味”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诗学概念或理论通常也是抽象的概念。以一种抽象的概念阐释另一种抽象的概念,在思维上必定会增加一道解构的工序,人们必须首先对“味”在诗学领域中的概念有一定的经验或知识的储备,才能以之类比另一种诗学概念。而具象化的“以食喻诗”,用以譬喻的饮食是具体的、直观的、形象的,故而减少了一道思维转换的工序,接受者理解的难度也随之降低了。“以食喻诗”这一诗学批评策略的初衷,其实就是为了有效帮助受众理解深奥抽象的诗学概念,以降低理解的难度。如若“以味喻诗”拿捏不当,便会让原本玄之又玄、难以索解的诗学概念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反而增加了理解的难度。尽管以“味”论诗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它的超越性仍是主要的。
5.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具象化的“以食喻诗”和抽象化的“以食喻诗”(“以味喻诗”)往往交织使用,两者不能截然分开。如唐代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云:“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酰,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34]8485在这段批评中,抽象的“味”以及饮食的“形”与“神”俱在。这实际上是“以食喻诗”的具象化与抽象化两种路径混而使用的情形,或也可视为“以食喻诗”的第三条批评路径,且具体的例子也极多。两者的经常性交织使用,也充分说明了古代批评家善于统合这两条逻辑理路各自的优缺点,为具体的批评而服务。尽管如此,这仍然没有在实质上突破具象化和抽象化这两条基本的逻辑理路。抽象化的以“味”论诗与具象化的“以食喻诗”互有超越和局限,这也赋予了“以食喻诗”这一诗学批评策略内涵的丰富性和具体操作上的灵活性,同时也为中国古典诗学批评增添了不少的趣味。
综上所述,与“以禅喻诗”等相似,“以食喻诗”亦为中国古典诗学的一种重要批评策略,其渊源有自、承传有序、体系严密,在长期的批评实践中演化出了丰富的形态和复杂的特征,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批评的传统。而其从饮食中所析出的“味”的概念,更是沉淀为中国古典诗学批评的一个核心概念,成为文学性或诗性的一种代名词,从此一意义上来说,这种影响是“以禅喻诗”等其他诗学批评策略所未能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