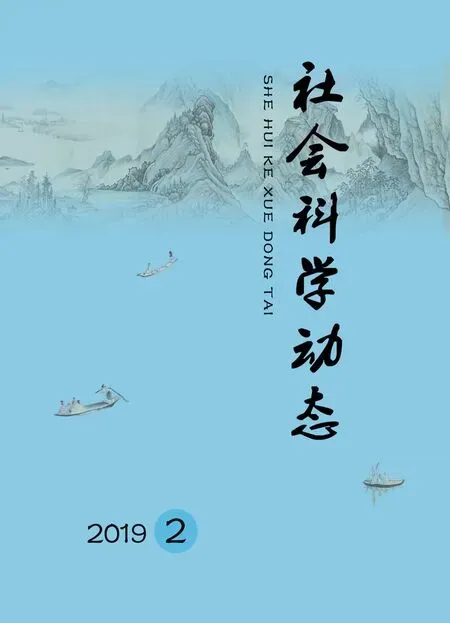展望未来发展动向 共抒新诗研究篇章
——“中国新诗接受史研究(1917—1949)高端论坛”会议纪略
陈柏彤
新诗诞生百年之际,为进一步推进新诗的研究,2018年4月26日,武汉大学举办“中国新诗接受史研究(1917—1949) 高端论坛”。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中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等高校以及《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江汉论坛》、《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等学术期刊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论坛。武汉大学资深教授於可训先生主持开幕式,武汉大学人文社科院院长王培刚教授、文学院院长涂险峰教授分别致辞。
在圆桌讨论环节,诸位学者围绕方长安教授的《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展开学术对话,对新诗传播接受研究的意义、文献资料的发掘与阐释、新诗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创新、传播场域与新旧诗歌之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不仅反思了百年新诗发展历史的局限与问题,且生发出新诗研究领域新的学术增长点。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高旭东教授主持,南京师范大学谭桂林教授评议。
一、传播接受:开拓新诗研究空间
历史地看,新诗的创作发展与传播接受紧密联系,新诗的生成离不开传播场域,读者接受也深刻影响经典塑造与诗学建构。从传播与接受角度研究新诗,为资源日渐匮乏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视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与会学者首先一致肯定了新诗传播接受研究的开拓意义。谢冕教授认为,《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是第一部研究新诗传播接受的著作,为新诗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洪子诚教授表示,过去关于新诗接受的研究零星散布于新诗史、单篇论文或诗人研究中,方长安教授第一次系统梳理了现代新诗接受历史,这是一项具有开拓意义的工作。罗振亚教授指出,该著从读者视角在现代时段的新诗历史中抽取出十余个“个案”,来探讨中国现代新诗的接受史问题,既暗合了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把握是作品、作家、世界、读者四要素合力作用的系统过程理论,是研究资源的拓域和扩容;同时也为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思考维度和新的学术生长点。
从新诗发展来看,传播问题关涉诗歌本身,从这一角度阐释新诗亦具合理性。李怡教授认为,传统诗歌通常发生于圈子唱和,在一定范围内流行后被结集刊印,因此是被经典化后才发生传播;但新诗在诞生之初就进入大众传媒视野,在大范围的传播过程中逐渐被经典化,这种传播形式决定了诗歌的写作形态、诗歌内在及诗歌形式,也形成了“诗歌与时代”“诗歌与社会”“怎么介入五四”等今人讨论新诗的话题,而传播方式的改变从根本上决定了诗歌面貌,新诗的传播接受研究是诗歌内在的研究,方长安教授从事的接受史研究及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17—1949)”为新诗研究扩展了空间。
正是由于新诗传播接受研究的创新与独特,所以无前例可循,缺乏现成资料及理论支持,研究过程面临诸多困难与不便,首当其冲的即是材料搜集问题。於可训教授谈到,读者接受一般分为两个层面:一种是专家的接受,这是一种专门性的接受活动,包括批评、选本、文学史等;另一种则是普通读者的接受,这类接受落脚于社会人群与人心,未能留下固定的文本,也没有物化形式,所以把握起来较为困难。刘川鄂教授从自己的教学经验出发,论及读者审美能力分层的问题,认为一般文学爱好者喜欢的诗歌与专家学者趣味可能有差异,因此读者之间的差异面也值得重视。针对这些问题,有学者提供了丰富读者接受资料的方法和途径。张均教授以当代文学的史料搜集经验为基础,认为报刊上的读者来信,以及已出版或未出版的日记(如《郭小川日记》)等均可作为扩大资料来源的有效渠道。王珂教授也表示,应重视如《黄药眠口述自传》等传统诗学论著之外的边缘性材料。刘保昌研究员则认为,诸如民间刊物、手抄本等局部性、地下性、分散性的材料,往往能够显示出读者真实的阅读兴趣,随着大数据统计时代的到来,这类材料的搜集问题或许能够逐步得到解决。
二、扎实精准:新诗传播接受文献资料的发掘与阐释
诗歌史研究的突破固然与方法思路的革新密切相关,但最主要还是依赖于新的资料的发掘、整理和解读,只有这样才会使学术研究走向科学化。在肯定新诗传播接受研究角度的突破意义之余,与会学者亦围绕文献资料的搜集和阐释问题,进行深入交流。
随着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文献数量越来越多,形式也日趋专门化、复杂化,为保证研究成果的客观合理,必须重视材料搜集的可靠性和系统性。一方面,要关注文献的来源问题和复杂面貌。罗振亚教授表示,新诗传播接受资料的抢救本身就呈现了历史事实的丰富性,因而必须强调对一手材料的整理。易彬教授进一步谈到,对文献资料自身的版本变迁和历史发展,也要给予充分辨析。另一方面,新诗传播场域不断变动,读者接受形式多元,因而从共时和历时的维度出发,史料搜集也需要重视全面性和系统性。张均教授认为,方长安教授的接受史研究以经典化为主要内容,在共时维度上清理选本、批评和文学史著三种样态与新诗经典形成的现象,在历时维度上兼涉启蒙、左翼、革命、新启蒙等话语变迁,其双重线索为接受史研究提供了思路启发。洪子诚教授提出,由于文本与阐释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因此不应忽视对政治背景、文化潮流、外来影响以及媒介方式与特点等方面的考察。
史料的全面可靠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条件。那么,在占有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如何对其进行择取、整合、分析与阐释?探讨新诗传播接受文献资料的研究方法,也是众位学者讨论的兴趣所在。
首先,运用技术手段进行实证分析,坚持论从史出的研究态度。刘为钦教授认为,单独一位诗人或一部作品的传播接受即能汇集成一部厚重之书,要使个案研究落实于新诗接受史范畴,就必须对海量信息进行提炼,量化统计是有效辅助手段。罗振亚教授举例指出,在《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一书中,著者多次运用统计学方法,对《尝试集》41首诗作入选各种诗歌选本的情况、1920—1970年代选本收录郭沫若诗作情况等进行统计,其间的缜密与严谨令人信服,强化了著作的可信度。刘保昌研究员表示,这种以精准数据为分析基础的方式,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方法论意味。
其次,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勾连新诗发展的重要环节,使接受史的呈现既具史料的完整性,又具学理的思辨性。王泽龙教授认为,方长安教授的研究从郭沫若接受史与自由体新诗合法性、李金发接受史与现代主义审美意识的生成、七月派接受史与政治和诗学的对话等不同侧面出发,对经典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展开研究,不仅避免了交叉重复,还达到互证的效果。刘为钦教授认为这种方法避免了平铺直叙地铺排,清晰地描述了现代新诗接受史的过程,为解决从个例到整体、由点及面的问题提供了模式和方法。
在一部接受史的述史要求中,不应仅仅是大量诗人、诗派、文本等接受现象的还原,还应具有理论思考上的创新色彩,即超越于接受现象之上的逻辑认知和提升。张洁教授指出,新诗传播接受研究的基本方法属于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话题,同时还涉及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多种理论背景。罗振亚教授认为,方长安教授在《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的导论和第十三章中深入考辨了传播和新诗生成、现代化特别是经典化之间的关系,显示了论者介入新诗接受问题的研究路径;同时,著者对批评、选本、文学史著作在新诗经典化过程中合作又分离的结构形态把握,对被普遍认可的经典的质疑,对非文学因素参与经典化历程的拷问,对伪经典的评说等等,都属于独特的思考结果。其中,有很多判断看到了对象的根髓,鞭辟入里,对诗歌史的改写也不无冲击和启发。
三、“诗的精神”:新诗研究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突破性学术视角、独特的统筹思路、扎实的研究方法、创新的理论话语,方长安教授的《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为新诗传播接受研究提供了新方法,打开了新局面。一个学术方向的开拓离不开对学科传统的继承,由此,众位学者追溯了武汉大学新诗研究传统,肯定了武大三代学人在新诗研究中一以贯之的研究精神与方法态度。
对新诗研究传统的继承,主要体现为深厚的诗歌研究功底、精准到位的择史眼光和不懈探索的学术精神。谢冕和洪子诚两位教授一致认为,《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诗歌研究功底。这部著作中所选的诗人和作品都是新诗传播与接受历史上具有代表性并且能让论者有话可说的现象,比如诗人有何其芳、卞之琳、冯至、李金发、戴望舒、徐志摩等,作品有《尝试集》、《凤凰涅槃》和《女神》等,其选择的结果体现了作者以精准的眼光把握诗歌发展规律的深厚学养。高玉教授表示,此著在理论、材料和话语方式上处理到位,可见方教授很好地继承了陆耀东和龙泉明两位先生的衣钵。何锡章教授则从刘永济先生、程千帆先生开创的古典诗词研究传统与陆耀东先生、龙泉明先生到方长安教授所承传的新诗研究传统两个脉络出发,追溯了武汉大学在诗词领域研究中薪火相传的历程,认为武汉大学在诗词研究领域具有真正的传统。於可训教授更是深情讲述了与陆耀东先生的学术交往,回顾了其《中国新诗史》从立项到出版的艰难过程,认为正是这种对学术研究坚韧不移的“诗的精神”,深深激励着几代学人在新诗领域持续耕耘。
学术方法和学术精神的传承固然重要,但其进步之处更在于创新。陈国恩教授从武大新诗研究的论著代继中阐述了新诗传播接受研究在传承中的进步意义,如陆耀东先生的《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对诗美的发掘有独到之处,龙泉明先生的《中国新诗流变论》侧重于对新诗流变关系的梳理和新诗现象的综合性研究,方长安教授则将传播接受之学纳入新诗研究中,凸显了武大新诗研究的新特点,这在国内新诗研究领域中也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四、新诗与旧诗:诗歌研究的一体两面
长期以来,以新诗标准非难旧诗,或以旧诗规范否定新诗,是诗歌创作和研究的突出现象。虽然新诗与旧诗分属不同的诗歌审美系统,在诗体上也有本质区别,但新诗的发展历史始终与旧诗相伴而行。在新诗传播与接受讨论的启发下,与会学者不仅重新思考了新诗与旧诗的对立关系,且生发出许多精彩学术话题。
一方面,将旧体诗歌作为参照,通过旧诗在传播当中的遭遇反观新诗的命运,发现新问题和新思路。高旭东教授谈到,以《沁园春·雪》这首旧体诗为例,其发表时仅重庆方面就出现二十余首和诗、三四十篇评论,它的影响远超于《凤凰涅槃》、《再别康桥》等新诗作品。在整个现代时段,就事实而言,还是旧诗的传播较为广泛。李怡教授表示,新诗和旧诗一直存在争夺传播空间的问题。五四前后,现代传媒手段首先给旧体诗词提供了一个现代传播的可能性和空间,但新诗却在后来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就当下诗歌创作整体而言,旧诗作者远多于新诗作者,但旧诗的影响在今天却被压缩到有限的范围之内。在这种新诗和旧诗传播空间彼此的消长中,可以看到中国诗歌的生态,由此也能够带来新话题。
另一方面,重新思考新旧诗歌在以往阐释体系中的对立关系,促使新旧诗歌研究从替代到统一的思维方式发生转变。姜涛副教授认为,20世纪新诗史研究长期将新诗与旧诗看作论辩的线性关系,事实上新旧诗歌的社会位置、文化空间、传播方式、文化功能和文体性格均有所不同,不仅不能简单比较,还要在共时框架中去理解,并以整体文化结构的视野对之进行把握。陈国恩教授表示,在考虑新诗传播接受时,应避免跟旧体诗词的对立,应从融合的角度去看待新旧诗歌在表现诗美本体、运用诗化语言等方面的经验。王泽龙教授提到古代白话传统对现代诗歌语言和形式等方面的深刻影响。由此话题的讨论出发,李遇春教授表示,以新诗传播接受研究对照旧诗发展的思路,对自己从事旧体诗词研究具有很大启发。
新诗与旧诗是会议研讨焦点问题之一,与此同时,众学者还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新话题,为未来新诗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向度。首先,从接受对象来看,在现有的重要诗人诗作之外,应关注非热点的诗人和诗歌现象。谢冕教授谈到,对工农兵方向的诗歌创作,以及《王贵与李香香》和《漳河水》等诗歌的传播等问题还能进行更深入地讨论。洪子诚教授赞同地表示,在诗歌接受史的研究中,有必要涉及一些数量不怎么重要、但在文化史上具有重要作用的诗歌现象。其次,从接受范围来看,不少学者认为对中国新诗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以及当代诗歌的传播接受也应及时予以关注。罗振亚教授认为,《中国新诗(1917—1949) 接受史研究》对资料的搜求已相当广泛,如若把域外接受维度的材料补足,会更加具有说服力。吴投文教授提出,可将研究视点转移至当代诗歌的传播,以构成对中国百年新诗传播的宏大把握。最后,从接受理论来看,也有许多可拓展的研究空间。何锡章教授期待加强宏观性研究和理论拓展,为新诗的发生与传播构建坚实的理论基础,使之能够为当代诗歌的发展提供启示意义。张洁教授也指出,如果能将后现代的述史观纳入新诗传播接受研究,或许会扩展新诗接受的描述范围。
会议由谭桂林教授做总结发言,这次会议集聚国内新诗研究领域的前沿学者,集中深入地讨论了新诗研究的热点话题,不仅分析了新诗研究现状,还展望了新诗未来发展动向,是新诗研究史上的精彩篇章。
——旧诗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