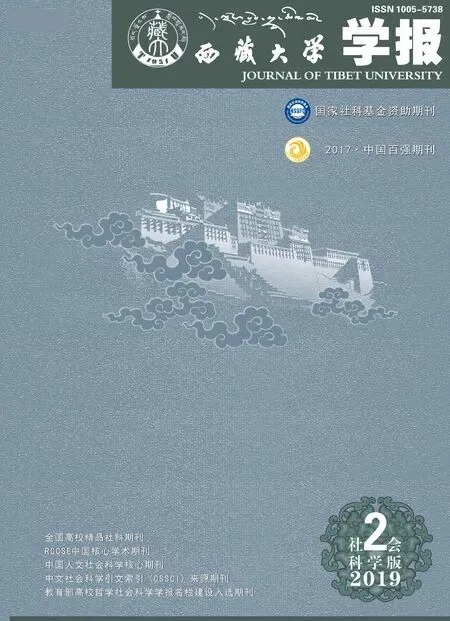论明清鼎革对西藏的影响
周燕
(西藏大学文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
1644年4月,清军入关,定鼎北京,成为中国历史上新的大一统王朝。明清鼎革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政权更替,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和持久的影响。明清鼎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西藏社会发展的影响尤其重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明清鼎革对格鲁派影响巨大
(一)明清鼎革为格鲁派优势宗教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契机
格鲁派是藏传佛教中的新兴教派,由宗喀巴大师于十五世纪初创立。因为西藏地方帕竹政权的支持和明朝中央政府“多封众建”政策的影响,格鲁派迅速崛起,成为与传统萨迦派、噶举派影响相当的重要教派。但到明朝后期,格鲁派却是危机频频,举步维艰。因为明朝的“多封众建”虽然基本实现“西陲宴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1]的政治意图,却在西藏地方造成宗教多元和政治多中心的格局。在明朝强大之时,还能有效制衡各政教势力的矛盾和冲突,而到了明朝后期,由于内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东北边疆女真人强势崛起后,明朝中央政府自顾不暇,对西藏地方的统治日趋衰弱,西藏地方的政教纷争冲突不断。特别是1618年藏巴汗政权取代帕竹政权后,因藏巴汗彭措南杰崇奉噶玛噶举派,开始不断打击格鲁派。直到1642年,借助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的帮助,格鲁派才将其政教对手彻底打败。固始汗控制了西藏地方军政大权,将宗教大权奉送给五世达赖喇嘛,并下令以西藏地方十三万户作供养,建立和硕特部与格鲁派政教分治的蒙藏联合政权,格鲁派也第一次获得在西藏的宗教优势地位。
但是,新生的蒙藏联合政权如何获得合法性却是问题。此时的明朝中央政府已似大厦将倾,显然无法满足格鲁派与和硕特部的要求。实际上,在明清鼎革前夕,格鲁派就曾希望获得正在迅速崛起的清政权的支持,并在1640年派伊拉古三胡图克图等人前往盛京。1642年,伊拉古三胡图可图等人到达盛京,受到皇太极高规格的接待和款待,但此时的清政权只是一个地方性政权,对千里之遥的西藏政教之争并无意卷入。所以,在1643年使节返藏时候,皇太极派察干格隆、巴喇衮噶尔格隆等蒙古喇嘛作为自己的使者,随行赴藏。因为对西藏地方政局的情况并不太清楚,皇太极分别致书达赖喇嘛、班禅呼图克图、噶玛噶举派活佛、藏巴汗和固始汗等西藏僧俗权贵,对他们的态度并未有特别区分。甚至在致固始汗的书信中明确宣称,要向西藏延请高僧,“不分服色红黄①清朝对藏传佛教各派的简单区分。对戴黄帽的格鲁派称黄教,戴红帽的萨迦派、宁玛派、噶玛噶举及其他藏传佛教泛称红教。,随处谘访,以宏佛教,以护国祚。”[2]
明清鼎革为蒙藏联合政权获得合法性提供了契机。1644年,当得知顺治皇帝在北京即位的消息后,五世达赖喇嘛“便派乌巴什科雅台吉去敬献祝贺的信件及方物”[3],并遣使朝贡清朝中央政府;固始汗也多次与其他蒙古王公联合向清廷建议延请五世达赖喇嘛进京。而清政权从地方性政权到全国性政权的嬗变也促使其改变对西藏地方的态度。对清王朝而言,如何用最小的代价统一西藏地方是最重要的政治目的。因此,藉着鼎革前夕皇太极对西藏高僧的延请和西藏政教势力的积极示好,清王朝多次遣使“存问”固始汗和五世达赖喇嘛,并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进京。
顺治九年(1652年)12月,五世达赖喇嘛在北京觐见顺治皇帝。顺治十年(1653年)4月,清廷正式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同时册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4]于是,清王朝以和平的方式将西藏地方纳入其大一统疆域的版图,并正式确立达赖喇嘛在藏传佛教中的领袖地位和独尊格鲁派的政策,为格鲁派在西藏的优势宗教地位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
(二)明清鼎革后,清王朝的支持和有效治理固化格鲁派的优势政教地位
清王朝在西藏独尊格鲁派的政策对格鲁派意义重大。因为蒙藏联合政权很快就出现矛盾。1654年固始汗病逝,蒙(和硕特部)藏之间的矛盾开始不断显现。虽然格鲁派在蒙藏之争初期不断侵蚀和削弱和硕特汗王的政治权力,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和硕特部与格鲁派两败俱伤。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蒙古准噶尔部首领策旺阿拉布坦趁蒙藏之争派兵侵入拉萨,杀掉拉藏汗,西藏政局出现严重危机。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和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康熙皇帝趁机派清军两次入藏,成功驱逐了拉萨的准噶尔军队,并果断终止了蒙古和硕特部在西藏的统治,建立了以西藏世俗贵族为主体的噶伦制。格鲁派则因蒙藏之争先后出现了三个六世达赖喇嘛,真伪六世达赖喇嘛之争不仅导致达赖喇嘛世系混乱,也黯淡了达赖喇嘛的神圣光环。雍正六年(1728年),清政府又因噶伦之争将第三位六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后被乾隆皇帝默认为七世达赖喇嘛)移居四川理塘惠远庙,远离西藏政教中心,格鲁派的政教影响一落千丈。
但是清王朝并未改变独尊格鲁派的政策。虽然在蒙藏之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清王朝对双方都没有明显的偏向,但却利用蒙藏之争,不断改造格鲁派,使其更加符合清王朝的统治需求。清初对格鲁派的改造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达赖喇嘛宗教权威的限制。达赖喇嘛名号本是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赠给格鲁派大喇嘛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简称。在明清鼎革前,达赖喇嘛与班禅胡图克图、甘丹赤巴在格鲁派内部具有同等重要地位。顺治皇帝对五世达赖喇嘛的册封不仅确立了达赖喇嘛在藏传佛教界的宗教领袖地位,也确立其在格鲁派中的最高地位。但是,清王朝给予达赖喇嘛“所领天下释教”的权力范围太广,除西藏外,蒙古、甘肃、青海、新疆、四川等地格鲁派的信徒众多,达赖喇嘛宗教领袖地位无疑会对这些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随着蒙藏之争初期五世达赖喇嘛权势的不断膨胀,特别是五世达赖喇嘛与吴三桂、噶尔丹等反清势力有所交往时,清统治者对五世达赖喇嘛的权势开始警醒。为了削弱和限制达赖喇嘛的权威,康熙皇帝不断在格鲁派内部推行多元分封。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清廷以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率领喀尔喀蒙古内附有功,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大喇嘛”,“于喀尔喀地方立为库伦,广演黄教”[5],负责漠北蒙古的格鲁派。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清廷封青海佑宁寺二世章嘉活佛为扎萨克达喇嘛,常驻北京,成为皇室最重要的宗教顾问;而后,二世章嘉活佛又被册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并驻庙多伦诺尔,负责漠南蒙古格鲁派。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皇帝又提升班禅地位,称“班禅胡土克图,为人安静,熟谙经典,勤修职贡,初终不倦,甚属可嘉。著照封达赖喇嘛之例,给以印册,封为班禅额尔德尼”[6],负责后藏地区。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和章嘉大国师四大活佛并存并分区管理的局面有效限制了达赖喇嘛的权威,避免了超级宗教领袖的出现。而且,由于四大活佛之间因“转世”而存在的特殊师徒关系,也使得格鲁派内部矛盾具有较好的协调机制,有利于格鲁派的稳定发展。
清王朝改造的另一方面是依法规范格鲁派。清初对格鲁派优势地位的确认并非清统治者的主观喜好,而是对明末西藏政教斗争结果的客观承认。实际上,清统治者对蒙古人崇信藏传佛教的弊病心知肚明。皇太极曾言“蒙古诸贝勒自弃梦古之语,俱学喇嘛,卒致国运衰微。”[7]康熙皇帝也批评“蒙古惑于喇嘛,罄其家赀不知顾惜,此皆愚人偏信祸福之说,而不知道其终无益也。”[8]而且蒙古统治者独尊萨迦派,致使一些萨迦派僧人“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9]这样的独尊在实践中既无益于萨迦派的发展,也无益于西藏地方的稳定。为了防范格鲁派重蹈萨迦派覆辙,清统治者一开始就注重依法惩处格鲁派的违法僧侣。正如康熙所言,“朕钦崇佛教,总持道法,但皈道法之人则嘉之,悖道法之人则惩之。”[10]如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因济隆胡图克图支持和参与噶尔丹叛乱事发,虽第巴桑杰嘉措以五世达赖喇嘛名义多次向康熙皇帝请求宽宥,康熙皇帝不许,称“凡奉使行人,不悖旨而成事,则赏以劝之,违旨而败事,则罚以惩之,国家一定之大法也。”[11]并将济隆胡图克图押赴京城看守。康熙三十六年(1697),丹巴色尔济、阿齐图格隆、巴咱尔喇木札木巴等大喇嘛奉命前往西藏查证五世达赖喇嘛是否仍健在,但是他们“乃知其已故,而谓之尚在,通同第巴诳奏”,康熙皇帝下令予以严惩,“丹巴色尔济从宽免死,革去住持大喇嘛,抄没家产,单身发往盛京,任栖一庙。阿齐图格隆,各处差遣效力,从宽免死并抄没,革去住持大喇嘛,准住其本庙。巴咱尔喇木札木巴亦从宽免死,并抄没,革去大喇嘛。”[12]
清初对格鲁派既尊崇优渥,又依法惩处的做法一直延续到清末。清王朝制定的《理藩院则例》《大清会典》《大清律例》《大清会典事例》中记载了大量处理藏传佛教事务的事例和规定,成为清朝依法治理藏传佛教的重要根据。
乾隆十五年(1750)十月,西藏郡王珠尔默特纳木扎勒因性格乖张,肆意妄为,被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诛杀,郡王制随之被废除,西藏贵族执政的短暂黄金时代宣告结束,格鲁派被清廷重新重用。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廷颁布《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将部分治藏行政权力赋予七世达赖喇嘛,建立政教合一政权,为格鲁派固化其宗教优势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但是权力容易滋生腐败,随着格鲁派权势的增强,其最根本的活佛转世制度弊病丛生。无论是通过各种“灵异”现象选择,还是“人神”兼任的护法神指认,活佛转世都充斥着舞弊和弄虚作假,就连三世土观活佛也批评称:“种种弊端如同妓女的舞步,花样翻新,不胜枚举。”[13]宗教事务的利益化倾向明显,直接导致各大活佛之间“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现象蔓延。[14]这些弊病既是对格鲁派活佛神圣性的损伤,同样也为世家大族膨胀势力和政教纷争埋下祸端。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和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王朝利用平定廓尔喀入侵西藏之机,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以下简称《二十九条》)。《二十九条》是清王朝对治藏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它极大地加强了清王朝对格鲁派内部宗教事务的管理权和监督权。如活佛转世需要驻藏大臣参与并通过金瓶掣签制度认定(第1条);寺院及僧尼数目需要向驻藏大臣衙门备案(第22条);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商上的财务收支每年春秋二季报驻藏大臣审核(第8条);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在世期间,其亲族不准任公职(第12条);各大寺院堪布应由达赖喇嘛、驻藏大臣及济咙胡图克图三人酌商遴选任命(第18条);甚至连寺院僧侣的俸禄也详加规定:“活佛及僧众之合法俸银,自应按期发放,不得提前支领”(第28条)。[15]
西藏是一个宗教影响极度广泛和深入的地方,不能有效治理宗教,就很难有效治理西藏。清政府通过对格鲁派的支持和不断有效改造,既固化了格鲁派的优势政教地位,同时又牢固地掌控了格鲁派,使其成为清王朝治理蒙藏地区的重要精神工具,有效维护了清王朝的统一和西藏社会的长期稳定。而格鲁派优势地位的固化也形成一个势力强大和影响力广泛的格鲁派寺院集团,对西藏社会的消极影响同样巨大。在政教合一制度下,西藏地方政治保守、经济落后、文化单一、人口增殖几乎停滞,有的消极影响至今仍在。
二、明清鼎革改变了蒙藏关系在西藏的发展趋势
蒙藏关系的密切始于元朝,由于1247年萨迦班智达与阔端凉州会谈,西藏地方被正式纳入元朝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藏传佛教也因此在蒙古人中大肆传播,并逐渐成为蒙古人的主要信仰。元明鼎革后,虽然蒙古人丧失了对西藏地方的行政管辖权,但并未改变对藏传佛教的信仰,萨迦派、噶举派、觉囊派及格鲁派都在蒙古地区流行,家家户户供奉神像,对大喇嘛“尊之若神明,亲之若考妣。”[16]由于明末明朝中央政府对西北边疆地区统治乏力,导致一些蒙古部族不断向青藏高原迁移。蒙藏特殊的宗教关系使一些蒙古部族不断卷入西藏内部的政教纷争,蒙藏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蒙古对西藏地方政教的影响力强势回升。最典型的事件体现在四世达赖喇嘛身上。
1588年,三世达赖喇嘛在蒙古圆寂,格鲁派很快选择了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的曾孙为转世灵童,即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加措(1589-1616)。之所以选择云丹加措,除了宗教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原因,即格鲁派希望借助蒙古人的势力发展壮大自己。五世达赖喇嘛坦言:“像雪域西藏这样的地方,最初也难以仅用佛法进行教化,必须依靠政治的方法,这在蒙古也是同样,因此达赖喇嘛会在蒙古王族中降生。”[17]四世达赖喇嘛转生于蒙古,也成为蒙古势力介入西藏政教纷争最有力的依据。1603年,蒙古王公护送四世达赖喇嘛到拉萨坐床。
1616年,27岁的四世达赖喇嘛突然圆寂,藏巴汗彭措南杰甚至“疑达赖诅咒,致感多病,即明令不许达赖再世。”[18]格鲁派面临严重危机,派人向蒙古王公求援。1617年,蒙古喀尔喀部派兵赴拉萨,与支持格鲁派的拉萨中小贵族共同进攻藏巴汗,但却被藏巴汗军队打败,卫藏地区大量格鲁派的寺院、寺产都被藏巴汗侵占(包括色拉寺和哲蚌寺),格鲁派处境更加危险。格鲁派再次向蒙古王公求援。1621年,蒙古土默特部派兵赴拉萨打败藏巴汗的军队,并迫使藏巴汗政权归还所侵占的格鲁派寺院和寺产。1622年,阿旺·罗桑嘉措被顺利认定为五世达赖喇嘛,暂时化解了格鲁派的燃眉之急,土默特军队也返回青海。
但是,蒙古人走后,新即位的藏巴汗丹迥旺布更加疯狂地镇压格鲁派。为了彻底消灭格鲁派,丹迥旺布与青海蒙古喀尔喀部的却图汗及康区的白利土司顿月多吉联合。在三方势力的围攻下,支持格鲁派的西藏地方贵族被打败,格鲁派又一次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格鲁派再次向蒙古王公求援,而正有心往青藏高原扩张势力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慨然应允出兵帮助格鲁派挽救危局。固始汗军队的加入使西藏地方政教纷争的态势迅速逆转。藏巴汗与却图汗、白利土司的联盟很快被打败,固始汗控制了青海、康区和西藏,彻底消灭了格鲁派的政教劲敌,并与格鲁派在西藏建立蒙藏联合政权,蒙藏关系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蒙古势力开始强势主导西藏地方政务。
但是,明清鼎革对蒙藏关系在西藏的发展趋势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清鼎革后,清王朝迅速与西藏确立了中央与地方的隶属关系。虽然清王朝暂时承认和硕特部与格鲁派联合治藏,但蒙古汗王的统治无疑是清王朝与西藏地方之间的一个楔子,这样的蒙藏关系在西藏很难持久。实际上,蒙藏之间的矛盾在固始汗病逝后便迅速显现出来。蒙古汗王的权力不断被削弱,而以五世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寺院集团势力则不断膨胀。正如著名藏学家杜齐所言:“固始汗的去世和其子孙的继位倒使达赖系统进入一个更繁荣的时期。达赖喇嘛的权势登峰造极。”[19]特别是五世达赖喇嘛在1679年任命桑杰嘉措为第巴后,和硕特汗王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弱。
桑杰嘉措(1653—1705)是五世达赖喇嘛的亲信,也是西藏贵族精英的代表,担任第巴时年仅27岁。桑杰嘉措深受五世达赖喇嘛宠信,五世达赖喇嘛甚至公开命令:“于教法与世俗之务,他(桑杰嘉措)之所为皆与我毫无区别。众人不得怀疑而议论,皆需果决听命。”[20]而桑杰嘉措执掌第巴之权时,适值蒙古汗王达赖汗在位。达赖汗虽然在位时间较长(1671-1701年),但性格软弱,桑杰嘉措可以随心所欲。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圆寂,桑杰嘉措隐匿不报。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十二月,桑杰嘉措以五世达赖喇嘛名义上书清廷为自己请封。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四月,清廷封桑杰嘉措为“掌瓦赤喇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王布忒达阿白迪。”桑杰嘉措假达赖喇嘛之名长期执掌政教大权,而且,为了增强自己的势力,桑杰嘉措还与蒙古准噶尔部的噶尔丹暗地勾结。
1701年,达赖汗去世。其子拉藏汗经过激烈竞争,于1703年即西藏汗王位。年轻的拉藏汗雄心勃勃,冀图重振和硕特部对西藏地方的控制,与桑杰嘉措之间的斗争不可避免。二人之间的明争暗斗越演越烈。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桑杰嘉措发动兵变失败被拉藏汗所杀。为了巩固统治,清除桑杰嘉措的影响,拉藏汗轻率地上奏清廷,废黜了桑杰嘉措所选立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并将其押解赴京,而新立益西嘉措为达赖喇嘛。虽然拉藏汗的做法得到清王朝的支持,但此举不仅遭到拉萨格鲁派多数僧侣的强烈反对,在青海蒙古王公内部也遭遇激烈反对。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仓央嘉措在押解赴京途中圆寂,青海蒙古王公和拉萨三大寺很快认定四川理塘出生的格桑嘉措为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蒙藏之争不仅没有停息,反而因为真假达赖喇嘛之争越演越烈,新疆准噶尔蒙古势力也趁势介入,西藏地方局势更加动荡和混乱。
清王朝是蒙藏之争最大的赢家,它通过蒙藏之争不仅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同时改变了蒙藏关系的发展趋势。清王朝对蒙藏之争采取了内外有别的措施。对西藏内部的蒙藏之争,清王朝并无偏袒,而只是支持纷争中有利的一方。三个六世达赖喇嘛的册封就是最明显的例证。虽然康熙皇帝最初对桑杰嘉措隐匿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并私自立仓央嘉措耿耿于怀。但因为此时桑杰嘉措在蒙藏之争中占优势,所以事发后康熙皇帝还是正式册封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对此,康熙皇帝解释称:“自古以来,好勤远略者,国家元气罔不亏损,是以朕意惟以不生事为贵。……第巴既如此奏恳,事亦可行。即此可以宽宥其罪,允其所请。”[21]而当桑杰嘉措被杀,蒙藏之争有利于和硕特部时,清王朝又接受了拉藏汗请求,重新册封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当拉藏汗被准噶尔军队杀害,和硕特部在西藏的势力受到重创时,康熙皇帝又同意青海王公和西藏僧俗的要求,承认格桑嘉措是达赖喇嘛的转世。清王朝这种貌似公允的态度使西藏内部的蒙古和硕特部与格鲁派相互内耗,为清王朝调整治藏政策创造了机会。
相反,清王朝对西藏外部的蒙藏关系发展却态度鲜明,既不允许西藏地方的政教势力介入藏外的蒙古事务,也反对西藏以外的蒙古势力干涉西藏事务。如康熙十九(1680年),理藩院奏称喀尔喀蒙古进贡,但因为以前负责进贡的车臣济龙被革职,而以厄尔德尼济农为首进贡,因达赖喇嘛所给的文书内并无以厄尔德尼济农为首的记载,询问是否接受其贡物。康熙皇帝称:“外藩蒙古头目进贡,其物应否收纳,理应即行议定,何必据达赖喇嘛文之有无?若必据此为贡,似在我疆内之外藩蒙古惟达赖喇嘛之言是听亦。以后蒙古进物,应否收纳,著该衙门即定议具奏,不必以达赖喇嘛之文为据。”[22]
康熙三十四年(1695)四月理藩院题:“达赖喇嘛及第巴皆谴使奏请勿革噶尔丹、策妄阿喇布坦汗号,并加恩赐敕印;其西海等处一带地方所置戍兵,请撤回。”康熙皇帝斥责称“第巴乃外藩人,何敢奏请撤我朝兵戍?”[23]
当拉藏汗之子与准噶尔策旺阿拉布坦之女联姻,康熙皇帝也多次提醒拉藏汗要多加提防,称“倘或事出不测,朕虽怜伊,伊虽倚朕,此间地方甚远,相隔万里,救之不及,事后徒贻悔耳,即朕亦无法也。朕此想甚属远大,伊亦系晓事之人,若不深谋防范,断乎不可,朕为拉藏汗时常留意。”[24]
当准噶尔军队占领拉萨后,清王朝又果断出兵西藏平准,并趁机终止蒙古和硕特汗王在西藏的统治,成功拔除了清王朝治藏的楔子。
青海和硕特亲王罗布藏丹津(固始汗孙子)曾随清军入藏,并妄图延续和硕特蒙古贵族在西藏的统治,遭到清康熙皇帝的拒绝。雍正元年(1723年),罗布藏丹津在青海策动叛乱,雍正皇帝命年羹尧、岳钟琪率兵镇压。雍正二年(1724年),罗布藏丹津兵败,清政府颁布《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加强了对青海地区的直接控制,阻隔了蒙古部族进入西藏最主要的通道,彻底铲除和硕特蒙古及其他蒙古部族重返西藏的可能,明末以来蒙古势力向青藏高原腹地发展,并主导西藏政局的趋势被终结。从此以后,蒙古各部在西藏的影响力急剧下降。相反,西藏(尤其是格鲁派)对蒙古的影响力却持久深远。这主要是清王朝对格鲁派的成功治理,使其成为统治蒙藏地区重要的精神工具。而清王朝在蒙古推崇格鲁派的政治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希望利用格鲁派对蒙古人“劝导善行”,“以慈悲销杀伐,以因果导犷狠”,从而达到“以黄教柔顺蒙古”[25]的目的。
三、明清鼎革后,清王朝不断突破传统治藏方式
西藏地处被誉为地球第三级的青藏高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高寒缺氧的恶劣气候,在相当长时期作为一个边疆政治单元独立存在。虽然石硕先生称“西藏的文明无论在地域、种族、或文化上都强烈地呈现一种东向发展的趋势。”[26]但是长期以来中原王朝却缺乏西向西藏发展的动力。无论是统一的吐蕃王朝时期,还是长期的西藏分裂割据时期,中原王朝对西藏地方的影响都十分有限。
元朝时期,西藏首次被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统辖,但蒙古统治者却倚重萨迦派的“帝师-本钦”制度治理西藏。由于蒙古统治者对萨迦派及其他藏传佛教的尊崇,形成了所谓的福田与施主关系,这种宗教供施舍关系严重弱化了蒙古人对西藏地方的实际治理。代之而起的明朝则通过“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继续将西藏地方维持在大一统的疆域内。作为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明王朝政策的内向性非常明显,对外如此,对边疆也是如此。在大一统的前提下,明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内部事务,甚至各种政教纷争较少介入。贡赐关系是明王朝用经济手段维系与西藏地方政治关系的最直接的体现。但是,厚往薄来的贡赐制度让明财政耗费巨大,为了减轻财政负担,明朝廷在统治后期甚至多次颁布诏书,命令西藏地方减少向朝廷进贡频次和人数。所以,无论是元朝的“帝师—本钦”制度,还是明朝的“多封众建”制度,本质上都是对西藏地方的间接治理。
清政权本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边疆民族政权,明清鼎革却让它突然变成一个中央王朝。由于清初的康雍乾三帝具有强烈的大一统观念,十分注重对边疆的实际治理,也实现了清王朝在治藏方式上的不断突破。
第一阶段(1652-1727):间接治理到直接治理的过渡。明清鼎革很快确立了清王朝与西藏地方的隶属关系,也改变了西藏在清政权中的地位。西藏成为清王朝西南边疆的门户,并得到清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即“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27]由于清初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巩固和扩大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故而对西藏地方最初也是依靠蒙藏联合政权实施间接治理。但是,间接治理常常使清王朝对于西藏地方出现的种种问题后知后觉,十分被动。随着清王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稳固后,清统治者对西藏的间接治理方式开始逐渐调整。如在桑杰嘉措被杀,真假六世达赖喇嘛之争激烈时,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康熙皇帝谕令:“西藏事务不便令拉藏独理,应遣官一员前往西藏协同拉藏办理事务。”[28]于是,派侍郎赫寿前往西藏,开启了清王朝派员直接参与西藏事务的开端。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王朝又利用驱逐准噶尔之机,建立了噶伦制,由于五位噶伦皆由清王朝任命,为进一步推进直接治理奠定了重要基础;雍正五年(1727)正月,为了进一步掌控西藏事务,推进直接治理,雍正皇帝利用噶伦之争,“著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差往达赖喇嘛处”[29],正式在西藏设置常设的驻藏大臣制度,开始对西藏事务的直接治理。
第二阶段(1727-1793年):有限直接治理。清王朝在此时期虽然设立驻藏大臣制度,并相继推行了噶伦制(1727)、郡王制(1739年)、达赖喇嘛政教合一制(1751年)及摄政制(1757年),但清王朝对西藏地方的直接治理仍比较有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驻藏大臣制度初设,机构、职责、人员编制都不完善。加之西藏地处边陲,人贫地薄,很多驻藏大臣对藏事并不热心。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西藏地方执政者大多能力较强。如在噶伦制和郡王制期间,清朝倚重西藏贵族颇罗鼐治理西藏。颇罗鼐为人勤勉得力,先后被清廷封为贝子(雍正六年,1728年)、贝勒(雍正九年,1731年)和郡王(乾隆四年,1739年)。在颇罗鼐的治理下,西藏社会稳定,各项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很多事情驻藏大臣并不参与。在政教合一制度时期,七世达赖喇嘛(1708—1757)、第六世第穆活佛阿旺降白德勒嘉措(1757-1777任摄政)和第一世策墨林活佛阿旺楚臣(1777-1781任摄政)也积极任事,藏事多由格鲁派首领实际掌控。正如乾隆皇帝批评:驻藏大臣“不过迁延岁月,冀图班满回京,是以藏中诸事任听达赖喇嘛及噶布伦等率意径行。大臣等不但不能照管,亦并不预闻,是驻藏大臣竟成虚设。”[30]
第三阶段(1793-1911):全面、深入的直接治理。1793年,清王朝在平定廓尔喀侵藏战争后颁布《二十九条》,对治藏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二十九条》极大地突破了清王朝对西藏地方事务的治理范畴,除了传统的行政、人事权外,以前很少涉及的宗教、经济、军事、对外交往等都被纳入清政府的治理范畴,为清王朝对西藏事务能够全面、深入的直接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此外,清王朝能够在实践上实现对西藏地方全面、深入的直接治理还有比较特殊的原因,就是1804年八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后继的第九——十二世达赖喇嘛年纪轻轻就圆寂①第九世达赖喇嘛(1805~1815年)、第十世达赖喇嘛(1816—1837年)、第十一世达赖喇嘛(1838-1855)、第十二世达赖喇嘛(1856-1875)、第十三世达赖喇嘛(1876-1933年,1895年亲政)。,直到1895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其间长达91年时间,达赖喇嘛几乎不能实际执掌政事,虽然有摄政代行达赖喇嘛职权,但无法与驻藏大臣相提并论,这也为驻藏大臣能够全面、深入治理西藏创造了难得的机会。
结语
综上所述,明清鼎革对西藏历史的进程具有根本性的影响。1642年固始汗遵奉第五世达赖喇嘛为宗教领袖,也将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甘丹颇章政权推上了西藏历史发展的舞台,一直到1959年,因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叛逃,甘丹颇章政权才彻底灭亡。甘丹颇章政权长达317年,是西藏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政权,历经明、清、民国、新中国四个政权,三种社会形态,被一些学者称为“甘丹颇章奇迹”。但是,如果没有明清鼎革,这个“奇迹”是很难出现的。因为格鲁派虽然依靠和硕特部最终在政教之争中侥幸获胜,其优势地位很快就因蒙藏之争而动摇;相反,因为明清鼎革的契机,清王朝确立独尊格鲁派的宗教政策,并通过对其不断改造,使格鲁派的发展有了更多的机会,从而在1751年获得了政教合一的权力。也因为有清王朝的庇护,无论是准噶尔部的噶尔丹、策旺阿拉布坦,还是和硕特部的罗布藏丹津等蒙古势力,在他们觊觎西藏地方时,清王朝都进行了有力的回击,成功阻止了明末以来蒙古势力向西藏扩张的趋势,为甘丹颇章政权的长期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样,也是基于明清鼎革,清王朝才得以有机会治理西藏。由于清王朝不断突破历代中央王朝的治藏方式,对西藏地方的治理达到了历史从未有过的广度和深度,治藏成绩卓著,有力地维护了西藏地方的长期稳定和统一,也使得中央与地方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即使在清末动荡、艰难的时局下,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面对英俄帝国主义的挑拨和西藏内部分裂分子的叫嚣,清王朝仍然能够控制西藏地方的主权,为后来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合法拥有西藏地方的主权提供了重要的法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