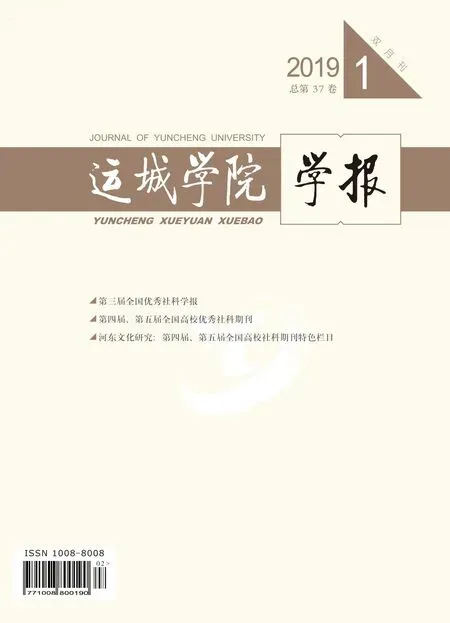追寻“自我”:《倾城之恋》细读及重释(上)
袁 少 冲
(运城学院 中文系,山西 运城 044000)
对《倾城之恋》主题的把握,白流苏、范柳原人物形象的解读,长期以来受到张爱玲本人强大“意图谬误”的干扰。她伪装成叙述者,常常在文本中对范柳原、白流苏做出论断,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解释。这些论断和解释穿插在文本的细碎角落,或隐或显,却在不知不觉间拘牵着读者的心神。其实,张爱玲本人说过这样的话,“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的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1]95。《倾城之恋》原本应该是这样的作品,然而它的光芒却被作者的主观意图遮蔽了大半。本文尝试重新细读《倾城之恋》,并在细节性分析中进行主题重释。
一、恋爱中的隔膜、“围城”与自我追寻
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相遇,似乎是个注定的偶然。范柳原的相亲对象本是七小姐宝络,但四奶奶出于私心生把其女儿安插进来,引起宝络的强烈不满,强拉流苏上车占座以挤掉金枝金蝉。换言之,与范柳原的谋面对流苏而言完全是被动的、计划外的。奇妙之处在于:一来宝络谋算着让流苏当帮手打击四奶奶,却没想到原本的陪衬成了主角;二来,偏偏是四奶奶的自私算计把流苏推到了范柳原面前,而她对待流苏原本最是刻薄。正应了那句老话:人算不如天算!
另外,从范柳原在小说前后的种种细节可以看出,流苏其人亦新亦旧,但恰恰这个亦新亦旧的女人才有可能吸引范柳原。比如在流苏与宝络中间,更旧式、更传统的应该是宝络,不料范柳原大概没有正眼看过她,因为太旧了就无法和新潮的柳原有言语行为上的沟通。而太新潮的女人柳原见得太多,这样的女人只是交际场合文雅游戏的对象。吸引柳原的恰恰是流苏身上的那种更传统、更中国化的气质,不过,二者最初的交往手段却是跳舞这种极西化、新潮的方式。可见,早在流苏与柳原故事的开端,就已经充斥着种种奇怪的新与旧、中与西的错位、纠葛。
当然,这其中亦有合理性在。首先,范柳原并不真的懂中国,他只能感受他相像中的中国;其次,囿于自己洋化、西化的背景,他对中国女人的相像有显然的局限。像宝络那样通过“珍珠耳坠子,翠玉手镯,绿玉戒指……花团锦簇”这种讲求以物显贵、门当户对的更传统、更中国的相亲方式,反倒令柳原无感。实际上这种方式恰恰是传统文化的僵化变质,不能代表中国文化更本质、更精髓的东西。[注]另一方面似乎也在暗示柳原所看重的并非物质,而更在意人的内在气质、心灵。所以,范柳原只能感受和接受其理解范围之内的“中国”,因为范柳原终究戴着一副颇为洋化、个人化的眼镜。流苏太新了不行,柳原对于新潮、洋气早已麻木无感[注]如萨黑夷妮口中的所谓上海人,柳原对之难有兴致。流苏则不像她眼中(洋气)的上海人,恰恰是这个“不像”,反倒吸引了范柳原。;太旧了也不行,太旧了就超出了柳原感知的界线,二者没有可供沟通的桥梁;不新不旧、亦新亦旧反倒刚合适。
和范柳原的初次会面,自然非常重要。柳原在众多相亲对象中,独独于流苏身上发现了他所欣赏的“中国味道”,初见之后竟不惜费心思、花大钱把流苏请到香港,制造单独相处的机会,很有些一见钟情的味道了。而在流苏心里,虽然对范柳原说不上有动情,但至少有了较深的印象和莫名的好感。三奶奶他们统共没听上范柳原三句话,他却拉着流苏跳了三支舞,还献上不少殷勤话。流苏在整个过程中虽说既无意又被动,但范柳原的青睐到底让她给了白公馆“一点颜色看看”,让平日里拿她当笑话看的人们也多少“刮目相看”一些。“他们以为她这辈子已经完了么?早哩,她微笑着”。可见,范柳原表露的那些爱慕之言(尽管流苏并不真信),既能挽回一些她的尊严,也能让她对此生重拾信心。毕竟,在和徐太太的对话中,流苏早把自己描述成一无所有、一无所长的二婚大龄妇女了。故而,流苏若对柳原生出一些感激,也是人之常情。
另外,流苏凭着自己过往应付男人的经验,看得出范柳原在交际场上对女人说惯了谎,不敢确定他是否真心,反倒戒心连连,“她不能不当心——她是个六亲无靠的人。她只有她自己了”。流苏的孤苦无依、无以聊生,形成极为沉重的生存压力,她要追寻的“自我”中经济成分(生活保障)愈重,愈使她难以打开精神与情感的大门(正常的恋爱一般情形下,往往是不计利害、不管不顾的)。这样的心态,遇上了做感情游戏的人还能自我保护,若遇到认真的对象却反而设置了两心互通的障碍。流苏和柳原之间,大体上属于后者。
鉴于这些复杂的因素,柳原在流苏心里有深切印象,否则她不会在徐太太提出一同赴港时就想到,“难不成是范柳原的诡计?”即使这么重的戒心,流苏也至少没对柳原有厌恶、反感,这是二者关系发生良性转机的基础。因此,就算是范的诡计,流苏也准备拿她的前途来下注了。值得一赌的原因还有一个,若能在白家人“虎视眈眈”下俘获范柳原,则可以“出净她胸中这一口气”,既报复旧家又提升自己的尊严。
再次相聚虽距初见没隔几日,且流苏也早有了心理准备,但她再遇柳原的反应却大大出乎自己的意料,“一颗心已久不免跳得厉害……那范柳原虽然够不上称作美男子,粗枝大叶的,也有他的一种风神”[2]175。流苏的这些下意识表现,跳出了她接近柳原的经济目的,是较为感性、单纯的女性心动,说明她对柳原确实颇有好感。只是她的前途,她欲重建的“自我”,太沉重,仅凭这点好感还不够,她须得先确定柳原的真心,还有名分及物质保障。
总体而言,两人的恋爱形成了这样的怪圈与僵局:虽然郎有情、妾有意,但流苏因为生活的重压,情感被物质绑架,使她患得患失地掖藏着真心,希求先得到婚姻[注]在流苏“自我”里,经济的比例更重,但这不是说,流苏没有精神上的追求,只是常常被前者压倒、吞噬罢了。而在柳原一方,在看不到流苏的真心、得不到心灵共鸣之前,他不会谈婚论嫁。一个要先得到保障才敢去爱,一个要先得到爱才给名分,互相都在自己的立场上坚守着、僵持着,看谁先迈出妥协的那一步。他们不是相互用真心去体察对方,第一时间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着想,而总是下意识地从自己出发。尤其是范柳原,他不愿自己的婚姻是具漂亮的空壳,这样的婚姻在他看来形同肉体上的长期卖淫;同时他也不愿让婚姻成为自己的约束,因为“犯不着花了钱娶一个对我毫无感情的人来管束我”;并且还认为这样的婚姻“太不公平”,对流苏而言“也不公平”。[注]这样的看法,多少也透露出范柳原心里的讲求平等、尊重女性的现代意识。在范柳原的心中,他是固执地要将爱情与婚姻画上等号的。此外,柳原特有的做派,习惯了调情、说谎、油嘴滑舌,即便讲些真话也令人真假难辨。所以,两人的恋爱之路曲曲折折,充满了误会、错解与隔膜。除了以上双方的主观因素外,二者客观上知识背景、人生经历、生活阅历、情感体验的差异、错位,也不免造成障碍、隔阂。当范柳原说流苏“特长是低头”“善于低头”的时候,流苏还无法听懂。此时,她对柳原的身世经历、脾气性情还太过陌生,无法清晰感知柳原究竟在意什么。比如,她不知道在柳原眼中,“低头”代表的是一种以含蓄、柔顺、羞涩为特征的东方美感与行为方式。在香港饭店的舞池中,柳原说他“认为好女人还是老实一些的好”,其实是把流苏当作老实的好女人珍视的,但流苏却以为没这么简单。其一,依据她较为传统、旧式的认知尺度,标准的老实女人不会这么四处抛头露面、应酬交际,与陌生男子跳舞寒暄、肌肤相触,自己就不算是彻底的老实女人。其二,她也不相信柳原会真的喜欢老实的好女人,不然宝络那样旧式闺秀为何提不起柳原的兴致。所以,她才会说柳原“自私”,以其以往对那些风月老手的经验去理解柳原的话,把他想成“你最高明的理想是一个冰清玉洁而又富于挑逗性的女人。冰清玉洁,是对于他人。挑逗,是对于你自己。如果我是一个彻底的好女人,你根本就不会注意到我!”[2]177这样的对话里,双方都听不大懂。有时候想多了,有时候又想少了;有时候想简单了,有时候又想复杂了;有时候把真的当成假的,有时候亦可能把假的当成真的。
其实,柳原与流苏的交往之初,已经比较坦诚地讲了许多真心话,这于他确属难得。无论称赞流苏“特长是低头”,觉得好女人还是老实些好,还是认为流苏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并且“真正的中国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永远不会过了时”,均乃其心声之倾吐。但流苏却不甚明白所谓“中国女人”到底何意,因其没有柳原那样华侨的视角及经历。柳原对中国女人的认识、想象,建立在其常年异国漂泊、养成了西化倾向的心理图式上;但又在西方文明中幻灭孤独,对故国之“(自)我”有浓烈、敏感的期待与感应——这些都不是流苏能猜得透的。是故,双方对“中国女人”的理解大相径庭,产生困惑在所难免。
流苏虽不知道柳原口中的“中国女人”为何物,但举手投足便自然流露出和“低头”相类似的“中国女人”气质。如柳原借口“白小姐有点头痛”把她领出来的时候,流苏虽有不快却隐忍着顺从;当柳原提议“到那边去走走”的时候,流苏“不做声;他走,她就缓缓地跟了过去”;“柳原靠在墙上,流苏也就靠在墙上”。这些细节都显露了流苏较为柔顺、依从、乖巧的一面,在柳原眼里即是典型的“中国女人”特征[注]小说中的那个萨黑夷妮也很有意思,自己是印度人却处处体现了西方女性的现代特征,很能代表柳原司空见惯的女人类型。他在小说中主要作为比较对象而存在:和柳原相比,她是一个较为彻底的“无根”者且安于这“无根”,柳原则一直想找到自己在中国的“根”;和流苏相比,后者身上的中国特征愈发明显,在柳原看来便愈是珍贵。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流苏与柳原在墙下的那段对话,都是最重要的细节之一。此时二者远远地撇开了众人、撇开了城市的烦嚣,这沉静的两人世界,适合倾诉心声、表露真情。并且,经过初步熟悉,相互的了解也逐渐加多,彼此开始试着打开心门。但实际的对话中,依旧充斥着各种误会与错解。
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2]180
在这段话里有一个深与浅的错位。柳原的告白,包含着他在长年流浪英伦时对西方现代文化的那种幻灭感、危机感、边缘感;以及生意场上、交际圈中处处虚伪、装假、势利、算计的疲惫与厌倦;还有关于现代人心灵遥远、真心难觅的感慨。这些复杂而深层的感触是柳原坎坷生命体验的凝结。但在流苏那里,则完全不解其中真味,只给出一个浅层的回应,还带着指责柳原为自己开脱的意思,“你自己承认你爱装假,可别拉扯上我!你几时捉出我说谎来着?”回应的浅是因为理解的浅,她只能听懂部分的字面意思,客观上既没有柳原特殊的视角与体验,主观上也没有意愿站在柳原的立场上去体会、揣摩。
柳原意识到流苏的不懂,但并不死心,继续吐露他郁积许久的心里话,从自己的身世经历说起:
我知道你是不快乐的。我们四周的那些坏事、坏人,你一定是看够了。可是,如果你这是第一次看见他们,你一定更看不惯,更难受。我就是这样,我回中国来的时候,已经二十四了。关于我的家乡,我做了好些梦。你可以想像到我是多么的失望。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不由自主的就往下溜。你……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2]180
这段话固然有对自己玩世不恭的现状作解释的意思,但更希望流苏能了解他的过去,知悉他回国后精神备受打击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更加明白、体谅自己。流苏却没有顺着柳原的思路去尝试着同情、理解,而是从自己的经历中来领会,“试着想象她是第一次看见她四嫂”。于是,答出了这样的话:“还是那样的好,初次瞧见,再坏些,再脏些,是你外面的人。你外面的东西。你若是混在那里头长久了,你怎么分得清,哪一部份是他们,哪一部份是你自己?”[2]180流苏此次反应,在层次上倒是加深了,包含着她痛彻的人生体验,是真心话。
麻烦的是:两人不说真话自然难有心灵的碰撞,而即便都说了真话也不一定能心意相通!此处的流苏和柳原已经渐渐有了深层对话,倾吐了内心深处的感受,且主观上他对她有情、她对他有意,但二人仍站在自己的世界里,固守各自的立场。实际上,他们的“自我”都是残缺的,要让“自我”完整,都需要对方来成就自己。然而,又都不愿率先放下自己,到对方的世界里主动去拥抱、体谅、慰疗他者的灵魂。于是,愈守着自己便愈没有“自我”,愈警惕别人反而愈捆住自己!看起来多么怪诞、可悲,然而,人性——往往如此。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描述了传统社会的一个怪诞结构,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
去了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3]451
这是一种前现代的人与人关系的写照,一种人与人“互相牵掣”的死结,然而即便破除这“吃人—被吃”的结构之后,是不是现代人就真的自由了呢?也许只是陷入另一种互相的“牵掣结构”之中:没有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般天经地义的义务关系,每个人都依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处世;每个人都不愿为了别人而奉献自己,每个人都又渴望且需要别人来为自己奉献;先奉献了自己固然能赢得真爱、完成自我,但也很可能受骗、吃亏,但不奉献又大体注定了孤独;每个人都既不愿吃亏、不愿奉献又不愿孤独,但多数时候正是前者造成了后者;每个人都总想成为被别人、被上苍万千宠爱的那一个,期待着少之又少的小概率事件砸住自己;而自身则永远无须冒险、受伤,无须先行主动地迈出第一步!
范柳原和白流苏之间即是这种现代式“牵掣结构”的典型。即便是真话,也是各说自话!流苏其实只是说了自己的真实体会,没有评判、批驳柳原的意思。但站在柳原的角度上,他自然不知道流苏想起了四嫂,喟叹的是她自己的伤痛,却以为这是对自己的异议与反驳。真心告白反遭指责,失望之情溢于言表,他默然良久方道“也许你是对的。也许我这些话无非是借口,自己糊弄自己”。于是,先是流苏不理解他,接着他也误会流苏。进而,柳原想来想去又不服气,因为“其实我用不着什么借口呀!我爱玩──我有这个钱,有这个时间,还得去找别的理由?”[2]180但这种抗辩早就偏离了自己的初衷,所以仍旧是沮丧,风度再难维持,只能烦躁地说“我自己也不懂得我自己──可是我要你懂得我!我要你懂得我!”这才是柳原的本意——希望流苏能懂他。虽然流苏连他的话都还不懂,但在这么多年来谋面的女性之中,至少流苏激起了他倾吐心声的欲望,所以,尽管他“心里早已绝望了,然而他还是固执地,哀恳似的说着:‘我要你懂得我!’”其实,二者沟通的不畅,从流苏话后柳原的反应中就能看出,“嗤的一笑道……静了半晌,叹了口气……默然,隔了一会方道……突然笑了起来道……思索了一会,又烦躁起来……心里早已绝望……还是固执地,哀恳似的说着”[2]180-181。这一连串表现,说明在与流苏的对话中:其一,柳原处处受阻,几乎每句话在流苏那里都会有错解,出乎他的意料,令其讶异;其二,谈文明的毁掉、人与人的真心,谈自己对家乡的期待与打击,是真得希望她能理解、能懂得。柳原的态度,与其说主动,毋宁说是相当迫切的。
故在二者的对峙之中:柳原是更主动、更敞开、更坦率的那个,带着无法把握自己的迷惘;他的率真也因为他有恃无恐,即经济地位的优势;他需要的主要是精神性的,然而,其精神需求程度很高,若达不到他便不会有婚姻的承诺。相比之下,流苏是更封闭、更具戒心的那个,封闭和戒心只因她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故需要找寻依靠;不能说他对柳原无意,亦非无情感欲求,但必须先求得生活(物质保障);她的凭借只剩下这点青春,由于太过珍贵,便愈是敝帚自珍。所以,流苏的追求中,物质的比重更高,经济的不安全致使她神经紧绷,紧紧攥着其唯一的砝码——真心与青春。从这个角度看,那个相互对峙中的“牵掣结构”又似乎含着某种“围城”:想要(围)城外之物,蜷伏自我(围城)之中。
流苏在自己的“围城”中是无法体贴入微地想柳原之所想、感柳原之所感的,虽然她面对柳原“我要你懂的我”的哀恳,愿意试一试,安慰道“我懂得,我懂得”。然而,恍惚中“她不由得想到了她自己的月光中的脸,那娇脆的轮廓,眉与眼,美得不近情理,美得渺茫”。这个细节非常典型地描画出流苏的立场与心态:嘴上安慰柳原“我懂得”,心中也分明愿意试一试,但心思偏偏无法真正留在他身上,而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的面庞、轮廓和眉眼,带着显明的自怜自珍,暗示着流苏对其立场的偏执与固守。这言与心的矛盾其实她自己也有所察觉,甚至也觉得不好意思,故“她缓缓地垂下头去”。范柳原当然也看得分明,难以再较真下去,恢复了他惯有的轻薄调笑。
晚上回到旅馆,流苏有一番仔细的思量:
原来范柳原是讲究精神恋爱的。她倒也赞成,因为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而肉体之爱往往就停顿在某一阶段,很少结婚的希望,精神恋爱只有一个毛病:在恋爱过程中,女人往往听不懂男人的话。然而那倒也没有多大关系。后来总还是结婚、找房子、置家具、雇佣人──那些事上,女人可比男人在行得多。她这么一想,今天这点小误会,也就不放在心上。[2]181
相处多天之后,流苏终于改变了原初对柳原的判断。正如此前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定的那样:范柳原在流苏那里想要的只是她的肉体,且一旦得手按照他浪荡公子的作风基本上就是始乱终弃了;所以流苏才千万要守身如玉,不能让柳原得逞,吊着他才有机会;两人的恋爱就是在此基础上的博弈算计、斗智斗勇。可能流苏此前对柳原的认识亦大体如是,所以处处提防他的侵犯,但预想中的不轨之举却始终未至,甚至连她自己都纳罕,好似一脚踏空。与柳原有深入接触之后,流苏却发现“原来范柳原是讲究精神恋爱的”,这个“原来”,开始修正了她的看法,在其内心,终于认识到柳原要的不是肉体那么简单——他是讲求精神恋爱的。
只是,她对柳原的防备还没那么容易顷刻消散,结果次日当柳原问她想去海滩或是进城的时候,她觉得海滩虽然热闹但未免“行动太自由一点”,才提议进城。在大中华的那番对话,又同样处处充满误解。
柳原说自己和流苏在一起爱干各种傻事,很有些恋爱中人甘心放下自己、情愿迁就对方的意味;流苏却说“你被我传染上了傻气,是不是?”想陪柳苏到马来亚的森林以回到自然,以便看到一个更真实的、更自然的流苏;流苏却以为他在占自己便宜,回道“少胡说”。柳原说她不适合穿偏暴露或洋气的西装,而满洲的旗装或许更合适,仍然是在赞美流苏身上的那种古典的东方韵味,和之前屡次提及的“中国女人”相呼应,并且强调这是正经话;流苏却说是不是人丑怎么穿都不合适。柳原分明意识到其中的误会,解释说流苏身上的很多下意识的小动作有着古典的浪漫气氛,不像是他熟悉的那些所谓现代人,倒像是唱京戏。若联想到流苏在与三哥四嫂吵翻后的某个细节——孤身于镜前打量自己,并随着四哥的胡琴“微微飞了个眼风,做了个手势……走一步路都仿佛是合着失了传的古代音乐的节拍”——这种感觉准确而传神,分明是赞美。不料流苏的错解更是离谱,她听话的重心全落在“唱戏”二字,以为柳原暗讽她作假。如此“驴口不对马嘴”的谈话,怪不得范柳原“黯然”起来。并且,通览其对话,流苏似乎每句话都误会柳原,柳原反倒是处处迁就流苏,谈话节奏始终被她的误解带着走偏了。
不过,柳原的话虽然流苏还不大懂,可种种行为、举动、态度已令她对柳原的先期判断从心底有了改观。
他每天伴着她到处跑,什么都玩到了,电影、广东戏、赌场、格罗士打饭店、思豪酒店、青鸟咖啡馆、印度绸缎庄、九龙的四川菜……晚上他们常常出去散步,直到深夜,她自己都不能够相信,他连她的手都难得碰一碰。她总是提心吊胆,怕他突然摘下假面具,对她做冷不防的袭击,然而一天又一天的过去了,他维持着他的君子风度,她如临大敌,结果毫无动静。她起初倒觉得不安,仿佛下楼梯的时候踏空了一级似的,心里异常怔忡,后来也就惯了。[2]184
所谓“日久见人心”,在长久的相处中,柳原的表现让流苏对他“多了一层认识”,逐渐放下戒心。于是,此前因为行动太自由而让她警惕的“海滩”,流苏也开始觉得“去去也无妨”,且一去就“消磨了一上午”。
当沙滩上有沙蝇叮咬,柳原提议“我来替你打,你来替我打”的时候,是流苏首先“果然留心着,照准他臂上打去”,并且还叫着“哎呀,让它跑了”。这种肌肤相触原本是流苏一直敏感提防的行为,此时反倒是她率先做出这明显亲昵的举动,从其叫喊中不难看出此举是下意识的。这个重要的细节,一来说明,柳原在流苏心中的形象已经转变,并且也已经逐渐赢得了她的信任,两人的关系进入一个更近的阶段;二来表明流苏也不由自主地打开了此前一直紧闭着的心门,哪怕只开了一条缝。这才会有“两人噼噼啪啪打着,笑成一片”。此时的两人处于自然、放松的状态,故作的矜持、生活的重压、僵持的泥潭、自筑的围城都统统被忘掉、被放到一边。张爱玲说过,“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1]94,这种像亲密恋人那般笑打一团之状,或许正是二人共同“放恣”之时。
然而,孤苦无依重压之下的长久矜持与淑女身份,在流苏心中毕竟既是自我保护也是和柳原相持的砝码。当她意识到自己是不是过了头、突破了底线的时候,便会本能地意识到(因放开自己而使她处于二者关系中被动境地的)危险,故而重启自我保护的心理机制。她在笑打中无缘无故地“被得罪了,站起身来往旅馆里走”,其实就是意识复苏后的(本能性的)自我保护行为。流苏回到旅馆,发觉柳原并未跟来,就拿望远镜往海滩上看,当发现一个女人躺在柳原身边时——“就把那萨黑夷妮烧了灰,流苏也认识她”。拿望远镜看,说明她紧张柳原;把萨黑夷妮烧成灰她也识得,说明流苏心里有了强烈的嫉妒;这些细节昭示着流苏其实已对柳原暗生真情,不再驻留于当初的“好感”阶段。不过,即便已有真情,但毕竟还有那么多经济、生活上的考虑,流苏依旧放不下自己。
此事过后的两天里,范柳原不是像往常那样向流苏赔不是,而是偏偏和萨黑夷妮厮混,故意把流苏晾在一边。细心的读者可能还记得,当初柳原以流苏头痛为由把她从香港饭店拉出来的时候,流苏乖乖随他离去的理由是“不愿得罪了他,因为交情还不够深,没有到吵嘴的程度”。而如今两人故意冷落对方的情形,分明带有互相赌气的味道,反而说明二者不像之前那么见外了,如同恋爱中正常的男男女女那样。所以,当柳原试探出流苏有为自己吃醋的意思时,立即言归于好。
至此,两人的关系有了推进,但那敞开心扉的刹那,远不能扫除其长久的隔膜,也不能填补经济落差带给二人的情感上主动、被动的沟壑。当流苏重又退到其心理保护伞之后,她仍旧难以真正理解柳原。流苏有她的小心思:表面上和柳原热了些,心里却有着别的盘算。流苏如何看待柳原乐见她吃醋呢?
他使她吃醋,无非是用的激将法,逼着她自动的投到他的怀里去。她早不同他好,晚不同他好,偏拣这个当口和他好了,白牺牲了她自己,他一定不承情,只道她中了他的计。她做梦也休想他娶她。……很明显的,他要她,可是他不愿意娶她。然而她家里穷虽穷,也还是个望族,大家都是场面上的人,他担当不起这诱奸的罪名。因此他采取了那种光明正大的态度。她现在知道了,那完全是假撇清。他处处地方希图脱卸责任。以后她若是被抛弃了,她绝对没有谁可抱怨。[2]186
流苏已经承认柳原对她有情感上的需要,但还是坚持地认为柳原“不愿意娶她”。并且,在夜话“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次日清晨,当柳原说她别枉担了“范太太”的虚名之时:
流苏吃惊地朝他望望,蓦地里悟到他这人多么恶毒。他有意的当着人做出亲狎的神气,使她没法可证明他们没有发生关系。她势成骑虎,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爷娘,除了做他的情妇之外没有第二条路。然而她如果迁就了他,不但前功尽弃,以后更是万劫不复了。她偏不!就算她枉担了虚名,他不过口头上占了她一个便宜。归根究底,他还是没得到她。既然他没有得到她,或许他有一天还会回到她这里来,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2]188-189
流苏的这两次心理活动,诱导了许多读者对二者恋爱性质的看法,及对范柳原的观感。比如所谓范柳原不愿结婚只是想包养她做情妇,以及二者之间的谋算、较量关系等等。然而,这些看法合理的前提是:流苏足够了解柳原,没有对他以及二者的关系产生误解。可通过前面大量的细节分析:流苏还没有真的走进柳原的内心,她连范柳原的话还听不明白,言谈之间误会百出,心与心的熟悉默契完全未建立起来,此情此境中流苏怎么可能不误解柳原(对柳原的误解将直接导致对二者关系的误解)。
站在流苏的立场上,她的所想所思不无道理。比如,在激将的当口投怀送抱,对于一般的浮浪公子也很可能确乎“不承情,只道她中了他的计”;若流苏当真要逼她做情妇,自己的迁就还真有可能便宜了柳原,所以不让他如此轻易得逞,才可能为自己增添砝码等等。从中亦能看出,流苏对人情世故还是有一套自己的认识,有一套应付人的经验。但若站在范柳原的立场上,何尝没有他自己的道理:为什么要给一个连自己的话都听不懂的女人以承诺、以婚姻呢?
所以,在这种隔膜情境中,同一恋爱,双方各自固守其立场,并有着不同的“自我”追寻之需要(一个偏物质,另一个几乎纯然是精神的),还秉持两种相互错位的爱情婚姻观念。范柳原在较为现代的英伦长大,不免耳濡目染地接受某种讲求情感基础的现代婚姻观念,再加上自身要追寻一个中国式“自我”的内在需要,更提高了对情感上相互理解、契合的程度。而白流苏生长在传统的旧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惯例,以及女性依附地位的社会文化,都造成对纯粹情感的欲求度不高,容易被婚姻所赋予的“自我”归属、安稳特征所覆盖,两者之间确乎有算计,但流苏与柳原所算计的,并非同一个东西,流苏只能依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去揣测柳原的算计,然而很可能是错的。比如,流苏认为柳原算计的是一个情妇,其实柳原想要的绝非一个情妇那么简单(仅仅找一个情妇无须如此费力劳神),他要的是一个能刺入自己灵魂的“真正的中国女人”。这种误解也是两人中西新旧标尺上的错位造成的:二人之中,流苏是更旧更中国的那个,她在自己的情感中屡屡想到家乡、望族、爷娘,说明她的爱情婚姻观还带有极大的传统烙印,在她的眼里一个男人把女人带往异地,独处这么多时日,出入肩并肩,深夜不避嫌地到海滩散步,连别人都觉得流苏应该是“范太太”了,到这种程度完全应该确定他们之间的名分或婚姻了;但柳原是那个更新潮更西化更现代的那个,在他的理解中(别忘了他在英国生活了24年)婚姻不是父母之命、门当户对,自由恋爱精神伴侣的现代观念在其头脑中有程度更浓的存在;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在流苏看似乎已经完全够了,可在他看来还太过稀薄,离谈婚论嫁的程度尚早。这些错位,也会造成流苏因达不到自己的预期而对柳原的过度揣测,而她却尚未真正了解柳原,所以,连这些揣测也无可避免地成为曲解。比如,她还听不懂柳原口中的“真正的中国女人”是什么,所以便不能理解,这其中柳原是寄托了他怎样强烈的情感需要、精神依赖和自我确证,于是,只能往她常常见到的浪荡公子与情妇红颜的方面去想。
因此,流苏的这些误解在《倾城之恋》的故事链条中既必然又合理,但读者和研究者把这些误解当正解看则实属不该。
流苏对柳原的这种“误读”,其根本原因是,他的形象一开始就被固化为“浮荡油滑、玩世不恭”,似乎把他当成一个生来就衣食无忧的富家公子,忘记了范柳原24年的异国流浪、颠沛穷苦。而这既与小说某些细节对柳原的描述有关,与流苏对柳原的误解有关,也与张爱玲自己的暗示、判断有关。然而,在文本内外,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他人[注]张爱玲认为流苏到最后也没有真的了解范柳原,并坦承自己也不了解他,“我从她(白流苏)的观点写这故事,而她始终没有彻底懂得柳原的为人,因此我也用不着十分懂得他”,所以文本中徐太太、白流苏对柳原的看法并不可靠。见张爱玲《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张玲爱全集5》第192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又何尝真的了解范柳原。在对文本细微处仔细爬梳之后,没有确切的信息表明柳原真的排斥家庭与婚姻。徐太太那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只是她自己眼里的范柳原,二人并无深交只做泛泛的介绍之谈,又有多大可信度呢?但流苏的揣测很可能受了徐太太的影响,同样不可靠。其实,范柳原不是没有考虑过婚姻,且很可能恰恰相反:他渴望婚姻,渴望借助婚姻找寻到那个属于中国的“自我”,只是在这样的婚姻中,他对女方的精神需求层次太高,高到了理想化的程度。
——张爱玲认为的真正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