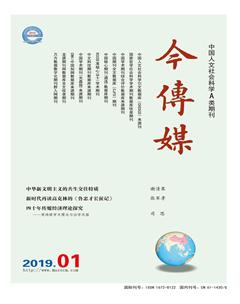受众观视角下的AI与主持传播
李坤
摘要:2018年11月8日的世界互联网大会,虚拟主播首次亮相,主持传播行业沸腾一片如临大敌,在2018年1月份,由人工智能进行配音的纪录片《创新中国》在央视播出,声音再现了著名配音艺术家李易的声音。面对AI的不断完善和无限仿真进程,传统播音员和主持人是否真的岌岌可危,本文将从受众的视角,利用话语实在论的受众观以及基于技术变革的受众观来分析,在大众传播时代AI的不断进步只能是作为主持传播的补充,无法替代主持传播中的实体。
关键词:AI;主持传播;受众
中图分类号:G20文献标识码:A[KG2.5mm]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1-0022-02
著名的咨询管理公司麦肯锡预言到2055年,全球的有薪工作里将会有49%的比例会由人工智能代替实现自动化,如气象播报员、新闻记者、配音员等涉及主持传播的的工种也在其中。在2018年年初,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创新中国》的配音就是已故艺术家李易老师的声音;而就在11月8日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新华社主播的模拟仿真播音员AI更是博人眼球,新闻一出整个传媒界一片哗然,如临大敌,各种唱衰的声音甚嚣尘上。这种场景似曾相识,每当有新的媒介技术出现的时候,这种负面的情绪会大肆蔓延,而事实上我们看到今天没有哪一种的媒介已经消亡,主持传播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中的一个核心岗位亦是如此。
一、主持傳播的概念化
主持传播,包括了节目主持人和出镜记者等作为传播主体的传播,其实是一种实现了大众传播主体的人格化,并在传播过程中体现人际性特点的大众传播方式,其中的人格化、人际性及大众传播是构成主持传播的关键。我们通常容易把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割裂进行研究,高贵武提出了主持传播利用大众传播传播的技术手段实现了人际传播,换句话说主持传播在冰冷的摄像机和受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营造了一种拟态人际环境[1]。
从主持传播概念本身出发,主持传播的本体是人,场域也是人际场域,或者更为具体的说,主持传播主持传播的核心要义在于人格化,这也是主持传播相较于其他大众传播方式的不可替代性,技术的不断发展是人格化的主持传播的支持和保证,如果说技术的发展能够完全替代人格化,恐怕也就陷入了技术决定论的误区了。
二、 话语争斗实在论下的受众
关于受众的研究由来已久,我们简单梳理一下作为心理实体的受众观,作为原子式的受众观是李普曼最先敏锐的发现并且开始焦虑:当今的普通公民就像坐在剧院后排的一位聋哑观众,他本该关注舞台上展开的故事情节,但却实在无法使自己保持清醒。杜威站在李普曼对面在《公众及其问题》中提出了在特定事件面前受众会成为积极的行动者。拉斯韦尔继承了李普曼从心理学立场去理解受众,用5W模式去研究理解受众。20世纪60年代卡茨提出的使用满足理论轰动一时,但是由于使用本理论无法给研究者准确答案而失去了繁殖能力。如学者胡翼青所说:把受众看作是客观存在的物,而不是不断变化中的关系、意义、观念和实践就会将受众研究推向教条主义的绝境。很显然当下传播环境下作为主持传播的受众,我们很难把他们独立于一种简单的受传框架,且这种框架不断的在产生变化。
霍尔在著名文章中《编码/解码》中传播过程是一个话语的过程:“并非没有其他‘话语的方面,它也完全是由意义和思想来架构的,即应用中的知识——这关乎日常秩序,历史地界定了技术技巧、职业观念、制度知识、定义和设想,有关观众的设想等”。
他创造性地给出了三种受众解码的模式:第一种为霸权式解读,就是在受众在编码者所构建的意识形态框架中进行解码;第二种为协调性解码,受众根据自己的观念的同时部分接受霸权式的编码;第三种为对抗式解码。胡翼青在三种解码模式做了补充,霍尔完全没有提到另一种在李普曼的思想中闪现的可能性,即受众根本不想了解主导性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也不想解码,因为这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无关[2]。
我们根据霍尔所提出的受众的三种解码模式来进行分析,首先来看霸权式的解码,霸权式解码的情况典型存在于迷群中,受众在主持传播接触过程中进行了身份认同的构建,构建之下的身份就是对传播者传递内容的霸权式解码,无条件的接受传播者所构建的意识框架,并且在主持传播接触过程中心理得到满足。
第二种情况是值得讨论的,因为在真实情境中实际上比较少的存在皮下注射,受众总是会根据自身的知识体系以及个人经验来协调性的解码,协调的程度在于他们对于主持传播主体的信赖程度。这个时代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受众淹没在大量的冗杂信息,将信息知识化应当是主持传播的一项根本要务,而传递知识的过程并非简单的信息传播,应当是伴随着人格化的传播主体向受体传播,这是一种交互过程也是一种协调过程,受众在知识的接受过程中不断调整自我的知识体系,以便在既有的知识框架中进行更新。
第三种情况则为对抗式解码,当下的媒介环境中有意思的是受众面对主持传播越来越多地呈现出迷群效应以及逆迷群效应,逆迷群效应并非消极的拒绝一切传播者所传递的内容,它同样在有着较高的互动频率,在当下媒介环境中受众拒绝接受主持传播者所传达的意识框架的表现不单单表现为冷漠,更多时候可能表现的更为激烈,这种激烈的表达过程中形成了互动,更多时候这种互动往来过程中受众感觉到身份的认同感亦或者更新了意识框架。毫无疑问,相对于AI来说人格化的主持传播者更加能够引起所谓的逆迷群效应。
最后,我们可以大胆的下一个定论,当下受众更感兴趣的并非文本本身,而是共同参与的群体,不断飞过的弹幕和评论比文本本身更加有吸引力,因此制造话题以及主持传播者本身的角色超越信息传递者的角色成为了受众更感兴趣的方面[3]。仔细分析受众感兴趣的点其实是在人本身,他们津津乐道的在于人格化的主持人他们的服装、他们是否整容、他们今天的状态等等充满变化的内容,人工智能相对于主持人来讲最大的特点在于稳定性和反应速度,当受众的注意力不在文本本身的时候,那么AI的优势就会被削弱。
三、 结论
利用话语争斗视域下的受众观来分析人工智能之于主持传播是很有意义的,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让主持传播不断贴近于人际传播,让信息传播更具有人情味,大众传播的初期阶段或许取胜的关键可能还是在于信息的拥有量以及反映速度,当海量信息时代背景下各家传媒单位的反应速度相差无几的情况下,人格化的主持传播才能够真正拥有受众并且掌握话语权。
参考文献:
[1]高贵武.生还是死:技术变革视野下的主持传播[J].视听传播,2018(9).
[2]胡翼青.超越作为实体的受众与作为话语的受众——论基于技术视角的受众观的兴起[J].南京师大学报,2018(5).
[3]王泽华.场景时代媒体传播环境及传播理念变革[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8(5).
[责任编辑: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