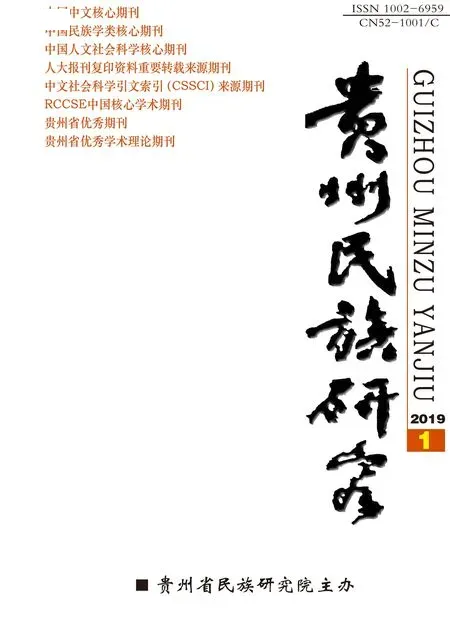建国初期少数民族医疗卫生建设的历史经验
万振凡 杨 杰
(1.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南昌,330022;2.江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南昌,330022)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各民族的团结、平等和共同发展,关系到国防巩固、边疆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虽然人口不多,但分布广泛,少数民族的健康发展,是中华民族健康素质的提高和国家繁荣富强的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情况是非常恶劣的,如“新疆近20万平方公里的阿勒泰草原,只有3个简陋的诊所,而且药价昂贵,一匹马只能换到一支青霉素,一只肥羊只换十几片阿司匹林。西藏的情况更落后,全西藏只有4个诊所和医院,而且只为三大领主服务,广大农奴是被拒之门外的。”[1]在恶性疟疾流行的云南西双版纳等地区,流传这样一些民谣:“要到芒市(德宏州)、普腾(西双版纳)坝,先把老婆嫁”;“只见娘怀胎,不见儿上街”;“秋收忙,病上床,闷头摆子似虎狼,十人下坝九人死,一人逃居到山冈”;“谷子熟,无人收,寨寨死人,家家哭”,就是对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情景十分悲惨。[2]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各种疾病流行,人口减少率达到惊人的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力发展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同时,积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事业,基本消灭了性病、回归热、痢疾及其他地方病,天花因普遍接种牛痘而绝迹,人口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在此过程中,我国积累了丰富的少数民族医疗卫生建设的历史经验。为正在开展的少数民族医疗卫生建设和“健康中国”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政治任务:高度重视,强力支持
其一,高度重视,书记挂帅。建国初,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建设,强调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要“极力发展这项工作”;要在经费等方面尽可能给予支持。[3]当时党中央和人民政府把搞好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建设问题,作为战略任务高度重视。卫生部在开展各项医疗卫生工作时,还邀请少数民族地区代表参加,并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提出具体的要求。1951年8月,卫生部遵照政务院1951年2月发布的《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定》,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卫生会议”,会议研究确定“卫生工作是少数民族地区首要工作之一,少数民族地区行政首长,必须亲自加以领导。”[4]1951年,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党组书记和主持全面工作的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工作任务》,强调:“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则应当以指导、协助支持卫生工作作为自己的政治任务。”[5]1952年开始的爱国卫生运动,地方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首长任主任委员,所属有关部门负责人担任委员组成。在实际开展过程中,少数民族地区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基本做到了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干部率先垂范。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专区的除害灭病工作,从1957年开始,经过不到三年的连续战斗便取得了显著成效,经验就在于“各级党组织加强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健全各级机构,指定各级党委专人负责。”[6]
其二,明确任务,制定方案。针对建国初少数民族地区性病、疟疾及妇产科,儿科疾病严重危害的情况,卫生部提出了逐步建立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组织,配备和培养干部等,并集中力量消除内蒙古、西藏地区的性病,以及中南、西南少数民族中的疟疾并防治妇幼疾病的任务。在1951年8月全国少数民族卫生会议之后,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同志于同年11月23日在政务院第112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全国少数民族卫生会议的报告》,该报告经会议批准,提出要“分别地区和疾病的实际情况,实行收费、减费和免费治疗”,为防治梅毒等性病蔓延,则采取免费为主。同年,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了《少数民族地区妇幼卫生工作方案》,对组织机构、培养干部、经费、宣传教育、调查研究等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卫生部也制定了《少数民族地区性病防治方案》,组织力量,大力开展了防治性病的工作。[7]此外,还向全国发布了《少数民族地区疟疾防治工作方案》、《全国少数民族卫生工作方案》等文件。[2]
其三,建立机构,全力扶持。1951年8月召开全国少数民族卫生工作会议,要求各级政府建立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机构,配备并培养少数民族卫生干部。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国家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拨付正常的卫生经费外,另外划拨卫生补助费。其他沿海、内地地区也经常从人、财、物上等方面予以支持,从而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技术人员和医疗机构都有了很大的发展。[1]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拨发人民币三百多亿元,用于少数民族群众免费治疗。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也经常派出医务卫生人员免费给少数民族人民看病并赠送药品及医疗药材。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新中国成立后三年的时间里西北各少数民族地区就建立和恢复了各级卫生机构二百三十多处。各省在派遣了大批汉族医疗卫生干部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同时,还注重培养了一批各少数民族卫生工作干部,使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医疗条件有了初步改善。[8]又如我国人口较少的鄂伦春族,千百年来,鄂伦春族人民居住的地区没有任何医疗设施,也找不到一个医生,患病后只能求神问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鄂伦春族已经濒临消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就派遣巡回医疗小分队,挨家逐户地为鄂伦春人普查普治各种疾病。鄂伦春自治旗成立后,党和政府把发展鄂伦春人口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对鄂伦春人民实行了全民族的免费医疗,制定了“面向猎民,以预防为主,加强巡回医疗”的医疗卫生工作方针,并派医务人员长年深入猎区巡回医疗,宣讲卫生知识。到1958年,严重威胁鄂伦春人民生命的天花、伤寒已经绝迹,麻疹也得到了控制。[1]
二、依靠群众:卫生宣传教育形式多样,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
“预防为主”“卫生运动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是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方针的重要内容。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就强调卫生预防工作只有积极宣传普及卫生知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卫生工作才能做好。鉴于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普遍文化水平低,迷信鬼神思想泛滥,传统习惯中有很多不卫生的陈规陋习,为此,党和政府在向少数民族地区同胞进行防病治病等卫生医疗知识宣传教育中,采取了形式多样、循序渐进的方式方法,开展耐心细致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活动,动员群众自觉行动起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自身预防疾病的能力。
其一,破除迷信,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宣讲卫生。建国初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闭塞,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中,同各种迷信保守思想展开了激烈斗争。如青海省组织了上千人的宣传队,通过辩论、回忆、诉苦、算细账、对比等办法,为爱国卫生运动扫清思想藩篱。在灭四害讲卫生运动中,做到各地书记挂帅,领导亲自动手。通过设试点的方式推广成功经验的办法,使卫生运动结合生产同时进行。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在深刻感受到爱国卫生运动的好处后,破除了迷信,讲卫生爱清洁蔚然成风,四害等疾病传染媒介得到迅速减少,1958年上半年青海省各种传染病的发病率比1957年同期下降了35.6%。[10]为使广大少数民族同胞破除顽固旧习,爱清洁、讲卫生,四川阿坝的医疗卫生工作者通过展览会、广播、幻灯等形式向群众宣讲除四害、讲卫生运动,通过努力该地区少数民族人民基本养成每日刷牙、洗脸、经常洗澡换衣的好习惯。[11]又如西北军政委员会和各省政府派出的医疗卫生工作队以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和采用歌舞、画片、幻灯、模型等形式宣传通俗的卫生科学常识。[8]
其二,推广“土方法”“两管”“五改”灭四害,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在向少数民族同胞作普及性的卫生教育时,不仅宣传教科书式除害防病方法,还注重推广民间自创灭“四害”的“土方法”。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回族农民马万太的捕鼠经验,曾在自治区各地开花结果;云南傣族老太太曹依秀和汉族妇女王翠兰,在昆明市举行有关老鼠生活习性的讲演。她们的知识和捕鼠方法受到了专家们的赞许,得到了广泛的传播。”[9]又如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历来被称为“瘴疠”之区。1950年调查显示该地区约有50 多万疟疾患者,疟疾发病率最高达到71%,最低也有17%,疟疾死亡率很高。经过大搞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和进行防病治病,这里变了样。过去“只见娘怀胎,不见儿赶街”成为历史。[9]此外,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两管”“五改”(管水、管粪,改水井、厕所、畜圈、炉灶、环境)的卫生运动中,“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塘岸大队,在两年里建成砖石机构的砂滤水池11座,联式猪栏厕所密封三格化粪池32座,猪栏385间,牛马栏296间,沼气池8座。通过这些预防措施,控制了蚊蝇孳生,减少了各种寄生虫卵和病菌,从而基本消灭了乙型脑炎、伤寒、钩端螺旋体病和皮炎。”[9]1962年,藏族人民通过医疗机构的努力和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过去在西藏比较流行的天花、麻疹、伤寒、痢疾等传染病,已开始被遏止。[12]
三、送医下乡:组织社会主义协作,建立健全医疗卫生网络
建国初期,为了弥补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缺医少药和医疗力量的薄弱及分布不均衡的不足,党和政府号召并组织广大医务人员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开展社会主义协作,全心全意为少数民族人民健康服务,并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卫生队伍建设,注重在当地训练初级卫生人员,培养又红又专的卫生队伍。经过广大支援医务工作者的努力,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医疗卫生网络。
其一,“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开展巡回医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少数民族地区卫生事业极其落后,不仅医疗卫生机构简陋而且数量极少,医疗卫生收费也很昂贵。如四川省阿坝州打一次针药,需要收费牦牛二头或青稞三石。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患病时基本采取求神拜佛的方式,造成死亡率极高。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大力培训医疗卫生队伍,为少数民族地区增添医疗设备和扩充医疗机构,并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巡回医疗。1951年卫生部陆续向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等少数民族地区派遣医疗队,据不完全统计,其中高级医疗卫生人员就达到5300余人,深受各族人民和外国边民的欢迎。[12]如四川省阿坝州,截止到1959年底,开展巡回医疗共达291万多人次,其中免费治疗就有23万多人次。[11]又如1950年北京大学医学院师生70余人利用暑假假期,组成“驱梅大队”到绥远蒙民地区进行梅毒防治,对当地性病的防治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13]通过医疗单位的努力工作和医务工作人员的忘我劳动,许多少数民族同胞恢复了健康,他们盛赞巡回医疗队员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
其二,注重培训初级卫生人员,在实践中教、在实践中学。除了派城市卫生医疗队开展巡回医疗外,为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地区医务卫生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党和政府还注重培训少数民族初级卫生人员,提高初级医疗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的覆盖率。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只有7个简陋医疗机构的阿坝藏族自治州,到1959年,仅全州公立医疗机构中,就有医疗卫生人员1300多名,各县还专门培训了2000多名农村卫生保健人员,各乡都有医疗机构或保健人员,基本建立起遍满全州的医疗保健网。[11]又如青海省乐都县,1952年在政府领导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建立了15个新法接生站;海晏县在藏族、蒙族牧区及农业区还建立起卫生小组,并在各个村训练了39个卫生员。[8]
其三,培养少数民族卫生高层次人才,建立少数民族地区专业诊疗机构。党和政府大力发展边疆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医学教育,培养少数民族医疗卫生高层次人才。从1952年起,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陆续开办了卫生学校,培养医士、助产士等。中央民族学院和部分省、自治区的民族学院开设了医科预备班,专门照顾性地招收具有相当高中程度的少数民族学生进入高等医药院校;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医学院开设了民族班,专为少数民族培养医学高级人才和管理干部。[2]从1955年起,采取老校支援新校、中专升格等办法,在这些地区新建了一批高等医学院校。如新疆医学院、内蒙古医学院等。[1]在培养少数民族卫生专业人才的同时,还大力建设民族地区专业医疗卫生机构,如西北地区青海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设立了湟中、互助、都兰等九个县卫生院;[13]1959年初,西藏地区的医疗机构仅有四十所、医务人员四百多名、病床一百多张,到1962 年,发展到一百五十七所、医务人员发展到一千五百名左右、病床发展到一千张。[14]截至1965年,“少数民族地区的医院已经发展到6275所,大部分公社(乡)已经建立起卫生院,有的生产队设有半农半医人员。”[15]
四、勤俭行医:充分利用和发展少数民族医药学,降低医疗费用
我国少数民族医药学如藏医、蒙医、维吾尔医、傣医等历史悠久,在医药卫生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医学,是中国医药学的组成部分。建国初期,少数民族地区乃至全国西医西药短缺且费用昂贵,为了弥补西医西药的不足,党和政府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医药学预防和诊治疾病,提倡在医药资源上的就地取材。由于土方草药成本低,可以就地取材、炼制方法简便,群众易于掌握,有效地实现少数民族同胞有医可治,有药可医,也使广大少数民族同胞看病治病少花钱。
其一,发动群众,搜集少数民族医药秘方,降低医疗成本。我国民族医学都有悠久的历史和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都有自己代表性的著作和相当数量的医药文献以及特有的诊疗手段,很多偏方药方散存于民间。为发挥少数民族医药学的作用,降低医疗费用,党和政府开展了耐心细致地宣传教育,动员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贡献偏方和祖传秘方,为本民族、本地区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繁衍昌盛作贡献。如195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仅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搜集到秘方验方四万六千多件,中医药书八百多册。[16]又如“在昆明举行的中医中药展览会上,介绍了受傣族丈母传授的草药医赵运,此外,还专门介绍了少数民族燃点火把防疫灭虫和“挑草子”的金针疗法等。”[17]内蒙古自治区卫生部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中医献出了各种祖传秘方和验方等三千多件,许多蒙医也热情地献出了祖传的秘方、单方、验方等。[18]
其二,因地制宜,培训少数民族医药学专业人员,建立少数民族医药学卫生机构。新中国成立不久,各级党政领导部门就开展了对具有本地区特点的少数民族医药学专业人才的组织和培训工作,不断地帮助他们进行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并予以多方扶助。如内蒙古自治区“从一九五四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和各盟、市加强了对蒙医药人员的培训,先后举办了26期蒙医进修班和研究班,使780多名蒙医通过进修得到提高,同时培养蒙医学徒500多名。一九五八年,内蒙古医学院增设了蒙医专业。”[1]自治区各地先后举办蒙医进修学校(班),建立了蒙医联合会、蒙医学术研究机构,开办中级蒙医学校,为国家培养蒙医专业人才。[19]又如维吾尔医药学不仅和中医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受藏医、蒙医以及阿拉伯、印度、古希腊医学的影响,维医集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5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和田县成立了卫生工作者协会和维吾尔族第一联合诊所,在喀什、乌鲁木齐、伊宁、哈密、库车等地相继建立了民族联合诊所和医院。[1]
其三,重视少数民族医药学研究,完善少数民族医药学体系,提高防病治病能力。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影响下,少数民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都非常重视发展少数民族医药学,并逐步建立起各民族医药学比较完整的医疗、教学和科研体系。1956年,内蒙古自治区建立蒙医科学研究机构,聘请知名蒙医专门发掘、整理、研究和编译蒙医药学遗产工作。1961年又发掘出300多年前的《但教经》和其他蒙古医学古代史料。以古纳为首的许多著名蒙医根据自身成功经验,写出了有关蒙医医疗小儿麻痹症、精神病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并编写了蒙医名辞词典和蒙医药物手册。著名蒙医老大夫敖玺臣以蒙汉两种文字把自身从医50年的心得和经验整编成《妇科病》 《伤寒》 《小儿病》等书稿。此外,还组织编写出蒙药学、蒙医诊断学、蒙医针灸与放血术以及蒙医外科学、内科学、儿科学、妇科学等讲义和资料。[19]又如傣医是云南傣族的传统医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州卫生科、州政协联合成立了西双版纳州民族医药研究室,吸收了各阶层的民族医药人员参加傣医药的整理研究工作,收集傣医药手稿100多册,并附设傣医门诊,深受各族群众的欢迎。[1]
五、结语
建国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少数民族地区医疗卫生建设发展迅速,少数民族群众盛赞:“毛主席的满巴(医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建国初少数民族医疗卫生建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成功的经验就在于:党的高度重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成功的关键;充分依靠群众,教育群众强化卫生意识,发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注重预防是成功的基础;发扬社会主义互帮互助精神,组织社会主义协作,建立健全医疗卫生网络是成功的组织保障;因地制宜,发展和利用少数民族医药学防病治病进而做到廉俭行医是成功的重要因素。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开展的各项建设必须重视本民族的历史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正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发展“健康中国”建设的伟大事业,只要认真继承和充分借鉴以往的成功经验和好做法,努力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充实新内容,创造好的方法,“健康中国”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