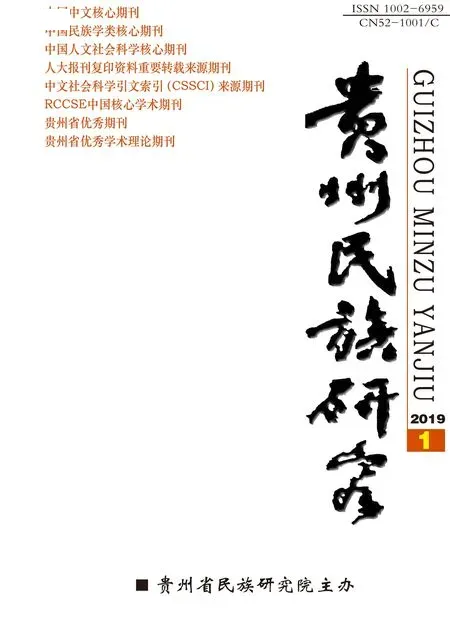民族地区跨文化艺术折射的心理反映
袁 月 吴永强
(四川大学 艺术学院 四川·成都 610000)
所谓民族艺术是少数民族在社会生产生活中依托生活环境和人文环境创造、演绎的富含民族特色的艺术与形式,比如:音乐艺术、舞蹈艺术、服饰艺术。民族艺术的文化点缀与镶嵌使艺术的审美与群体情感寄托得以超脱艺术本身形体承载。但是民族艺术表达的文化扩张和延展使“艺术文化”逐渐向“文化艺术”让渡,换言之,民族艺术的审美在文化差异的掩盖下逐渐泯灭。比如对独龙族“纹面艺术”的研究基本上着眼于简单脸庞纹样态势的粗略分析,本身艺术的魅力基本上聚焦着纹面艺术的人文情怀和心理情感折射。民族地区跨文化艺术的心理折射需要民族艺术的审美性与民间性诠释以跨文化视域的适应与接纳为基础,使跨文化艺术的本体性艺术锻造以民族情感的表露为艺术的核心驱动。因而透过文化与艺术,以民族心理为基调,探究民族艺术的魅力所在,成为跨文化艺术比较中稳定性维度之一。
一、民族地区跨文化艺术的渊源与形态探究
(一)文化视域下的民族艺术形态
所谓民族艺术是少数民族在社会生产生活中依托生活环境和人文环境所创造、演绎的富含民族特色的艺术与形式。民族艺术的发展离不开特定地域环境[1],跨文化视域下民族艺术认知与审美定位需要突破艺术文化的面纱,以真善美的心态和全球化艺术交流趋势下的思维定势审视民族艺术。就民族艺术的社会可视化形态而言,民族艺术以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为主,视觉艺术在民族艺术发展轨迹中不断扩展,从艺术的自然浓缩到艺术的时代嫁接,民族艺术在发展中始终以民族文化的内在反映为主线,以民族群体的情感认同为价值观指引。特别是民族雕塑艺术和剪纸艺术等视觉传达设计对民族文化的依赖和民族情感的释放尤为显著。比如:裕固族“转经轮”浮雕、格萨尔王人物雕塑等,在情感故事和宗教文化的包裹中裕固族典型的“根雕艺术”和“造型工艺”魅力几乎被人文元素所湮没。听觉艺术以民族音乐艺术为主,民族音乐艺术在发展中基本上以民族传统文化为题材,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效载体,特别是民族音乐的仪式承载,同样也使得民族音乐艺术的美学呈现以独具特色的器乐与典型声乐的强调为基础,民族音乐艺术的文化蕴意成为艺术的主导和民间性集中折射。比如:哈尼族《跳丧舞》和瑶族《盘王歌》在音乐艺术的要素剖析中艺术的本身魅力基本上被轮回转世、灵魂不灭的传统文化所掩盖。总之,跨文化视域下民族艺术的形态认知与深究务必要在认同民族传统文化适应民族文化基础上,以艺术外在的形态捕捉民族心理情感的变动,从而更深切地领略民族艺术的“形美”与“意韵”。
(二)文化视域下的民族艺术渊源
民族艺术的形成与发展始终以传统民族文化的塑造为中心,使得民族音乐艺术“音而非乐”的仪式音乐占据着民族音乐的主导地位[2]。比如:哈尼族《跳丧舞》意不在音乐的享乐与愉悦身心,而是哈尼族自然宗教文化和传统孝道文化的心理折射。跨文化视域下民族艺术的渊源基本以自然艺术的模仿、文化习俗的艺术白描、个体心理情感的释放的发展源头为基石。对自然的模仿是早期民族艺术最为显著的特征,一方面,民族地区的传统民族艺术基本上是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自然临摹;另一方面,民族群众在同长期依山傍水的自然生活中,逐渐形成了“敬畏自然”的群体心理,民族艺术中对自然临摹是对自然的敬畏、感恩的民族心理,比如:鄂温克族等游牧民族在绘画、环境艺术设计中多注重水元素的植入和山水元素的临摹,彰显着游牧民族对自然界无独有偶的敬畏与感恩。文化习俗的艺术白描是民族艺术渊源的枢纽。民族艺术的美学构建基本以民族传统文化为骨骼,艺术是民族传统文化习俗审美手法的艺术塑造。比如:怒族群众认为万物有灵,在绘画中通常以“水神”“火神”“土神”为主,除干栏式竹楼的构建不受自然宗教文化的影响外,服饰艺术、装饰艺术等基本上都依托自然宗教文化。侗族特色建筑艺术“风雨桥”也是对图腾文化的艺术直白。个体心理情感的释放是跨文化艺术比较和民族艺术审美的最为稳定的艺术表达[3]。比如:土家族音乐《哭嫁女》除音乐元素外最为显著的便是对父母依依不舍心理情感流露,白族服饰艺术以白色为主彰显着白族色彩忌讳的心理。当然,从文化视角审视民族艺术主要是民族宗教文化、图腾文化等典型传统文化的有效演绎。
(三)文化视域下的民族艺术特征
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有机结合。换言之,民族艺术的显著文化表达是其最主要的特征。一方面,民族艺术在发展中文化韵味逐渐占据了民族艺术的审美航标,民族传统文化成为民族艺术的灵魂。比如:藏族群众《砌墙歌》的音乐艺术旋律则基本上被热爱劳动的群体情怀所笼罩,艺术成为文化表达的有形载体。另一方面,民族艺术的粗造性使得民族艺术外在审美和艺术评价总是以文化蕴意弥补艺术要素的欠缺。比如:珞巴族的舞蹈动作多以模拟动物鸟兽的形态,就舞蹈艺术优雅和舞姿而言:珞巴族传统舞蹈与同时期中原舞蹈艺术相差较大,但是动物崇拜的民族文化成为舞蹈艺术的有效补充。民族艺术的民间性、多样性是文化视域下民族艺术特征的重要特征之一,民族艺术的民间性是民族艺术维度最为宽广的特征,民间性是民族艺术地域性、民族差异性的总和,一方面,不同民族之间艺术差异特征也尤为突出,比如:同是“花儿”艺术的发展地,但是临夏东乡族花儿和回族花儿无论在艺术表达还是文化蕴意也具有着明显的差异[4]。另一方面,同一民族艺术的不同地域差异影响也不断延伸。比如:苗族刺绣的地域性差异在实际生活中尤为突出。黔东南苗族刺绣注重针线的细腻和图案的对称,而云南地区苗族刺绣的民族独特性基本上荡然无存。
二、基于时空维度的民族艺术性群体心理折射
(一)基于时间更替的民族艺术审视
跨文化艺术的群体心理折射是艺术灵魂铸就和人文价值取向现代转换的必要选择。民族艺术的文化性和多元性需要以民族思维定势和情感取向为准绳,在民族艺术岁月更迭的洗礼中彰显特色民族艺术魅力。基于时间更替的民族艺术审视要以古代、近代、现代为节点,使民族艺术的文化蕴意与心理情感折射依托并表露于艺术形态的基本框架边缘。古代民族艺术的发展是艺术内外驱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古代民族艺术的审美构建主要以民族艺术的群体性仪式表达为主,换言之,民族艺术的发展不是以艺术的本体为主轴的发展而是民族艺术发展辅助于民族群体社会运行与管理的需要,比如:阿昌族服饰设计艺术除色彩审美的喜悦外,男士以蓝色、白色的对襟上衣为主,主要衬托阿昌族群体父权社会的威望,而在社会制度转变的过程中服饰艺术中的权力色彩有所褪色[5]。另一方面,民族艺术的发展源于民族融合中多民族艺术的嫁接和移植,民族艺术间的混同逐渐强化。比如:回族、撒拉族、回族等少数民族“花儿”艺术在表达形式方面基本趋于一致。近代民族艺术逐渐摆脱了民族传统文化仪式的捆绑,民族艺术逐渐成为民族社会元素中的独立领域。比如:傈僳族在古代自然崇拜中以水鬼——埃杜斯尼为主的绘画艺术涉及建筑装潢等诸多领域,但随着近代基督教的传入,宗教信仰改变所引起的艺术变异屡见不鲜。特别是以火为图腾纹样的艺术设计逐渐减少。西洋元素逐渐充盈到民族艺术设计中。现代民族艺术同艺术设计技术相关联,民族艺术的现代化气息逐渐明朗,民族艺术的审美视觉也逐渐现代化。
(二)基于时间更迭的民族艺术群体心理折射
跨文化艺术的群体心理折射是艺术灵魂铸就的关键,基于时间更迭的民族艺术群体心理折射是跨文化视域下民族艺术最为裸露、最为真挚的价值所在[6]。总体而言:一是古代民族艺术的群体心理折射的简易明了,古代民族艺术的创造基本依赖于自然界的元素符号,或模仿动物姿势、植物抽象符号等,一方面,通过对自然的热衷,折射出少数民族在落后生产力面前积极乐观的心理,这是民族艺术傲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根本原因,艺术对群体生命轨迹的朴素性写照,是民族群体不断发展的动力所在。比如:藏族群体音乐《砌墙歌》,通过对自然劳动场景的白描彰显着藏族群众不辞辛劳、乐观向上的群体心理[7]。另一方面,对于自然崇拜和坚信万物有灵的民族群体而言:在绘画、音乐、舞蹈、雕刻等艺术表达中对动植物的模仿则折射着少数民族群体基于宗教神秘主义的驱动,赋予自然界超凡力量,旨在通过模仿寄托群体自然敬畏的心理,比如:怒族在“尼玛”(祭祀)中通常以模仿自然树木的舞姿“达比亚舞”祈求自然神灵的庇佑和对水鬼等鬼神的敬畏,即折射着群体祈求庇佑和诚恳的敬畏心理。二是近代民族艺术对民族群众反压迫、反剥削的抗争心理的折射。比如蒙古族群众音乐《江格尔》通过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在聚焦民族认同心理的同时折射着反压迫剥削的心理。三是现代民族艺术对新时期社会生活的歌颂与热爱[8],比如傈僳族群众在传统音乐特色“颤音”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的生活阅历创作了新的音乐形式“颂歌”,通过新旧对比折射着傈僳族人民对新社会的热爱心理。此外,回族“花儿”通过对小康社会的憧憬,折射出民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热爱。当然,民族艺术对群体喜怒哀乐的情感流露是民族艺术情感折射的常态化。
(三)基于空间维度的民族艺术变迁
跨文化视域下基于空间维度的民族艺术变迁是民族艺术地域性差异和民族艺术间彼此碰撞的结果。具体而言:民族艺术的空间维度变迁主要体现在民族艺术融合中以嫁接与移植为主要形式的原生态民族艺术的统一。一是跨文化艺术的审美以摒弃民族文化的艺术点缀为基石,通过对繁琐民族文化的拆解,透析民族艺术粗中包致的艺术魅力,使民族艺术的地域性、民间性以艺术应有的体态承载,进而使民族艺术的变迁转化为对民族艺术地域性、民间性的解读。比如裕固族、藏族的音乐、舞蹈等艺术都受藏传佛教的影响,跨文化视域下艺术地域性差异突破了祁连山的阻碍,使之成为游牧民族艺术的群体认同差异[9]。二是民族融合中民族艺术的民族性空间差异的放大,在民族融合中少数民族艺术交流为民族艺术间的融合提供了天然桥梁,民族艺术发展中的不断糅合,民族艺术之间的特有形式逐渐被共享,基于空间维度的民族艺术变迁逐渐向艺术表达手法、艺术情感的表露转移。一方面,同一民族艺术的民族性逐渐淡化,比如:回族、东乡族“花儿”艺术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除特定情感表露外表达形式基本一致。另一方面,不同民族艺术在糅合中民族性逐渐弱化,民族性的差异基本上以跨文化视域下的群体心理折射所替代。
(四)基于空间维度的民族艺术群体心理折射
基于空间维度的民族艺术群体心理折射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族艺术在空间维度变迁中以艺术为载体的喜怒哀乐常态化释放,比如蒙古族音乐艺术《马儿马儿快快跑》以欢快的节奏,折射着群体欢快的心理,而婚嫁音乐《哭嫁女》却折射出传统文化习俗影响下的矛盾心理——喜中生悲,当然,以建筑艺术、城市环境设计艺术等为主体的民族艺术在民族群体心理反映中往往以中性情感示人[10]。二是基于空间维度的民族艺术在民族融合中凸显的强烈民族认同情感和民族自豪心理。比如:蒙古族在工艺艺术“科库尔”制作中夹杂着复杂的民族心理,但是以“科库尔”牛头雕刻的设计折射出新疆蒙古族与乌海蒙古族共同的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认同心理。
三、基于“形美”与“意韵”的群体心理折射
民族艺术心理从自然到人文的过渡同自然与人文锻造下的民族心理表露是基于“形美”与“意韵”下群体心理反映的关键[11]。一方面,民族艺术中对于审美美学心理的追求是跨文化视域下民族艺术“形美”不断被大众接纳认同的关键所在,比如仡佬族民间文学艺术《阿仰兄妹造人烟》《竹王》等通过对勤劳、聪明的赞美,折射着民族群体是非心理以外民族审美情感。另一方面,民族艺术中通常以艺术形态外在的魅力折射民族群体心理,特别是针对男女情爱等难以表达的情感心理,少数民族群众通过艺术形式来表达。比如:“顶翁罗”是仡佬族青年吐诉爱慕的舞蹈,他们通过舞蹈化解语言表达的羞涩与尴尬,折射着民族群体爱慕、羞涩的心理。总之,无论何种形态的民族艺术,跨文化艺术下民族群体心理的折射是民族艺术最为显著的精髓,就民族群体心理而言:艺术只不过是群体心理表露的镜子而已[12]。
新时期民族地区跨文化艺术下的民族心理情感聚焦必将以民族艺术最为开放的姿态塑造全球化视域的艺术美学,以人民最为迫切的心理,以最为简易的艺术符号构建艺术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民族艺术作为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载体,是民族群众以剪纸、雕塑等形式表达着对民族伟大复兴的情感认同。在决胜建成小康社会时期,民族艺术终将是民族心理最为归一、最为强烈的时代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