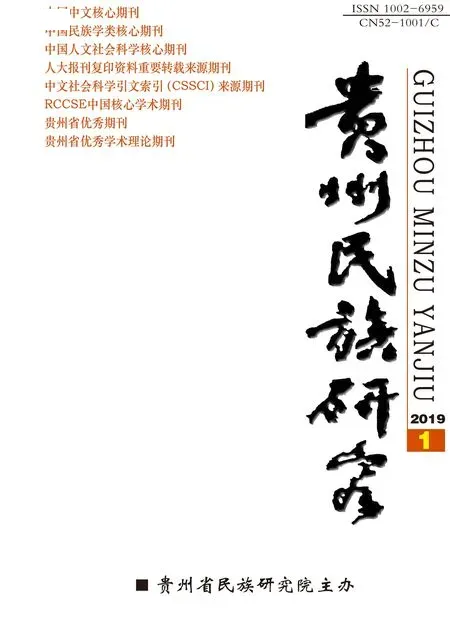蒙古文法典中的法文化研究
王宏庆
(吉林大学 法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北华大学 法学院,吉林·吉林 132013)
在蒙古族长久的发展历史当中,蒙古文法典也经历了多次改进与完善,最初蒙古高原诸部落遵循的是习惯法,即部落习惯与宗教诫令;至蒙元时期,成吉思汗制定并颁布了蒙古族的首部成文法典——《大札撒》;北元时期,蒙古统治者已退出中原,内部纷争日趋激烈,各封建主积极推进立法,以期治理好动乱时期的蒙古,蒙古文法典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清朝时期,清政府为更好地统治蒙古部落,先后制定并颁布了众多法典,目的在于加强其权力的渗透。蒙古文法典的发展,贯穿在蒙古族发展的全过程,对其中法文化的研究,有利于对蒙古族历史及整体民族文化的了解。
一、蒙古文法典评介
蒙元时期,成吉思汗制定并颁布了蒙古族的首部成文法典——《大札撒》,虽这部法典的原文已经失传,但其部分内容散见于《史集》 《蒙鞑备录》 《蒙古秘史》 《马可波罗游记》等典籍中,通过大量的文献研究能够证明,《大札撒》代表了蒙古族法制史上依法治国的开端,甚至可以说,这部蒙古文法典,奠定了横跨亚欧大陆的世界帝国建立的基础。不可否认, 《大札撒》 的颁布,对于蒙元帝国管理民族事务以及提高民众的认同感和凝聚力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却也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比如在军法以及刑法的条款方面的处罚十分严重。
成文于16世纪的《十善福经教白史册》,旨在对佛教的“十善”理念进行宣传,并争取建立一个皇权与教权分立并行的神权国家。在这种统治体系当中,法王国师与皇帝享有同等地位,各执其政。当前,学界对于这部蒙古文法典仍有很多争论,如刘金锁先生认为其成文于13世纪,是忽必烈的作品;而鲍音先生则认为,这部法典名义上为忽必烈颁布的,实际上则是呼图黑台·彻辰·洪台吉等为传播黄教而制作的伪书。无论《十善福经教白史册》的真实作者是谁,其宣扬的佛教思想,对后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阿勒坦汗法典》的颁行,可以看到二者理念有诸多契合之处。
《阿勒坦汗法典》是一种地方性的法规,由阿勒坦汗颁布,与《十善福经教白史册》相同,意在推行政教并行的政策。整部法典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且将法律维护的对象扩展至社会各阶层百姓。《阿勒坦汗法典》的颁布和推行,对蒙古族统治的加强方面以及促进黄教的传播方面,都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对当时民众的法律思想,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甚至对促进当时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价值。
此外,《白桦法典》的颁布与执行,在相比于其他法典,对私法的规定更为细致,有明显的进步,但关于刑事法规中的惩罚力度,仍然较为严苛。《白桦法典》对《蒙古-卫拉特法典》及后来的《喀尔喀法典》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喀尔喀法典》,在其制定过程中,相关内政、婚姻、治安等方面的内容,有很多源于《白桦法典》。而《蒙古-卫拉特法典》出现的时期较为特殊,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期,不仅沙俄向东进军,清政府的兼并实力也日趋强大,而《蒙古-卫拉特法典》就是为了巩固当时喀尔喀、卫拉特蒙古僧的封建统治而颁布的一部蒙古文法典,其中明确了喇嘛教的唯一宗教地位,正式禁止萨满教与翁滚在蒙古族境内的传播。
除上述法典外, 《青海卫拉特联盟法典》《阿拉善蒙古律例》等,对于蒙古族的政权巩固、统治改革等,也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对蒙古族法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蒙古文法典中法文化的特点
文化是一个较为广泛的概念,可将其视为一种社会现象,是民族、团体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也可将其认为一种历史现象,由社会历史积淀而成。文化涉及的领域与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习俗、制度、规范、宗教信仰、语言知识、礼仪礼貌等等。这种形成、存在、传承特点,让文化同时具有独立并固定的传统性、较强的适应性与变革性。法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也同样具备这些特点,而与其他文化不同,法文化的载体——法律是立法者为了实现其统治意图,对各种社会关系、需要以及社会规范的一种制度化转变与升华,更是当时社会物质条件、国家与民族意志、阶级意志、社会存在等的体现。因此,法文化也就是制度与规范领域当中,民族共同体独特的价值体系以及社会行为等进行规范以及制度化的具象体现。
对于法文化的研究,我们需要对法典进行研究,这具有一定的必要性。所以,在研究蒙古法文化的过程中,同样应重视对蒙古文法典的剖析,上文当中列举的几部蒙古文法典,虽颁行时间和意图有所不同,但就其整体内容而言,却也多有重合之处。例如,各部法典当中,为巩固王权,都着重要求民众应对统治阶级忠诚;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妇女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对于偷盗、叛变等背信弃义之人,也制定了严厉的惩罚制度。是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蒙古文法典所反映的法文化也不尽相同,例如,由于《大札撒》颁行于元朝建国初期,为巩固皇权,对军事法十分重视,且保留了习惯法当中的大部分内容,用于规范社会民众;也纳入了大量的审判、祭祀、禁忌等神权法习俗;成吉思汗也通过法律制度,对当时的宗教势力进行了有效的制衡。发展至北元时期,由于王权旁落,导致蒙古族的统治政权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各部首领分崩离析,由此提出了会盟立法活动。
通过对蒙古文法典的研究,能够对蒙古的法文化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包括孝道、忠义、行善、团结、互助、诚实等价值观念。在众多法律当中,要求民众尊重长辈与统治者;对于犯下偷盗、叛变、进谗言等罪行的人要严惩;在司法审断的过程中,应以有力的证据作为审断的依据;在发生自然灾害之后,统治阶层应及时向受灾地区展开救援,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救济制度。多数蒙古文法典,都经历了较长的编纂实践,这与蒙古族生存地区地广人稀,法律的制定多以社会现状为依据,并需要在间断的会盟过程中,不断累积成熟,进而形成较为完善的法典相关。本文认为,蒙古文法典中体现出来的法文化特点,与其游牧生活习俗有很大关系。
三、对蒙古文法典中法文化的分析
(一)蒙古文法典中的宗教立法及法文化
通过蒙古文法典来分析蒙古族的法制历程,能够发现其法文化当中,处处体现着务实、宽简的特点。不同时期的蒙古文法典,虽由于社会背景的变化而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但其指导思想却较为统一,例如,很多法典当中提到,从灾害当中救出人或动物,都可获得相应的奖励,《阿勒坦汗法典》当中提到,每从火灾、沼泽或河流当中救出一峰落难的骆驼,救助者可获得一只上好的绵羊作为赏赐。
蒙古族作为游牧民族,长期生活在地域广阔的蒙古高原上,人们在出行过程中,往往需要向途径的住户寻求饮品或食物,以保证自己不在途中饿死。对于此种社会现状,有文献表面,《大札撒》当中曾明确规定,路人食用主人家的饮品或食物,可不必经过主人的允许。在《阿勒坦汗法典》也同样保留了这条规定。而在《蒙古-卫拉特法典》中则规定,若主人拒绝向远行口渴的客人提供饮食,罚绵羊一只。
在蒙古文法典当中,能够明确感受到蒙古人注重内部团结、宽厚仁爱、互助互信等立法指导思想。而随着佛教逐渐传入到蒙古社会,蒙古族的统治体系逐渐出现了“政教二道”并行的趋势,在中世纪左右,蒙古文法典当中对佛教的赞美更为普遍,久而久之,佛教文化的传播已经逐渐成为了蒙古法律的指导性的立法原则。
佛教文化对蒙古法典中的法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如《十善福经教白史册》颁行后,蒙古族的统治体系开始实行政教并行的治国政策,通过法律赋予了佛教高僧以崇高的社会地位和特权,这导致当时的蒙古族统治时期,形成了较为特殊的社会阶层。[3]在北元时期,更是打破了以往宗教制衡的发展状态,在禁止萨满教与翁滚传播之后,将佛教放置到了唯一宗教信仰的地位上。随着佛教黄教在蒙古族统治地区的不断扩散,导致此后蒙古文法典中的法文化,受到了更多佛教文化的影响,如在《阿勒坦汗法典》明确了宗教与行政立法并行的统治模式之后,卫拉特和喀尔喀等蒙古贵族也纷纷效仿,这从此后的许多蒙古文法典均以佛教训言为序即可看出,且在每部法典当中,都着重强调了保护寺庙、尊重喇嘛权益等内容。
清朝统治时期,满族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用蒙古社会对佛教文化比较推崇的社会实际,免除喇嘛的兵役、徭役与赋税等,可以推动黄教势力在蒙古族境内的不断扩大。由清朝统治者制定的蒙古文法典,在扩大佛教文化对蒙古族底层人民的影响的同时,削弱了教权对政权的影响,在巩固清朝统治政权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二)蒙古文法典中的行政立法及法文化
在蒙古文法典当中,行政立法与法文化之间的联系极为紧密,这与行政立法与政治体系具有较强的变革性关系很大。在蒙古文法典当中,官僚体系随着社会背景的变化,也曾几经改革。大蒙古国建立之后,成吉思汗就制定了千户制,其基本原理就是将属民按照地域划分成万户、千户、百户、十户,此后,蒙古族统治阶级采用的行政立法与政治制度,以千户制为核心。大蒙古时期,怯薛制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政治制度,制度名称的含义即为“轮班守卫制”,怯薛可被视为成吉思汗的守卫军,同时,由于队伍当中编进了许多那颜与自由人的子弟,使其成为了防止地方贵族反叛的一种有效手段。
此后,大蒙古国时期的法文化与相关法制规定在很长时间内得以延续,且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至元朝时期,忽必烈采用了“蒙汉藏分而治之、各依其俗”的统治手段,以汉法制汉人,而对吐蕃则施行“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政策,将蒙古社会的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移植到吐蕃境内。[4]北元时期,蒙古族的统治政权逐渐没落,已经不再是帝国政权了,官僚体系也一再发生变动,千户制逐渐转变成了鄂托克制度。到了清朝统治阶段,蒙古社会的官僚体系再一次发生变化,清朝统治者则施行较为灵活的政策,让他们能够在接受统治的同时,享有一定的自主权,以巩固清朝的统治地位。
不同时期对蒙古文法典当中,其行政立法都体现了当时蒙古社会的统治特点,这也是蒙古文法典中,法文化的有效体现。
(三)蒙古文法典中的刑事立法及法文化
在成吉思汗统治的大蒙古国时期,蒙古文法典中的刑法内容,可划分成六大类,分别是杖笞、斥罢、籍其家、罚畜刑、流放刑、死刑;元朝时期的刑罚体系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其中,将杖刑、流刑、徒刑、笞刑以及死刑作为主要内容,元朝时期的刑事处罚,在蒙古文法典当中明确设立的诸多不平等原则,包括主奴、僧俗、良贱之间,蒙古人和汉人以及色目人之间同刑而不同罚等不平等原则。北元时期,通过《阿勒坦汗法典》对刑法的种类进行了细化,刑罚体系涉及杀人、过失杀人、殴打伤人、偷盗、逃人等诸多方面,但所定处罚内容,为不同数量的罚畜刑,而不适用死刑。《蒙古-卫拉特法典》中涉及到的刑罚体系更加丰富,除杖笞、斥罢、籍其家、罚畜刑、流放刑外,增设了监禁、握斧立誓、烫烙印、将罪犯卖与他人等。清朝统治阶段, 《喀尔喀法典》及《阿拉善蒙古律例》中的刑罚体系,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融合了蒙古族统治下的习惯法、刑罚制度以及中原法。这些法律制度逐渐融合在同一部法典当中,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这种形成特点,使其并未因法文化差异而在法律执行过程中发生冲突或排斥现象。
清朝的蒙古律体现了“刚柔并济”的特点,无论是《蒙古律例》还是《理藩院则例》,都以中原制度为依据设立了裁判制度与诉讼手段,这种司法与行政的结合,让蒙古文法典当中的法文化,融入了更多的中原文化。[5]
在蒙古族的发展历程中,作为游牧民族,其生存环境相对较为恶劣,且所处蒙古高原地广人稀,人口并不兴旺,这种社会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蒙古文法典的颁行,对死刑并不推崇;后续又受到佛教文化的很大影响,对生命的重视程度空前提升,体现在蒙古文法典当中,一度取消了死刑这种处罚方式。由此可见,清朝时期蒙古文法典当中,引入的凌迟处死、斩立决、绞刑、刺字等中原特有的刑罚规定,违反了蒙古社会的立法原则与法典精神。
(四)蒙古文法典中的民族习惯及法文化
蒙古族作为游牧民族,其生存环境与社会行为特点等,导致相关规范化与制度化的统治有一定难度,相关民族文化习惯,就成为了约束其思想与社会行为的主要因素。在大蒙古国建立之后,相继颁行了众多蒙古文法典,而在这些法典当中,对于蒙古族的民族文化习惯与习俗进行了保留与延续。
例如,蒙古文法典当中体现的蒙古人的婚姻观与家庭观,就是对蒙古族习惯的一种延续。在古代蒙古社会当中,女子只能嫁与外族男子,同一氏族内的男女不能通婚;在母系氏族制的影响下,蒙古族外婚制当中,还保留着入赘的习俗。这类婚俗在北元时期《阿勒坦汗法典》当中仍有明确规定,可见蒙古族的习惯法对蒙古文法典订立与颁行的深远影响。
除外婚制,蒙古族当中还设有收继婚习俗,在一个家庭当中,若父亲死亡,则其子可继承亡父的妾(除生身母亲之外),纳其为妻;若兄弟死亡,则死者兄弟可将其嫂或者其弟媳作为自己的妻子。[6]收继婚习俗在后续的蒙古文法典当中,也都有所继承。
四、结语
探究蒙古文法典中的法文化,对研究古代蒙古社会的统治特点、社会阶级特点等,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别从宗教、行政法、刑事法等角度着手,对蒙古文法典中蕴含着的法文化进行分析,以期能够了解不同统治时期,蒙古法文化的独特之处与共通之处,有利于拓宽学界在研究蒙古族历史及文化时的观察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