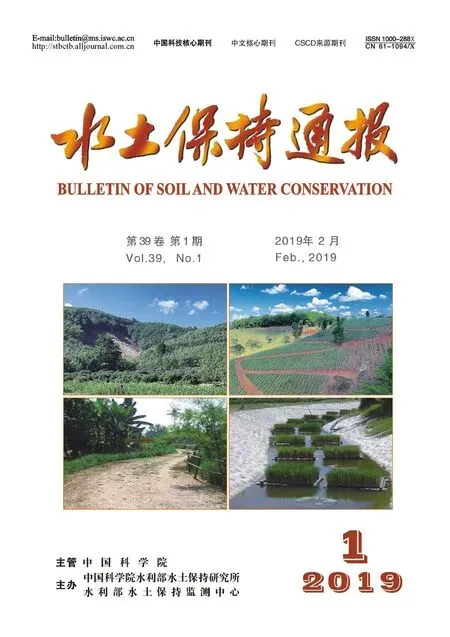特大暴雨条件下小流域沟道的泥沙连通性及其影响因素
——以陕西省子洲县为例
张意奉, 焦菊英,, 唐柄哲, 陈一先, 王 楠, 白雷超, 王颢霖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水土保持研究所 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陕西 杨凌 712100;2.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陕西 杨凌712100)
黄土高原作为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其水土保持及其对黄河泥沙变化的影响一直是相关管理部门和学术界关心的热点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家对黄土高原实施了一系列的水土流失治理。在实施大规模退耕还林(草)与淤地坝建设等一系列生态修复工程后,侵蚀环境明显好转,入黄泥沙显著减少,黄河潼关水文站年均输沙量已由20世纪70年代前的1.60×109t锐减到2000—2015年的2.57×108t,特别是2010—2015年平均仅为1.65×108t,已明显改变了以往人们对黄河泥沙的认识,被认为控制到了人类活动影响之前的程度[1]。然而,在流域出口监测的输沙量是把整个流域内部当作“黑箱”处理,很难解释整个流域内多重尺度上的土壤侵蚀过程与程度[2-3]。近期发展起来的泥沙连通性概念,指流域内泥沙通过分离与输移从源到汇的传输程度[4],可刻画流域侵蚀产沙与泥沙输移过程及其时空变异特征[5],弥补流域出口输沙量信息的不足,而成为土壤侵蚀与泥沙输移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与研究的热点[6],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基于过程的流域侵蚀产沙动态的研究[7-8]。
连通性及其相关概念最开始是地貌学家提出的[9]。连通性可分为景观连通性、水文连通性和泥沙连通性,其中景观连通性是指地貌之间的物理联结,如坡面到沟道;水文连通性是指在径流过程中,径流中物质、能量、有机质以及径流内部元素之间的连接;泥沙连通性是指通过泥沙分离和泥沙输移使泥沙从源到汇的运输[10]。在泥沙连通性评价方面,泥沙输移比(SDR)[11-12]等可用来反映流域的泥沙连通性;图论也被用于泥沙连通性评价,反映泥沙路径的网络结构及上下单元的功能连通性[13]。目前,更多的研究借助GIS分析方法和预报模型,计算能够反映土壤侵蚀和泥沙沉积潜力的区域及景观单元间联系的地貌学指标来评价泥沙连通性[14-15]。其中,Borselli等[16]基于地形特征,提出了坡沟到河流泥沙输移的横向连通性指数(IC),可提供源与汇潜在的连接信息。在随后的研究中,Cavalli等[17]在对该IC指数的坡度、泥沙贡献面积及权重因子的计算方法进行了改进;Gay等人[18]通过引入反映景观渗透和饱和特性的参数对IC指数进行了修正;Vigiak等[19]将IC指数与SDR结合起来评价泥沙连通性。另外,流域泥沙贡献有效面积也被用来作为评价流域泥沙连通性的指标[6,20]。然而,基于地形的IC指数和流域泥沙贡献有效面积只能表征流域潜在的泥沙连通性,不能反映流域泥沙连通性的实际状况,而且目前针对连通性的实地观测研究并不多[21]。在黄土高原,关于连通性的研究也刚刚起步,目前仅见于相关综述性文献[22],以及少数相关研究,如基于人工降雨模拟试验的坡面水文连通性[23]、Liu Yu等[6]采用流域泥沙贡献有效面积和开关值(源和汇流路上的最小产沙量)评价黄土高原小流域的泥沙连通性。
沟谷纵横是黄土高原的一大特点,沟道是径流对地表产生冲刷、搬运形成的线性排水排沙渠道[24],可将坡面径流和泥沙有效输移到沟道乃至河流[25]。黄土高原经过多年的生态恢复及水土保持工作,在一般降雨条件下,坡面侵蚀已基本得到了控制,淤地坝也会出现无沙可淤的现象。但是,随着近些年极端天气的增加,暴雨条件下的土壤侵蚀及洪水危害依然严重。同时,黄土高原沟道受人为的干扰性也在增大,沟道的形态以及沟道内泥沙的输移过程也发生了改变。因而,沟道泥沙连通性及泥沙输移过程也成为解释河流泥沙变化原因的重要方面。为此,本文以陕西省子洲县为例,调查与分析“7·26”特大暴雨后小流域沟道的泥沙连通性,研究大暴雨下小流域沟道泥沙的连通程度及影响因素,以期为黄河泥沙变化原因分析及沟道防洪措施的布设提供依据。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本研究在陕西省子洲县(东经110.03°,北纬37.62°)境内进行,研究区位于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土质疏松,多柱状孔隙,粉粒含量占60%以上[26]。具有干旱少雨的大陆性气候特征,据1971—2017年的实测资料可知,多年平均降雨量为434.4 mm,降雨季节比较集中,年降雨量的70%集中在6—9月,且多为强度大、历时短的暴雨,实测最大降雨强度达3.5 mm/min;年平均温度为9.5 ℃,年温差比较大,最高温度达41.1 ℃,最低气温至-25.7 ℃。霜冻期约为半年,风力最大9级以上[26]。由于该地区地形破碎,地势陡峻,洪水具有陡涨陡落、历时短的特点,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本研究在子洲县城的城西选择了水库溃坝的清水沟小流域,并以毁损程度较低的蛇家沟小流域为对比,流域面积分别为5.91 km2和4.72 km2,清水沟直接汇入到黄河中游无定河的一级支流大理河,而蛇家沟汇入大理河的一级支流岔巴沟流域。清水沟和蛇家沟的流域面积相近,但清水沟流域为扇形而蛇家沟流域为长条状,且清水沟内的淤地坝为并联坝系而蛇家沟淤地坝为串联坝系。此外,在清水沟出口修建有水库,为子洲县城的饮用水源地,总库容3.70×105m3,在“7·26”暴雨中水库发生溃坝,损失和危害严重。
1.2 “7.26”暴雨情况
2017年7月25—26日,黄土高原无定河中下游地区遭遇特大暴雨,降雨历时8 h,无定河流域面平均降雨量为67.5 mm,其支流大理河流域面平均降雨量为139.0 mm,子洲县雨量站降雨量为206.6 mm,其中最大1 h(26日1—2时)降雨量为52.0 mm[27-28]。同时,该次暴雨洪水流量和含沙量高,大理河绥德站洪峰流量达3 290 m3/s,最大含沙量达837 kg/m3,是1959年建站以来的最大洪水;小理河李家河最大含沙量为260 kg/m3,岔巴沟曹坪站为271 kg/m3[29]。子洲和绥德县城受淹,水深可达3 m,泥沙大量淤积,淤积量约为1.40×107t[29]。
1.3 沟道淤积情况调查
依据坝地和自然沟道两种类型,对清水沟和蛇家沟沟道的淤积情况进行实地观测。对于坝地,根据坝地宽度和实际淤积情况确定观测点位置,通过开挖挖槽,根据玉米气根位置以及土壤分层情况确定并测量此次暴雨坝地内泥沙淤积厚度;当坝地宽度≥50 m时,在坝宽的1/3和2/3的位置处取平行的两排观测点,求其平均值来计算其淤积厚度;当坝地宽度<50 m时,取一排观测点。同时,在挖取土壤剖面位置处进行环刀取样,当土壤有明显分层时进行分层取样用于计算各淤地坝淤积层次的容重。对于自然沟道,依据植被状况判断草本植物是否有倒伏(泥沙输移通过)、挂淤(泥沙有沉积)以及沟道内是否有冲淤的痕迹来判别沟道泥沙的输移与淤积情况。
将自然沟道和坝地沟道进行分段处理(图1),便于细化流域内沟道的具体情况。在Google Earth将遥感影像与野外调查记录对照,同时选择3个地表几何形态特征指标包括流域面积、流域形状系数和沟道比降,以及淤地坝的类型与分布,来分析对沟道的泥沙连通性的影响。

图1 蛇家沟和清水沟的沟道分段
1.4 流域及沟道形态指标的提取
流域面积、流域形状系数、以及沟道比降常用来描述流域及沟道的形态特征。基于相同的降雨,流域面积越大,上游的来水量越多,洪水过程会相对较为平缓;流域面积越小,来水量越小,如遇短时间暴雨常容易形成陡涨陡落的洪水过程[30]。通常用流域形状系数表示流域形状特征,流域形状系数的值越接近1,流域形状近于圆形,汇流速度快,洪峰流量出现时间早,流域易形成大洪水;流域形状系数值距1越大,流域形状越趋向于狭长,等流时线短,径流变化平缓,流量变小,延长峰现时间[30]。沟道比降是影响沟道中水流流速的主要因子,比降越大,则沟道中的流速越大,动能越大,易产生更大的洪峰流量[30]。可见,流域面积表征着泥沙侵蚀和淤积发生的区域范围;流域形状系数反映了降雨等流时线以及汇流洪峰值出现,影响着泥沙冲淤的位置;沟道比降控制着径流的流速以及作用力,影响着泥沙输移量与泥沙冲淤位置;淤地坝的分布影响着泥沙连通性以及对洪水的防御能力。
通过在Google Earth中对清水沟和蛇家沟流域以及分段沟道勾绘,利用Google Earth提取流域和分段区域面积。同时,利用Google Earth的高程剖面功能,获取蛇家沟流域主沟道和清水沟流域两个支沟的沟头到沟口的高程和水平距离,然后采用高度/水平距离,计算得到比降。形状系数为流域分水线的实际长度与流域同面积圆周长之比[30],公式如下:
Ke=L/C
式中:Ke——流域形状系数;L——流域分水线长度(km);C——同面积圆周长(km)。
1.5 淤地坝的分布与类型
淤地坝对沟道泥沙的输移起到阻碍作用,但是淤地坝的类型与分布情况会影响其对沟道泥沙的阻拦作用。淤地坝根据其放水建筑物的类型可以分为一大件(只有坝体,也称闷葫芦坝)、两大件(坝体与竖井或卧管;或坝体与溢洪道)和三大件(坝体、竖井或卧管与溢洪道)。依据淤地坝在小流域沟道中的分布位置,可划分为串联坝系、并联坝系和混联坝系。本研究中,清水沟为并联坝系,而在蛇家沟为串联坝系(表1)。

表1 陕西省子州县蛇家沟和清水沟淤地坝的基本情况
1.6 泥沙连通性强弱判别
泥沙连通性的强弱可通过沟道中的泥沙冲淤情况来反映。在子洲县“7·26”暴雨条件下,沟道中冲淤出现明显的现象就是淤地坝存在不同程度的损毁、沟道植被被泥沙淹没、沟道冲刷和淤积痕迹。因此,选用淤地坝坝体损毁及坝地拦沙状况、沟道植被倒伏现象以及沟道冲刷和淤积痕迹来对泥沙连通性强弱进行判定(表2)。

表2 泥沙连通性强弱判别依据
2 结果与分析
2.1 沟道泥沙的连通性
将蛇家沟和清水沟这两个小流域按照自然沟道和坝地沟道进行划分,得到的划分结果为蛇家沟自然沟道长度占44.5%,而清水沟中自然沟道长度占62.9%(图3)。在蛇家沟,靠近沟头的坝地沟道居多且坝体损毁严重(沟段Ⅰ),在中游和下游则是坝地沟道与自然沟段交替(沟段Ⅱ和沟段Ⅲ)。同时,上游沟道淤地坝的坝体损毁严重、自然沟道中的植被大多被泥沙覆盖且沟道内有被冲开的沟渠;在中游,淤地坝的坝体完好而放水建筑物损毁、自然沟道存在被冲刷沟渠且植被倒伏现象明显;在下游,淤地坝和自然沟道几乎没有损毁。因此,蛇家沟的泥沙连通性则是上游的泥沙连通强,中游呈现中等连通性,下游泥沙连通性减弱。

图2 蛇家沟和清水沟局部沟道连通强弱情况
在清水沟,左侧沟头为自然沟段(沟段Ⅰ),在左侧中游部位(沟段Ⅲ)坝地沟道仅占6.7%,右侧沟头自然沟道和坝地沟道交替(沟段Ⅱ),而在右侧中游部位(沟段Ⅳ)为自然沟道;左右两侧支沟汇入主沟后(沟段Ⅴ)都为自然沟道。左右两侧沟头的自然沟道基本是淤积状况,没有冲刷痕迹;而在左侧中游淤地坝的坝体垮塌且自然沟道内玉米被泥沙淹没;同时,主沟道出现多条被冲刷的沟渠。因此,在左右两侧沟头(沟段Ⅰ和沟段Ⅱ)泥沙连通性较弱,左侧中游沟道泥沙连通性呈现中等状态,汇入主沟(沟段Ⅳ和沟段Ⅴ)后泥沙连通性增强。

图3 自然沟道与坝地沟道长度比例
2.2 淤地坝的类型与分布对泥沙连通性的影响
淤地坝具有拦泥防洪作用,在沟道中淤地坝是连通性的开关点,并且在一般降雨条件下淤地坝为关闭状态,但是在“7·26”暴雨中,淤地坝大部分呈现打开状态,泥沙连通性增大。
蛇家沟的淤地坝为串联坝系,从上游到下游淤地坝对沟道中泥沙的输移起着阻碍作用。蛇家沟沟道3—8号淤地坝坝地的淤积总量从33.57~226 397.85 t,从3—8号淤地坝沿沟道泥沙淤积总量以102的倍率逐渐增大。在此次暴雨中1—4号淤地坝坝体都被冲毁,泥沙便从毁坏的坝体之间输送;5号淤地坝仅是在卧管的地方被掏蚀出1.8 m×1.5 m的洞穴,泥沙从洞穴连通;6,7和8号淤地坝坝体完好,泥沙只是通过卧管连通(表3)。
清水沟的淤地坝为并联坝系,泥沙在坝地淤积总量为299.61~76 094 t,1和2号淤地坝坝体完好,竖井处被冲毁,泥沙通过损毁的竖井进行连通;左侧支沟(沟段Ⅲ)内的3和4号坝地内淤满,泥沙漫过坝体并通过排水沟进行连通,5号淤地坝坝体没有垮塌,但是在竖井处的坝体被掏蚀1.5 m×1.8 m的洞穴,泥沙通过洞穴来连通;流域出口的水库溃坝,沙泄入大理河(表4)。

表3 蛇家沟沟道坝地的淤积量

表4 清水沟沟道坝地的淤积量
2.3 流域与沟道形态特征对泥沙连通性的影响
2.3.1 流域形状系数 清水沟和蛇家沟两个小流域面积大小相似,而清水沟的流域形状系数为0.57,蛇家沟的流域形状系数为1.55,很明显清水沟形状呈扇形,蛇家沟形状呈长条形。
从图4可以看出,蛇家沟各坝控流域的形状流域系数比清水沟各坝控流域的值要大,且蛇家沟从上游到下游淤地坝控制流域的形状系数整体呈现递增状态,也就说明从上游到下游达到淤地坝洪峰流量出现有延迟的趋势,洪水量和汇流域速度都小,同时洪水对淤地坝的损毁程度也就逐渐降低,而且蛇家沟上游淤地坝坝体损毁,中游和下游淤地坝坝体完好,淤地坝拦沙量大。
清水沟各淤地坝控制流域的形状系数值都趋近于1,洪水流量集中,汇流速度快,由于淤地坝来不及泄洪而受到的冲击力较大,所以淤地坝坝体损毁较多,集中下泄使得下游水库发生溃坝现象,清水沟泥沙连通性从上游到下游也呈现增强趋势。

注:d1—5代表清水沟1—5号淤地坝控制流域的形状系数; d1—8代表蛇家沟1—8号淤地坝控制流域的形状系数。
图4蛇家沟和清水沟淤地坝控制流域的形状系数
2.3.2 沟道比降 通过图5a可以发现清水沟沟道的整体比降大于蛇家沟沟道比降,并且清水沟整体比降为5.05%,蛇家沟整体比降为3.70%,清水沟的沟道比降比蛇家沟比降高出1.35%,说明清水沟泥沙在沟道中输送的速度较快,水流动能大、挟沙能力较强,也使得泥沙连通性较强,而蛇家沟运输泥沙的水流动能相对较小,泥沙在输送过程中泥沙易沉积;由于清水沟沟道中洪水流速大,动能大,在到达下游水库时,水库不足以承受上游汇流来的洪水,这也是成为造成水库溃坝的原因之一。
按照从上游到下游排序,通过比较蛇家沟和清水沟的自然沟道和坝地沟道比降(图5b)以及蛇家沟和清水沟坝地沟道与其淤地坝对应下游的自然沟道比降(图5c),结果发现蛇家沟坝地沟道比降与清水沟坝地沟道比降相差较小,但是蛇家沟自然沟道比降却小于清水沟自然沟道比降。蛇家沟自然沟道比降几乎都小于坝地沟道比降,并且蛇家沟坝地沟道比降最大值大于20%,自然沟道比降最大值小于10%,同时坝地沟道比降较大的位置出现在沟头,这也就是蛇家沟沟头淤地坝损毁严重,泥沙连通性强的原因之一。清水沟自然沟道比降与坝地沟道比降相差较小,尤其是位于沟头的自然沟道比降小于坝地沟道比降,并且清水沟坝地沟道比降最大值达33%,自然沟道比降最大值小于20%。

注:从左到右代表小流域从上游到下游。图5 蛇家沟和清水沟坝地沟道和自然沟道比降
3 讨 论
在此次暴雨下,小流域沟道泥沙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连通状态,淤地坝类型与分布,以及流域面积、沟道比降和流域形状系数均影响着沟道泥沙连通性,由于淤地坝损毁严重且大部分呈现打开状态,在此次暴雨条件下淤地坝类型及分布是影响沟道泥沙连通性的主导因子。
在小流域尺度上,不同坝系级联方式在调节流域洪水过程中发挥不同的作用[31]。有研究也表明在20世纪70—80年代,流域内溃坝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形成完整的坝系[32-33],而且不同坝系布置类型的稳定性表现为:混联坝系>串联坝系>并联坝系[31]。本文通过对比串联坝系和并联坝系小流域沟道的泥沙连通性,发现串联坝系能够对暴雨条件下洪水的冲击层层拦截,在防洪过程中淤地坝虽然有损毁,但是由于逐级拦截,最终蛇家沟中下游淤地坝损毁程度小且泥沙连通性减弱;而并联坝系没有逐级防洪的效果,因此会导致清水沟下游出口处的水库溃坝且泥沙连通性增大。
对于淤地坝来说,不同结构配套形式对防洪拦沙也发挥着不同作用。淤地坝三大件和两大件配套方式抵抗洪水毁坏的能力大于一大件[32]。闷葫芦坝对上游来水来沙几乎是全部拦蓄,倘若没有发生溃坝洪水泥沙基本无法连通,但是当遇到暴雨,无排水设施,极易被洪水破坏,如蛇家沟1—4号淤地坝为“闷葫芦坝”坝体全部垮塌,泥沙连通性变强;2013年延河流域冲毁的淤地坝也大多是“闷葫芦坝”坝体垮塌[34-35]。设有卧管和竖井的淤地坝,洪水泥沙通过放水建筑物排出,但是当超过放水建筑物的排洪设计标准后或排水口排水不畅时,放水建筑物不足以排出洪水,就会使得竖井和卧管损毁,如清水沟1,2号淤地坝;而此次暴雨中王茂沟淤地坝垮坝大多是放水建筑物和漫顶溃坝[45]。设有溢洪道的淤地坝,洪水会通过溢洪道排出,如岔巴沟阳燕沟淤地坝,在此次暴雨中坝体完好;如果排水闸没有及时打开,就会发生溃坝,如清水沟水库。
同时,坝控流域面积、坝地沟道比降以及坝控流域形状系数对淤地坝安全都有影响,通过上述研究发现淤地坝的控制流域面积越大且其放水建筑物修建完善,淤地坝被损毁程度越轻;淤地坝所在沟道的比降若大于9.5%则不适合修建坝高>10 m的淤地坝[36]。同时从表1也可看出,坝体垮塌淤地坝的坝地沟道比降都大于竖井和卧管毁坏淤地坝的坝地沟道比降;同时淤地坝控制流域形状系数越大则增大汇水时间,减弱汇流速度为洪水下泄提供了时间,使得洪水对坝体的冲击力减小。
综上所述,为了让淤地坝能更好的发挥作用,使得泥沙不出沟,流域沟道淤地坝修建应为串联坝系甚至混联坝系,这样有利于淤地坝对洪水泥沙的层层阻挡,减弱泥沙连通性。尽量修建设有卧管或竖井以及溢洪道的淤地坝,保证防洪蓄水安全;改善淤地坝排水泄洪管理机制,确保排水建筑物的畅通,保证淤地坝与水库安全。修建单坝选址要避免沟道比降较大的位置以及坝控流域形状系数接近1的沟道,这样可以减小上游来水对淤地坝的冲击作用,增加淤地坝的安全性。同时淤地坝是小流域泥沙连通性的决定性因素,增加淤地坝安全也可以降低泥沙连通性,有效地控制泥沙的输送。
4 结 论
特大暴雨条件下,泥沙连通性的影响因素也发生了改变,淤地坝将作为主要的连通性阻碍点,淤地坝的类型以及坝系级联方式对联通性起主导作用。
(1) 流域形状、流域面积和沟道比降均影响着沟道泥沙连通性,而淤地坝类型及分布是影响沟道泥沙连通性的主导因子。
(2) 从单坝角度来说,淤地坝应修建于沟道比降较小且坝控流域形状系数远离1的位置,同时,淤地坝尽量修建有放水建筑物和溢洪道,尤其是靠近沟头位置的淤地坝,以保障淤地坝的安全运行;从小流域坝系角度看,串联和混联坝系的淤地坝防洪能力更强。
(3) 加强对淤地坝的管理,保证在暴雨情况下放水建筑物和溢洪道的畅通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