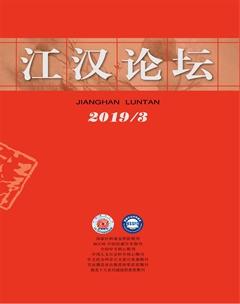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地主制经济的变化
摘要: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抑制了地主制经济规模的扩张,但并未能促使其向现代农业经营方向转化。地主阶级通过租佃制和高利贷剥夺农民的生产剩余,转而投向城市部门。农业部门缺乏积累与投入,技术进步停滞,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效率低下。这不仅削弱了农业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也使广大地主顽固地坚持租佃制经营,反映出中国地主制经济与农村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尖锐矛盾。实践表明,只有彻底摧毁地主制经济,中国农村经济才有发展的可能。
关键词:20世纪上半叶;城市化;地主制经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村地籍整理研究”(12BZS059)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03-0113-06
一、引言
关于旧中国地主制经济的特点,已有广泛讨论。第一种观点强调中国地主制经济的封建性。① 第二种观点认为地主租佃制经济在唐宋以后逐步得到确立,地主和农民近似市场经济中的平等主体,租佃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②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封建地主制的社会经济结构,实际上是政治权力、土地权力、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综合体,因此具有很大的融通性,显示出“弹性”的特征。③ 近代以来的经济社会变迁,使地主制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一种看法是封建地主制经济在近代趋向衰落。④ 相反的观点是封建地主制经济仍在农村占据统治地位。⑤
本文的重点是考察城市化进程对地主制经济的影响。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也有初步探讨。⑥ 近代中国工业与城市部门的发展,对传统农业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关于旧中国地主制经济的特点及其变化,需要结合工业及城市部门的影响加以分析。以往研究虽有涉及,但是关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特征缺乏辨析,因此,城市化进程对地主制经济的影响,也没有得到十分清晰的说明,以致人们对地主制经济的发展状况莫衷一是。本文拟以20世纪上半叶为中心,进一步考察近代工业与城市化对地主经济的影响,并希望能对旧中国地主经济的特点有所辨明。
二、工业化与社会动荡所推动的城市化进程
据美国学者斯金纳尔估计,1843—1894年,中国城镇人口从2072万增至2351万,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5.1%增至6%。从1894—1949年,城镇人口从2351万增至5765万,城镇人口所占比重由6%增至10.6%。在长达近110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城市化率大约为5.5个百分点的增长。⑦
德怀特·珀金斯认为,1900—1910年,中国城市人口数(不含香港)1464万人,1938年为2456万人,1953年为4753万人。⑧据卜凯调查,1929—1933年间,中国城市人口约占10%;市镇人口约占11%,村庄人口约占79%。⑨ 刘大中和叶孔嘉对1933年人口的职业分布作过详细估计。1933年,全国就业人口为2.5921亿,其中2.0491亿人即79%从事农业;5430万人(包括一定比例从事双重职业人口)即21%在非农部门就业。总人口中,有73%生活在以农业为主的家庭里,27%为非农家庭成员。⑩
从1912年至1949年,中国人口几乎以1%的年平均率增长,城市人口的增长率可能达到2%。{11} 20世纪中叶中国各省区城市化水平,以东北最高,在20%左右;广东、江苏等10余省在10%以上;其余在10%以下。{12}
近代中国城市化有两个动力源泉:一是工业化所推动的城市化,一是社会动荡所导致的城市化。
19世纪80年代,农业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6.79%,非农业占33.21%。非农业部门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业、贸易、金融等。不过这时的制造业,几乎全是手工业。{13}
19世紀末期,小型的近代工业部门出现。1894年前,商办和官办工厂合计108家,资本1.8亿元,雇佣工人约8万人。{14} 1913年中国工厂数698家,资本3.3亿元,雇佣工人27万人。{15} 1920年,中国工厂数1759家,资本约5亿元,工人约56万人。{16} 1933年,中资工厂数3167家,雇佣职工55万人,总产值约14亿元。{17} 到1943年,在大后方有工厂3758家,工人24万余人。{18}
在中国近代工业经济中,还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外资部门。{19} 巫宝三推算,1933年工厂总数为3841家(中资3167家,外资674家),雇佣工人73万余名,总产值约22亿。在计入满洲工业发展数据后,刘大中和叶孔嘉推算出1933年工业产值超过26亿,雇佣工人超过107万。{20} 1937年中国工业资本38亿,其中中国资本约10亿,占26%,外资资本约28亿,占74%。{21}
在中国工业制造中,手工业制造要超过工厂工业制造。1933年,工业制造净值约为19亿元,其中手工业净值约为14亿元,约占工业制造净值的72%。{22}
从工业的年均增长率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工业明显扩大(1912—1920年,13.4%),随后是1921—1922年的战后衰退;从1923—1936年,平均增长率为8.7%;1912—1942年为8.4%; 1912—1949年平均年增长率为5.6%。{23}
根据刘一叶的估计,1933年国内生产净值为288.6亿元,其中农业净值187.6亿元,约占65%;非农部门净值101亿,约占35%。{24}
在工业与城市部门就业的工人,其工资水平远高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25} 近代工业与城市化进程使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流动有了新的变化。
1922年江苏等5省9县,南方省份农村离村率约为3.85%,北方省份农民离村率为5.49%。{26} 离村农民流动的方向,一是往西北、东北新垦区流动{27};一是流徙海外{28};一是流入城市。
江苏宜兴“附城乡村,颇有入城进工厂工作者,甚有往苏、沪、锡等埠在纱厂纺织者”。1927年,进城务工的农村妇女达6000人。{29} 随着无锡工厂的增加,周围农村过去的雇农,都进厂当工人去了。{30} 镇江每年从苏北和山东涌入的季节工4000—5000人。{31} 礼社为无锡一个镇,在1932年前后,流动出去的人口有755人,占该镇总人口的21%。约四分之三的人流动到外县,其中上海最多,400余人,其次是苏州。流往本县城区的100余人。{32} 山西农民发现种田不能维持生计的时候,都跑到太原寻求仆役之类的工作。{33} 由于“武汉工厂林立,商业繁盛”,“附近居民贫穷者多入工厂”。{34} 据1934年调查,山东泗水县农民外出谋生,远者至东三省,近者至南京。{35}
据有关学者研究统计,在1935年21个省1001个县中,有1.7%的农户和4.2%的乡村青年弃农进城。{36}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商业产权的价值相对于农村产权迅速上升。图1 显示,1934年,各省城市地价都要远高于农村地价。整体而言,工商业发达的南方各省要高于北方各省。根据重庆等13市县1931—1943城乡地价资料计算,商业地产价格指数每上升1个百分点,农村地价指数仅上升0.669个百分点。{37}
说明:根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中央土地专门委员会1937年刊行)第60页“第四十二表·各省历年平均城厢地价”绘制。
抗战前的苏南农村,土地投资年纯利润只有8.7%左右,而工业投资的平均利润为30.2%,商业投资的平均利润为31.4%。{38} 以前地主的钱用于在农村放高利贷。随着城市投资机会的增加,地主开始投资城市的商业活动,或将钱存入城市银行中。{39} 凡稍有资产的人家都由乡而镇,由镇而城,由城而市,这可以说是资金的逃亡。{40}
持续的社会动荡从另一个方面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导致城市的畸形发展。
20世纪20、30年代,天灾人祸频仍。{41} 据不完全统计,1912—1930年间,军阀之间共发生战争152次。{42}
如表1所示,1934—1935年间,江苏等16省176个县中,只有4县没有发生灾患,约为总数的2.3%;超过70%的县灾情都比较严重;更糟糕的是,政府基本上没有采取十分有效的救灾措施。卜凯认为,匪患、兵灾以及自然灾害是影响农村发展最主要的原因。{43}
各省盗匪横行,稍微富裕的家庭,就有被抢劫的危险。{44} 河南辉县,因为遭遇“匪患”,地主富农出卖田地较多,中农、贫农由于没有被绑架的危险,田地数下降反而较慢。乡村土地的购买者多为城市地主及商业高利贷者。{45} 1928—1933年间,江苏邳县,由于匪患甚烈,收获不佳,很少有地主商人愿意买进田亩,导致地价降落。{46}
一些小有资本的人还留在农村,靠出租土地、经营高利贷等生活,农村最为富有的阶层则逃往城市。{47} 在匪患的影响下,使南阳城居民由2万人骤增至4万人。{48} 四川华阳县地主住在乡村者,占57.6%,住在场镇者,占12.2%,住在城市者,占30.2%。{49} 江苏宜兴和桥镇是宜兴最大的一个市镇。在30年代,城镇人口逐渐增加。镇里的地主,有地1000—1500亩的,有十五、六户;有地100—1000亩的,有五、六十户;总计土地在30000亩以上。{50}
1924年,各地居外地主的比重,江苏昆山为65.9%,江苏南通为15.8%,安徽宿县为27.4%,湖北武昌为50%。{51} 据实业部1934年调查,上海、江苏(16个县区)、浙江(9县区)、安徽(4县)、江西(43县区)地主城居比例分别为20%、27.7%、37.2%、18.7%、22.6%,平均为25.1%。{52}
如图2所示。efg是总人口曲线,lmc是必要的工业化曲线,在这个水平上,所有剩余劳动力都转移到城市中来了。ijc是现实工業化水平上,可能达到的城市化进程。但是,由于社会动荡,一部分农村居民被迫迁往城市,导致现实的城市化程度abc曲线所在的位置要高于可能的城市化程度ijc曲线。
三、地主制经济的变化
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黄宗智描述了两个“力农致富”的地主代表,河北丰润县米厂村的董天望和平谷县大北关村的张彩楼,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他们上升到一个小地主的规模。{53} 这两个农户主要是靠力农致富。其现金收入来源于经济作物的生产和销售,正是现金的积聚让他们有能力不断扩大土地规模。一个颇具规模的农产品市场帮了忙。
但是,对于大多数小农来讲,正是市场制度恶化了其生存处境。{54} 很多农户耕作一年,收支不能平衡,必须借债以敷生计。根据土地委员会1934年调查,全国农户负债百分比为43.87%。{55} 各省农户借贷年利率集中在2分至4分之间。{56} 中国农村借款来源,主要是典当行、钱庄、商店、地主、富农、商人等。{57} 由于利率奇高,使本利的累积格外迅速。{58} 据土地委员会调查,农村借贷,信用借贷占33.6%,田地抵押占46.61%,房屋及其他不动产抵押11.65%,物品抵押8.38%。{59} 一些农户在债务的重压之下被迫出售土地。{60} 大多数情况下,农户出卖土地并非通过一次交易来完成,常常要经过抵押、典当、绝卖三个步骤。{61} 一些土地所有者在土地卖出去之际,还坚持保留耕作的权利,即所谓“田面权”。{62}
表2显示,1931年与1912年比较,自耕农略有减少,佃农略有增加,半自耕农没有变化。在20年间,约有3%的农户从自耕农下降为佃农。1931—1936年间,自耕农没有变化,半自耕农增加1%,佃农减少1%。
珀金斯估计,佃农占农户的百分比,1912年为28%,1917—1918年为27%,1930年代初为33%,1931—1936年为30%。{63} 可见,尽管入不敷出,债务繁重,但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大批农民破产。《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写道:“在相对和平时期,中国经济表现出惊人的恢复力,显示出传统技术和地方化了组织拥有压倒一切的顽强性的确切标志。”{64}
一部分農民在债务压力下失去了土地,一些农民上升为富农或地主。但是,对于力农致富的小地主而言,其家庭的财富优势很难保持。一个重要的威胁来自分家制度,地主的大家庭在村社中的地位很少能维持一两代人以上,然后就被别的家庭所替代。{65}
黄宗智指出,传统中国农村社会贫富差别的周期性变化与劳动人口/家庭人口比率的变化有莫大关系。尽管由于缺乏系统的统计资料,不能确切地知道最佳比率是多少,但最佳比肯定是存在的。超过这一比率,一个富裕家庭就开始了一个向下衰落的过程。在抗战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出现大比例的农民破产的问题,土地供给由农户平均人口压力周期决定。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在近代中国农村,由于小农生产的韧性,土地的供给会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规模上。土地价格的变化主要由需求来决定。
图3显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地价整体来说是上涨的。但是,结合物价变化曲线,我们会发现,在抗战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地价与物价基本重叠。说明地价的变化主要是物价变化所致。剔除物价的影响,农村地价变化较小。1906—1928年期间,地价有较小幅度的涨幅。在1930年以后,农村地价出现小幅下跌。由于这时物价有比较明显的上涨,涨跌之间,彰显出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下中国农村经济的萧条,契合了以往研究的看法。1935年前后地价涨幅又在物价之上,表明真实地价又在上涨。直到1937年后,地价才大幅上涨。1937年后地价上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通货膨胀的影响。但是,剔除物价上涨部分,1937年后大部分时间里,地价也还是保持了上升的趋势。这可能与数据来源有关。抗战爆发后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区。有资料表明,随着大量游资涌入大后方,促使后方农村地价上涨。{66} 根据重庆等13县市1931—1943年数据计算,1937年之后的农村地价比1937年之前的地价高出1.716倍。{67}
说明:地价指数变化趋势根据《中国土地利用》表4、《中国各重要市县地价调查报告》(1944年)合并计算并进行对数化处理后得出;物价指数变化趋势根据《中国土地利用》表4、《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48年)》表65合并计算并进行对数化处理后得出。
由于农村土地供给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规模上,地价主要由需求决定。抗战前地价变化不大,说明这一时期的需求也基本保持稳定。{68} 关于浙江、云南、河南、湖南等地的调查都表明,1928—1948年间土地向地主群体集中的趋势并不显著。{69} 珀金斯指出,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出现了许多新兴的有利的投资场所。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土地并不是一个安全的投资方式。{70}
尽管民国时期土地集中趋势没有进一步加强,土地占有不平等问题依然是突出的。耕地在农户中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588;按人口分组后的计算结果是0.492。{71}
在城市化进程中,传统士绅地主走向衰落。{72}地主阶级分化为“乡居地主”与“城居地主”两大群体。“乡居地主”由于小农内部经过分化而形成,其购买土地的资金主要来自农业,大多是小地主,而且容易在人口压力下走向衰落。“城居地主”往往都是中等及以上的地主。{73}
关于城居地主的报告大量见于当时的文献中。{74}珀金斯写道,被调查的8省37个村庄中,四分之一的耕地为本村人所有,四分之三的耕地为外村人所有。{75} 据金陵大学农经系30年代对鄂、皖、赣三省调查,居乡大、中、小地主平均田产分别为892、200、57亩;居外大、中、小地主平均田产分别为1364、713、375亩。{76}
根据江苏省民政厅1930年对514户大地主调查的结果,军政人员占27.23%,高利贷者占42.86%,商人占22.36%,资本家占7.45%。{77} 另外,在一些地方,土匪等恶势力也趁势崛起。豫西土匪猖獗,导致一些土地荒芜,并逐渐为豪绅所控制。{78}
据珀金斯估计,地租约占到农业总产量的30—35%。{79} 曹幸穗估计,旧中国苏南地区农业产值,佃农消费21%,自耕农消费42%,地租20%,赋税7%,贷款利息4%,商业利润6%。{80} 地主通常都是地主、高利贷与商人的“三位一体”。他们不仅垄断了城乡之间的贸易,又是高利贷的主要金主。{81}1930年对江苏南部161户大地主(1000亩以上)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17户涉及到商业、金融或实业,其余44户则拥有军职或官职。{82}
调查表明,与乡居地主比较,城居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更加疏远。{83} 在华北,城居地主依靠所谓“中人”与农民打交道。{84}在江南,城居地主通过“租栈”来管理佃户。{85} 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失去人情味,在此背景下,佃户对地主的反抗大大升级。{86}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农民抗租事件频繁发生。在1922—1931年这10年间,从上海的两家报纸《申报》和《新闻报》上,总共记录下197起与地租有关的事件。{87} 1922年至1931年,江苏共发生佃农风潮125起。{88} 这反过来又会加剧地主群体对乡村的疏离。
随着地主精英从乡下徙居城镇,诸如兴修水利、农村饥荒救济等重要工作就无人顾及了,而在以往,这些事务均由作为社区领袖的大土地所有者承担。{89} 在一些地方,这一现象直接导致了村政的恶化。{90} 杜赞奇指出,在华北农村,由于不堪国家的赋税勒索,“保护型经纪”纷纷隐退,村庄领袖的位置被“赢利型经纪”所取代。{91} 这是国家索取无度的结果,又反过来加剧了农村的负担。{92} 及至20世纪30年代初,江南地主不得不将地租收入的1/5-2/3向政府纳税。到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四年,地主更是每况愈下,税收扶摇直上。{93}
在农民反抗与政府赋税榨取的双重压力下,土地所有权变得无利可图。{94} 在这样的压力下,地主经济的扩张得到一定程度的阻遏。白凯将发生在江南农村的这一过程视为地主阶级“统治的动摇。”曹幸穗则将其视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在商品经济的初兴阶段,地区趋于集中,这时握有货币的富有者竞相购买土地,而当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土地以外的工商业投资获利更丰时,最富有的人非但不会添置田产,还会变卖土地转而投资于工商业。{95} 农业成为一个单向性开放系统。不仅大部分农业剩余,乃至农村人才等都流向了城市。{96}
四、結论
在春秋时期,中国土地的私人所有制就初步确立。在中国历史上,关于土地产权的争夺是激烈的。土地经营方面,除了农民的自耕外,地主土地主要是租佃经营。庄园制经济,以及地主的自营土地在某些时候或地区出现过,但并不占据主导地位。究其原因,一是在经济上,土地相对于劳动力更加稀缺,农佃竞争使地租一直高居不下,对地主而言,租佃经营与自主经营的收益差别不大。一是在政治上,由儒家思想所主导的国家意识形态与制度设置,并不鼓励地主阶级致力于农业生产的进步,而是汲汲于科举仕途。
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发展。到20世纪上半叶,已出现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城市部门。这一城市化进程由两个方面的力量所推动。积极方面的力量来自近代以来的工商业发展;消极的方面则是民国鼎革以后持续的社会动荡。这样一个独特的城市化进程对地主制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
商业产权价值相对于农村产权价值大幅上涨,投资于城市工商业部门较之投资于农业部门,获利差别悬殊。在持续的社会动荡中,城市不仅能为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更好的保障,还能为富裕人群提供高品质的生活享受。所以广大地主纷纷离开农村,选择在城市居住并投资。农村精英与资本的流失,国家制度供给能力的缺失,使农村政治生态恶化,农村金融枯竭,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同时,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农村经济,在世界经济发展周期的影响下,于各种天灾人祸之外,又增加了一层不确定性。不断恶化的农业生产条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资本的逃离。因此,在土地经营方面,租佃制继续占据着主导地位。地主阶级以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方式,将农业生产剩余输入城市与工商业部门。
总之,20世纪上半叶的城市化进程,抑制了地主制经济规模的扩张,但并未能促使其向现代农业经营方向转化。地主阶级通过租佃制和高利贷剥夺农民的生产剩余,转而投向城市部门。农业部门缺乏积累与投入,技术进步停滞,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效率低下。这不仅削弱了农业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也使广大地主顽固地坚持租佃制经营,反映出中国地主制经济与农村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尖锐矛盾。实践表明,只有彻底摧毁地主制经济,中国农村经济才有发展的可能。
注释:
① 李根蟠:《“封建地主制”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大成果》,《河北学刊》2007年第1期;江太新:《对明清农业发展史研究中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5期。
② 方行:《中国地主制经济的经济强制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1期;盛邦和:《中国土地权演化及地主租佃、小农自耕模式的形成》,《中州学刊》2009年第1期;李德英:《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的押租与押扣——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③ 郑振满、郑志章:《森正夫与傅衣凌、杨国桢先生论明清地主、农民土地权利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5页。
④ 王宜昌:《从农业来看中国农村经济》,转引自余霖:《介绍并批评王宜昌先生关于中国农村经济底论著》,《中国农村》1935年第1卷第8期;赵槑僧:《中国土地问题的本质》,《中国农村》1936年第2卷第6期;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四章”;白凯:《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高王凌:《地租征收率的再探讨》,《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⑤ 薛暮桥:《现阶段的土地问题和土地政策》,《中国农村》1939年第6卷第1期;孙冶方:《财政资本底统治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国农村》1935年第1卷第12期;陶直夫:《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社会改造问题》,《中国农村》1935年第1卷第11期;余霖:《中国农业生产关系底检讨》,《中国农村》1935年第1卷第5期;余霖:《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答》,《中国农村》1935年第1卷第12期。
⑥ 罗晓翔:《土地回报与资本流动——从善堂投资模式看清末南京城乡经济关系变迁》,《四川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洪璞:《乡居·镇居·城居——清末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社会和空间范围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辑;安宝:《地权流转·不在地主与乡村社会——以20世纪前期的华北地区为例》,《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等。
⑦ 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版,第261页。
⑧{63}{70}{73}{75}{79} 德怀特·希尔德·珀金斯:《中国农业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03、115、129、118、117、231页。
⑨ 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6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3页。
⑩{11}{18}{20}{23}{24}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59、48、47、53、40页。
{12} 蔡云辉:《城乡关系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13}{19} 费正清、刘广京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页。
{14}{15}{16}{17}{21}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4、55、56、57、960—961页。
{22}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14页。
{25}{26}{27}{28}{29}{30}{31}{33}{34}{39}{51} 章有义:《近代中国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64—465、637、637—639、640—642、639、639、639、639、639、320、305页。
{32} 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新创造》1932年第2卷第1、2期。
{35}{48}{50}{54}{78}{81}{83}{86} 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上编),上海黎明书局1943年版,第234、201、40—41、120、176、176、22—23、22—23页。
{36} 章开沅、罗福惠:《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7页。
{37}{67} 中国农民银行土地金融处:《中国各重要市县地价调查报告》,中国农民银行土地金融处1944年印行;上述数据由本人利用Eviews软件计算得出。
{38}{77}{80}{85}{95}{96}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8、70、50、70—71、36、51页。
{40} 千家驹:《救济农村偏枯与都市膨胀问题》,《新中华杂志》1933年第1卷第8期。
{41} 章有义:《近代中国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09页;《荒旱灾互为因果之河南》,《农业周报》1929年第2期;《陕灾奇重》,《农业周报》1929年第2期;《吴县被灾田亩统计》,《农业周报》1929年第2期。
{42} 章有义:《近代中国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09页;姜君辰:《一九三二年中国农业恐慌底新姿态——丰收成灾》,《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389页。
{43}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台湾学生书局1971年版,第674页,“第二十四表·农业情形”。
{44} 汝真:《目前农民最困难之两问题》,《农业周报》1930年第14期。
{45}{46}{61} 《中国经济年鉴》,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32、324、343页。
{47} 李若虚:《大冶农村经济研究》,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21054页。
{49}{66} 叶懋、潘鸿声:《华阳县农村概况》,《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21、723页。
{52} 《中国经济年鉴》(民国二十四年续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G114—117页。
{53}{90}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2—74、284,280页。
{55}{56}{59} 土地委员会编:《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1934年)》,中央土地专门委员会1937年刊行,第50、51、52页。
{57} 《农情报告》(1934年1月1日),中国经济情报社编:《中国经济论文集》(第2集),生活书店1935年版。
{58} 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上编),上海黎明书局1943年版,第7—8页;《中国经济年鉴》,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34页;《昆山县徐公桥乡区社会状况调查报告书》,《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51页;李树青:《清华园附近农村的借贷调查(1933年)》,《清华周刊》1933年第40卷第11、12期等。
{60} 《中国经济年鉴》,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42—343页;《云南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89页;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上编),上海黎明书局1943年版,第162、163—164页。
{62}{82}{88}{89}{93}{94} 白凯:《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50—1950)》,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38、231、19、312、19—20、330页。
{64}{87}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9、281页。
{65}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246页;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8页。
{68} 《浙江省农村调查》,学海出版社1933年版,第28—77页。
{69} 《浙江省农村调查》,学海出版社1993年版,第8、138、182、24、22页;《云南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78、129页;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上编),上海黎明书局1943年版,第58、211页。
{71} 根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中央土地专门委员会1937年刊行)第32页“第21表·每户所有面积大小各组户数及总面积之百分率”计算得出。
{72} 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上编),上海黎明书局1943年版,第238、44页;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新创造》1932年第2卷第1、2期。
{74} 章有义:《近代中国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3页;《中国经济年鉴》,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37页; 《浙江省农村调查》(1933年),学海出版社1933年版,第7页;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上编),上海黎明书局1943年版,第24页;叶懋、潘鸿声:《华阳县农村概况》,《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24頁。
{76}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经系:《豫鄂皖赣四省之租佃制度》(1936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农经系1936年刊行,第77—79页。
{84}{91}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173、160—167页。
{92} 江国权:《安徽省芜湖县第四区第三乡农村调查》,《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603页; 章有义:《近代中国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66—571页;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转引自叶美兰:《1912—1937年江苏农村地价的变迁》,《民国档案》1999年第1期;《浙江省农村调查》,学海出版社1933年版,第11—12页。
作者简介:李铁强,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