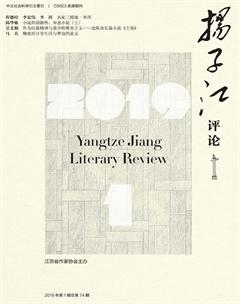历史的技艺与技艺的历史
方岩
一
上海的正史,隔着十万八千里,是别人家的故事,故事中的人,也浑然不觉。a
这句话出自小说的第一章,被印在单行本的封底上,大概是想引导读者注意到,这是一个与大历史相对疏远的故事。这其实是个误导。虽说王安忆在历史叙事上一向克制、内敛,但未必就意味着她倾心于历史的例外状况。把这句话还原到小说的语境中,便不难发现,在这句话之前,小刀会如何让富贵之家走向没落的故事点到为止,而这句话之后,世家弟子在亡国之前的歌舞升平、吃喝玩乐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平静的叙述语调与大历史呼之欲出的压迫感、颓败感构成了紧张、饱满的张力关系。所以,与其说王安忆试图描述一个游离于大历史之外的世情故事,倒不如说,她在刻意保持一种距离,从而能够更为从容地描述大历史的丰富表情,或者说,去深描大历史的某个不为人知的面孔。
故事才过三分之一时,小刀会又被重新提起,这倒印证了前面的判断。
大伯却摇头了:世人都以为恶报,其实不然,那小刀会可说是绿林中人,吃野食的,倘若造化大,就坐龙椅了,这就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所以,大伯指指东墙:千万不要惹!陈玉书点头了。b
此时,已是解放后。“东墙”这边是昔日的世家,“东墙”那边是新社会的无产者。世家因为院落被侵占而欲向无产者伸张权利,结果是“身后‘哗啦一响,一块半砖抛过来,碎成齑粉”c,于是便有了前述的对话。时代的吊诡之处正在于大历史中显赫的革命和暴力,与世情中潜隐的戾气和蛮横,很多时候是气息相通的。所以,细描日常中隐忍和逆来顺受未尝就不是直面大历史的一种姿态。重新审视这样的场景,便会发现隐忍未必是置身事外的表现,很可能源于对即将展开的大历史的恐惧和担忧。
油毛毡下已经钻出一个女人,叉着腰,昂头指了他道:拆房子吗?新社会了,社会主义了,穷人翻身了,不受剥削了……连珠炮的一长串,他几度张嘴,几度遭遇狙击,发声不得,何况论理。大伯拉他落地,来不及撤梯子,掉头避进内厅,身后“哗啦”一响,一块半砖抛过来,碎成齑粉。稍事喘息,大伯道:历来刁民最可怕,赵匡胤、朱元璋、李自成——本已经坐了龙廷,想不到来了个更野的,忽必烈,茹毛饮血之类,不是有句俗话,乘车的敌不过穿鞋的,穿鞋的敌不过赤脚的;又有一句,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王者”是谁?正是草莽中人!d
两种声音在这里交织,显得意味深长。一方面是尖锐的冲突。前者嘹亮、直接,但不免有权力的噪音的嫌疑,“它是权力——不论何种形式——的附属物”e,因为政治正确的词汇打断了是非的讨论,或然的历史正义以粗暴的形式表现出来。与此相比,后者的低声细语更像是某种暧昧历史评价。尽管相形之下,后者在欲说还休中闪烁的那些词汇和评价,在今天看来更像是某种陈词滥调。但是,在新的历史并未向世俗社会展现其足够的说服力的时候,这未尝不是特定语境中存在的一种真实的历史感受,这种感受正是源于反复循环的旧历史的经验提醒。这与面对尚未充分展开的未来所怀有的恐惧和担忧,其实是一种感受的两种面相。所以窃窃私语其实是一种压抑、隐忍的状态。然而,不管是理直气壮还是低眉顺眼,两种声音却分享了非此即彼的对抗逻辑,旧历史的幽灵飘散在新历史的高昂的情绪中。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种声音似乎又在某种程度形成了互证。正如旧历史可以用一栋老宅的墙区隔出两个阶层,而新历史却用一道看不见的墙重新划分了群体:
时代将人划分了两边,这边是过去,那边是现在,奚子划到了那边,剩下的他们几个在这边。陈玉书逐渐意识到,界限是难以逾越的……事实上,过不过得去不由自己说了算。f
二
然而,《考工记》并不仅仅只是一个被历史挟裹或抛出轨道的世情故事,因为王安忆的叙述的焦点,从未离开过一栋老宅,包括前述的那些引文所涉及的事件也是由老宅引发的。小说的第一句便是从陈玉书回到老宅开始叙述:
一九四四年秋,陈玉书历尽周折,回到南市的老宅。g
小说的最后一句,老宅成为了文物,摇摇欲坠:
四面起了高楼,这片自建房迟迟没有动迁,形成一个盆地,老宅子则是盆地里的锅底。那堵防火墙歪斜了,随时可倾倒下来,就像一面巨大的白旗。h
除了离家的两年,陈玉书在老宅里度过了一生。老宅见证了晚清、民国、解放后至今的时代风云,在祖辈的故事里或许还见证了更早的历史,而陈玉书亦亲历了从民国的繁华和凋敝、1949年之后的曲折和稳健,直到新世纪的来临。历史从未在别处,一直在雕刻塑造宅子和宅子里的人,而宅子和宅子里的人也在努力辨析那些历史痕迹,以试图理解历史的风向和表情。最后,历史昂首向前,留下一具老迈的肉身和一座颓败老宅相互守望,铭刻着“煮书亭”的石碑便成了历史曾经来过的证据。
这是颇具匠心的叙事结构设置,正如小说中老宅的选址、外观、选材、内部结构、布局、图案装饰都出自匠心独具的设计。而要将这一切匠心精细地呈现出来,只能依靠出色的手艺,或者说技艺,这对于小说的创作是如此,对于一栋建筑来说亦是如此。技艺的结果一方面关乎实用,另一方面则事关审美,而不管是审美还是实用,都带有时代的烙印。因此,当技艺问题被讨论时,从来就不仅仅是技艺本身的问题,这就是科技史在谈论具体的技艺问题时,为何总是要以特定时空下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思想等要素作为基本背景来讨论i。更何况技艺造物何尝不能在隐喻意义上来形容历史塑造、赋形诸种状况呢?
这样便不难理解王安忆何以会用《考工记》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对古代典籍《考工记》的直接借用。它是我国第一部手工艺技术汇编,据考证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后来被奉为经书,又称《周礼·冬官·考工記》。在目前较为通行的版本里,开头如下:
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或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或饬力以长地财,或治丝麻以成之。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知得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j
在这样的表述中,各种工匠(百工)的职业身份和职责虽在国家制度层面予以承认,但是重点却是在强调“百工之事”出自“圣人之作”,即工匠们的技艺是圣人的发明。可见,除却工具性、物质性价值,技艺更是与制度、历史、伦理相关。《考工记·匠人》便是个很好的例证。“匠人建国”“匠人营国”是对匠人职责的总结。“国”就是城邑,所谓“建国”“营国”就是“建置城池、宫室、宗廟、社稷,并规划国城周围之野。”k所以,“匠人”远非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其实是个特定的称谓:“匠人所负责的建筑工作是属于官营建筑范围。匠人是专门为王室即政府服务的建筑工匠。”l可见,“匠人”不仅意味着技艺和谋生,更是职责和服务对象都非常明确的官职,他是国家机器的构成部分,是从周代开始延续了数千年的工官制度的中心。事实上,“百工”既可以被理解为各种工匠,亦可以被理解为掌管营建制造之类事物的官职名称m,即“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何以“百工之事”在礼教、礼制的语境中经常被提起。比如,《论语》中曾有“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n的说法,在隐喻意义上以工匠技艺的习得来描述君子得道的方法,在另一处则引用《诗经》中描述打磨玉器玉石过程的句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o来形容修学问道的过程p。还有一处需要提及: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q
《论语》中的这个片段旨归固然在别处,但是“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这个细节却传达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即祭祀器物的选材与制度沿革、历史变动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技艺的政治性。小说里的一些细节聚焦的正是一点:
祖父说,这宅子的原主当是京官,因宅基正北正南。上海地方,设在江湾滩涂,高低左右难以取直,街市房屋互相借地,这里出来,那里进去,但从这宅子的形制,却可推出中轴线来。r
如果上述《论语》片段涉及的还只是三代祭祀的具体器物,那么《考工记·匠人》则记载了夏商周三代王城、王宫的整体设计方案,并成为后世王朝模仿对象。所以,这也是何以在现代建筑史研究中,有些学者一定要把《考工记》这样的技术文献视为“营造法”,而区别于来自西方的“建筑学”这个概念:
从基本性质上来看,建筑学是一种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的研究,本身并不含有政治性,它是科学的、学术型的;而营造法作为政府法规,是由朝廷颁布强制推行的,它是政治性的、制度性的。s
这倒是印证了小说中那些关于老宅的描述:
他顺势问几句祖宅的来历,大伯母说是老祖宗从一名大官手里买下,至于哪一朝的官,什么品级,大伯母说不上来,只是领他到前天井里,抬手向天一指:看见吗?要不是皇帝恩准,谁敢墙头游龙!门头上果然二龙抬头,向两边逶迤。t
所以,典籍《考工记》并非单纯的技术资料汇编,更重要的是它是作为“礼制”的重要的构成部分而得以保存下来的。所谓“礼制”用现代性话语转译一下,就是大写的“政治”,即各种权力/话语关系编织的意义网络,它上及国家政治、法律制度、伦理道德、文化教育、艺术审美、礼仪仪式,下涉生老病死、衣食住行。这一切都是以人的塑造为中心,人又使用或发明器物展开社会实践,因而器物便兼有了实用和意义符号两种功能。同时,技艺本身抽象,只有附着于人具化为器物才能被看见、谈论。于是,历史、人、器物和技艺便有了复杂的互文和映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把典籍《考工记》视为小说《考工记》的基本语法来看待,或者说,典籍《考工记》所凸显的技术政治化、器物历史化思路是理解小说《考工记》的关键。
三
其实,历史本身便是一种技艺,雕刻人与万物,庞大到苍茫、渺小至微尘,无处不在却又无法描述,我们只能在历史雕刻过的人和器物中去辨析它可能的样子。所以,当王安忆反反复复地在小说中描述老宅的设计、图案、材质、工艺,以及围绕着老宅流传的故事时,她其实在追溯消逝的历史、制度、传统、伦理,以及能够记录、呈现这些事物的审美。但是在一个惯性被中断、未来亦不具有确定性的新的历史时空中,这一切注定以碎片的形式出现。碎片拼贴出历史可能的形状,小说便是历史可能的形态之一。
书案收拾得很干净,整块瘿木面板经几代人手摩挲,油光锃亮映得出人影。他看见自己的脸,又似乎是祖父和父亲的,他们彼此相像。u
这是《考工记》里很典型的句式。器物被凝视,孤单的个体便延展出血缘、代际、家族等群体关系,于是叙事的时空、视野也随之蔓延、拓展。相对于肉身易逝,器物的纹理、裂痕隐藏着历史的秘密。器物有如历史的碎片,在它被肉身凝视的时刻,叠加的时空便被释放出来。
那么如何让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人重新审视自己的居所及其器物,也就是说,如何让凝视合情合理地发生,便成了一个问题,这便涉及到王安忆小说技艺问题。在小说的开头,我们看到,陈玉书在离家两年后返回老宅,时间和距离提供了陌生化的前提,凝视便有了可能:
木的迸裂,从记忆的隧道清脆传出来,既是熟悉,又陌生。他回家了,却仿佛回到另一个家。v
陈玉书离开老宅时,太平洋战争爆发,返回时抗战即将结束,紧接着便是国共内战,解放军接管上海,更何况他离家的两年还与抗战时期诸多大学西迁内陆有关。于是,在历史、人生的十字路口陈玉书重新面对老宅,便成了一个颇具匠心的设计:首先,个人轨迹和历史大事件的交错为重新审视老宅提供了差异化的经验背景。这不仅为他回忆战争前的略显浮华的小开生涯提供了参照,并且陈玉书的放浪生涯又变成了回忆祖辈、父辈生活的参照。于是在一系列差异性经验背景的铺展中,叙事时空开始从战前上海最后的歌舞升平逐步拓展到晚清上海开埠。其次,离家两年亦为当年形影不离的“四小开”后半生迥异的人生道路埋下伏笔,由此,王安忆可以追随各自的人生经历将叙述伸向更加广阔、多元、具有差异性的经验领域。换而言之,正是离家两年才让“四小开”失散成为可能,由此四种人生才能成为四条叙事线索,也正是这四条线索的交织才能让王安忆在叙述1949年之后的故事时呈现出深刻的历史总体性。
事实上,王安忆的匠心在叙事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正始于陈玉书第一次全面审视老宅的时候,初入家门时的回忆和感叹已经开始转向带有历史感的评价:
终于有一天,他骑车回家,看见自家宅子,宛如海水中的礁石,或者礁石上的灯塔,孤立其中,茕茕孑立。始料未及的,一阵心惊袭来,他感到了危险。就在这同时,他看出老宅的美。他向来不喜欢中国建筑的形制,觉得阴沉和冷淡,也许是心境相合的缘故,他忽就领略到一种萧瑟的肃穆的姿容。w
“美”和“危險”都是历史和人生的不确定性结果。“美”是丧失的预感引发的,而“危险”则是对未知缺乏准备。围绕着“美”与“危险”的是历史的胶着、家族的聚散、友朋的亲疏、个人的困顿,而最终表现于老宅内部的居住格局的变动和日常生活的龃龉。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陈玉书在祖父的指点下和讲述中,开始重构老宅的“美”,以及那些“美”背后的历史和世情,眼光愈发抛向过去的时空。于是,当“危险”真的来临的时刻,“美”却成了另外的样子:
新气象之下,那宅子显得颓然。不是因为陈旧,而是不合时宜。厅堂的高、大、深,本是威严和庄重,但时代是奔腾活跃,一派明朗,于是就衬托出晦暗。木质结构的房屋,紫檀的幽微的光,仿佛古尸身上的防腐剂。x
“危险”似乎真的杀死了“美”。在新历史的语境下,老宅充满了死亡的气息,像是宣告一个时代的落幕。历史的连贯性也似乎断裂了,“危险”变成了新历史的赞歌,与“美”阴阳两隔。然而,当历史把一座现代化工厂移进老宅的时候,生机勃勃的“危险”和奄奄一息的“美”似乎又建立起某种关联:
这一年,也就是一九五八年底,工厂开出了。一爿瓶盖厂,占据宅子的东西两部,以及后楼一排北房,将主楼的南面留给他家,其实也就陈书玉一个人……
工厂开班早他一个钟头,下楼推车时候,工人正陆续进厂,走了对面,两边人都偏一步。y
社会主义的工厂嵌入世家的老宅,是个容易引发惯性思维的场景。事实上,两种历史狭路相逢,新历史既没有摧枯拉朽,旧势力也没有负隅顽抗,一切仿佛自然生长,工厂建成后,老宅里的人与工厂里的工人按照各自的社会角色及其秩序按部就班地履行着职责。换而言之,王安忆发现了一个奇妙的景观,映照出我们自身关于历史理解的肤浅和固执: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化和记忆在老宅中的狭路相逢时,竟不是虎视眈眈地仇视和对抗,反倒多了几分小心翼翼地凝视和谦让。或许我们早就习惯了大历史气势汹汹地碾压一切的那种简单、粗暴的身影,却从未仔细地体察过历史在细节处繁复、多变、丰富的面相。即便是简单、粗暴,也未必要以明火执仗的样子表现出来:
大虞喝一口酒,说,进院子时候,看地坪的青石板,有几块碎得厉害,大约是机器运送碾压,过廊上的歇山顶也损了好多片,这木质的建造,到底抵不住铁物,五行里不是说“金克木”?陈书玉自己丝毫没注意,在他眼中,这宅子早已经颓圮,都可以上演“聊斋”中的鬼戏。倒是工厂开办,充斥进人气,活过来似的。z
“金克木”是来自传统的世界观,但这并不代表它不能解释新历史的速度和力量。新历史的雄心和暴力就藏在破碎的青石板的缝隙里、损坏的走廊歇山顶的裂纹中。正如,工厂食堂的老厨子和后来新建的值班室的守夜人一直作为新历史拟人化的存在如幽灵般打量着这栋老宅。前者意味着秩序的重组和权力的重新分配,后者则意味权力的震慑、监督:
老厨子说,当年跟父亲进来办宴,也是这厨房,柴灶上坐着高汤的瓦钵,昼夜不熄火。老厨子用筷子根夹起自己盘里的虾,送到他盘子,似乎感谢有人听他说话,不是别人,正是园子的后人。谁想得到,会有一日,面对面坐着吃饭……
机器声隆隆响,厨房里则充斥一股慵懒的空气。@7
时代的轰鸣和世俗的气味的奇妙混合,竟然有了温暖、安详的氛围。或许这稍稍松动了疾风骤雨时代里的严肃表情。然而,这安详显得意味深长,因为听与说的位置早已置换,老宅的主人成了沉默的聆听者,隐隐的不安也就弥漫开来。
老厨子犯事被捕以后,工厂便安排了守夜人,然而他与宅子的主人却从未谋面:
他家宅子,怎么说呢?不只他一个人,还有一个,一个什么人?隐身人!他忽觉得,身前身后都是隐身人,就像旧时好莱坞电影里的化身博士,消失形骸,视和听的功能却全在。他不敢出声,用眼神示意对方,神情忽变得诡异,使奚子大惑不已。@8
很多时候,沉默和静寂亦是宣称权力在场的一种方式。正如被陈玉书多次提及的那句话:顺其自然。而这个词汇正来自历史和权力的代言人“弟弟”的建议。所以,“自然”其实便是历史本身,是权力主动伪装、隐匿起来的历史。老宅的主人正是在权力的暗中庇护之下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劫难,所以“上海的正史”从没离开过这栋老宅和陈玉书,只不过在历史狰狞的时刻,他总能被推开。
四
事实上,从工厂嵌入老宅的那一刻开始,老宅及其宅子中的人与器物就成为目睹新的历史进程的动荡和稳健的观察者和亲历者。大炼钢铁时,那些金属器物成为新历史激情的燃料;“文革”时,那些线装书和字画则付之一炬,燃起的火焰和留下的灰烬见证了历史的嚣张和虚无;恢复高考以后,老宅则成为补习场所,平添了几分抚平历史创伤、庇护幸存者的意味;市场经济来临之时,老宅又成为可以交换商品房的硬通货,并再次见证了世情和人心;直到新世纪来临,老宅被挂上“文物”的招牌,与历史的告别才刚刚开始……
当我们意识到不同时代的记忆一直在老宅中叠加或铺展时,其实老宅已经完成了百年中国历史联系性的重建。此时再去讨论是新历史赋予了老宅新的功能和生命,还是老宅包容了新历史的自信和躁动,已经毫无意义。因为,历史的技艺和技艺的历史彼此交织、相互矫正,早就把老宅变成了器物,上面花纹和刻痕隐藏着百年中国的历史和世情及其背后“美”和“危险”的秘密,如同老宅中的窨井盖上面那些让陈玉书始终难以确认的奇异图案,它们未必就与特定时代的工艺相关,它们的造型可能就是过去时代的诸种历史和审美层层积累、相互包容的结果。
【注释】
abcdfghrtuvwxyz@7@8王安忆:《考工记》,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
e[法]贾克·阿达利:《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宋素凤、翁桂堂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页。
i参见[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jk闻人军译注:《考工记译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112页。
l孙大章编著:《中国古代建筑史话》,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
m参见闻人军译注:《考工记译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注释(1)”。
nq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26页、33页。
o程俊英:《卫风·淇奥》,《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9页。
p参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页。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s柳肃:《营建的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建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亚马逊(kindle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