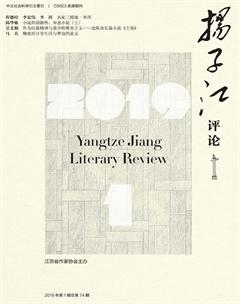王苏辛中短篇小说片论
顾奕俊
一、 从“同时代人”出发:“冒犯者”的“特殊性”
读完王苏辛相关小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事实上我多少有些“不知从何谈起”。之所以如此,源于缺乏自认为“唯应如此”的门径进入《白夜照相馆》 《战国风物》《袁万岁》 《马灵芝》 《我不在那儿》 《犹豫的时候最接近道德》这些具体的文本。当然,我也时常注意到当下部分文学批评从业者在陷入“不知从何谈起”处境时惯用的“技法”——借助若干生僻冷门的舶来品理论“挥毫”出一篇洋洋洒洒的“套路批评”,但若依循为之,则问题随之而来:假如相同的理论可以毫无违和感地套用于不同年龄層次、不同形式风格的作家作品,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理论的“强制阐释”,倒更可能暴露出批评主体在批评范式选择与实践上的力所不逮。尤其是当本文所要讨论的是跟我同龄的王苏辛时,我更加愿意将有关“同时代人”的讨论引申向趋于“狭隘”的“特殊性”,而绝非形同“套路“的“普遍性”。
由此也牵扯出另一个问题:王苏辛和相类似年龄段的青年作家(我们或可称之为“王苏辛与她的小伙伴们”),是否真正获得了能够与之相匹配的“同时代人”的文学批评?应该承认的是,更多“王苏辛与她的小伙伴们”的“同时代人”早已习惯承袭在固有文学史叙述的逻辑框架下进行模式化、空洞化的“流程操作”,因此他们论述的起点、终点早已受到显性的预设和干扰。甚至,暗作蠡测,假如未来的某日“王苏辛和她的小伙伴们”将有可能会被吸纳进当代文学史“经典化”的讨论范畴,这种“经典化”的阐释过程估计与现今学界对莫言、余华、王安忆、苏童、贾平凹等人“经典化”的论证过程差不离太远。这当然不是说“王苏辛与她的小伙伴们”与莫言、余华、王安忆、苏童、贾平凹真的能够形成“无缝衔接”的置位替换,而恰恰植根于“同时代人”的批评声音对于权威缺乏必要的“冒犯”。或者说,模仿先辈的一切,反而让年轻的“同时代人”获得了某种“暧昧不清”却又“心安理得”的自我认同。这也局部回应了部分青年学者抛出的困惑:为何如同胡风之于路翎、吴亮之于马原、陈思和之于王安忆这样的“良性的互动在现代的年轻一代那里还未形成”?a
当然,有关“经典化”的讨论,对现今的王苏辛及其作品而言也许尚且过早。至少是近期的一个阶段,王苏辛显然并没有对自己的创作抱以过高的期许。在谈论小说集《白夜照相馆》诸篇的写作过程时,她就自我检讨是“顺着过去的轨道”:“即使已经看起来不一样,但那个最该动的部分没有动,因此整个写作过程都像一块离开了水源的海绵,挥洒体内剩下的叙述感觉。”b细读这篇题为《练习面对自己的能力》的创作谈,至少可以窥探到当下两种关乎创作批评的较为常见的症候现象:其一是对比过往那些涉及王苏辛小说的批评文字,身为作者的王苏辛反而成为了其作品最为凶狠、也最为精准的“冒犯者”。很多时候,她披沥的火花毫无顾忌地弹射到小说内——尽管其未必意识到那些被击中的批评对象中也包括她自己。尤其在较为完整地细读了一批王苏辛的作品之后,以下这段出自《他经历着常常不被理解的最好的事情》的人物对话,也就具备了颇堪玩味的内质:
“《中国街》上的人看起来还是高扬以前画里面的人,可高扬自己变了。”齐彭说着,渐渐少了些紧张。他把手放进口袋,接着又拿出来,然后他双手交叉在前胸。
“他是变了,可画的还是他自己。还是那一个市声。”
“很多声音也可以复合到一种声音。”齐彭说,“《中国街》之后,高扬画了《白海豚》。”
“我喜欢《白海豚》。”张卿微笑起来,“不过那画得不像海豚,像鲸。”
“有可能本来就照着鲸画的。”二人说罢,都停了下来。c
需要指出,作者对于批评者的“角色凌驾”,在现今文坛大体已演变为极其普遍的“怪现象”。转而以批评者角色亮相的作家屡屡能提供令人耳目一新的言论或视角,而专业批评者们对作者的“角色凌驾”却多半表现得相形见绌而又力不从心。相当数量的专业批评者只是热衷于去“服侍抽象的观念或冷酷、遥远的神”d,并试图借此营造出一种“众声喧哗”的“壮观”场景。但所谓“众声喧哗”,又与批评者本人没有太多关联。极具讽刺意味,对于域外文论的“顶礼膜拜”,恰恰让这些批评者反而困顿于狭隘的文学观,继而将这种狭隘的文学观视作展开文学批评的唯一标准。如此情况底下,批评者的无所适从与力不从心也就得到了合乎情理的解释。更为糟糕的是,当批评者的一切不尽如人意的表现都能得到合乎情理的解答时,这个职业遭受奚落与轻视的命运也就在所难免。
其二,《练习面对自己的能力》涉及到写作者关乎自身经验的焦虑心理。深重的经验焦虑与创作恐惧也笼罩在小说《所有动画片的结局》中。王苏辛寻求一种“新”的改变,这种改变能推翻“那个最该动的部分”。尽管她又让《所有动画片的结局》的人物以果断的口吻道出“没有什么真正新的吧?有的只是正在发现和尚未发现”e。当1991年出生的王苏辛开始担忧“挥洒体内剩下的叙述感觉”之后该何去何从,我们或许可以将之解读为作者对自我的“冒犯”。王苏辛的自我“冒犯”显然是有必要的。从她近期发表的若干篇小说来看,王苏辛多多少少已陷入到因经验瓶颈引发的书写形式同质化问题。王苏辛的诚实之处在于,她深知自我对于经验的不可循环的竭取,并为此真切地感到羞赧。对比而言,诸多不思进取的“一本书作家”更愿意选择以纨绔子弟的面目去挥霍所剩无几的经验资源。有学者在分析作家的可持续写作问题时,就描述过这样一种在创作者群体当中极其普遍的情况:“在当代,曾经写出过有影响的作品,曾经广为人知,而很快难乎为继,这样的作家实在太多了。要举例的话,那可真是举不胜举。”f无疑,王苏辛的自我“冒犯”也就成为了一种无法回避的自我挑战。她需要通过自我挑战摆脱初始经验的覆盖,去勘探“尚未发现”的地域。
另一方面而言,这些晚近以来问世的中短篇作品也呈现出“冒犯者”王苏辛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她在“冒犯”意愿上的强烈与“冒犯”形式上的重复;她对于“冒犯”界线划分的清晰判断与“自我”身份定位的焦虑心理………近乎相悖的特征也构成了考察王苏辛中短篇小说“特殊性”的取径方式。
二、 “人”的畸变:“冒犯”的逻辑起点
一定程度上,王苏辛进行“冒犯”的逻辑起点源自对“人”的畸变形塑。在她的小说里,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狂飙突进及社群资源结构的重新整合,普通个体反而被剥夺了最为基本的外貌特征与生理功能。“离婚的人会变成雕像镇守自家的宅子”g(《我们都将孤独一生》)、身上长出羽毛的少年与没有影子的少女(《鸟人》)、普通家庭内部,“奶奶长出智齿、妈妈长出尾巴,叔叔则长出鱼鳞”h(《再见,父亲》)、“在一个黄昏因为笑得太久”i而离奇死亡的父亲(《昨夜星空璀璨》)、抢食猴肉的人最终自己变成了猴子(《猴》)、如同空气一样存在的女人(《直立行走的人》)………王苏辛以含混的寓言手法诉说着人类文明史是如何在时代裂变中步入难堪的尾声。“智齿”“尾巴”“鱼鳞”“羽毛”这些充满“返祖”色彩的意象也时刻纠缠着人类文明史的源头——小说的“尾声”恰恰意味着最为原始的“人”(更为恰当的说法也许是“类人”)的诞生,而物种的进化或灭绝并不影响整个世界的“归零”,亦如作者在《下一站,环岛》这篇小说里难以抑制的主动介入与情感渲染:“一切都开始恢复秩序。世界上的一切开始重新建造。正如这列绕着一个圆形运转的地铁,每个人都会回到最初的那个位置。”j
所谓“尾声”的表述,其实质应该归结为作者王苏辛本人的叙事策略。汉斯·贝尔廷针对艺术史发展的“尾声”问题指出:“尾声意味着什么,是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还是现代派或绘画的终结,这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人们对尾声的需要,因为这种需要刻画了一个时代的特性。”k而另一方面,“对尾声的需要”也成为写作者的某种富有深意的结构设置。王苏辛选择以“末日”状态作为“尾声”的表现方式,从而确立了小说的时代特性,而“末日”的起源则是“人”的畸变,这也构成王苏辛小说创作的逻辑起点。
王苏辛小说中的个体畸变与群体畸变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生理层面的畸变。如前文提到的“人”在相对应因素催化下“返祖”向“类人”进行过渡,或是“人”的物化。另一类是精神层面的畸变。《白夜照相馆》 《你走之后,我开始对着墙壁说话》可算是两篇覆盖在这一主题底下的小说。尽管王苏辛有意识地抽空文本的具体时间及背景,但《白夜照相馆》 《你走之后,我开始对着墙壁说话》大致可被嵌进现代城市建设的线性发展脉络内进行言说。《白夜照相馆》里,“白夜照相馆”的存在意味着被人为重构的“伪记忆”。照相馆经营者赵铭、余声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拍摄出符合顾客需求的家庭照。家庭照,在固有认知中是身份血脉的证明。不过赵铭、余声则可以依据相应要求“篡改”顾客的身份与血缘,各怀鬼胎的顾客凭借子虚乌有的家庭照去向自己的情人、朋友、同事,甚至是陌生人,兜售着自己未曾经历过的岁月。这篇小说的每一个人物都隐藏着令人生疑的“过去式”,但照相,这种用以存储个人或群体容貌的常规操作手段,却由于现代技术的更迭让心存不轨的人获得“重塑自我”的伪饰良机(在王苏辛另一篇小说《喀尔敦大道》中,照相机就被颇具意味地指认为“是在凸显人的意图上面精进”l),以全然虚构的过往维系当下并不牢固的人际关系。然家庭照愈是美满热闹,现实生活愈发脆弱不堪,那些借助技术修改自我身份、适应全新生存环境的人离自己原本“位置”也越来越远。
《你走之后,我开始对着墙壁说话》将离奇与惊恐统统留在小说结尾。一对无法进行正常交流的夫妻回到家后,发现自己的孩子正对着卧室墙壁不断说话:
她热情洋溢,像是舞台表演嘉宾。她化着精致的妆,非常美。只是脸上很油腻,显然好几天没有卸妆。她不停地说着,重复着一套我似曾相识的动作——做饭、插花、拍照,时而对着社交网络大笑。m
女孩行为举止的诡异在当下的社会中其实已司空见惯。因为在各类网络直播平台上,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会有形形色色的男孩女孩对着网络媒介的“墙壁”开始“自言自语”。他们想象着接受者在虚拟空间的某一端真实存在,而更为重要的是言说者自我思绪情感的单向度传递——她们要让想象中数以千万计的观众围观自我演绎的喜怒哀愁。无法正常交流的夫妻与具有疯狂言说欲的女儿,旨在揭示当下社会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沟通交流正趋于无效,交流的手段、过程替代了其本应抵达的终极意义。这一语境下的“交流”也就逐渐脱离固有词义,沦为永远无法抵达彼岸的自我表演与自我陶醉。尽管王苏辛在结尾处缺乏沉稳的处理,削弱了小说本应贯穿至尾的强烈的反讽气息。但《你走之后,我开始对着墙壁说话》无疑奠定了王苏辛小说创作的某种基调。
如同绝大多数热衷暴行实践的青年作者,王苏辛毫無克制之意地让那些或残缺或肢解或变形或异化的“身体”(body)在文本间肆意横陈。不过,这与我先前所言及的“末日”状态并没有直接关联(那些无处不在的“身体”诛戮,或许更应该被理解为“末日”场景的形式部分,而“末日”状态则指向个体面临生存绝境时的精神意绪)。不同于我们对“绝境”的常规认知,王苏辛小说的“末日”状态往往起始于看似平淡无奇的幽微细枝处。如《马灵芝》的奶奶,她的存在“已经成为家门口一件毫无存在感的摆设”n,只能通过自娱自乐来排解无人问津的日常生活。突如其来的死亡,反而让老人在濒临家庭“绝境”时获得了彻底的解脱。《战国风物》演绎的则是另一种家庭内部景象:女儿须旦为防止母亲时常在门口偷听自己打电话,“用针在门缝处扎来扎去”o。针,作为具有修补作用(同时却又不乏攻击性)的日常物件,击中的不仅是母亲的耳朵,也包括母女间长期存在的隔阂与误解。门内须旦不断“用针在门缝处扎来扎去”的行为正是对于由血缘决定的至亲关系的质疑,而门外附耳偷听的母亲则指向那个从未被须旦真正信任过的隐秘世界。这对母女也陷入了难以彼此接近、理解、共通的“绝境”。此处的“绝境”,消解了母女在彼此关系中原本不可替代的角色,“关系”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被削弱。
由此可以看到,王苏辛试图作纵深向“冒犯”的是“关系”在现代社会的有效性。《我们都将孤独一生》是对这一命题更为具象化、也更为极端的文本呈现。夫妻一旦离婚就会变成镇守在家门口的雕像,两者“关系”的亲疏决定了雕像间距离的远近,以及雕像是否能够复原为人形:
对比《下一站,环岛》 《荒地》,《袁万岁》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作者创作视野的自我超越。剥离各种故弄玄虚的“形式外衣”,《下一站,环岛》 《荒地》更像是对已知世界所进行的并不到位的缩略复述。纵然王苏辛有意通过“空间体”与“空间体”的彼此“冒犯”,进而强调她笔下句子想要点明的人际矛盾、阶层纷扰,然而如果小说的目标仅仅只是为了告知读者“冒犯”是怎样产生,及“被冒犯”的“类”“个”在何种摇晃不定却又无比相似的悲惨境遇底下忍受煎熬,那么我坚信,长期蹲守在“现场”的社会新闻记者完全可以取而代之。
写作《袁万岁》的王苏辛则选择将叙述聚焦在现实与梦境间那段狭长而多义的区域,她借助“我”之口指出了梦境的不确定性:“梦的记忆总是会在叙述中被随意篡改。”s梦境的不确定性被延伸向由文本构建的现实,作者的迟疑态度也从未间断过:她借由一副布满半透明隐喻的身体对“自我”(ego)的合理性进行着重新审视与衡量t;她创造了“袁万岁”这个人物,但“袁万岁”又可能只是叙述者“我”臆想出来的一类“空间体”的符号集合。“我”的遭遇必然嵌合着作者的个人印记,而真实记忆中得到确认的部分又在叙述中转向不稳定状态。这些未必是王苏辛事先设想的,但“不稳定状态”的的确确赋予《袁万岁》以更为明朗宽阔的格局。如果将“空间体”视作喻体,小说的现实性勾勒出了一类“空间体”,小说的虚构性被表述成另一类“空间体”。尽管作者在《袁万岁》里建立了多组具有“冒犯性”的异质对象,但她没有让现实同虚构这组“空间体”抵牾对峙(或者说,主动去寻求某种定义“冒犯”的书写规范),而是任其延展、任其生长,并在不经意的间隙形成交汇。相较而言,《下一站,环岛》 《荒地》 (包括《直立行走的人》 《自由》 《在湿地与海洋之间》)的致命问题在于,王苏辛实在过于熟稔现实与虚构、本体与喻体的区分界线,这也就意味着其本人明确知道应该相信什么,不应该相信什么;应该让读者相信什么,不应该让读者相信什么。倘若作者遣使所剩无几的经验资源只是为了设置出连她自己都坚信“只能存在一次的世界”u,我们只能将荒诞归还给荒诞,将现实归还给现实。因为作者自以为公允的定夺已然暴露出具有重复性的偏见,而毫无自省意识的“冒犯”总容易散发令人厌倦的平庸。
所有的问题,应该回到最初那个困扰王苏辛的“最该动的部分”。当“冒犯”显现出从未有过的司空见惯,如何克制呼之欲出的“冒犯”冲动反而更为关键。夹杂着强烈偏执的“四处出击”并不能真正撼动“最该动的部分”,倒更形同拒绝颠覆的遁词。所谓偏见,是草率地厌恶一类事物,也是轻易地推崇另一类事物。如果一个写作者过分沉溺于由自我偏见所编织的评判关系中,便注定了“冒犯”的无功而返,也注定了“自我”的虚无缥缈。
【注释】
a金理:《历史中诞生——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中的青年构形》,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2页。
b王苏辛:《练习面对自己的能力》,《名作欣赏》2018年第1期。
c王苏辛:《他经历着常常不被理解的最好的事情》,《小说界》2017年第4期。
d[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陆建德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12页。
e王苏辛:《所有动画片的结局》,《收获》2018年第4期。
f王彬彬:《当代作家的可持续写作问题》,《扬子江评论》2007年第1期。
gp王苏辛:《我们都将孤独一生》,《白夜照相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46页、50页。
h王苏辛:《再见,父亲》,《白夜照相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52页。
i王苏辛:《昨夜星空璀璨》,《白夜照相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61页。
j王苏辛:《下一站,环岛》,《白夜照相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123页。
k[德]汉斯·贝尔廷:《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洪天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l王苏辛:《喀尔敦大道》,《小说界》2018年第3期。
m王苏辛:《你走之后,我开始对着墙壁说话》,《白夜照相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82页。
n王苏辛:《马灵芝》,《青春》2016年第3期。
o王苏辛:《战国风物》,《白夜照相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28页。
q[日]小森阳一:《作为事件的阅读》,王奕红、贺晓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rs王苏辛:《袁万岁》,《白夜照相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95页、87页。
t2018年7月22日,在清华大学、《收获》杂志共同召开的清华大学青年作家工作坊活动上,王苏辛的發言就涉及到“自我”的阐述:“自我不是一个单独的人,一个单独的个体,当一个人决心写出他想写的他想表达的,其实他是想写出很多人心中的话、写出很多人的共同经验。自我正是这种渴望下生长出来的那个形象。”这或许可与小说《袁万岁》中的“自我”互为参照。相关发言内容见“收获”微信公众号:《跨时代写作者与写作形态的碰撞》,2018年7月25日。
u王苏辛:《自问自答》,《小说界》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