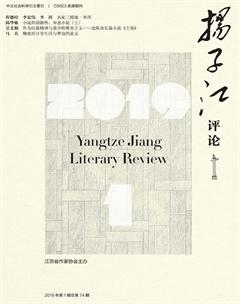新世纪诗歌民刊的困境与可能
王士强
在中国当代诗歌的变革中,诗歌民间刊物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以《今天》为首的诗歌民刊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新时期诗歌之发生的策源地,在此后的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民刊无疑都是诗歌中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部分,最为敏锐地感知和体现着诗歌的新变,在思想上与艺术上均极具先锋性。而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年以来,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整体变化和诗歌生态本身的逻辑演变,诗歌民刊的地位与作用也在变化,其先锋性、影响力、作用似乎都在下降。应该如何看待这一时期的诗歌民刊,它还有没有价值和意义,是否还值得人们更多的期待?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的辨析和厘定。
一、 一个回顾:民刊作为当代先锋诗歌的“小传统”
诗歌民间刊物在相当程度上是自发、自在、不受规训的,可以较大限度地绕开一些障碍而自由、独立地发声,成其所是。这种特征与普遍意义上诗歌的自由本质,与诗歌的先锋性(尤奈斯库所谓“先锋就是自由”)是高度契合的。故而,民刊在当代诗歌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不是偶然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一体化社会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诗歌民刊生存空间比较有限。只有极少数比如大学校园里学生办的刊物(如北京大学的《红楼》 《广场》)或者有一定家庭基础、在若干同好之间组成文艺沙龙性质的交流圈子自制文艺作品集(如“X诗社”“太阳纵队”)在短时间内有零星存在,此后“文革”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手抄本”流行,在自发、隐秘的状态下传递着艺术的火种,磨砺着一代青年人的思想与技艺,诗歌如野草般在意识形态管控的荒芜与薄弱之地生长,并如翻滚的岩浆般找寻着喷薄而出的突破口。1970年代后期社会、思想的裂隙以及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动、转型无疑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今天》等民间刊物先试啼声,鸣响了思想解放和精神启蒙的号角,得风气之先,发出了一个时代的强音。可以说,《今天》构成了当代诗歌民刊序列中一个光辉的起点和高点,这种地位一方面与其诗歌的质量、水准、价值有关,同时与其时代背景、历史境遇、外部环境密不可分,这两者的结合是可遇不可求的:它开启了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也成就了它。在此后的80年代和90年代,诗歌民刊都事实上成为了诗歌变革的先导和诗歌实绩的最重要体现者,《他们》 《非非》 《莽汉》 《撒娇》 《北回归线》 《发现》 《葵》 《独立》 《存在》 《女子诗报》等众多民刊如星火燎原般整体性地改变了当代诗歌的品质,推进了当代诗歌的变革。关于这一点,诗歌界、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能够代表当前的当代诗歌史研究水准的《中国当代新诗史》述及这几个时段的诗歌民刊时便指出:“文革”后到80年代初,“‘文革期间延续下来的传抄仍是手段之一;而自办诗报、诗刊、自印诗集,也开始风行。许多城市,特别是各地的大学,在80年代初,都出现同人性质的诗刊,并形成各种诗歌‘小圈子。最早创办、影响广泛,并成为‘新诗潮标志的自办刊物,是出现于北京的《今天》。”80年代后期,“在这个阶段,‘新诗潮中的实验诗歌、第三代诗的写作,主要在自办的‘民刊上出现。”而在90年代,“‘民办的诗刊、诗报,在支持诗歌探索、发表新人作品上,是‘正式出版刊物所无法比拟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展现最有活力的诗歌实绩的处所。” a这样的观点应该说是持中公允、客观公正的,能够代表学界的主流观点。
就当代诗歌民刊的地位与作用而言,可以说,它一方面是“先锋”的,是这一时期诗歌中最为新锐、前卫,最具实验性、活力和创造性的部分,“民刊策略已经构成中国新时期先锋诗歌的基本生存与传播方式”b。而同时,在历史的河流之中,这种先锋性已经内在化、历史化为一种惯性或基因,成为了“中国诗歌小传统”c或者“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d。这里面“先锋”与“传统”有一种纽结、矛盾或者错位,“先锋”往往意味着非传统、反传统,意味着断裂,而“传统”更多的是常识、常态、秩序,意味着连续,两者之间有龃龉和分野,但其实也可以这样理解:“先锋”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而成为“传统”,或者说,我们的“传统”本身便是包含了变革、自否、超越自我的因素,本身便包含了“先锋”。如此,两者的结合使得“先锋”不只是为求新而求新,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传统”也不是一成不变、僵硬固化的,不是一潭死水,其间有着一定的双向激活、促进的效应。
二、 近年来诗歌民刊的新处境与新变化
回溯过往,诗歌民刊的历史可谓光荣,但是回到现实、回到当下,形势确又有所不同。21世纪网络语境中的诗歌民刊“存在感”降低,似乎已经荣光不再,其影响力和所发挥的作用都在下降。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一系列的新变化,并对这一时期的诗歌民刊进行界定、评价?
考察近年的民刊状况不能不与近年来社会的变化和诗歌的处境相联系。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中国社会整体是往更为开放、自由和多元的方向发展,人们的思想和价值取向更为多样和丰富,诗歌在这一时期也更为边缘化,其在公众生活中的主导趋势是后撤、退隐的。当今的时代总体而言已经失去了整体性而进入了碎片化的时代,而民刊也陷入了“无物之阵”,此前的那种作为“对立面”的庞然大物已经消失,诗歌更多的是进入了悄无声息、无人喝彩的状态。在新时期之初,民刊面对的主要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围困与冲突的命题,在80年代中后期,民刊面临的是作为时代“共名”的现代化的焦虑以及凸显自我、自由发声的问题,到90年代,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着此前的民间与官方的二元對立结构和紧张关系,民刊仍然有着向主流秩序挑战的意味,当时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其实并不是如表面所看来的对立,其共同的对立面应该是既有、超稳定的文化结构与秩序。这样的状况在进入21世纪之后则有了很大不同,支持“先锋”的那种叛逆冲动已经逐渐耗尽,网络时代最初几年的狂欢和无下限的表演也很快便偃旗息鼓,我们时代的文化更多的进入了与权力和资本的合谋之中,先锋诗歌作为一种群体性的运动基本已经消歇、止息了。这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因素是网络。网络在世纪之交的出现和此后的快速发展对于诗歌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它改变了诗歌的整个生态结构和存在方式,并迅速成为了诗歌的“第一现场”。应该说,网络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对于民刊确实构成了一定的冲击,许多诗人的兴趣和注意力转到了网络上面,对于民刊的关注度和重视程度必然会有一定的下降。在这其中也发生着如评论家张德明所指出的“民刊网刊化”的变化:“为了适应新世纪以来日趋显在的网络文化语境,不少民刊也纷纷上网,民刊的网刊化成为民刊存在和传播的重要形式,从前纸质版的民刊逐步变成了网络版的民刊,这虽然节约了民刊出刊的成本,但无意间将从前实体化的民刊变成了虚拟化的存在,大大弱化了它的文本权威性和充当艺术先锋军的诗学力量。”e这是其一。其二,公开(官方)刊物与民间刊物之间壁垒森严的状况不再如此前那么明显。如果说此前的公开刊物有些“高高在上”,落后于诗歌的新变,从而造成了公开刊物与民间刊物之间一定程度上的对立,在近年来公开刊物则已经“放下身段”并向民间刊物敞开怀抱,多家公开刊物设专门栏目或定期不定期从民刊选取作品,一些作品在官刊和民刊同时面世抑或先官刊后民刊发表,如此造成了官刊与民刊界限的模糊,此前先在民刊发表作品而后引起官刊注意从而形成一种时间差序和功能区隔的现象而今已不再明显,两相对比,官刊的作用似乎在增强而民刊的作用在下降。民刊的作用和影响一定程度上被网络诗歌和公开刊物有所稀释了,这是造成民刊的影响力没有此前那么突出的原因。当然也应该看到,无论是网络诗歌的发展,还是公开刊物对于民间刊物的接纳甚至竞争,都是时代的进步,对于诗歌的发展而言是有益的。
这一时期的诗歌民刊本身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其存在形式更为丰富、灵活、多样,民刊与官刊之间的边界更为模糊。许多的民刊也有公开出版、公开发行或者官刊化的趋向,有的是用正规刊物分出来的“下半月刊”(如数年前老巢、安琪所办《诗歌月刊·下半月》以及潘洗尘所办《星星·下半月》),有的是由出版社正规出版的以书代刊的“丛刊”形式(如张执浩主编《汉诗》、泉子主编《诗建设》、阎志主编《中国诗歌》、张尔主编《飞地》、潘洗尘主编《读诗》 《评诗》、娜仁琪琪格主编《诗歌风赏》 《诗歌风尚》等),有的则是用香港、澳门、台湾、海外的书号出版(如《中西诗歌》及近期的《非非》 《女子诗报年鉴》等),还有的刊物时而自印发行时而有书号公开发行(如杨黎主编的《橡皮》)。此外还有一种独立出版现象,此类出版多以出版基金、出版计划名之,由个人、团体资金支持或者众筹募集资金,自行编印诗文集而不必经过出版社的出版审查程序,因而更具自由度和独立性,如评论家赵思运所指出的,“汉语诗歌资料馆、不是出版基金(The Atypical)、黑哨诗歌出版计划、坏蛋出版计划,彰显了不同于现有出版体制的特征,即‘独立、‘非典型、‘非商业、‘非政治”f。如此等等,而今的民刊形式上极为多样,许多是此前未有的。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资本的进入诗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诗人(或“前诗人”)的经济能力已较为可观,愿意出资反哺诗歌,还有一些机构、个人也愿意资助、赞助诗歌活动、诗歌出版等,如此催生了诸多的诗歌出版物,这对于诗歌的发展整体而言无疑是有益的。当然具体过程中也存在诸多的问题值得认真辨析,但这些现象的存在本身是值得肯定的。这里面许多刊物的性质有些模糊,亦“官”亦“民”,可“官”可“民”,有必要对民刊进行一种界定。或许可以将民刊分为狭义和广义两者,狭义的民刊指此前那种自筹资金、自印、无刊号或书号的诗歌印刷品,广义的民刊则指非官方出资、无“主办单位”的连续性诗歌出版物,上述所谈及的几种公开出版、发行的出版物可归入广义的民刊。就“民刊官刊化”而言,人们对之评价的分歧主要在于其经过了制度化处理措施,是否还具有“民间”的性质。有学者便对民刊公开出版发行的形式进行批评,认为这是对于其“独立自主性和先锋探索精神”的背离:“一些民间诗刊为了在现实语境下夯实自己的存在合法性,采用以书代刊的形式来出版发行,这存在着损害民刊的独立自主性和先锋探索精神的消极意义。民刊的独立自主性和先锋探索精神,是与其自行印刷、免费交流、圈内传播等联在一起的。民刊一旦纳入正规化的出版体制,必将受到体制化运行规范的制约,其不遵常规的先锋性思想表述和形式探求肯定会受到一定冲击。”g这种分析是有道理也有必要的。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无论如何这样的出版形式总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度和灵活性,更容易体现出一些个性化的色彩,更容易办出一些特色来,它们毕竟不是官刊,所受到的束缚较之官刊还是要更少一些。就其现实表现而言,许多的刊物确实也办得水准较高,形成了自身的优势栏目和品牌效应,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其存在显然是有益的。加之有的出版物具有书号、刊号,能够公开发行,能够到达更多读者的手中,其传播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具有一定的市场回报,可持续性也更强,这对于刊物的品牌建设和长远发展来说也是更有益的。当然,就诗学价值而言,诗歌民刊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恐怕仍然是那种狭义的同人性、有较为明显的诗学主张和追求的,这样能够保证它的纯粹性,形成和保留自己的个性与特色,如此也是最有可能办好并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一个时代民刊的品格与特色仍然主要需要由这些刊物来承担。当然也不可否认一些综合性的民刊(如《诗歌与人》)也很有价值,也可以形成品牌并产生大的影响。归根结底,编选者的眼界、品味和襟怀,以及由之形成的刊物的品格与质量,是决定一份刊物价值的决定性因素。
近年来诗歌民刊有所合流、分化,虽然就其现象层面仍是热闹、活跃、繁荣的,但其影响力和诗学价值、创造性与此前相比确有下降。就其数量而言,诗歌民刊的数量较之此前仍有过之无不及,就其质量来讲,应该说更显芜杂、暧昧、平庸,能够产生较大、较为广泛影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太多。当然,在整体性的匮乏、苍白之中,应该看到也仍然有刊物是沉潜、有定力、有独特追求、戛戛独造、不从俗流的。由诗评家张清华主编、主要以民刊为载体展示中国当代诗歌成就的《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h厚厚两大本,百余万字。该书共收录39种民刊,下卷主要是21世纪以来的重要民刊,收录《诗歌与人》 《第三条道路》 《零度写作》 《漆》 《或者》 《人行道》 《新城市》 《终点》 《南京评论》 《行吟诗人》 《极光》 《诗歌现场》 《野外》 《不解》 《蓝风》 《新汉诗》 《活塞》 《低诗歌》 《大象》 《后天》 《海拔》 《城市诗人》等共22种,其中所体现的诗学主张、诗歌追求、风格面貌可谓多样,呈现了当代诗歌内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些刊物当然还不是当代诗歌的全部,但就目前所看到的已非常可观,足以让人惊异。总体观之,或许可以这么说,这一时期的诗歌民刊大致是由“先锋”来到了“常态”,已经失去了此前的某种桀骜不馴、解构性、革命性的特质,不再咄咄逼人,不再剑拔弩张,没有了“假想敌”,“先锋”特性有所流失、离散,而更多的是进入了一种日常的、不显山不露水的状态。但是也还是应该看到,最优秀的诗歌民刊其内在并没有失去先锋性,它仍然是诗歌创新最为敏锐、最具活力的部分,只不过这种“先锋”其表现和其内容确实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不再是徒具其表、形式大于内容的口号、概念、形式实验,而更多是有内在根基和依据的个人化创新、创造,这可能是更为有效的先锋。或者说,这一时期的诗歌民刊看起来是进入了一种“常态”但实际上是“先锋”和“常态”的结合,它其实是一种先锋的常态或者常态的先锋,说它是常态的时候,它是包含了先锋性的常态,说它是先锋的时候,它是更为内在和可持续、表现为常态的先锋。
三、 展望:民刊的不可替代与生生不息
关于诗歌民刊的发展前景,应该说它仍然有其不可替代性和价值意义,它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相反仍大有用武之地。诗歌民刊仍然代表着创新与创造,代表着不可规约与不可驯服,代表着丰富性与多样性,代表着对诗歌宽度、广度、深度的勘探和测量。诗歌民刊在我们时代固然面临着重重问题,面临着权力与资本的围困,面临着被瓦解与被耗散,面临着自我消解与自我阉割……但是,仍然有少数在坚持,在发出不同的声音,在维护着诗歌本身的尊严,它不会轻易地就被击败、被剿灭或者自我退场。学者何言宏曾就诗歌民刊与知识分子精神、先锋精神的关系阐述道:“我们也能自然地感受到当代中国的民刊实践与中国早期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联结。一种职志于文学、诗可以群、亦以现代以来的印刷媒介而群,并且以此自主性地发表作品、表达自己的诗学观念与文学主张的精神追求,容有可能,向未断绝。”“虽然在总体上中国文学的先锋大潮兴许已落幕,但先锋的精神、先锋性的诗学追求仍未死灭,它仍潜藏在我们文学的深部,潜藏在我们的民间诗刊中。”i就诗歌的自由精神、先锋品质来讲,很大程度上民刊在当今仍然是一个最佳、最值得信赖的载体,它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相比另外的两种发表形式,民刊也仍然有其优势和长处。相比官方刊物,民刊仍然要更自由、更灵活一些,更容易形成自身的品格和特色,作品形态也可能更为真实、丰富、有力一些。与网络诗歌相比,诗歌民刊也具有一些优长,网络上的作品更为芜杂、参差不齐,而民刊总的来说是经过过滤、遴选的,其作品的质量相对来说要更高、更整齐,也更为可信、有效些。就此而言,民刊的意义其实不仅在当下,它的一个可能的用途是作为我们时代诗歌的“足本”或“善本”成为后人文学版本考辨和“知识考古”的对象。
诗歌是对自由的追求和对不自由的克服,诗人周伦佑曾言:“写作是对不自由的意识。诗,不是词语通过技巧和韵律的任意排列,而是人类自由的最高书写形式。”j就现实可能而言,诗歌民刊正是承载这种自由的一种不可替代的载体,它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对诗歌自由精神的体现和诠释,代表着诗歌自由生长的意志,它有璀璨而光榮的过去,有面临压力与诱惑而负重前行的现在,其未来也定然是与诗同行、生生不息的!故而,当今时代的诗歌民刊既面临着困境,也面临着新的可能,先锋性在这其中有褪减、遁失、消泯于无形的危险,但同时也有着续存、光大、再度跃升的可能。对于诗歌民刊现状的评价以及其未来前景,固然不必盲目乐观,却也不必过于悲观。正如我们应该相信诗歌的发展有一种内部制衡、自我纠偏的能力一样,诗歌民刊同样如是,它仍然值得人们更多的关注、付出与期待。
【注释】
a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6页、245页、301-302页。
② 罗振亚:《亚文化选择:民刊策略与边缘立场》,《诗探索》2003年第3-4辑。
③ 西川:《民刊:中国诗歌小传统》,《扬子鳄》总第3期,2002年4月。
④ 于坚:《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4期。
⑤⑦ 张德明:《探知先锋求索踪迹的有效窗口——论当代诗歌民刊的诗学意义》,《岭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⑥ 赵思运:《从民间出版到独立出版——以近年民间诗歌传播为例》,《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⑧ 张清华主编:《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
⑨ 何言宏:《当代中国民间诗刊的文学文化意义》,《文艺争鸣》2017年第9期。
⑩ 周伦佑:《见证黑铁的诗与思》,周伦佑主编:《非非》总第13卷,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