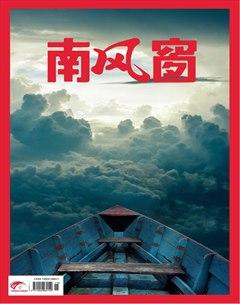臧鸿飞与90年代的中国摇滚
姜雯
1990年2月17日、18日两天,后来被称为“中国首届摇滚音乐节”的演出在首都体育馆进行着,这场震撼并影响无数人的演出,又被称为“90现代音乐会”。
当时的首都体育馆大概去了3.8万个观众,座无虚席。场地安置了200个巨型喇叭,一群平均年龄只有24岁的年轻人在舞台上释放青春的压抑,释放摇滚的力量。
演出阵容有唐朝、崔健的ADO、眼镜蛇、臧天朔的 1989、宝贝兄弟、呼吸等国内顶尖摇滚乐队。盛况空前绝后,鼓声和音乐声刺激着听众的耳膜和神经,让人血脉贲张。
“那个演出对所有去的人,对他此后的人生都挺重要的。我印象中好多人,比我大的那些孩子,表现比我更疯狂。我感受到那种音乐带给人的刺激、快感,对我来说,是自由。”那一年臧鸿飞13岁,在此之前他在学习古典乐,这场与摇滚的意外邂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后来他成为国内顶尖键盘手,和许巍、郑钧、张楚、姜昕等知名音乐人合作过,经历了90年代中国摇滚乐的黄金时期,也见证了时代变迁下中国摇滚乐的起落。
90年代的摇滚
那是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正在深化,时代的巨轮风驰电掣。一切都朝气蓬勃,一切又飘摇迷茫,未知、神秘但充满活力。人们谈论诗歌、谈论尼采、谈论理想。人们渴求知识、渴求新鲜事物、渴求广袤的世界,如同动物破壳而出,迎着太阳,饥饿,好奇,无畏。
崔健在1989年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是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摇滚乐专辑,并且在1990年开始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全国巡演。接着还有黑豹乐队1991年发行的 《黑豹》,唐朝乐队1992年的《梦回唐朝》。
1994年是中国摇滚史上的巅峰之年。“魔岩三杰”窦唯、张楚、何勇同时推出了《黑梦》《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垃圾场》。崔健推出《红旗下的蛋》,郑钧推出 《赤裸裸》。許巍发行单曲 《两天》《青鸟》。11月,汪峰的“鲍家街43号”乐队在中央音乐学院成立。12月,“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在香港红磡体育场举行演唱会,震撼世界各地媒体和近万名在现场的香港观众。
从现在残存的影像资料再去回顾当年的盛况,90年代的确是摇滚乐最蓬勃最鼎盛的时代。但90年代的摇滚也被过分美化了,让现在动不动就怀旧的年轻人误以为那时的一切很轻易,误以为一切唾手可得。
即便中国社会在90年代如日方升,那还是一个相对匮乏的年代。臧鸿飞说那时候没有渠道找到想要的音乐资源,没机会听到更小众的东西,即便知道一些乐队的名字,也未必能和别人聊,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所以会想尽办法得到信息,去认识玩乐队的人,然后慢慢和他们一起玩。
“我觉得现在已经没有摇滚圈这个概念了,那时候真的有圈子,知道哪里有party,哪里有谁,你不认识圈内的人,就不知道。”
越是匮乏就越是要努力寻找。臧鸿飞说那时候他们会去语言学校和外国小孩聊,从他们那里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他们在听什么样的音乐,甚至会带着磁带去录自己喜欢的歌。“有点像是野生动物在觅食的感觉。而现在的年轻人,完全是喂养式的,整个流行文化,就是像饲料一样喂给你。”
90年代的摇滚也被过分美化了,让现在动不动就怀旧的年轻人误以为那时的一切很轻易,误以为一切唾手可得。
“就像前两年,年轻人都要听说唱,你问他,知道说唱音乐是怎么来的吗?没人知道。怎么来的街头文化,也没有人关心,他们只关心节目里选出来的那些人。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喜欢摇滚乐,我们一直追溯到摇滚乐的最开始,并以那个状态来生活。”
臧鸿飞喜欢90年代,摇滚乐在90年代很火,但他认为那时候也更艰难。“90年代是整整10年,10年间北京出现过那么多乐队,可留下的却只有这么一点影像,你有想过他们平时的生活吗?没有出路的绝望。”
摇滚乐队没有任何渠道宣传自己,也没有演出会主动找上门,只能自己办摇滚party。臧鸿飞回忆当时唯一的宣传办法,是去大学贴自己印刷的海报,还经常被撕掉。一场party最多来一两百个人,大家没办法靠这个生活,那时候的地下是真的地下,摇滚乐和整个音乐圈是完全割裂的状态。
虽然“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登上了红磡的舞台,从仅存的照片和影像中让人觉得那时很酷,光芒四射,但现实生活中大家过的都还很艰苦,没有人因此过上一个音乐家的生活,生活依旧非常拮据。
可90年代的音乐人是怀抱理想的,他们将社会责任投射到摇滚乐中,将理想主义的悲壮和浪漫化作音符和歌词,他们对时代不妥协,并希望藉由音乐去改变这个社会。其实更像是一种绝望与希望的并存,正因为心怀希望,才得以在现实的绝望中继续前行。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摇滚乐已不复当年的盛况。2000年互联网普及之后,对独立音乐人来说都不是一个更好的时代,从前中国摇滚乐队有巡演意识的时候,每场只有几十人、几百人,到现在一个音乐会能去上万人。越来越多摇滚乐队出现,但却变得更商业化、更娱乐化了。
可以说时代变了,变得越来越娱乐化了。也可以说时代变了,变得更幸福了。臧鸿飞认为他那一代人,觉得自己跟社会格格不入,但现代的年轻人物质生活更丰富了,也更乐于投入到当代生活中,他们有参与游戏的快感。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不一样,因此音乐的表述也不同。
摇滚精神
什么是摇滚精神?这可能是摇滚门外汉常会问的问题,带着对摇滚乐朦胧的喜爱与好奇。但其实摇滚精神并没有明确定义,就像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崔健曾在知乎上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摇滚不仅仅是一种音乐的概念,而是一种态度和人生观的概念。”“其实摇滚精神是人的精神,不用太强调摇滚两个字。”
臧鸿飞认为,摇滚乐的态度是质疑的,真正喜欢摇滚乐的人,不盲从偶像。摇滚乐让人崇拜偶像,学习偶像,质疑偶像,最后推倒偶像。从质疑偶像到推倒偶像的这个过程中,人就成为了自己,更加完整的、独立的自己。
这让人想到尼采,这也是摇滚乐与流行文化最大的区别,流行文化更像是一种“造神”的文化,它让你觉得偶像是十全十美的,它让人们盲目追随。而流行文化本质上是消费文化,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将之定义为“文化工业”,偶像不过是被物化、被量身订制、按照计划打造的商品,以此达到娱乐的效果,其最终目的是消费。
阿多诺描绘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现象,摇滚乐起源于40年代末期的美国,在50年代开始流行起来,那时正是战后美国经济高速发展和消费社会形成的时候。摇滚乐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工业的产物,但它又是一则反例。
说它是文化工业的产物,是因为摇滚乐的流行也得益于技术革命,唱片技术让不同形式的音乐得以传播给不同听众。说它是反例,是因为阿多诺批判的是技术带来的让大众沉溺而失去思考能力的同质性,但“大西洋”“国王”“太阳”等专门服务于小众的独立公司开始录制R&B和乡村音乐,这恰恰被那些大唱片公司认为是“不雅的、专门为特殊群体(黑人) ”提供的服务。而越来越来越多的年轻白人也开始转换电台频道去收听这些所谓的特殊群体的音乐。

摇滚乐通常被认为是“节奏布鲁斯”和“乡村和西部音乐”的结合,但这不能代表全部,摇滚乐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非裔美国人的音乐传统。当时的布鲁斯唱片会被贴上“种族唱片”的标签,但节奏布鲁斯随着美国南方黑人向北迁徙时,摇滚乐也逐渐演变,并受到白人的关注。所以某种程度上,摇滚乐的诞生和流行是反文化工业的、反主流的。
不盲从偶像是摇滚乐与流行文化最大的区别,流行文化更像是一种“造神”的文化,它让你觉得偶像是十全十美的,它让人们盲目追随。
从表面上看,摇滚是通过堕落、颓废、躁动、混乱、黑暗、死亡等元素来揭露社会的黑暗面,来发泄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但摇滚仅停留在宣泄吗?当然不是。批判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批判的力量来自思考,而思考是人类最伟大的力量,所以保持独立思考才不至于走向真正的堕落。
摇滚乐不仅仅是一种音乐形式,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处世态度、一种审美品位。臧鸿飞认为,真正的搖滚人,他的生活是一以贯之的,是一种摇滚乐的生活状态。从穿的衣服、作息、饮食、读的书、看的电影、交友圈,都是以摇滚乐的审美在贯彻,这不是唱片公司企划和包装出来的。
流行歌手披着摇滚的外套是摇滚吗?流行音乐使用大量吉他营造一种躁动的氛围是摇滚吗?当然不是,那还是流行音乐,不一样的是其精神内核。崔健早就是崔健了,但他还是去看演出,去小酒吧看年轻乐队,臧鸿飞觉得这是真正的摇滚乐。
“这个就是真的摇滚乐,而不是被那种流行公司包装出来的,他(指流行歌手)平时的生活也不是那样子。我个人认为,摇滚乐是有破坏性的,对现实不满的年轻人,他们发明了这个东西,有破坏性、颠覆性、反抗精神在里面。”
但臧鸿飞也表示:“我觉得摇滚乐从90年代到现在,从最早的那种悲壮的、理想主义的摇滚乐,变得更商业了,变得更娱乐化了。”
那么回到前面提到的问题,摇滚乐是否已经被文化工业所吞噬?又或者说,每个时代都是最坏的时代,每个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