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长城》到《珠穆朗玛的眸子》
付如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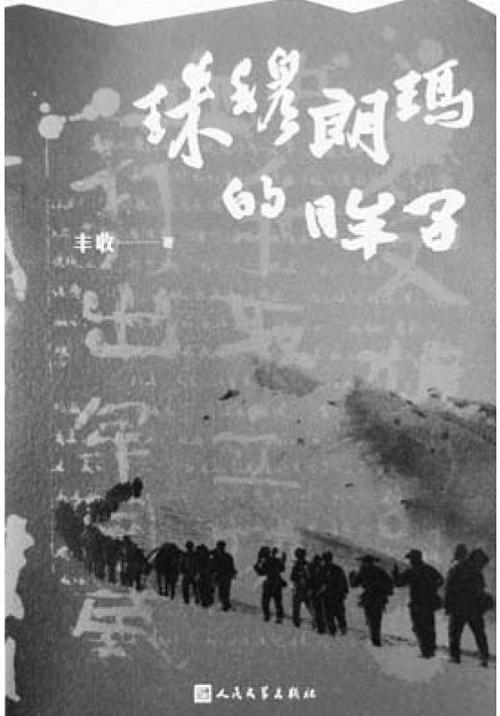
“非虚构”的力量与困境
作为一种文体,“非虚构”的边界很宽泛,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历史文学、口述实录,甚至包括传统媒体的特稿、深度调查报道等等,都可以划到它的范畴里来。具体到中国文学,一度被称为“时代轻骑兵”的报告文学是主流,后来随着王树增的战争系列和历史系列,随着《中国在梁庄》《我的阿勒泰》等一系列本土原创作品的走热,以及以《寻路中国》为代表的引进版“非虚构”作品的大受欢迎,报告文学的文体逐渐产生变化,使得“非虚构”的概念逐渐生成并渐成主流。尤其是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非虚构”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对这类文体的勃兴更是一种提振的力量。
应该说,这是一种创作者充分尊重事实,将“个人”无限“隐藏”在事实和真实之后的文体;也是一种能够直接记录时代、直面真实、直面问题,对读者的认识能够直接产生作用的文体。如果一部作品,在事实的基础上,讲生动的故事,理性冷静地看待人与事,并最大限度地体现人文精神,语言表述上清晰而不冗赘,真挚却不滥情,就可以称之为成功了。
然而,要获得这种成功却很难。因为无论是选材还是叙述角度,都必须在历史语境和现实语境下。与虚构相比,“非虚构”写作面临的语境压力似乎更为直接,也更为强劲。于是,“事实”变成了写作者眼中的事实;“故事”变成了写作者筛选、截取来的故事;而“理性和冷静”,或者换句话说,写作者的见识,也变成了“个人偏见”。至于“人文精神”,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文艺作品的根基,都有魅力、都有力量,但同时,在发挥作用的时候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好在,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非虚构”写作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萎靡。社会现象越是复杂多变,知识传播越是便捷快速,读者对于理解世界和认识世界的需求越旺盛,作家对真实和客观的敬畏也越强烈,俯身田野调查、埋头真相发掘的责任感也越迫切。在这样的作家队伍中,新疆兵团作家丰收的身影是颇为引人瞩目的。
从《中国西部大监狱》到《西上天山的女人》,从《梦幻的白云》到《绿太阳》,从《镇边将军张仲瀚》到《王震和我们》,从《铸剑为犁》到《来自兵团内部的报告》,尤其是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西长城——新疆兵团一甲子》,丰收堪称采集新疆故事的第一人。他踏遍了新疆的每一片土地,触摸了新疆的每一段历史,交付了自己最旺盛的创作生命。他的采访对象成百上千,积累的素材浩瀚驳杂。而新近出版的《珠穆朗玛的眸子》,又把目光聚焦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聚焦于那些曾在“世界屋脊”上为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而奋战的普通将士。
可以说,作为兵团二代,丰收一直在自觉地关注大历史,关注大历史中普通人的命运遭际。同时,他也一直瞩目于今天的现实。且不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古至今,几乎所有专注于历史书写的人,无不是在“现实问题不可解”的苦虑焦思中,力图在历史中寻求根源和路径。同时,作为“非虚构”作家,丰收在书写过程中,严格保持了一个修史者的敬谨真诚,从未露才扬己;即便在现实语境的重重压力之下,必须削句减辞,牺牲一些结构布局的匠心,牺牲文学作品以情动人的感染力,他也从未在厚重丰沛的大历史面前稍有怠慢,更没有放弃自己作为兵团二代、作为一代中国作家的家国情怀。
兵团家史和西线丰碑
《西长城》序言中写,解放战争打到1949年9月西宁解放的时候,以马步芳为首的西北“五马”残部图谋撤聚新疆,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解放新疆的战略布局,一野司令员彭德怀命令第一兵团第二军挺进南疆、第六军挺进北疆。两军会师酒泉的第二天,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通电起义,第三天,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通电起义。1949年12月17日,解放军驻疆部队、三区民族军、新疆起义部队会师迪化,新疆军区、新疆省人民政府同时宣告成立。之后,新疆开始剿匪平叛、建政维稳、筑路引水、屯垦戍边。
随着局势的平稳,中央决定驻新疆部队除保留一个现役国防步兵师以外,绝大多数就地转业,“铸剑为犁”,在新疆落户从事农业生产。1954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首任司令员正是率部起义的陶峙岳。之后,新疆兵团和新中国一起,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一段岁月,全国人民熟知的八千湘女上天山、十万上海知青进新疆、“伊塔”事件之后的“三代”戍边等都发生在这期间。
《珠穆朗玛的眸子》中写,1962年10月,刚刚完成剿匪平叛不久的130师,返川归建,突然接到军委命令,中印边境吃紧,自卫反击战即将开始,于是,各路人马紧急从四面八方集结,奔赴“世界屋脊”。新疆兵团立即向中央请命: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全力支援边防部队作战。于是,新疆边防部队组成了“新疆军区康西瓦指挥部”,同时,西线六百多公里战区的战略物资供应任务落在了兵团汽车第一团,兵团独立汽车第三营的肩上。盘山路贴山临崖,冰雪覆盖,几乎每一次行军和物资输送都是在走“鬼门关”,就这样,兵团一千一百二十五名精兵强将,为自卫反击战输送军用物资六千五百吨,组成了名副其实的“生命线”。
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1975年新疆兵团被撤销,改为新疆农垦总局。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决定》指出:“生产兵团屯垦戍边,发展农垦事业,对于发展自治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防御霸权主义侵略,保卫祖国边疆,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82年6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恢复,直至今天。如今的新疆兵团有14个师,174个农牧团场,是“军政企合一的特殊社会组织”,有37个少数民族。兵团的发展也开始从“屯垦戍边”向“建城戍边”转变。
多年之后,丰收开始对这些历史的当事人进行采访,留下他们的回忆,感受他们岁月足迹中的峥嵘,同时,也为历史保留惊心动魄和令人五味杂陈的真实瞬间。无论是《西长城》还是《珠穆朗玛的眸子》,丰收都致力于为历史寻找更多的见证人。他尋找、探访、倾听、记录,让历史在人身上复活,也让人在回忆和见证中不断树立自己的价值和尊严。或许,英雄创造历史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从来就不是问题的两极,它们水乳交融,难分彼此。
《西长城》:“飘荡在新疆大地的种子,哪一粒都有一部人生传奇”
粗略说起来,《西长城》里的故事主角有几类:一是部队官兵,二是周总理说的“自动支边人员”,三是天山湘女,四是上海知青,实际上他们也是兵团的主要人员构成。他们的故事,就是一个国家从战争状态走向和平岁月的全部反映——战争是历史的极端状态,靠信仰、靠集体主义精神可以激发不可思议的潜能,正如《珠穆朗玛的眸子》写到的那样——但和平岁月,需要面对的是吃喝拉撒、婚丧嫁娶的日常生活,单纯靠信仰、靠意志恐怕不能行之有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初创时期,正是处于两种状态的过渡阶段,信仰支撑下的集体主义精神仍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怀也不可避免地提上日程,于是四类故事主角之间就发生了很多或悲或喜的人生传奇。
首先是部队官兵。书里讲到,王震的三五九旅进疆后变成了六师,进驻大芨芨草滩哈拉毛墩,一坎土曼下去,见不着土,粮食问题首当其冲:进疆部队二十万,国家解决不了军粮的问题,除了自力更生,别无他法。王震说:驻守新疆,兵少了不够用,兵多了养不起,解决这个难题就是走南泥湾的道路!于是,昔日的战斗英雄变成了今日的种田能手。
书中讲到老兵李洪清,曾在毛主席警卫连当过连长,是被聂荣臻元帅赞赏的著名的一一五师的“蛮子”排长。他参加过五次反围剿,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百次,百团大战、平型关战役、淮海战役都有他的身影。他先后七次负伤,靠白求恩的无麻醉手术才保住了右腿,获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奖章”,进疆之后他是巴里巴盖草原的一名仓库保管员。在中国最需要粮食的1961年前后,巴里巴盖人给国家贡献了上百万斤粮食。1981年,李洪清和王震在石河子重逢,他对司令员说:“攻打兰州时,你说,打不下兰州我要你的头,现在我的头还在。”看着书中照片上,昔日的戎马将军和士兵相对露出忠贞赤诚的笑容,会让人感叹激情燃烧的岁月从未离他们而去,而這种信仰和意志在角色转变过程中所发挥的凝聚人心的力量,如今看来,何其珍贵!
三五九旅唯一的知识分子团长、曾写下兵团史诗《老兵歌》的新疆军垦奠基人张仲瀚,用“十万大军出天山,且守边关且屯田。塞上风光无限好,何须争入玉门关”的豪迈诗句勉励官兵,身体力行,亲自拾粪种田。他一生都在倡导的南泥湾精神真正融入了自己的血液、官兵的血液。而这种精神背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是超出想象的苦难。《西长城》说:“十年、一百年,时间越久历史越长才越明白,他们的牺牲太大太大,他们的给予太多太多。”1980年,经历了“文革”苦难、无儿无女的张仲瀚在北京病逝,1993年他的骨灰随王震的骨灰重返天山。
新疆和田有一个四十七团的墓园,叫“三八线”,是以累死在田里的老兵周元开垦的长八百米、宽三百米的田地命名的,而此时,恰逢朝鲜战争期间。作家沈从文曾说:“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天山脚下,有太多如此遥望故乡的老兵……
关于八千湘女,早已无需回避历史的真实。在被命名为“家国 女人”的第三卷,书里写明了来龙去脉。部队的婚姻问题战争年代就已经存在,扎根新疆,这个问题更是严峻:“没有老婆安不下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于是,王震给自己的老搭档、湖南省委领导王首道写信求助:“……在湖南招收大量女兵,十七八岁以上的未婚女青年,不论家庭出身好坏一律欢迎,要她们来新疆纺纱织布,生儿育女……”没几天,长沙的报纸天天有号外:新疆军区招聘团征召女兵!参军去新疆上俄文学校,开拖拉机,进工厂……随后湖南、山东、河南、四川、湖北、上海的女青年踊跃奔赴新疆……
太多的文学作品写到了湘女的眼泪,写到了时代对湘女的索求,丰收也并未回避这一点,但除了这些有代表性的故事,他还找到了其他,比如他写到我党早期,和刘少奇、何叔衡、谢觉哉齐名的革命家肖学泰的侄女肖业群,就因为在新疆找到了“根正苗红”的婚姻而受到了保护,免遭“文革”中的政治牵连。组织包办的婚姻在制造了很多悲剧的同时,也成就了很多喜剧,甚至护佑了很多人的命途。历史从来就不单一和绝对。
除此之外,作者还找到了大量的史料,包括入疆后女兵因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而发病的《癔病情况报告》,还有《部队五年来婚姻问题总结报告》等等。作为报告文学作家,他有更为宏阔的历史观:西部的爱情和婚姻,也与所有地方的爱情和婚姻一样,有悲剧也有喜剧,有感天动地的忠贞和生死不渝的誓言。而且,人生终究不能纠结和沉湎于苦难,“悲剧前奏、喜剧谢幕的人生长剧”更该被人记住,也更是以“真善美”为宏旨的文学作品应该具有的历史品格和美学风范。
在历史转折的关键点上,一代人的命运应该被记取,但无法被改变。那些美丽的进疆女子和背井离乡的老兵一起,用青春谱写了一曲西部悲歌,当然也谱写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西部血色浪漫。
关于上海知青,问题显然更复杂。它不是一时一地的问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全国性的,因而遗留的问题也是全国性的。与鱼珊玲同为知青典型人物的杨永青出身书香门第,但她们都积极投身时代潮流,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作者说:“对于热血青年,古往今来都是一样,血亲的力量在时代潮流面前苍白无力。”只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血亲也往往会成为她们命运转折的理由。那时候的中国,“唯出身论”制造了多少历史的悲剧!
杨永青说:“谁也超越不了时代。”如今看来,没有进疆的老兵、湘女、“盲流”,就不会有新疆的今天,而没有上海知青,兵团的教育也不会有后来的发展和改变。“时代导向他们的人生,他们也雾里看花云中望月地影响时代。历史是一场风云际会,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都会裹着你往前走。沧桑世事,潮汐人生,看世事还是看人生,他们都有了过来人的淡然恬静。”
人生朝露,艺术千秋。当《西长城》挥笔写下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他们的淡然恬静早已化为一种铅华尽洗的境界。而这种境界又反过来直接影响了《西长城》的风格,回顾故事的时候平实家常,甚至略显絮烦,但评点人生的时候意气平而旨趣深。这种点到即止、引而不发的风格,也影响到了《珠穆朗玛的眸子》的创作。当然,后者的题材更难处理,所以也更需要把握历史和情感的分寸感。
《珠穆朗玛的眸子》:
“战争,终究要由每一个战士来完成”
与《西长城》的写法不同,《珠穆朗玛的眸子》因为选材敏感复杂,所涉历史对普通读者来说相对陌生,于是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篇幅,尽可能梳理清楚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包括中印边界纷争的历史由来、历史演变,这又涉及到西藏、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历史,也涉及到英属印度期间英国在喜马拉雅一带的诸多政策和活动;同时,西藏在新中国解放前后的复杂局势,平叛的艰难,以及中国军队在解放西藏前后所做的各种准备等等,也都需要逐一厘清。
对作家而言,历史既是基于客观现实的观察,也是一种叙事,但叙事逻辑的建立总是受制于现实语境的影响,《珠穆朗玛的眸子》显然无法超越这样的影响。于是,丰收只能以“人”为核心,讲述普通官兵的战斗准备,写战斗过程中的主要战役,写勇敢、写牺牲、写骨肉分离、写幸存者的回忆……借助这些,丰收力图把历史的幕布掀开一角,让有心的读者窥其一斑,思其可能。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部分,在人类战争史上也具有别样的意义。以在瓦弄大捷中建功立勋的54军130师官兵为代表的我军将士,需要面对的不只是敌人,还有大自然。如果说,靠信仰、靠集体主义精神,将士们面对敌人的时候能够做到视死如归的话,面对平均海拔四五千米自然环境的肆虐,面对随时可能粉身碎骨的悬崖峭壁,面对高原缺氧、水土不服、物资匮乏等等直接挑战人生理极限的困难,意志的物质基础——身体本身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书中不断写到,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也不断感叹,这次作战,艰难程度远远超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书中还写到了其他复杂的情况,比如趁战事又蠢蠢欲动起来的叛乱,比如因宗教习俗而产生的与当地百姓交往上的困难等等。至于战争本身面对的,地形侦查、敌情侦查上的困难,后勤保障的困难,信息传达的困难,武器装备落后的困难,部队临时集结的困难等等,更是让整个战事雪上加霜。可以说,这种情形下的战果,尤为来之不易;这种情形下的牺牲,更为让人肃然起敬。尤其是那些刚刚入伍的新兵,几乎还来不及感受青春的昂扬,就倒在了高寒缺氧的“第三极”。所以,当我们读到为四百七十座烈士墓所建立的纪念碑碑文,尤其是背面的挽联的时候,内心的感受尤为复杂:“忆当年保家卫国血洒边关,看今朝治边援藏告慰忠魂。”
书中设立了一个贯穿始终的被采访人,就是时任130师师长的董占林将军。他的回忆和讲述,既有指挥员的决策、老战士为国牺牲的悲歌慷慨,更有作为新中国从成立到建设的见证者的深入思考。
据说,丰收采访的人物有二百八十多位,书中记录的有名有姓、有确切编制的亲历者不下五十位,兵种涵盖了骑兵、炮兵、步兵、汽车兵等所有参战兵种,军阶从普通士兵到将军。他们除了讲述自己的感受,更追忆了那些足以让整个民族铭记的战斗英雄。所有人在战争面前,都只是血肉之躯;在大历史面前,也都只是普通人。他们无法看到全局,更无法体会这场战争在整个历史发展中的意义和作用。如果不是丰收的采访,不是文学的记录,他们或许会一直在历史的角落里沉默。
由此让人想到诺贝尔文学奖给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颁奖词:“她以复调式写作,为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树立了纪念碑。”而相对于“纪念碑”这样中规中矩的表述,我更倾向于用“文学的尊严”这种更道德化的词语来形容“非虚构”写作。我想,写《西长城》和《珠穆朗玛的眸子》的丰收,也堪当“文学的尊严”的评价。
踏遍青山人未老
如果书是有气质的,那么《西长城》是一本冲淡平和的书,《珠穆朗玛的眸子》则是一本欲说还休的书。面对历史、面对苦难、面对战争、面对牺牲,甚至面对成绩、面对战果,丰收都没有表现得煞有介事,历史的沉重、复杂,足以让他冷静、理性、克制、隐忍。
曾经,一些主旋律题材的报告文学有过这样的弊病,即为了弘扬正确的价值观而一味增加文本的教化作用而不是感动功能,于是原本具有质感的故事变得空洞了,原本可亲可感的人物变得概念化了。实现文学的真实,不管是小说的还是报告文学,都有一个技术手段或者说语言方式上的要求,那就是恰如其分、适可而止。《文心雕龙》所谓“夸而有节、饰而不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西长城》又不是一味地书写平面化的“感动中国”的故事,它注重故事和细节的意味深长,擅长在历史的缝隙中,在超越时代局限的人之常情中展现写作者的智慧。《珠穆朗玛的眸子》也不是一味地写英雄主义,它努力建构历史的逻辑,努力寻找能够确立历史见识的空间。在整体“无我”的写作格调中,那个充满洞察力和反省精神的“我”又会适时出现。当然,跟整体风格相匹配,“有我”的时候也是中正持重的。
《西长城》中写,兵团人荣誉感极强。战争中培养起来的集体主义荣誉感是兵团人的精神底色。但同时,又因为拉开了历史時空的距离,很多一线的劳动者也被动地卷入了历史大潮之中,经历了命运无常和人生无奈,所以,似乎只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才能让文学扎根。《珠穆朗玛的眸子》中写,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走过来的中国军队,早已练就了不怕吃苦、排除万难的“铁军”底色,英雄主义、家国使命早已融注在血液中;但同时,又因为历史时空往纵深发展,活下来的老战士开始从更深层次追忆金戈铁马,从更内在的角度思考忠诚的意义,所以,似乎只有“英雄永垂,人民不朽”才能让文学立足。
“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文心雕龙》),所有的人物,都是作为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尊信仰的雕塑,站在丰收的文本当中;所有战士的经历,也总是作为活生生的生活、战斗场景,而不是抽象的爱国主义信念站在丰收的文本当中。自然,这样才能够走进时下读者的心里。
两本书里俯拾皆是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烽火硝烟中小战士的精神,书中也试图捕捉他们的喜怒哀乐中所包含的共同的精神支撑,一种毫无保留的牺牲精神,以及由这种牺牲精神而衍生出来的荣誉意识、集体意识、大局意识,久而久之,这种精神和意识就转化成了信仰。
无论是《西长城》还是《珠穆朗玛的眸子》,都是在讲信仰,讲一种与生命、与人文精神血肉相连的信仰。托尔斯泰说:“信仰就是生命。”而对兵团人、对中印自卫反击战中的战士来说,信仰帮助他们战胜恐惧和困苦,信仰帮助他们征服自然和敌人。它是时代永恒发展、历史永恒轮回的精神底蕴,甚至,它是历史的各种淘洗和时代的各种筛选中唯一能够留下来的“真实”,一种永远能够在文学中得以保留的、有魅力的“真实”。
丰收在《西长城》的后记《乡关何处》中说:拓荒者用倒下的身躯唤醒了荒原,用一生的血汗滋养了戈壁,“老兵不死,他们只是慢慢离开……”在《珠穆朗玛的眸子》的后记《天梯,一个古老的传说》中说:“青山不老,忠魂千古。”当文学记录下这些无名英雄离开的时候,他们已经和丝绸之路,和林公车、左公柳和艾青的诗一起,和雪域高原上的蓝天、冰雪、格桑花一起,变成了“中国故事”不可分割的文化组成部分,而这些故事和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关,是我们共同的文化积淀。
栏目责编:刘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