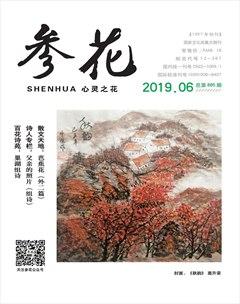骆宾基《北望园的春天》语境义补阙
摘要:20世纪40年代,骆宾基的描写对象和战时背景有文史补充的价值。在《北望园的春天》这部小说中,骆宾基从小人物日常生活、人物心理着墨,一方面以反讽手法表达了个人、群体、时代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又处处通过反讽照见作者、读者、文本、世界之间的相互慰藉,最终引发了文本内外的共鸣。“北望园的春天”令作者逃避,但通过语境义的补阙,这一时间段每每又在日后令作者向往不已。
关键词:骆宾基 《北望园的春天》 语境义
早在1938年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发表时,文坛就开始了关于抗战文学要不要暴露、讽刺的论争,其后“暴露与讽喻”一时成为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文学的主流,其中作家叙述调子的选择则构成了一种值得关注的写作现象,“讽喻”的分寸不仅反映了作者对新的小说观念和形式探索的认知,更集中体现了他们在战争年代的世界感受和人生态度。
救亡图存,给许多进步的、革命的作家提供了走向前线、走向大众的契机,骆宾基和丁玲、碧野、刘白羽一样,都纷纷写起了报告文学作品,创作的小说都有关战时背景。1940年末,皖南事变爆发,骆宾基被迫离桂,经博白、转广州、入香港,遇见了心上人萧红,结下了深厚情谊。萧红病入膏肓,含愤逝于香港,由骆宾基料理萧红丧事。破碎一场壮阔的梦,紧接而来的太平洋战争迫使骆宾基取道澳门,撤回桂林。此时的桂林已是抗战时期全国文化的中心,骆宾基也摆脱了初期写作时的粗糙,文笔较一年前更为成熟、深刻。
不同于张天翼使用的讽刺格调,骆宾基采用的叙述调子是反讽。吴晓东认为,反讽是“一种用来传达与文字表面意义迥然不同的内在含义的说话方式”,讽刺的语调是明显的、猛烈的,容易为读者所认知;反讽的解读通常需要依靠语境,说话者的真实想法在表层语义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语用含义。总的来说,小说中的反讽特质是文学文本细致化的体现,是骆宾基早期小说创作的闪光点。
第二次回桂是骆宾基创作的黄金时期,发表于1943年的短篇小说《北望园的春天》就是一部值得分析的经典反讽作品。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在离开桂林赴重庆前大约一个星期的时段内,暂住在聚居着几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北望园。小说集中书写的是“我”对北望园住客的观察与评判,呈现出战时寓居在桂林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样貌及精神状态。
反讽多次使用在杨村农、胡玲君、赵人杰的刻画中,仅就《北望园的春天》这一标题,骆宾基都在非常自觉地使用反讽。北望园是怎样的?“北望”有含义吗?标题的重点在于“春天”,而小说中的春天是生机盎然的吗?
北望园是一个身份分化的集合,是时代阶级的缩影。“我”不甘于桂林战时生活的荒芜与生命的空洞,对安于现状的北望园的居民带有几分不满与居高临下的自命不凡。同时“我”对北望园中的生活也并不十分满意,往往萌生马上离开桂林的想法,把自己当成旅客。此时“北望”一方面表达了小说人物对安稳的故土的向往,另一方面也透露了作者对抗战胜利、“踏平胡虏”的期望。
探究战时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时,必须结合小说作者本人的现实经历:回桂林后,骆宾基无固定工作,仍靠卖文为生,当时稿酬很低,再加上通货膨胀,骆宾基往往入不敷出,在桂林需要与好友合住一间公寓。由此观之,作者骆宾基的生活经历映射的是“我”与“赵人杰”这两个人物的。
对《北望园的春天》来说,通向战时文化语境的关键是战时的人性状态和心理处境。战火中的贫困、朝不保夕的空洞以及希望的缺失,都在打击着小说主人公和读者的内心。而如果仔细观察“我”对赵人杰的态度、“我”对林美娜的描述,读者则会发现“我”在小说中也是一个被反讽的对象,进而读者会对小说中所有的人物产生同情和反思。不管骆宾基在“南中国”如何不断辗转,始终还是逃不出对祖国蒙难中的落寞,而当读者最后突然领悟到不仅是小说文本值得同情,突然发觉自我在进行着的体验也弥足珍贵,小说便来到了有些许暖意的春天,战时荒芜的北望园便得到了慰藉。
在共和国蓬勃发展的今天,面对《北望园的春天》,批评家会叹惋,希望当代文坛上有更多体现时代厚度和现实思想意蕴更加深刻的作品继续出现,能够和骆宾基等量齐观。这或许是苦难的抗战给予灾难经历者的馈礼。何止是当下的文学创作者,即使是駱宾基本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创作内容也发生大变,后期因某种原因,更转入了古文字研究。这是他北望的远方吗?反观之,套用赫拉克利特的哲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个北望园。
参考文献:
[1]骆宾基.北望园的春天[M].中流出版社,1953.
[2]吴晓东.战时文化语境与20世纪40年代小说的反讽模式——以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为中心[J].文艺研究,2017(07).
[3]张天翼.华威先生[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吕腾崟,男,广西师范大学2016级国家中文基地班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