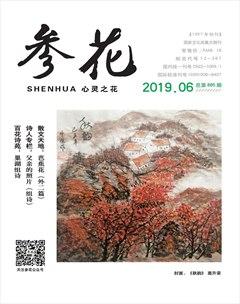从傅山对赵孟頫、董其昌的评价看其书学观
摘要:傅山,初名鼎臣,字青主,别号公之佗、石道人、啬庐、朱衣道人、石道人、西北老人等。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医学家、书画家。其中最为后世称道,影响巨大的,是他的书法艺术。本文从傅山对赵孟頫、董其昌的评价看其书学观。
关键词:傅山 赵孟頫 董其昌 书学观
一、傅山对赵孟頫、董其昌书法的评价
赵孟頫和董其昌是元、明两代最具影响的书法家。傅山在评价他们作品的时候却颇多微词,其《训子诗》题跋:“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香山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此无他,即如人学正人君子,只觉觚棱难近,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其日亲日密,而无尔我者然也。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始复宗先人四五世所学之鲁公而苦为之。然腕杂矣,不能劲瘦挺拗如先人矣。比之匪人,不亦伤乎!不知董太史何所见,而遂称孟頫为五百年中所无。贫道乃今大解,乃今大不解。写此诗仍用赵态,令儿孙辈知之,勿复犯此。是作人一著,然又须知赵却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心手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尔辈慎之!毫厘千里,何莫非然?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①
傅山自述二十岁上下遍临晋唐法书,但皆“不能略肖”。偶得赵孟頫《香山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傅山告诫子孙正因为赵书容易学,所以如“与匪人游”,能“日亲日密。”傅山因赵孟頫人格,而“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
傅山“大薄其为人”的缘由,就是赵孟頫以赵宋王孙降元,元不但是蒙古人,而且是异族。傅山在明清鼎革之际面临的境况也类似。但傅山以明遗民自守,入清后服道袍,号朱衣道人,面对清廷强征博学鸿词,以死相拒,对待异族统治,采取了和赵孟頫截然相反的态度。傅山说:“不知董太史何所见,而遂称孟頫为五百年中所无。”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董其昌会对赵孟頫评价如此之高。
傅山《训子书》又评价董其昌:“晋自晋,六朝自六朝,唐自唐,宋自宋,元自元,好好笔法,近来被一家写坏,晋不晋,六朝不六朝,唐不唐,宋元不宋元,尚煗煗姝姝,自以为集大成。有眼者一见便窥见室家之好。”②看来傅山对董其昌的书法也不大认同。而赵孟頫和董其昌的书法,一个是元代高峰,一个是明代集大成者。
赵孟頫如果除去降元之外,堪称完人。元世祖初见赵孟頫,惊为“神仙中人”。他政治上是理财能手,擅长行政和司法;学术上,是经学家、文学家、诗人、精通道释;艺术上,通晓音律,善鉴定,书画开一代风气。但因为入仕元朝,后世往往以气节诋毁他。赵孟頫一生特别用心于书画,晚年常谓人,后世当以此知我,不难窥其用心,即是想在书画史上争得一席之地。但后人多有因他是贰臣,而轻视他的书法。明代王世贞评:“赵承旨各体俱有师承不必己撰。评者有奴书之诮则太过。小楷于精工之内,时有俗笔。碑刻出李北海;北海虽佻而劲,承旨稍厚而软。”莫是龙评:“吴兴最得晋法者,使置古帖间,正似圜阓俗子,衣冠而列儒雅缙绅中,语言面目立见乖迕。撇欲利而反弱,捺欲折而愈戾。”王世贞、莫是龙等批评赵书,结点都在“奴”“俗”“软”等处,其实都是借书法批评赵孟頫人格。傅山对赵书的不满,也将其归结为“无骨”“软美”。
董其昌虽然早年对赵孟頫的书法也有苛刻的批评,但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和书法水平的提高,对赵书的认识也逐渐发生着改变。董其昌首先不太满意明代人对赵孟頫的争相效仿,自赵孟頫之后,书坛的发展,基本都是继承了赵书的余波,鲜有能出藩篱之外者。董其昌称:“今眼目为吴兴所障。”再者,他虽有不满,但学书路线还是沿着赵孟頫的复古说直追“二王”。因此他也将赵孟頫视作一个目标,一面批评指责,一面追逐比较,称:“自元人后,无能知赵吴兴受病处者。自余始发其膏肓在守法不变耳。”“赵书无弗作意,吾书往往率意。”随着年龄的增长,认识的提高,愈发佩服,謂“余素不学赵书,以其结构微有习气。至于用笔用墨,文敏所谓‘千古不易者,不如是,何以名喧宇宙!前人自谓可轻议。”“子昂书中龙象。”“画与书皆入妙品。”到了晚年,感叹道:“余年十八岁学晋人书,得其形模,便目无吴兴,今老矣,始知吴兴书法之妙。”厘清董其昌的书学经历,就不难理解董其昌为何佩服赵孟頫。因为董其昌是以赵孟頫为学习和超越的目标,他们所走的道路基本相同,都是以“二王”为旨归。傅山一生也钟情于王羲之《兰亭序》,那么为何傅山不理解董其昌称赵孟頫“为五百年中所无”这句话。这得从傅山的书学经历去认识和探讨。
二、傅山对赵书“复古”的认识
傅山晚年在他的《训子书》中回忆:“吾八九岁即临元常,不似;少长如《黄庭》《曹娥》《乐毅论》《东方赞》《十三行洛神》,下及《破邪论》,无所不临,而无一近似者。最后写鲁公《家庙》,略得其支离,又溯而临《争坐》,颇欲似之。又进而临《兰亭》,虽不得其神情,渐欲知此技之大概矣。”③可知傅山八九岁便开始临习钟繇的书法,然后“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但可惜的是“无一近似者”。最后临习颜真卿《颜氏家庙碑》,“才略得其支离”,然后又临习颜真卿《争座位》,能“颇欲似之”。最后临习王羲之《兰亭序》,且终身不倦。他去世前六年回忆“常临二王,书羲之、献之之名几千过,不以为意”。可见其终身对二王书法迷恋之深。那么根据傅山这一段叙述来看,他的临帖、学书的经历和赵孟頫、董其昌大略相同。也是取法晋唐,直追二王一路。那么为何傅山会对赵孟頫、董其昌的书法有成见。其实傅山对赵孟頫复古,学习二王的书法,是没有意见的,但是傅山认为学习二王书法不能只停留在二王上,应该进一步去探索二王的出处。
傅山《杂记》:“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钟、王之不可测处,全得自阿堵。老夫实实看破地。工夫不能纯至耳,故不能得心应手。若其偶合,亦有不减古人之分厘处。及其篆隶得意,真足吁骇,觉古籀、真、行、草、隶,本无差别。”④傅山认为钟繇、王羲之书法的过人之处即是“知篆隶之变”。晋书称王羲之“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游云矫若惊龙”。傅山认为赵孟頫的书法“润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在傅山看来,赵孟頫只是取法《兰亭》,而稍微变化。
傅山《杂记》评《兰亭》:“真行无过《兰亭》,再下则《圣教序》。两者都无善本。若必求善本而后临池,此道不几息耶?近来学书家多从事《圣教》,然皆婢作夫人。《圣教》比之《兰亭》,已是辕下之驹,而况屋下架屋,重台之奴。赵子昂善抹索得此意,然楷中多行,殊不知《兰亭》行中多楷也。”⑤这里提到赵孟頫以行书的笔法写楷书,而王羲之的《兰亭》则是以楷书的笔法写行书。所以傅山认为王羲之的过人之处是懂得“篆隶之变”。赵孟頫不及《兰亭》之处,即是不懂去取法“篆隶”,因此如“婢作夫人”、如“重台之奴”。傅山认为学习晋唐,但止于晋唐,是不够的,应该注意晋唐之前的书法,即篆书和隶书。这和当时的学术风气有一定关系。
三、金石篆隶对傅山评价赵书的影响
傅山在清初的学术圈名声很大,和当时的一些知名学者,多有往来。其中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王弘撰等均对金石碑版有着浓厚的兴趣,曹溶、戴廷栻是清初著名的金石收藏家。在当时风气影响下,傅山对金石碑学也非常重视,阎若璩在《潜丘札记》中谈到了他和傅山对金石遗文的探讨:“金石文字足为史传正讹补阙,余曾与阳曲老友傅青主极论其事。”“傅山先生长于金石遗文之学。每与余语,穷日继夜,不少衰止。”
傅山在研究金石碑版,考证史籍之余,也喜作篆、隶。清初王士禛评价傅山:“工分隶及金石篆刻。”清人郭尚先评价:“世争重其分隶,然行草生气郁勃,更为殊观。”近代马宗霍评:“青主隶书,论者谓怪过而近于俗。然草书则宕逸浑脱,可与石斋、觉斯伯仲。”基本上都认为傅山的隶书不如他的行草,傅山则对自己的篆隶则相当自豪,认为这是他写其他书体的根基所在。
《霜红龛集》卷三七《杂记二》载:“至于汉隶一法,三世皆能造奥,每秘而不肯见诸人,妙在不知此法之丑拙古朴也。吾幼习唐隶,稍变其肥扁,又似非蔡、李之类。既一宗汉法,回视昔书,真足唾弃。”“吾抚拟《百石卒史》;眉得《泰山》《太守》处多,间亦作梁鹄方严体;莲苏专写淳于长,略得其疏拙之似。”傅山认为祖孙三代都能通晓汉隶之法。“一宗汉法”,以前所学都可以放弃。他说:“汉隶之妙,拙朴精神。如见一丑人,初视村野可笑,再视则古怪不俗,细细丁补,风流转折,不衫不履,似更妩媚。始觉后世楷法标致,摆列而已。故楷书妙者,亦须悟得隶法,方免俗气。”他还说:“不知篆隶从来,而讲字学书法,皆寐也。”“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所以楷书若要写得好,得“悟得隶法”。即是用隶书的用笔去写其他书体。因此他说:“及其篆隶得意,真足吁骇,觉古籀、真、行、草、隶,本无差别。”赵子昂以行书笔法写楷书,在傅山看来当然不如以篆隶笔法写楷书取法高。
四、傅山的自然书学观
傅山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书法理论便是“四宁四毋”说:“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从他的观点看“拙”“丑”“支离”方能“直率”。傅山《杂记》中说:“旧见猛参将标告示曰:‘子初六,奇奥不可言,尝心拟之,如才有字时。又见学童初写仿时,都不成字,中而忽出奇古,令人不可合亦不可拆,颠倒疏密,不可思议。才知我辈作字,卑鄙捏捉,安足语字中之天。此天不可有意遇之,或大醉后无笔无纸复无字,或当遇之。世传右军见大令拟大令书,看之云:昨真大醉。此特扫大令兴语耳。然亦能书人醉后为之,若不能书者,醉后岂能役使锺、王辈倒臂指乎?既能书矣,又何必醉?正以未得酒之味时,写字时作一字想,便不能远耳。”⑥傅山举例猛参将的告示,学童字都没有受过书法学习的束缚,偶尔之间却能达到“忽出奇古”“不可思议”的效果。而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往往“卑鄙捏捉”,没有天趣。因此傅山说天趣若能偶遇,可能是在大醉之后,但真正能书的人,不在于醉与不醉,在于“写字时作一字想”。便能达到“不可思议”的效果。
傅山的这种思想,反映了明末以来的美学思潮。明末李贽提倡绝假纯真的童心说,提倡“童心”“真心”,认为人人都有其可贵的真实之处,即本心,不必依傍圣人,模拟前人,代“圣人之言”。傅山的性格、思想和学术取向,决定了傅山对书画的见解。
顾炎武曾说:“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傅山说:“写字无奇巧,只有正拙。正极生奇,归于大巧若拙已矣。不信时,但于落笔时,先萌一意,我要使此为何如一势,及成字后,与意之结构全乖,亦可以知此中天倪,造作不得矣。手熟为能,迩言道破。王铎四十年前字,极力造作,四十年后,无意合拍,遂成大家。”他说写字重要的是“正”是“拙”,不能“造作”,须知“天倪”。而能反其道行之,“极力造作”后,“无意合拍”者,是大家王铎。傅山原先说过不喜欢赵书,是因为赵的人品,但却对王铎另眼相看,须知王铎和赵孟頫一样,都是贰臣,同样大节有亏。但有明一代赵书风行,傅山不喜欢赵书,赵书“熟媚绰约”“润秀圆转”,他觉得赵书有“媚”态,有“奴”态,所以傅山告诫子孙:“作字先做人,人奇字自古。”他喜欢的是更能合于“自然天机”一路的书法。所以他说“汉隶之妙,拙朴精神” “汉隶之不可思议处,只是硬拙,初无布置等当之意。凡偏旁、左右、宽窄、疏密,信手行去,一派天机”。
五、结语
傅山對赵孟頫的批评,从他《训子诗》来看,是不喜欢赵孟頫的人品,但这可能只是一方面的原因,他不喜欢赵孟頫的书法风格可能才是其主要原因。否则他也不会喜欢王铎的字,恰恰是王铎和他喜好略近,才使傅山对王铎和赵孟頫、董其昌有不太相同的看法。因为董其昌是和赵孟頫同属于帖学大家,所以傅山对赵孟頫、董其昌既不理解,也不认同。傅山和赵孟頫、董其昌在对书法的认识和实践上其实走的是不太一样的道路。赵、董是取法晋唐的集大成者,傅山却要超越晋唐,取法篆隶,在当时的书坛颇有些变革派的倾向。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侯文正辑注:《傅山论书画》,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10、79、42、50、19页。
参考文献:
[1]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5.[2]侯文正.傅山论书画[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3]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4]潘伯鹰.中国书法简论[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刘涛,男,硕士研究生,吕梁学院艺术系,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美术史)(责任编辑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