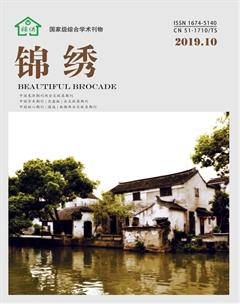浅析清中后期徽州慈善组织的发展
林玉润
摘 要:善会善堂始于明末,是一种济贫的教化组织,其创建和管理也是地方公共事务之一。清中后期,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开始走向衰弱,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产生了慈善救济思想,并付诸实践。本文结合清中后期的背景,探索古徽州慈善组织的发展,并对他们的慈善救济思想和活动进行闸述,使人们了解他们的慈善救济思想在整个慈善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为当今社会慈善组织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徽州;慈善组织;慈善救济思想;小社区
徽商贾而好儒。以儒家思想为人生哲学的徽州商人,大多数在经商致富之后,也富有利他精神:在别人处于困难时,慷慨地伸出仗义之手;在社会建设需要时,能慷慨解囊,支持社会事业。明清时代在地产成立的各类慈善组织约为3580个,安徽地区均在数量上占了重要的地方。乾隆以后,慈善组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清嘉道年间国势由盛转衰,经济发展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求,政府在思想控制上不同于康乾时期一样苛刻,“新生后进,顾忌渐忘,稍稍有撰述”。[1]面对着政治腐败、社会问题丛生、粮食短缺、自然灾害频发等诸多问题,国力渐衰的清政府已然没有十足的能力来应付和解决。这样便使得善堂所面对的局势不再如以前一般单纯,由此,善堂逐渐发展出与前清不同的施济模式,尤其是其组织形态体现了小社区的特色,为这一时期徽州的慈善救济事业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善会善堂的慈善行为有多种,比如保婴保育、停棺施棺、施药养疴等,清中后期保婴会以及以施棺为主的综合性善堂其组织形式根据特色,故以下从这两个方面研究清中后期徽州慈善组织的发展。
一、保婴保育
中国的育婴组织,起始于宋代的慈幼局。《宋代·理宗本纪》记载“癸亥,诏给官田五百亩,命临安府创慈幼局,收养道路遗弃初生婴儿,仍置药局疗贫民疾病”[2]。明清时代育婴堂总计约973个,1850年以前约有579个,1850年后约有394个。
民国的《重修婺源县志》曾有记载“婺贫俗,多溺女”,“族大人繁,贫户甚多,溺女之风日炽”,由此可知徽州,尤其是婺源县溺女之风盛行。婺源的百姓们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故以保婴育婴为目的慈善组织机构便应时而生。如“中云人痒生王燃承父志,昌集保婴会,以拯溺女”,[3]“乡有溺女俗,巽集乡人立育婴会,此后无淹毙者”。[4]
清初的育婴组织拘于官僚形式,主要由政府控制,组织要称为育婴堂还需官方的首肯。
从嘉庆开始,育婴堂的数量愈来愈多,组织形态也比前期更为灵活。19世纪初期,育婴会的运作主要配合认同感较强的聚落,如安徽宁国的泾县则在19世纪初期就有济族中婴的“好生堂”及“济婴堂”。[5]一般一个大族内的育婴数目就有十余名。清嘉道二十一年(1816年),婺源县韩家坞设有育婴堂,在道光乙酉(1825年)至癸巳年(1833年)年间进行了重新修建。[6]当时有识的学子们也曾为保婴育婴的慈善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臧坑的太学生臧起震也曾为当地的保婴育婴的慈善组织出资办理和资助其公共事业。由溪人附贡生程鸿绪,“尝输千余缗置休城玉堂巷屋卑为育婴公所”。[7] 嘉道之际,经济发展无法跟上人口的大幅度增加,溺弃婴问题又成为议论的焦点之一。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国传教士Mline曾访问过宁波的育婴堂,据他记载,堂内的婴儿:“是一群我所见过的最肮脏、最褴褛的小东西;乳母每人要负责两三个弃婴。”由此可见,当时能给予弃婴的生活环境有多不堪。目前还没有这个时期堂内婴孩死亡率的资料,不过夫马进的研究表明,同治时期松江地区育婴堂的婴孩死亡率高达48%~50%,[8]海宁育婴堂在1890年代初期婴孩死亡率是31%~39%。虽然这些数字是嘉道之后的统计,但在嘉道期间著名的育婴堂都被讥讽为“杀婴堂”。连最早建成的的扬州和苏州育婴堂在18世纪末已经臭名昭著。相继而出的便是各种变革济婴制度的计划方案。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商人王喜孙认为应当每月给予有幼婴之穷困人家金钱上的补助,使其不致抛弃亲生婴儿。而道光末年,社会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中央政府对善堂的监管日渐松懈,从而间接地使得育婴堂里的婴儿死亡率提高。
19世纪新的“保婴会”之法是由绅士余治在道光年间设想出来的。主要目的就是阻止亲生父母溺婴,据他所言,“四乡窎远,跋涉为艰,故贫乏之家生育稍多,迫于自谋生计,往往生既淹毙……。不特生女淹,甚至生男亦淹,不特贫者淹,甚至不贫者亦淹,辗转效尤,日甚一日”。[9]新保婴会的主要原则是收集善款,给予有新生婴儿的穷苦人家每月600文的補助,相当于当时约3斗米的价钱,或一个二等工10天的工价,为期5个月。若5个月后,还是无能力抚养婴儿,保婴局会立即将婴孩送往县城内的育婴堂。这样既可以降低溺婴的几率也可以减少育婴堂的负荷。另外保婴会的救济范围:“以十里为限,十里外的家庭不受补助”。这便使得这个时期的善堂逐渐体现出较小社区的基本特点。随着余治等人对保婴会的奔波宣扬,到了清宣宗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安徽省已经正式下文推动保婴会局制度,这种保婴会的方式正好符合各地所需,故而马上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不到十年各州各县的保婴会比比皆是。严辰曰:“育婴必须建堂,而保婴会则无论寺院祠宇及人家间屋。皆可借以举行;堂必建于城市,而乡村之惮于远送或不能周;会则一乡一村,但得善士为之倡导,皆可举办;又其法能大能小,可行可止”。[10] 换言之,同治时期保婴会在组织上更为灵活,具有较强的小社区、邻里网络的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咸丰年间,徽州商人在其经营地也热心于各种各样的慈善事业,如太学生胡大沺曾捐几百金给苏州建造育婴堂;[11]棠樾人鲍志远于扬州复兴育婴堂。[12]同治后期,运婴网络困难,婴数逐渐饱和,育婴会继而产生婴多的压力。光绪初年(1880年)婴堂的收婴量逐渐减少,故使得仍有弃婴的现象,进而新的保婴会局才普遍成立。其服务于城外较小的社区,且就地取材以接济贫苦人家的婴孩。新的策略具有新的分散组织形式,同时小社区的特色愈发明显。后期,社会对育婴愈发重视,为了保证运作,大多育婴堂都制定了相关的管理条约,例如,婺源育婴堂董事制定了《婺源育婴章程二十四条》和《婺邑源育婴堂征信录》等。
不经思考,这育婴效果到底如何呢?
以婺源育婴堂为例,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婺源育婴堂一共收养118位婴孩,且全为女婴,有97位存活,其存活率高达82.2%。再后来,除了使溺婴的数量大大降低,而且在一些抚教局中会为儿童提供基础教育和相关技能的训练,较前期更加注重儿童日后的发展出路。另外,晚期的保婴机构更加接近现代的相关机构,提供较为完备的医疗保健服务,如为婴孩接种,提供三黄汤、除胎毒等药剂,强调洗热水澡的必要,准备必用的火盆熏熨等设备。
二、施棺
施棺给予贫人是最基本的积德善举之一,且历史上施棺济贫的善者很早就出现了。
徽州山多田少,耕获三不赡一,民人不得不远徙他乡,求食四方。生老病死乃是自然法则,异地的游子叶落归根,不愿客死他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意识。故漂泊在外的徽州人不幸在他乡离世,也希望能回归故里。
在外谋生的徽州商人数不胜数,尤其是新安商人,且集中于江浙地带。于是整个清代的施棺善会约58%以上设在这两省。新安之人为商,旅于吾浙之杭嘉湖诸郡邑及江南之苏松常诸郡邑者甚众。不幸因病,物故欲归榇于故里,途必经于杭州。[13]道光年间,司事胡骏誉、金高德等人除自己捐赀以外,还将募集所得的善款用于购买基地以建设善堂,名为“惟善堂”。堂内不仅有办事的大厅还有二十多间房屋,周围建有厚厚的墙和院坝。这使得善堂既牢固又可以安置较多的棺柩。而“惟善堂”与其旁边的“六吉堂”被人合称为“新安会馆”。
创建于道光丙午年(1846年)的祁门同善局,组织劝捐物资,经常救济当地的百姓。局内置有多口棺木,若是发现死在路上的暴毙者且无法查明其故里便让局内的雇夫收埋。当时的知县林用光和知府李兴锐以及祁门县教谕都曾有捐助,共捐银七百二十两给同善局,作为长远之际。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时期,邻村人逃到祁门县的人数数以万计,灾病频发,尸横遍野。局内每日施棺数以百计,费用甚多。城内的乡绅、士绅或以银钱捐赠,或以物资救济。甚而有些地方官员也为其解囊相助,如诰赠中宪大夫的郑国恂曾向同善局提供一千余秤。光绪六年(1880年)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间,为了寄存更多的棺木,惟善堂也一直在置办新的基地,除了内外堂,还有五十九处。由此可知晚清时期施棺的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当然其所耗用的经费也相当多。从光绪七年(1881年)到光绪二十七年(1891年),惟善堂的收入已从当年的一千洋元涨至六千洋元。可见投入其中的经费之高。
明末清初时期,各地大多都是施棺助葬会,主要是一个自助式的组织,一会有40人。善会真正执行工作往往是在一个較小的社区里,且均设立在镇中,只为当地社区服务。直到嘉道年间,各个镇市各自均有“民捐民办,官吏不经手”的善堂,而其中又以施棺助葬着居多。故这些镇内施棺会的规模被限制于邻里性较强的小社区内。同镇内不同社区内的施棺善局也会相互照应着,以求得正常的运作。如休宁万安镇和黟县渔亭镇等,其镇内的同仁堂与后来的怡善堂,两个善堂仅“隔图相距”,故堂内的经理董事们都相互地照料管理。后来,小社区的特色愈发明显使得一些善会不如清前期那样宣传大同理想,而是纯粹的以当地居民的利益为中心。且具有“内”和“外”以及“良”和“贱”之分,即属于社区内的良民才能得到善会的救助接济。此时善会的目的分两大类,一是保障当地社区居民的生活环境;二是救济社区内部的贫困良民。内外、良贱之分使得社区的自我界定更加地明显,加深了善会对社区的认同感。换言之,善会是另一种可以界定社会身份的新策略。施棺助葬善会如保婴会一样,善会在一个较小的社区内运作,才能发挥它的真正作用,也可能因为小规模的经营使得行政管理更加便捷,主办人对社区内的人际关系也比较熟悉,使得善会发挥较大的功效。
三、余论
清中后期时期,善会善堂主要分散在各个乡镇中发展,且愈发具有小社区的特色。其一可能是中央权力的松懈。嘉道时期政府面临诸多问题,进而只好鼓励地方开设善堂,而乡镇的善堂善会主要是由地方人自动组织起来的。之后代表中央的县政权威不如从前,使得乡镇对设立小社区的善会不再有所顾忌。换言之,乡镇以下的小社区内的善堂善会到清后期才普遍发展起来,且地方的社区按照已有的善会模式发展小善堂以照顾当地的百姓。其二可能是价值取向。贾而好儒,小社区内的慈善组织离不开“儒生化”的思想。受惠人要受社会共同监视,是否违反相关规定,同时善会对受济者的身份也有较为严格的要求。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不断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不断增加,更有利于对“儒生化”价值的宣扬。以道德划分贵贱,重新界定社会身份。慈善组织的主要功能是整合社会,而不是分化社会阶级。清中后期以来的慈善组织已经逐渐达到这样的目标,正如梁其自先生曾指出:“此时善会相当有效地凝结着一个日益庞大的中下阶层。”
慈善济贫组织的发展,从明末到清末,其数量上有大幅度的增加,且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嘉道之后的善会组织更加规模化,规范化,灵活化,但却一直没有将救济问题转化为“经济问题”。其重点仍是“行善”,其目标一直停留在教化社会或意识形态的灌输之上,以施惠人的主观意愿为主,强调道德,而没有转化为经济层面。而善堂不过是一直扮演者保守性的角色,即维护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秩序和价值。因此,慈善组织也没有真正解决救济贫人的真正问题——“脱贫”。这对当今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要打赢脱贫攻坚战:要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林则徐全集》第七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版,第78页
[2](元)脱脱,阿鲁图,欧阳玄,等.宋史·卷四十三本纪第四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7:840
[3]道光《续修婺源县志》卷二十六,《人物·质行》,黄应均、朱元理等纂修,清道光五年刊本
[4]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四十五《人物·质行》,葛韵芬等修,江峰青等纂,民国十四年刻本
[5]《泾县续志》1825,5:10上
[6]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五《建置二·公署》,葛韵芬等修,江峰青等纂,民国十四年刻本
[7]道光《休宁县志》卷十五《人物·乡善,何应松等修,方崇鼎等纂,清道光三年刻本》
[8]夫马进1986B,74-75;1990,171-172
[9]余治《得一录》1969[1869],2/1:上一下《保婴会规条》
[10]余治《得一录》1969[1869],2/1:37上-38下严辰《桐乡严比部善后局举行保婴会序》
[11]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三十八《人物十一·义行三》,葛韵芬等修,江峰青等纂,民国十四年刻本
[12]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志·义行》,石国柱、楼文钊等修,许志尧等纂,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13]胡敏 《新安惟善堂前刊征信录序》《新安惟善堂征信录》,光绪二十九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