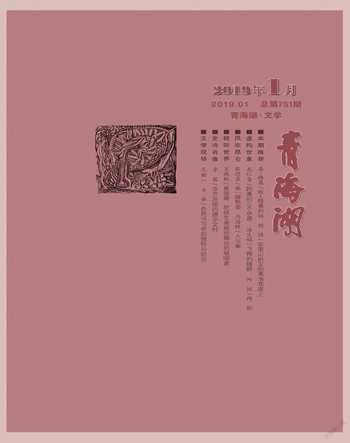六双布鞋(外一篇)
春节过后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下了几场不大不小的雪,似乎扯住了物候变换的脚步,还没从寒冷的躯壳中缓过神来,突然间清明节又到,应该是上坟祭扫的日子。
每年的这个时候,妻子总要从衣柜里搬出一个包袱,放在床上打开,取出里面的东西,整整齐齐地码成一排,然后如数家珍般念道:“一双、两双、三双、四双、五双、六双……”
我知道,此时此刻,她一定是想起了她的母亲,我的岳母。睹物思人,此时打开的心门,充溢的该是怎样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怀?
六双布鞋,新崭崭的,没有一点灰尘,黑条绒鞋面泛出黝黑的光芒,衬托着白色的鞋底,黑白分明,入眼也入心,像一件件精工细作的艺术品,被灵巧的手和岁月的风霜雕琢出来。
这是岳母做的布鞋,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留给我的馈赠。
岳母有七个子女,妻子是她的小女儿。我和妻子结婚的时候,岳母已经六十多岁,但身体还很硬朗,家里家外,都是她操心做主。苦日子里熬过来的人,对逐渐变好的生活十分珍爱,每天忙忙碌碌,一双小脚走过来走过去,似乎感觉不到一点累。每逢这个时候,她的姑娘们就会说:“您这个老奶奶,总是闲不住,叫我们坐在这里不自在。”
岳母就憨憨地笑起来:“我是做活做惯了的,不像你们的命金贵。只要你们把日子过好,我受这份苦也就值了。”
想到的总是别人,从来不为自己着想,这就是岳母的性格。
亲戚们来了,坐了满满一屋。这时候,岳母就特别兴奋,亲自动手做饭,把自己忙成一个仆人。
亲戚们就都纳闷:“我们是多来还是少来呢,多来呢把老奶奶忙成这样,少来呢又显得我们薄情。”
岳母问我:“你们上班的人,穿的是皮鞋,穿不穿布鞋?”
我说:“有时也穿。我妈给我做。”
岳母沉吟不语。
母亲去世后,有一次我听见岳母对妻子说:“这娃没妈了,没妈多可怜。今后,我给他做鞋。”
此后每年,岳母都要给我做一双布鞋,还有许多的鞋垫。每次接过鞋和鞋垫,倏忽间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在岳母的眼里,无论年龄多大,我们似乎都是没长大的孩子,似乎还需要她的呵护和照顾,我们用的面、馍、油、肉、菜等,都是岳母打发家人送来。
有一次我出差,给岳母带回一只蓝田玉戒指,她很喜欢,马上戴起来。过了两个月我去看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真没用,把你送的戒指弄碎了。”
经常干活难免磕磕碰碰,石头嘛,碎了也就碎了。我说:“下次给您买个大的。”
但是岳母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惋惜道:“你说我怎么就那么不小心呢?”
我知道,岳母看重的并不是物的价值,对她而言,蕴含在物上的亲情弥足珍贵。
岳母家境一般,房子也是老房子,但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如果是冬天,火炕煨得热乎乎的,坐上去,有童年的味道。
倘若一段时间不见,岳母就会念叨:“他们怎么不来看我呢,也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样。”
有时把她接到县城来,还没住上几天,她也会念叨:“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猪喂了没?鸡喂了没?狗喂了没?”
所以她要回去,理由是:“住在这儿太闲,给你们做做饭,也不知道灶咋用,你们的房子里都是电。”
那个夏天晴好的一天,妻子带孩子去娘家。我因有事,说好等一会儿过去。后来听妻子说,快中午的时候,岳母一边念叨着女婿娃该来了吧,一边叫她的小儿子杀鸡,一只大公鸡,好肥。
这边,我因事情没有办完,就打电话过去,说今天去不了了。
那边,岳母听到我不去了,急忙喊道:“快快停下,今天不杀鸡了!”
姑娘们哭笑不得,都说老太太偏心,凡事向着女婿。岳母站在一边憨憨地笑:“下次吧,下次你们都来。”
那只鸡因此多活了一个多月。
一次我要去南方,顺路给岳母带点东西过去。岳母叫我吃了饭再走,排骨都炖在锅里了,伙房里烟熏火燎。我因忙着赶飞机,坐了一会儿就起身告辞。
谁料岳母拦在门口,急切地说:“吃了再走嘛,马上就好了。你打个电话过去,叫那个飞机等一下,赶紧打。”
排骨还没熟透,我连着吃了几块,出门,泪崩!
岳母七十多岁的时候还下地干活,一双小脚在田间穿梭,回来一身土和草。乡邻们劝道:“奶奶,您这么大的年纪了,家里又不缺劳力,缓缓吧。”
岳母说:“多少年还不是这么过来的?坐在家里,会生出闲病来的。”
做完田里的活,回家再接着做家务、做针线、看孙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岳母80岁的时候,终于不能下地干活了,但还是忙个不停。有时她走出巷子,看打麦场上许多忙碌的人,便回家做上一大锅饭,然后把众人招呼到家里,将饭菜端上桌。一条老巷里住着,岳母的温良恭俭让有口皆碑。
姑娘们说:“您怎么找活干?别把自己累倒。”
岳母说:“人家忙啊,顾不上做饭,干的又是重活。行善干好事是做人的本分,再说我也闲着。”
邻居们说:“这老奶奶,菩萨一样的心肠,有好吃的,总会想到我们。我们有难处,也喜欢找她说事。”
只因有着极好的人缘,岳母的生活就变得充实满足。如果岳母几天不出门,邻居们就会前来打探,看这老奶奶是不是病了。
如果岳母的门前停着汽车,邻居们也会走进来看看:“奶奶,是您家的姑娘女婿来了吗?您老好福气啊。”
这个时候,岳母挂着一脸的笑容,忙不迭地让座递茶,然后把我们带去的东西摆到桌上,让大家品尝。
多年来,这条老巷里的许多人,我几乎全都认识,见面打招呼,有时还会受到他们的邀请。
光阴如水。岳母对我说:“我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我得给你再做几双鞋,不然哪一天我走了,就没人给你做鞋了。”
于是,在暖阳照射的屋檐下,岳母畫出鞋样,裁剪好布料,钢针扎下去,厚厚的鞋底被丝线带出“簌簌”的响声,然后拉紧,一个针脚,耗去几分钟时间,付出一份心血。
岳母羸弱的身体已经经不起岁月的煎熬了,吃饭很少,走路也蹒跚起来,但她从来不用拐杖。子女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做完家里的活,庭院里沉寂下来,岳母望着挂在墙头的黄昏神情落寞。
2010年12月,岳母84岁。
一场突如其来的感冒压垮了岳母的身体,在乡卫生院打了几天点滴,不见好转,我和妻子接她到县城治疗。
几天后她居然能下地了,又开始念叨起来:“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猪喂了没?鸡喂了没?狗喂了没?”
这时候妻子要去外地学习,我们只好将岳母送回家里,当她看到猪儿鸡儿狗儿都很好时,便憨憨地笑。
回去没过几天,岳母又一病不起。医生给出的结论是:“老病,这老太太,怕是过不去这道坎了。”
庭院里走马灯似的晃动着前来看望的人,亲戚,邻居,老巷里所有的人,向眼前这位慈祥的老人送上最后的问候。
岳母静静地望着我,嘴唇嚅动着说不出话来,但我已经听清了———她在等待一个人。
几天后妻子学习结束回来,岳母已在弥留之际。当我们一家三口站到岳母面前时,她的目光不时地在我们脸上移动,看了好多遍,好多遍,然后一汪浑浊的泪水禁不住喷涌而出!
我懂了。我的世界开始下雪。
———岳母走了。
一堆布鞋,用花布包袱裹着,打开来,新崭崭的照人。妻子将它们排成一行,数道:“一双、两双、三双、四双、五双、六双……”
这辈子我有幸和一位老人相遇,彼此的心凝结成割舍不断的亲情,在一同走过的岁月里,真诚善良和我们相伴,信任关怀与我们同行,这种难忘的情结,这份博大的母爱,让我今生今世受用不尽。
莲花落
出没在街头巷尾的叫花子,一手拎饭碗,一手持竹竿,有意或无意地将行乞的口诀用歌谣的形式表达出来,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创造的奇迹,成就了千百年来流传在南疆北国的经久不衰的莲花落!
原本形成于江南水乡的莲花落,穿越了历史厚重的迷雾,选择在河湟谷地落地生根。不知过了多少年,起初缭绕在深巷老宅里的低回婉转的曲调,借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不时迸发出强劲的生命力,成为民间曲艺的奇葩,引来世人惊奇的目光。
我曾经探究过这种词曲形成的过程,发现这条道上走过的人实在太多,他们穿着宋朝或明朝的衣服,走在狭窄的胡同,饱尝人情的冷暖。当然,是春天还是冬天并不重要,但不可缺少微雨或薄雪,也不能没有蝉鸣和犬吠,很符合民间吟唱者出道时的落拓模样。我甚至做过这样的猜想,这个最初的词曲作者一定是个心性高洁的文化人,不知何故沦落街头,自叹莲花掉入泥潭的无奈,吃饱了的时候,便挣扎着把肚子里那点墨水硬是给挤了出来,变成词,变成曲,来自草根的莲花落就这样得以口耳相传,其目的是劝人乐善好施,智慧德相。佛的莲花盛开,以此化解人心浮躁,找回慈悯本真。
一段乡曲声动梁尘,谁能知道,这莲花落的前世今生?
我惊讶于这种行乞路上诞生的优美曲调。细数江南无数红情绿意的胜景,那里比比皆是的水塘,无数的莲花逞妍斗色,掩映着岁月深处的朝代更迭。歌舞升平的朱门外,车水马龙的驿桥边、青石板路上,时空隧道里不停歇地攒动着前赴后继的歌者,吟唱着不同曲调的莲花落。起初这只是挂在乞丐嘴上的,不登大雅之堂,但因其唱起来好听,很接地气,广有人脉,久而久之就登堂入室唱到大户人家的饭桌上去了,解闷谁不会呢?文化是没有疆界的,很快就走向四面八方,并不断花样翻新,唱腔说辞快板各领风骚,受众不分山野朝堂。那些年铁窗里的囚歌飘出大墙,倒把外面的人唱得泪流满面,仿佛里面的人就是自己,自己就是里面的人,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可能从宋朝开始,或许更早,千百年来,莲花落的歌词已不再囿于原先的劝化说教而不断被赋予新的说唱内容,唱起来温婉动人、朴实流畅,具有寓教于乐、淳化民风的功能,充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而至今以“莲花落”“落离莲”一类句子作衬腔或尾声帮唱过门的,自江浙至青海河湟堪称一脉相承。
不久前,文友六月荷花参加了在浙江绍兴举办的民间曲艺交流活动,其中就有莲花落专场汇报表演,有这样的唱词:
我也曾高车驰马着锦袍
四书五经读朝朝
为只为引凤院中结情好
恩爱夫妻难轻抛
莲花莲个莲花落吆喝
我看了她发送的视频,这段说的应该是一个王孙公子误入烟花巷,以致家道败落沦为乞丐的故事。猛然想起,自小耳闻目睹的关于以莲花落唱腔分段或结尾的一些河湟民间小调,原来与数千里之外的绍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扎根在高原上的许多河湟人的先祖,据考证就来自明洪武年间的南京。
六月荷花久久地注视着面前的舞台。幕布拉开,琵琶、扬琴、二胡等一齐奏响,演员登场,唱腔婉转,载歌载舞,举手投足间,洞见人世百态。六月荷花深信不疑,六百年烟云散尽,江浙富贵风流之地,应该就是莲花落久违的故乡!
而在河湟,与此曲调相近的,则少了几分婉约多了几分悠扬,莲花落承载着千百年的流韵遗响,不时把别样的精彩带入我们的生活:
一把扇子一朵花呀
一溜莲莲哪花儿哟
哎莲哪莲哪花上儿落
孝顺父母人人夸来么
芦花叶叶儿莲花上落
似曾相识的歌词,其间借助“莲花落”的衬托,唱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不难看出,这词中推崇一种高尚的品格,意境就是江南水乡,时令应该在七八月,芦花和莲花共生,微风吹来,芦叶轻抚高洁的莲花,好一幅精美灵动的荷塘景色!
如此,莲花落传播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日臻成熟和不断改编的过程,无论它在哪里传唱,哪里的传统习俗和文化元素就会潜移默化地渗透进来,千百年斗转星移,地域之間便有了较大的差异,比如说津门的快板和东北的二人转,你会相信它们就是由莲花落演变而来的产物吗?
稀奇的还在后头。
在河湟谷地,如果你随便走进一个村庄,问莲花落为天下何物,保证许多人摇头,不知道或不认同有这样一个曲种,但要是给他唱上两段听听,他一定会说,这莲花落就是某某小调的衬腔。这样就好,说明莲花落是真实地栖息在我们身边的,这美妙的歌声就挂在我们的嘴上,飘荡在节日里、宴会上、社火中,把我们的生活点缀得如此有模有样。
那么说词呢?也就是俗称的“说道”,不唱只管说,伴竹板,词句押韵,随编随说,简洁明快,妙趣横生。它跟现在的快书一个模板,只是所处地方不同,乡音有些改变,河湟民间还有如“倒江水”“打搅儿”等无不是这种说唱艺术的衍生物。
我爷爷那辈,万恶的旧社会,日子不怎么太平。家族中有人择地筑墙建房,众人前来帮忙。这时有个人闪出巷子,骑到对面的墙头上,击膝盖作节拍,猛不丁整出一段莲花落:
养大狗哟垒高墙
不如给我杀只羊
一顿好酒我喝上
从此你家少祸殃
大家认得他是贼,明知惹不起,内中有会说唱的,向他陈情,这边也是贫困户啊,家道消乏,捉襟见肘,妙手空空先生你可要担待:
养大狗哟垒高墙
用尽家中油和粮
你要想来只管来
一天三顿喝拌汤
那人从墙头上跳下来,尽管名声不好听,但似乎很通情达理,和大家有说有笑地吃了一顿午饭,作揖投邻村而去。
这是我爷爷给我爹说的,我爹给我说的,我想找个机会说给孩子,关于老去的莲花落的故事。
許多时候,我们总是把好奇的目光投向新鲜事物,却往往忽略了自己身边最珍贵的东西。记得小时候没有电视和收音机,家家梁头上挂着一个有线广播,听不懂普通话的老汉们耐不住寂寞,冬天农闲,便请来对岸的把式唱曲儿。老花窗打开来,把式坐到上位头,嘘溜溜喝一口茶,山羊胡子一翘一翘。
屋子里挤满了人,窗外也挤满了人,旱烟飘过来,咳嗽声此起彼伏。崽娃们挤在大人堆里,一边跺脚一边吸溜着长长的鼻涕,看不见把式,呆眉呆眼看头顶的夜空。
是的,那时候天好冷,夜好沉,星星像灯。也是那时候,我记住了“莲花落儿开”这一句歌词,此后念念不忘,只是没怎么上心,直到现在悟出点因为所以来,俱往矣四十多年过去!
我老家的婶子和嫂子们,这几年过得好滋润。原来她们在家看孙子,后来孙子一个个长大了,才想起把自己的嗓子给耽误了。她们寻找后悔药的办法是把大家集合起来,买了扇子在院子里扭啊扭,将遗落在老巷里的河湟小调重新拾起来,找回年轻时的感觉。村里已经好多年不耍社火了,大家都忙着挣钱,挣不动钱的就在家里准备争一口气。
她们准备了一些行头,铲平了一处废弃的院落,音响打开,轰隆隆的乐曲直冲云霄,耍社火、唱小调、喝老酒,老树发新枝一时办得风生水起,后来又借助网络的推送,每天在我的手机上恒舞酣歌。
她们唱《八洞神仙》,有这么一段:
一洞神仙汉钟离
赤面黄发大肚皮
莲花落儿开
手里拿的阴阳扇
一扇福绵万万年
莲花落儿开
花儿点着开
我问“福绵”是什么意思?她们一起摇头。我想了想,好像是表达“幸福绵绵”的意思,查查其他曲种的词,有时为避免句长走调,也存在刻意删减的现象,虽然叫人摸不着头脑,但不影响整体效果。
她们唱《十二个月》,有这么一段:
正月里到了是新年
纸糊的灯笼挂门前
风吹着莲花转
二月里到了龙抬头
三姐高楼上打绣球
打得个莲花转
我问不是灯笼和绣球吗,怎么又是莲花在转?她们一起摇头。我想了想,认定那时人眼所看到的景象,必定与心情有关,彩色的穗子飘起来,旋转成美丽动人的花瓣,因此比喻为莲花更具猜测想象之空间。
对于这种现象,六月荷花的解释是:越是不理解莲花落中的个别词意,说明这种传统曲目越接近原始和完整,否则容易被改动,那样就会失去它最初的韵味,这也是莲花落至今得以保存和延续的原因之一。不容易啊,几百年!
今夜的老家,窗外月色正好。谁家飘来的歌声,一曲平调清耳悦心。它来自岁月深处,回响在乡村人家,活跃在流动舞台,或低吟浅唱,或凤鸣鹤唳,或荡气回肠,绕不开的情结抹不掉的印记我的念兹在兹的莲花落!
作者简介:王月邦,1964年10月生,互助县人民法院工作。1988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发表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一百余万字。长篇纪实小说《曾国佐将军》获青海省第九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