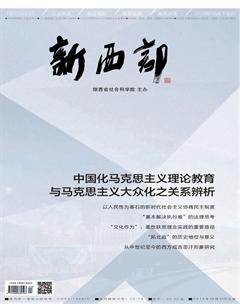“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法理思考
【摘 要】 回望全国各地法院在攻坚“基本解决执行难”过程中的种种考评举措,文章指出存在着两种侧重点不同的评估考核思路,即实体正义考核思路和程序正义考核思路,进而对这两种考核思路在实践中的实施效果以及存在的缺陷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结论:过于强调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中任何一方都是不完整的,而把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统一起来,既是更深层次把握执行工作规避的需要,也有助于人民法院在下一阶段更平衡、可持续地提升执行工作。
【关键词】 基本解决执行难;实体正义;程序正义
2019年3月,周强院长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这一阶段性目标已经如期实现。回望全国各地法院在攻坚“基本解决执行难”过程中的种种考评举措,尤其是对比最高人民法院督导全国各地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时反复强调的“三个90%、一个80%”核心质效指标与社科院第三方评估课题组在评估过程更注重“规范办案”的差异,[1]笔者发现这两种判断人民法院是否基本解决了执行难的评估思路,其实折射出不同评判者对正义内涵的不同理解。在最高人民法院看来,是否基本解决了执行难,核心质效指标无疑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指标,具有“一票否决”的地位。[2]而在社科院第三方评估课题组在赴各省进行实地评估并与各地法院交流时,则表达了更看重的是人民法院是否“规范办理”执行案件的意见倾向。[3]本文在分析两种不同考评思路在考评实践中面临的种种考评盲区的基础上,结合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各自的法律内涵及价值,对下一阶段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努力方向作出探讨。
一、两种评估思路
2018年11月上旬,社科院第三方评估课题组抵达湖北,对湖北法院执行工作进行第三方评估。根据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反馈,社科院第三方评估课题组在实际评估时,更注重通过查阅卷宗,核实法院的案件办理流程是否规范、执行权力是否规范行使,如保全是否及时、是否依法发出了报告财产令、是否对拒不申报及申报不实者进行法律制裁、是否在法定期限内发起网络查控等等。显然,第三方评估课题组更倾向于采取一种“程序正义”的标准去检验、去衡量人民法院是否实现了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目标,这一评估思路的路径是:如果一个法律结果形成的程序和过程具有正当性,那这些程序和过程所达至的法律结果也必具有正当性。而对于此前法院系统内部反复强调的“三个90%、一个80%”等核心指标,据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介绍,第三方评估课题组并没有做更多的要求。
相反,从最高人民法院对各地法院执行工作的督导来看,“三个90%、一个80%”等一系列指向执行案件办理结果的核心指标显然摆在了更重要的位置。在最高人民法院一份关于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的调整说明的通知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提出了“为了回应人民群众对执行案件办理结果的关切,提高了执行质效指标的权重,并增加了执行完毕率等关键质效指标”,并进而提出终本案件合格率、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率、信访办结率三个核心指标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4]在2018年11月29日召开的全国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视频会议上,周强院长再次强调要依法公正高效办理执行案件,确保“四个90%、一个80%”的核心指标。细读上述核心指标,除终本合格率外,其余各项基本上都是指向案件办理的结果,是一种对法律结果的追求,强调的是民事权利的实现,这无疑是一种实体正义理念的折射。
二、两种评估思路各自面临的实践问题
民事执行权,究其本质,就是运用国家强制力去实现一种私权。民事执行制度的基本功能就在于实现从“观念上形成权利”到“事实上实现权利”的转变。从这一基本功能来看,民事执行权、民事执行制度存在的依据就在于其能够实现一种结果上的“实体正义”。
但从当前的民事执行实践来看,实体正义的实现绝非易事。在民事执行中,有些被执行人通过将财产登记到其他人名下,隐匿财产、规避执行,而无论是申请执行人还是法院,都很难取得这些被执行人隐匿财产的证据,正如那句老话:一人藏得巧,千人难寻找。这些恶意逃避法律義务的“老赖”,不乏过得衣食无忧者,而申请执行人则不得不蒙受债权受偿无望的损失,从实体正义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结果无疑是一种不正义。但这样社会现象的存在,恰恰说明在执行领域实现“实体正义”的道路何其漫长。这其中涉及立法部门对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的认定,如何识别、打击转移财产的行为,失信联合惩戒的推广等相关社会制度的构建。从这些角度分析,要实现“诚实地生活,不去伤害他人并给予每个人应得之物”即各得其所的实体正义,难度非常大。
与此同时,对实际执结率指标的考核,也诱发了一些新的问题,如部分法院开始延缓立案、推迟立案,或者动员权利人放弃部分权益、以达到通过执行完毕方式结案的目的,或者只对那些有可能执行到位的案件立案,对那些无法执行到位的案件直接不受理,或者先执后立,无法执行到位就不立案等等。这些实践中的错误做法既损害了申请人的利益,又带来了新的风险和不正义。
而社科院第三方评估课题组采取的则是“程序正义”的路径。相对于结果意义上的实体正义来说,“程序正义”的思路让考核评估的重心从执行案件的实际结果转移到了执行行为本身。在2017年1月社科院公布的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中,中级人民法院规范执行、阳光执行的权重占35%,基层人民法院规范执行、阳光执行的权重更是达到了50%。第三方评估课题组对执行行为本身、对程序正义的关注由此可见一斑。按照现代法理学观点,程序正义无疑具有其独立价值。在民事执行中,注重程序正义,一方面可以防止和排除执行机构和执行人员的违法行为,弥补承办人员知识局限的不足,对当事人及案外人的合法权益也能提供有效保障,而且,通过充实和重视程序本身,可以让争议双方在心理上愿意接受裁判结果,也更容易化敌为友,达成合意或谅解,并对裁判结果产生信任和尊重。在执行实践中,经常有一些被执行人明明可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但就是抱着侥幸心理,在隐匿各种财产后拒不履行。一旦法院对这种被执行人采取拘留措施,此类被执行人则往往立即改口称自己可以立即履行、请法院不要拘留等等。这些戏剧化的效果恰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在民事执行中重视程序正义、用好用足各种强制措施的重要性。在这类案件中,若法院出于风险考虑,没有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结果自然就是老赖逍遥法外,实体正义也难以实现,当事人对执行结果既不会信服也不会尊重。
可以說,社科院第三方评估课题组对“程序正义”的考察,虽然其目标最终也是实体正义,但这种评估思路却指出了一种达成“实体正义”的途径,而人民法院系统内部对“三个90%、一个80%”核心指标的强调,却只是一种对预期结果的描述,并没有直接指出达成这些目标的路径。从可操作性来讲,程序正义的思路显然更胜一筹。
但是,程序正义在民事执行实践中,同样存在一些考核盲区。而且,如果仅仅流于对各种流程启动的考核,或仅仅满足于“完成规定动作就交差了事”,则很有可能滑入“程序空转”的泥潭。比如,按照法律规定,要求对被执行人财产除进行网络查控外,还需要线下的传统调查。那怎么进行传统的线下调查呢?部分法院的做法是对执行案件统一都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对不动产进行查询,只此一举,就算是完成了线下的传统查控。查阅这些法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案件卷宗,我们会发现,这些案件的传统查控纪录往往就只有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查询回执,看不出根据案件的特殊性进行过其他线下传统调查。就这些终本案件的办案流程来看,表面上既有网络查控,也有线下传统查控,但是,其线下传统查控是否充分,仅凭程序是否启动等程序正义的判断标准,是很难得出准确结论的。也就是说,单凭程序正义的考核维度,对部分比较隐蔽的不规范执行、消极执行,仍有考核盲区。
三、解决执行难必须同时重视实体结果和执行行为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裁判的价值在于执行。生效裁判的执行,是整个司法程序中关键一环,既关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兑现,也关系社会正义能否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从法理学的观点来看,正义的内涵,从来都是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结合。民事执行权行使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民事权利,这一基本价值取向决定了“实体正义”的重要地位。实体正义往往表达着一种道德上努力的目标,但在评估过程中,如果仅采用“实体正义”单一指标体系,则不仅不能准确评判法院已尽力查找但受限于被执行人实际履行能力而不能实际执结的案件的办理质量,而且会诱发法院推迟立案、先执后立等一些新的弊端。
反观程序正义的评估思路,我们会发现,这种思路更着眼于通过规范执行案件办理流程,通过规范执行权力的行使,既防止乱作为,又监督不作为,从而达到案件办理结果能让当事人满意、接受。可以肯定的是,程序正义无疑具有独立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基本解决执行难的过程中,法院可以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割裂开来,片面拘泥于程序正义,则可能滑入“程序空转”的泥潭,办理程序虽然一环扣一环,看似严密衔接,但一直空转,不触及实质问题,也解决不了问题,严重损害司法权威。法理学中的正义,一定是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相互统一、相互结合的正义。过于强调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中任何一方,都是不完整的,也必然会存在内在的缺陷。第三方评估课题组在2017年1月公布评估指标体系后,在大量基层调研的基础上,在2018年5月进行了修改,增加了直接体现实体正义的执行质效等核心指标,恰恰说明了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融合的必要性。把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统一起来,既是更深层次把握执行工作规避的需要,也是全社会正义观念不断健全、深化的折射,也是社会公众理性、客观认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思想基石,同时也为“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实现以后,人民法院下一阶段执行工作的改进指明了方向。
【注 释】
[1] 三个90%一个80%,是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在考核全国各地法院在攻坚“基本解决执行难”活动中提出的一系列考核指标,具体是指: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率达90%、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合格率达90%、执行信访办结率不低于90%,以及三年以来执行案件整体执结率不低于80%.
[2][4] 在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5月29日下发的《关于下发“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地方三级法院版)”的通知》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提出了三个90%的核心指标将在第三方评估过程中起到“一票否决”的作用.
[3] 在2018年11月27-28日举行的湖北省全省法院执行业务培训会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反馈第三方评估课题组在湖北的评估验收时表示,第三方评估课题组并不看重法院当前的质效指标,而是更看重法院是否规范办案.
【参考文献】
[1] 童兆洪.民事执行的法理思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2.
[2] 雷蒙德·瓦克斯著.谭宇生译.法哲学:价值与事实[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59.
[3] 江必新.真抓实干 确保基本解决执行难关键之年取得卓越成效[J].法律适用,2017.9.
[4] 秦红,房桂涛.法理学视野中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由“木腿正义”引发的思考[J].品牌,2015.6.
【作者简介】
郑天铭 (1984.11—)男,汉族,湖北钟祥人,硕士研究生在读,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从事民事执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