啼血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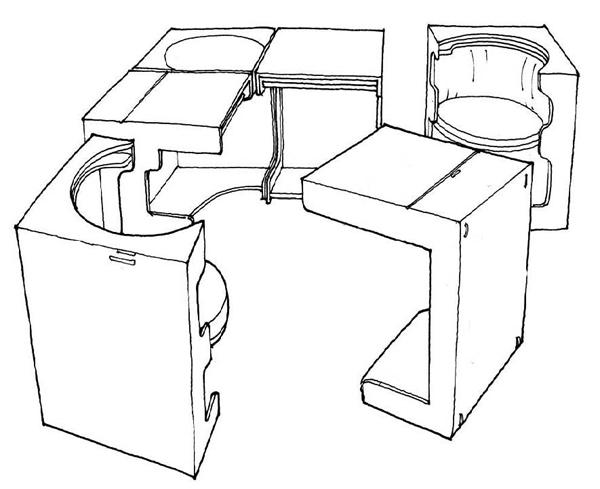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宋剑挺,中国作协会员。先后在《当代》《山花》《飞天》等期刊上发表作品百余万字,多部作品被各类期刊杂志、媒体转载。多篇小说获《当代》擂台赛冠军、“飞天”文学奖、“阳光”文学奖、中石化“朝阳”文学奖、中华铁人文学奖等二十余项省级、国家级文学奖项。
王领往地里一瞅,风像个醉汉,一栽一栽地往前跑着,冬天就这样咯噔一声到来了。王领还没准备好棉衣哩,他穿件夹袄,里面裹了两件毛衣,但风手似的,一会伸进他的前胸,一会钻向他的后背,浑身的热气瞬间便被吸光了。他的胳膊在胸部抱着,膀子缩着,像个冬眠的刺猬。其实他真的想冬眠呐,试想,吃饱了,往床上一卧,用棉被裹住,阳光在窗外嗞嗞地燃着,屋里满是热气,连心里都是热气呀。
这时他想把眼闭上,但眼皮刚一粘住,脑里就似乎长出了一溜藤蔓。他叫不出这是哪种东西,反正是繁繁茂茂的,每片叶子都绿得让人心疼。他并没注意这些,不过眨眼间,藤蔓就散开了,里面冒出一张俊俏的脸,这是他的堂弟王留书的媳妇铁红。每每她出现时,王领总是斥责自己,不该这样想的,但每次这张脸还是坚定不移地跳了出来。次数一多,见的部位就越来越细了。他瞥见了她的脖颈,细细的,白白的,脖梗处的两道细筋快把皮儿撑破了。
一股风咚咚地撞在王领的脊梁上,他趄了趄,又挺挺地直起了身子。路被吹得白白的,像冻实的肉块,砍也砍不出个白痕。马上就到镇上了,他一闭眼,铁红的样子又牢牢地印在脑里了。他一遍一遍地想,铁红的脖子应该戴条啼血链的,这样的话,她会显得更美的。
啼血链是本地妇女常戴的一种饰品,是用红珠串就的。一般来讲,新婚的女人是必戴的,只要条件允许,娘家人是也一起陪送的。铁红没有。
她去年结婚时,也是这样的天气。风挟着沙子,急急躁躁的,它们好像被冻恼了冻烦了,把败叶枯草一股脑地洒向了空中。铁红下了婚车,头上是裹着袄的,她被伴娘引向了院门,门前有个陡坡,铁红的右腿刚往上一迈,一片落叶就挂在了她的头上。袄是红色的,叶子是淡黄的,在灰蒙的天光下,显得鲜鲜艳艳的。王领正痴痴地瞅着,红袄被人拉掉了,叶子沾在刘海上。铁红伸手拨掉了叶子,顺势张开手指,把乱发抿到耳轮上。这时她的眼睛露了出来,她抬起头,眼睛嘀溜一转,大家都觉得看到了自己,并友好地对自己笑呢,于是“咦咦”的声音便高高低低地响起了。
王领站在门阶上,也就是铁红的侧面,他听到“咦咦”声,斜着一瞅,铁红正好抬起头来。他看见铁红的眼皮是叠了多层的,且潮潮湿湿的,像吸饱水的叶子,他还没见过这样的眼睛呢。王领瞅呆了,也随着“咦”了一声。一个女人顺口问,她咋没戴啼血链呢?大家鸭子似的勾头瞅,然后一个说,肯定是条件不好,要不连条链子都舍不得买呀。又一个说,人长得好,要不要链子也没事,说完,咯咯地笑了笑。这人是王保堂的媳妇,她笑完了,一担脸,发现了旁边的王领,王领正呆呆地瞅着新娘呢,于是,她一脸严肃地说,你嘴张着,眼瞪着,色得忒很了吧,要不再把你那条腿打瘸?王领左腿残疾,王保堂的媳妇这样一讲,大家便高高低低地笑起来。王领被这突来的笑声击蒙了,他对着她们眨眨眼,然后尴尬地挤出一丝笑容。笑容冰似的结在脸上,随即叭啦叭啦地掉在了地上。
王领没有媳妇,父母死得早,又无兄弟姊妹,是个标准的光棍。和他年龄相仿的都打工去了,王领却没法去,只有靠土地养活了。对于这里来说,种田不可能致富,富裕不了,腿又有毛病,娶媳妇自然就没指望了。他的腿瘸,村人叫他“地不平”,并戏弄他说,啥时你把地整平,你的媳妇也就娶来了。这话王领听得多了,也听惯了,他要么把眼一低,瞅着面前的地面,要么默默走开,把耻笑声撇在身后。王领明白,他成为大家开心的对象了,连十几岁的孩子,也会跳到他面前,学他一歪一歪地走路。遇到这些,他觉得有根铁针,在他背上一点点地戳着。他已感不到那是疾痛了,他只认为有种碾磙一样的东西,把他吱吱地挤压着,他变成一张薄薄的肉片了。
接近年关,王保堂打工回来了。他在街上碰见了王领。王保堂故意不吭声,而是在他前面踢踏踢踏地走着。他走得很慢,等王领赶上了,他才神神秘秘地说,我想给你瞅个对象。王领头一低,不想理他,但他的眼还是猛地亮了一下,这些被王保堂瞧见了,于是他凑近他,压着声音说,真的给你瞅个对象,你有意的话,就给我买瓶高粱大曲吧。王领认为这次王保堂不是骗他,说话时他的眉头锁着,脸上的每块地方都沁着真诚。他这样一想,心里像有个蜜块,一点一点地化开了。
过了几天,王领在一个小卖部门前找到了王保堂。他正和几个人说笑,王领故意在他面前晃了晃,想引起他的注意,但王保堂瞅瞅他并没吭气。王领想,王保堂可能记着那瓶高粱白酒吧,不给他买酒,他咋会开口呢。王领钻进商店,利索地买了瓶高粱大曲。王保堂还在那里说笑,他不好意思拿出去,就立在门口,向他招招手。王保堂走到跟前,故意瞪大眼,直直地瞅著那瓶酒,然后一板一眼地说,你左腿瘸,我给你找的这个女人是右腿瘸,不知你愿意不?他的声音很大,大家听后都哈哈地笑起来。王领这才发现自己被耍了,而且耍得很利索,他只好红着脸,夹着尾巴逃跑了。
王领蒙头睡了三天,三天后的王领更是没了筋骨,疲疲沓沓地走路,疲疲沓沓地说话,就像一块脏了的抹布,每到一处总是躲在角落里。他的腿瘸得更重了,但王领已不在乎这些了,他的魂灵好像跑了,留下的肉身,软软地溜到这里,又软软地溜到那里。
按当地习惯,新娘过门后要拜见亲朋的,须一一给大家磕头。王领是王留书的堂哥,当然是要受头的。王留书上门找他,他把磕头钱往王留书怀里一塞说,我不去了,你瞅我这样,坐那净给你丢人呐。王留书死让活让,最终没有说动他。他虽躲在屋里,但他的心早溜到外面了,他听到了哈哈的笑声,像风吹动的树叶。笑声粗细不一,中间杂着清脆的声音,这些是娘们的笑声,他害怕这些声音。他把门关上,但笑声挤进门缝,烟似的荡开了。王领用棉球塞住耳朵,又用被子裹住头,声音才隐隐约约的,离自己有点远了。
王领越来越不愿出门了,由于地里没活,他就往门口的草窝里一靠,阳光像群虫子,围着他嘤嘤嗡嗡地转着,他喜欢听这种声音,他认为阳光是在跟自己說话呢。他想回应它们,就极力想些要讲的话语,但脑袋像个房子,空空荡荡,里面啥也没有。他有点沮丧了,他沉沉地想,我不跟别人说话,再不能不跟阳光说话呀。他睁开眼,阳光在跟前蹦跳着,他伸手想揽住它们,但阳光孩子似的走开了,他的手再次展开时,却发现铁红站在面前了。她穿身红衣,太阳一照,把王领的眼都耀花了。铁红愣愣说,哥,不能光在家闷着,今黑儿在俺家吃饭吧。
他几乎是被铁红逼着走出家门的。菜都放好了,油炸花生米,麻辣豆腐,蕃茄炒鸡蛋,都是他喜欢吃的。饭桌就搁在堂屋里,四面放了四把凳子。王领走过去,背对屋门坐着。王留书说,今个没外人,你是老大,你该坐在主位上。王领忸怩着不肯坐。铁红说,哥,今个专门请你咧,你不坐主位,谁坐主位呢。王领听后,泪水哗地涌出了。他今年已经四十岁了,长恁大,别人还没这样说过呢。他挤了下眼,尽量不让泪水流出。
他坐在主位上,王留书和铁红坐在两边,酒盅已经摆好了,铁红掂着瓶子,先给王领倒满了。酒水流淌的声音清清脆脆的,像只小手,在他肚子里轻轻地搅着。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了,一个真正的叫做王领的男人了。这时他再抵挡不住了,眼泪哧溜流了下来。他不愿让他们看到,就侧过脸,做个揉眼的动作。铁红随即说,领哥,喝酒,喝酒呀。王领滋溜喝光了酒,瞅着桌面,又不吭气了。铁红看看他说,领哥,吃菜,吃菜呀。说完,她往他面前夹了些菜。王领慌张地说,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这时王领的心里暖了一下,他觉得自己猛地变小了,他从铁红身上,看到了母亲的影子,他的泪水又涌了出来。母亲也喜欢炒些花生米,但那时花生米少,只有过年时才能吃上。他喜欢一把一把地吃,母亲说,那样吃不香,最好一粒一粒吃,并且一粒一粒地数着,这样吃着才有滋味。他认为母亲就在跟前,姊妹们也在跟前,他颤颤巍巍地捏着筷子,伸向了盘中的花生米。他用力一夹,花生米滚向一旁,又一夹,还是滚向了一旁。这时一把小勺伸了过来,王领伸手去接,胳膊却僵在半空了。为不让泪掉下,他用食指摁住额头,拇指却把泪抹掉了。
铁红再次把斟酒满,然后大大方方地坐下了。按当地的习惯,女人一般是不入宴席的,但王领认为铁红还是坐下好,有男人,有女人,这才像个家,自己才像个真正的主人。 这次王领主动喝了一盅,他的脸早红了,但他还想喝。他认为这是自己的家,他想喝就喝,不想喝就不喝,今天自己说了算。他的耳根都是红的,红色一拐,漫到了脖子上,仿佛看见面前燃着一堆火,头发好像就要燃烧了。这时铁红端起水说,哥,你喝水吧。王领听后,泪又在眼里打转了。多少年了,没人这样亲切地喊过他了,这样猛的一叫,他还有点受不了呢。他接过茶杯,喝了一口,泪水却滴进了茶杯里。他听到嗒哒一响,清清脆脆的,整间房里似乎都能听到了。王领出口长气,他端端地坐好,认为这才像他们真正的大哥。
喝过酒后,王领的心情好了许多,他往门口草窝里一歪,又昏昏地闭了眼,他极力回想昨天喝酒的情景,他不知怎样离开的,只记得出了门,身子歪了一下,铁红赶紧把他扶住了。铁红的个子跟他一样高,细细挑挑的,很是匀称。这回他彻底瞅清了,铁红确实没戴啼血链,她细细的脖子躲在领子里,像只胆怯的鼠。他想铁红应该有啼血链的,这样好的媳妇咋能没有啼血链呢。
王留书打工走了,王领想帮铁红干点活儿。他看了南地,又看了北地,发现玉米已浇过水,谷子也浇过水,棉花杈也打过了。王领再从北地来到南地,南地地肥,种了些黄豆。黄豆长得粗壮,绿绿腾腾的瞅不见地皮。王领拨开枝叶,看到地上满是杂草,就拿了锄,一点点锄起来。没多久铁红也过来了,她谦谦地说,领哥,叫你操心了,这两天一忙把锄地的事忘了。王领看着她讲,以后再甭这法说了,谁叫我是你大哥呢。
地身很长,王领锄得很快,几支烟的工夫,就折回头了。两人离得很近,能听见铁红柔柔弱弱的呼吸。她穿件白色上衣,阳光哗哗地落下,被绿色的豆秧一映,也像一片茁壮的禾苗了。锄地时,她的腰身自然地仄斜着,宽肩细腰,舒舒缓缓的,真有点晃眼了。他们照面的当儿,铁红停下了,她把锄把往肩头一依,掏出了擦汗的手帕。她解开了上面的扣子,脖子露了出来,仍然是细细嫩嫩的,脖根的两条细筋,立立正正地凸在外面。王领想,她确实该戴条啼血链的。这时铁红侧身问,领哥,你渴了吧?王领发现,铁红的两眼仍和原来一样明亮,她的眼皮一层层叠加着,润润泽泽地,再次烙在他的心里了。
两人正在说话,发觉后面有重重的呼吸声。回头一瞅,王保堂就站在后面。见王领瞅他,王保堂松松身子说,你干得真卖力,说完,对着他使劲地眨眨眼。王领不理他,他就学着王领的样子,一斜一抖地锄草。铁红一撂锄头说,论辈份该叫你叔咧,你也是四十岁的人呐,咋能这样欺负人呢。王保堂咧嘴干笑几声说,你甭管,我跟他开个玩笑。铁红噤着脸说,他是俺哥,我不管谁管。王领听后,心里酸了一下,他觉得自己的身子缩了下来,缩得跟豆棵一样高。瞅瞅腿,腿是软的,胳膊也是软的,软得跟棉花一样。铁红又叫他一声哥,他感到自己身子硬了,腰板直了,但个子仍跟豆棵一样高。他瞅着铁红,想说些什么,可是嘴一绷,又咽了下来,不过他的眼已湿湿的了。
王保堂顺着大路走了,他们两人收了工,沿着小路回了村,谁知在村里又碰见了王保堂。他凑近王领说,这回给你提个真事,我干活的那个工地,缺个厨师,你去不?王领瞥他一眼说,我不想说话,你也甭吭气了。王保堂撇着嘴说,我跟你正经吧,你反倒不认了,你说你是啥人呢。然后他剜了一眼铁红,响响亮亮地说,我知道你心里想的啥。王领听他一讲,脸陡地红了,腿一拐一拐地,瘸得更厉害了。铁红气鼓鼓地说,王保堂,你看着俺哥好欺负吗?王保堂笑笑说,我可是跟他说正经的,你以为我骗他啦?铁红拧着眉毛说,你想弄啥,你心里知道,王保堂摇摇头说,好好,我不说了,我不说了,他边说边往前面走,没走多远,左腿突然一斜,学着王领走路的样子。铁红安慰王领说,哥,甭理他,你别把他当人看。
风哧溜哧溜地大起来,王领用棉袄裹住头,沙子还是虫似的往衣内钻去。地里都是树,风摇着枝杈,弄出悦耳的声响。这声音没有完全钻进他的脑里,而是在他的面前,嗖嗖地打著旋儿。他仿佛听到了铁红的声音,而铁红多半是哥呀哥呀地叫他。他觉得这种叫声,就像一双小手,在他脸上摸呀摸的。每每这样回味时,他的眼总是湿湿的,有星星点点的泪滴挂在睫毛上。王领揉了揉眼,又把手插进衣兜里。兜里掖着一张存折,上面有1100元,这些钱是卖棉花和黄豆的。本来这笔钱已计划好了:500元翻新屋顶,500元买化肥农药,100元零用。现在他已想好,屋顶不修了,用这500元给铁红买条啼血链。他该有条链子了,恁好的女人,该有的应该都有的。
镇上有两条街,一条大街和一条小街,大街上有商店,有商场,货多人也多。小街里则藏着发屋发廊和一些食品小店。大街上都是人声和车响,嘈嘈杂杂的,小街里则是低声细语,隐隐晦晦的,可是银行就在小街里。王领在小街口站住,把袄从头上取了下来,使劲一甩,沙子便哗哗地落下了。然后他一歪头,伸手拍拍头发,上面的沙子也哗哗落下了。他正要把袄穿上,猛听到吃吃的笑声,笑声很是羞怯,躲躲闪闪的。他抬眼瞅去,一个女人在门口闲坐着,她的眼显然是纹过的,粗黑粗黑的,像个熊猫。王领准备走开,女人开口道,大哥,今个风大,过来洗洗头吧。王领没有讲话,只朝她摆摆手。女人继续说,大哥,十块钱一洗,真是跳楼价,要不过来试试?王领没有回头,而是直直地走了。
王领从银行取了500元,放进贴身的口袋里,然后用手摁了摁,才放心离开了。这时阳光已把小街晒热了,发廊里的女人们都坐在门口,她们穿着鲜艳的衣服,像一片片散落的花瓣。王领本想快速地走过的,可是将到大路口时,被一个女人勾住了腿。他侧脸一瞅有点吃惊了。女人的眼睛大大的,眼线一层叠着一层,不仔细看,还以为是铁红呢。王领想说话,但不知说啥,话到嘴边,又咽回了。女人不讲话,只默默地瞧着他。她的眼虽大,但淡而无光,仿佛是个深洞,丝丝地冒着凉气。王领觉得自己的身子轻了,轻得像根鸡毛,忽闪忽闪的,像要被旋了进去。他把眼一闭,铁红的影子却腾地跳了出来,她的眼神是平静的,充满了温暖。王领觉得它像个草窝,暄暄腾腾的,自己多想躺上去呀。
王领愣了愣,女人终于说,你想按摩吗?不等王领回答,她又说,我们还有别的服务……一听这话,王领的心里扑腾一声,像水桶掉进井里,不知咋的,他变得惶惶的,不想离开,也不想站着。女人似乎看透他了,伸手拽住了他的胳膊,由于动作过块,女人的手碰到了他装钱的口袋,王领咯噔一愣,把女人甩开了,女人噘着嘴,娇娇地瞪着他,眼里的怨恨水一样地流出了。王领心里陡地疼了一下,他想起了铁红。王留书打工走后,铁红一个人做饭,她让王领搭伙吃饭。王领说,我是哥,你是弟媳,这样做不好,铁红笑笑说,这都是什么年代了,还计较这些。王领说,这是农村,你不计较,别人计较。王领这样讲着,铁红已经生气了。她瞪他,眼神从他身上,腾地溜到了地上。现在王领还能想起那种样子,眼里浸着的满是温暖,那温暖像条丝线,牵牵连连地缠在他的身上了。
王领还是走开了,但女人没走,仍呆呆地站在原地。王领觉得后面有双手,轻轻地拽他一下。他扭过身,那女人正望着他呢,她的眼明明亮亮的,眼线一层叠着一层,活脱脱一双铁红的眼。王领的身子颤了颤,心想,她咋恁像铁红呢。
王领没有多想,他逃也似的离开了,他还得买啼血链呢,他要给铁红买条最满意的链子。阳光暖融融的,洒得满地都是。王领的脚下像抹了油,轻轻快快的。他从没这样兴奋过,他觉得这才像个男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
他钻进一个商店,橱窗里满是啼血链,价格多是100元至200元的。王领挑几个瞅瞅,发现珠子大小不一,心想,这咋能送人呢。他沿街继续往前走,前面有个新开的商店,门额上挂了鲜艳的彩带。王领走进去,见里面的啼血链摆满了两个橱柜。卖货的男人拿出六个,个个包装都很精美,王领不敢摸了。男人挑出一个,他折开外层硬壳,掏出了里面的绒包,啼血链哧溜跑了出来。王领掂着瞅瞅,珠子大小匀称,色泽也算纯正,他拿到亮处一瞅,觉得颜色杂乱,深浅不一,又遗憾地放下了。
出了商场,王领有点泄气,他想,既然买了,当然得买个满意的,咋能对不住铁红呢。这样想着,只顾急急地往前走,右脚踩进了烂泥里,弄得鞋上都是脏物。这是铁红做的鞋,以前穿的布鞋都是买的。由于左腿残疾,左脚变得比右脚小,买的鞋穿在左脚上,总是松松垮垮的。铁红知道后,一次给他做了五双。现在的年轻人哪有做鞋的,可铁红就这么做了,她一针一针地纳着鞋底,一针一针地缝着鞋帮,终于做好了五双鞋。王领把鞋揣在怀里,眼睛又湿湿的了。
再往前走,人越来越多,多日没来,前面又开了一个商场。王领随着人流扎了进去。来到柜台前,卖货的姑娘笑着迎住了他。姑娘和铁红一样高,一笑露出了白润润的牙齿。姑娘问,大哥,你要哪一种链子呢。王领说,哪一种好,就拿哪一种。姑娘拿出了三种链子。王领瞅瞅这个,摸摸那个,认为哪个都好。姑娘戏谑道,干脆都买了。王领说,钱不够哇!他磨叽半天,搔搔头皮说,你年轻,懂行,给我挑个吧。姑娘对着链子端详了一阵,从中拿出了一条。王领捧着,觉得链子柔柔的,软软的,似乎还有些温度呢。咋一瞅,表面是光滑的,手一摸,却带有粉似的感觉。他静静地想,我回去交给铁红,她就能戴在脖子上了,以后就再也摸不着了。越这样想,他的手就越不能松下,他边摸边看,快把链子贴到脸上了。姑娘笑着问,是给媳妇买的吧。他慌慌地答,是,但又马上改口说,不是。姑娘瞧他的窘态,笑得更响了,边笑边说,我猜你肯定是有问题呀。
王领把钱付了,正准备离开,又有点犹豫了,几百元买的链子,铁红戴上合适不?只要一走,商家是不会退货的。这时他脑里蹦出一个念头,干脆让姑娘试试。姑娘的脖颈白白嫩嫩的,和铁红的一样。他一提,姑娘爽快地答应了。她立立正正地站着,王领也立立正正地站着。姑娘是圆脸,铁红是长脸;姑娘的脖子稍短,铁红的细长,戴上啼血链,是辨不出好坏的。姑娘站了一阵,身子一松问,大哥,你觉得咋样?王领违心说,我觉得不孬。实际上,姑娘戴上还算可以,但没达到他想要的效果,是她的脖子短?还是她不是双眼皮呢?他还想找个人试试。
王领在商店门口顿了顿,然后坚定地走向了大街,可是他在街边呆住了。街上人还算不少,要试试链子,去找谁呢?他的脑子空了,空得就像个房间,虚虚幻幻的,但忽然觉得该有人给试的,但这人似乎藏起了。这时他空空的脑袋里现出了一只手,这只手抓了一下,没把那人抓住,又抓了一下,还是没把那人抓住。他认为,那人就躲在暗色里,只能对他突然袭击的。于是他让那只手停住了,警觉地扒在角落里,突然它又腾跃起来,终于牢牢地把她逮住了。她不是别人,就是发屋里,长得像铁红的那个女人。但转念一想,发廊里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些浪荡女人,他不想和她们多打交道,于是决定往家走。
天说黑就黑了,它像一块帷幕,扑嗒一声落在了小街上,王领加快了脚步。路两边发屋的灯都亮着,似乎是那种蓝色的光,满是怪异和隐晦。王领低头走着,突然被一个人拦住了,抬头一瞅,正是发廊里的那个女人。王领惊了一下,女人看看王领说,恁急干吗,到屋里坐坐。说完,就把王领拽到了屋里。
女人对他笑了笑。她的笑几乎也跟铁红一样,眼眯着,眼线缩成月牙状,所有的笑容都挤在眼上了。王领觉得有种暖流从脚心开起,漫过腰肢,漫过脊背,一齐涌到脸上了,他的脸红红的。女人又笑笑说,你按摩吗?王领张张嘴,没有吭声,女人忙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你跟我来吧。女人一挑门帘进去了,王领顿了顿,也进去了。里面是些格子房,房里有张小床。王领跟进去,女人已经坐在床上了。女人瞥瞥他,伸手解开了扣子。王领有点紧张,他犹豫一下说,我没别的意思,你给我试试这条链子吧,没等讲完,已把链子戴到了她的脖子上。女人摸不着头脑,王领就嘟囔着说,铁红跟你一样高,跟你一样瘦,戴上它更是好看了。女人拧着眉头问,铁红是谁?王领顾不上说话,他正瞅着女人的眼线呢。她的眼线叠了三层,并在眼角处轻微折了折,更显得滋润美丽了。他把链子推了推,让鸡心链坠垂向中间,正好和过耳的头发匹配了。王领发现女人的脖子粉嫩粉嫩的,像过滤的二道面粉,脖根的两道细筋,和铁红的一样,鼓鼓翘翘的,快把皮肤撑破了。啼血链往上一戴,就像镶上去的玉石。王领的头歪着,眼眯着,他幽幽地说,真漂亮呀!
这时女人已把上衣扯掉了,两个乳房鸽子似的跳了出来,王领没看她的乳房,他瞅着她的眼线,忽地挤起,忽地散开,挤起时像个月牙,散开时也像月牙,于是他轻轻叫声“铁红”,扑上去吻起了她的眼。女人惊也似的说,我不叫铁红,我叫……还没说出口,王领的嘴唇已把她死死地堵住了。
王领正要解开裤带,膀子被狠狠地拍了拍,这人的手很凉,凉气针一样地刺到他心里。他想大骂一声,回头一瞅,却是个警察。
王领被带进了派出所,他叹着气想,肯定是老板报的案,要不咋能正好逮住呢。他低着头,准备把前后过程想一遍,看看哪地方出了错。但他刚一眯眼,警察就说,嫖娼罚款最高五千,你是农民,就罚你两千吧。王领的脸青了,他哆嗦着说,我不是嫖娼,我是想……还没等讲完,警察的拳头咚地一声砸在了桌面上,他狠狠地说,我没空听你啰嗦,啥时拿来钱,啥时放你。说完,把门嘭的一关走了。
屋梁上吊个灯泡,昏黄的光,像个铁网,牢牢地罩住了他。王领往墙角一蹲,脑袋始终想着一句话:到哪弄钱去?他想了一圈,除了王留书和铁红,再没别的亲人了。王留书打工走了,唯一能帮的只有铁红了。这事能让铁红知道吗?咋能给她说得清,她又怎样看我,不能叫村上唯一看得起我的人,再瞧不起我。他想了一阵,又想了一阵,再想不起别的办法了。他觉得这些念头,像个铁球,他费力地挑起来,却又咚地掉在地上,如此反反復复的,快把他累死了.
门一开,天亮了,王领还不知有这样短的夜。他一抬头,过来一个年长的警察,他和和蔼蔼地问,你嫖娼了?王领搔搔头说,说实话,我裤子都没脱。警察笑笑说,不管你成不成功,反正你有那种动机。王领木着脸说,我是光棍,我长恁大,这事还是第一次。老警察又想笑,但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他的嘴一咧,笑容便水似的洇掉了。然后他一板一眼地说,法规上没允许光棍可以嫖一次,或者说,第一次嫖娼不罚款。法规没给光棍特权,我们当然也不能给……
老警察讲得极有道理,王领不知咋说了。这时他一个劲地想,肯定是发廊老板报的案,越想就越气,所以老警察再次问他时,他就不住地说,我确实没嫖,我年龄不小了,咋能哄人呢。老警察说,你已把腰带解开了,再停上几秒,你就上床了。王领听后,像吃个辣椒,嘴张着,再也合不上了。
第三天,老警察又来了,他还是那句问话:你是哪村的?这回王领头也不抬了,就是闭口不说,老警察掂了两个馒头,捏着一袋咸菜,说,你已三天没吃东西了,先吃点馒头垫垫吧。他见王领不吭,就往前凑凑说,我请示过了,先交一千块罚款吧,交了钱,你就可以回家。这回王领抬起了头,他翻眼皮说,我没脸再回村子了……说完,像个废弃的皮囊,倚在了墙角上。
早上,老警察照例打开了门,房里却不见人影,他正感奇怪,往上一瞅,发现王领已在屋梁上吊死了,身子变得硬硬的,像捆悬着的干柴。他更感奇怪的是,王领手上抓着一条啼血链,灯光一照,哧哧棱棱地闪着金光,似乎要把屋子照亮了。老警察倒吸口凉气,他仿佛瞅见啼血链上的金光碎片似的撞在墙上,然后又叭叭地落下,发出凌厉的响声,他吓得不知所措了。
责任编辑/何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