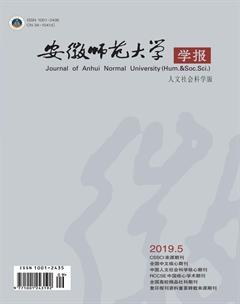历史与文学:吴组缃《山洪》对安徽抗战传播的贡献
钱果长
关键词:《山洪》;历史写真;文学想象;安徽抗战传播
摘 要:《山洪》作为抗战初期较早的一部长篇小说,文本内潜存历史写真与文学想象的复杂纠缠,呈现文学与历史紧密呼应的内在张力。小说中的真实地名,准确完整地呈现出日寇进犯皖南的路线和方位,不仅成为小说谋篇布局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且使小说在表现抗战这一题材时烙下明显的安徽地理标签;历史事件潜在参与小说文本的建构,小说描写的广德、宁国遭轰炸和游击队开展的发动群众工作等场景,与相关历史事件具有明显的互文关系;小说对皖南农民众生相的刻画及其心灵觉醒的揭示,为抗战时期皖南民众经由战争而改造,也留下了富有历史意味的艺术写真。小说在历史之真与文学之真的艺术融合上尽管存在瑕疵,但客观上为安徽的抗战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
Key words: Shanhong;historical portraits;literary imagination;the spread of Anhui AntiJapanese War
Abstract:As an earlier novel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Shanhong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mplex entanglement of historical portrait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showing the internal tens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The real place names in the novel accurately and completely present the route and orientation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southern Anhui province,which not only become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novel layout,but also makes the novel branded the obvious Anhui geographical label when it shows the theme of the AntiJapanese War.The potential participa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ovel texts and the scenes where Guangde and Ningguo were bombed and the launching of mass work was carried out by the guerrillas show obvious intertextual relations with the related historical events.The novels portrayal of the peasants sentient beings in southern Anhui and the revelation of their spiritual awakening leaves a historical artistic portrai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eople of southern Anhui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Despite the defects in the artistic fusion of the truth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the novel makes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spread of Anhui AntiJapanese War objectively.
2019年第47卷 《山洪》是吴组缃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动笔于1940年冬天,1942年完稿,历时近两年。“上篇”七章最初刊于《抗战文艺》,1943年,作为“抗战文艺丛书”之一,由重庆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出版,书名为《鸭嘴涝》;1946年由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再版,因书商嫌《鸭嘴涝》之名“别扭晦涩,影响销路”[1],由老舍帮助改名为《山洪》,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山洪》修改本(本文写作依据此版本)。这部小说,无论于吴组缃个人创作史还是现代文学史,都有其独特性。一、吴组缃以短篇小说创作为胜,其收入《西柳集》中的短篇,堪称“每篇都很精当,有分量”[2]305,《山洪》則是其唯一的长篇创作,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也容易引发读者的阅读期待。二、《山洪》是应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刊《抗战文艺》的编者之约而作,[3]208属于“奉命写作”的“遵命文学”,尽管这“命”是作者愿意“所奉”“所遵”之命,但这对于既强调文学的社会性时代性,又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艺术性的吴组缃而言,应该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据作者言,此书“前面七段,因为凑着了闲空,一气就写成了。后面十段写的可实在艰难:有时写半页,搁他三五天;有时两三个星期不能写一个字;后来索性摆开了,大约整一年没有摸他”,后来也是“一字一句的挤着”,“总算挤完了篇”。这其中的写得艰难,除却战争环境下的不得空闲之外,应该与“奉命写作”的内在窘迫也不无关联。作者后来也承认此书是次品,因为自己对所写的内容不熟悉。参阅吴组缃《山洪》的《赘言》和《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08、210页。三、《山洪》是抗战初期较早出现的长篇小说之一,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都蒙受评论界和文学史的关注,也成为文学史写作不可忽略的一个存在。也许正缘于诸多独特所在,此书甫一发表和出版,时人老舍、韩伧、李长之、余冠英等都积极撰文评介,后来的文学史写作也推崇其为抗战初期长篇创作的重要收获,认为它反映了“抗战初期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农村农民心理的变化”[2]493494,更有被誉为“抗战初期民众觉醒的心灵史诗”[4]。但综观诸种评价,大都侧重于《山洪》的思想艺术成就,对于文本中潜存的历史写真与文学想象的复杂纠缠鲜有关注。此书既然为“奉命写作”,要写到作者所不熟悉的生活,那么这种“不熟悉的生活”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又如何编织进小说,并最终使其成为小说?这些问题既是作者在创作中必须面对并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也是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不得不审视的问题。吴组缃本就是一位善于对社会生活进行剖析的小说家,其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对皖南农村社会的衰落描写,其间就掺杂有历史写真的印迹。有研究者已经指出《一千八百担》文本存在历史现象与文学场景的交织情况,认为它高度还原了民国历史情境中“乡绅困于破落与佃农陷于破产之不同境遇”,“保持着文学与历史之间紧密呼应的内在张力”。[5]《山洪》也不例外。对《山洪》中历史写真与文学想象的纠缠现象的审视,不仅可以见出作品对安徽抗战传播所作的贡献,也可对文本内在的艺术裂缝作出新的认识。
一、真实地名的双关意义
吴组缃的短篇小说皖南地域色彩浓厚,这在《山洪》中也有突出表现,但与众多短篇不同的是,其皖南地方色彩不仅通过风物、方言土语彰显,还在于其运用了大量的真实地名。作者曾夫子自道:“篇中用的地名,许多是实有的;这不过为了行文方便,读着也显得亲切逼真些。实际却和故事童话里的‘从前某处地方相似。若是有人翻出地图来,想根据那些地名核对什么事实,那可成了笑话。作者恕不负责。因为这是小说创作,不是史实记载。”[3]208这段话,我们不可不信,但也不可全信。我们自然不可按图索骥,比附史实,但问题是这里的“行文方便”。为什么非要在小说创作中运用真实地名才能保证“行文方便”,虚构的难道不行吗?这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地方。
小说中用到的真实地名,大到上海、南京,中到市、县名,小到村镇、山岭名,较多的都是围绕鸭嘴涝四周的安徽境内地名。这里暂且列出几条线路和地理方位,以窥一斑:
小说第12节:鸭嘴涝人们传闻广德州宁国府失守,到处是溃兵,他们“要过万峻岭开青阳大通”,“城里同三里店那边还是潮水样的涌”。
小说第15节:“战争象一头巨兽,突然张牙舞爪逼了近来。在短短的期间,广德州、宁国府失守了,芜湖和南京先后放弃了。南陵县那边,敌人的铁蹄冲到了黄墓渡和石硊镇;芜湖、宁国府那边,我们还有大军在湾沚、芳村以及寒亭、西河一带撑持着;在西面,大通和悦州也岌岌可危,青阳铜陵的人民一窝蜂的向里边山乡挤来。”
小说第16节:“消息十分简单,说是有一支官军要从徽州那边翻山过来,经过本县,开到清弋江前线去。”
小说第21节:“眠牛山桥是这里山乡一条要道。以镇上为起点,向北经过黄龙溪,通到县城、清弋江和宁国府;从黄龙溪转而向东,通到三里店、南陵和芜湖;从鸭嘴涝西行,可达青阳、铜陵,以及大通和悦州。”
小说第26节:“广德州收复以后,宁国府和芜湖,竹丝港、白马山一带都连续获得胜利;可是西面十分危急:大通和悦州都已随着安庆而告失守,敌军正在猛攻青阳,我方军力单薄,节节后退,目前这个距离本村不过一百里的县城怕已经陷入敌手。现在南陵和清弋江的驻军将加紧调到黄柏岭和万峻岭守御,游击队也在准备出动。”
小说第33节:“……清弋江和南陵相继失守,丫山、鹅岭也发现敌人的骑兵了。”“寿官继续说,敌人这回进攻,分做三路:一路从铜陵、青阳打向南陵丫山,这是原来在西面进攻的一路;一路由石硊、黄墓渡扑南陵,直趋本县和三里店;一路由清弋江逼近南陵。”
以上涉及市、县的名称有广德、宁国、青阳、芜湖、南陵、铜陵、徽州、安庆等,村镇的名称有大通、三里店、黄墓渡、石硊、清弋江(青弋江)、湾沚、芳村(方村)、寒亭、西河、竹丝港、白马山、丫山、鹅岭等,山岭的名称有黄柏岭、万峻岭等。在小说中大量使用真实地名,非吴组缃独然,现代作家老舍就曾把北京城里的街道胡同乃至店铺名直接搬进了小说中。据舒乙对《骆驼祥子》中祥子由西山逃往城里的路线的考察,发现地理背景完全真实,其“地名对、方位对、地势對”。[6]从《山洪》中出现的地名来看,吴组缃也完全做到这点,地理方位完全准确。吴组缃家乡泾县,地处皖南山区腹地,东与宣城区、宁国市接壤,南与黄山区、旌德县毗连,西与池州青阳县交界,北与芜湖南陵县为邻,其出生地茂林镇属于泾县“西乡”,靠近南陵,翻过黄柏岭和万峻岭即可到青阳。据吴组缃交代,《山洪》中章三官一家的原型是其姨妈家,坐落在从泾县去茂林的必经地溪口村,小说中的鸭嘴涝就是以溪口村为原型的。[7]137作者对家乡自然熟稔,所以准确呈现地理路线方位并非难事。
整个抗战期间,吴组缃积极从事抗战文艺工作。早在1937年3月,他就曾应葛琴之邀,与邵荃麟、叶以群等在宜兴丁山聚会,讨论如何积极投身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以及文学创作问题;[8]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参与“文协”发起工作,与老舍共同起草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且担任“文协”常务理事和“文协”会刊《抗战文艺》编委会委员。这次应《抗战文艺》之约创作反映抗战的文学作品,凭藉“一点抗战激情和对故乡风物的怀念或回忆”[9]210,将笔触伸向家乡土地上的人民也是顺其自然之事。也许,对于彼时身处陪都重庆的吴组缃来说,故乡土地上人民的生与死更让他挂念。在《山洪》里,我们看见了日寇轰炸下皖南大地上的惨相,小说借回家参与鸭嘴涝开河捕鱼的章二官之口(尽管是卖弄的、猎奇的、没心没肺的),叙述了他在黄龙溪得到的关于宁国府被日本飞机惨炸的见闻:戳娘的日本飞机像织布样的你来我去,要炸那里,就炸那里。鼎老板庆和布店所在的玉笙阁,一条十字大街,炸的连影子都没有。鼎老板像死了老子娘样的,两三万的家当一夜间就捋了把痰唾呀!鼎老板自己躲在小东门的稻草堆子里,旁边庄稼人家放在晒场上的一袋袋棉花,被戳娘的飞机当是什么火药,孔通孔通地放了两三个弹,鼎老板被炸得跳的离地三尺,好半天扒出来,吓得眼睛吊直,不知自己是死是活。从南门到杨柳铺的难民,像蚂蚁子搬家样,队伍拉去有十里长,没一个人脸上有人色,眼睛都是直吊吊的。小说又借由青阳逃难到鸭嘴涝的老农之口,叙述了日寇在皖南大地上的种种暴行:“他们占据一个地方,到处搜寻粮食细软,粮食都运走,财物私人上腰包;其次搜索妇女和牛羊鸡鸭,遇着男丁就杀死。妇女们被关在一间屋子里,走的时候还挑年轻美貌的带了去。他们所到的地方,牲畜杀光,吃喝不了的就向毛坑里倒。凡他们打算放弃的村镇,就放火烧。”当然,小说更多的笔墨还是描写以章三官为代表的皖南山区人民的心理蜕变和灵魂觉醒,以及在游击队发动下终于汇入伟大的抗战洪流的历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对日寇暴行的描写,完全借人物之口道出,其间虽不无文学想象,但多少暴露了作者借历史当事人口述实录的方式,还原历史情景的意图,客观上既弥补了作者对家乡战事景象不熟的缺陷,又达到了借人物之口控诉日寇暴行的目的。因此,上述种种,不仅揭露了日寇在皖南的罪行,而且展示了家乡人民在日寇铁蹄下的生存图景和奋起抗争,较早地向外传达了抗战时期皖南地区的景况。而真实地名在小说中的运用,就使得抗战传播中的安徽地理标签更为直截了当。
综上,无论是深入历史深处,对鸭嘴涝农民缺乏民族国家意识的揭露和剖析,还是对他们走向觉醒抗战的历史发展必然的揭示,《山洪》都高度遵循现实主义文学精神。鸭嘴涝农民由落后走向觉醒的历程,不仅使《山洪》充分实现了抗战宣传主题的表达,而且使其主題与“五四”新文学所开创的人的文学传统、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传统又联系了起来。因为正是在这场战争中,鸭嘴涝农民的心灵开始了觉醒,精神得到了改造。从此角度而言,《山洪》对抗战时期皖南农民经由战争而改造,不仅给予了富有历史意味的艺术写真,同时也因此所包含的主题丰富性,使其成为抗战初期长篇创作中较具有独特艺术价值的一部作品。
四、余论
阅读过《山洪》的读者,大都有这样的艺术感受,小说前半部叙写皖南乡村生活体验,写得细针密线,精雕细刻;后半部写民众觉醒抗战,则是笔法匆匆,大刀阔斧,在小说叙事艺术上存在明显的分裂。由此《山洪》也只赢得了“半部好小说”的艺术评价。《山洪》艺术表现上的裂缝,固然与作者对战争生活不熟悉有关,但在文本中却是通过历史写真与文学想象的复杂纠缠表现出来的。在《山洪》里,历史不仅作为叙事的背景出现,同时也直接呈现,参与文本建构,成为了挤压文学想象空间的力量。虽然历史与文学都具有求真的品格,但文学是以审美想象的方式求真,历史则以客观实录的方式求真,两种不同的方式在一部小说中生硬地结合在一起,必然导致小说艺术上欠缺和谐圆润。而这种复杂纠缠,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抗战文学创作中,应该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查吴组缃抗战时期的日记,吴组缃与友人谈得最多的还是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思考。在全民抗战的伟大时代,吴组缃在理论上非常坚定,认为“政治与文学须配合一致”[1],尽管他对文学创作有着非常明确的艺术理性认知,但具体到《山洪》的创作,艺术理性认知是一回事,顾及抗战现实需要又是一回事,在这里,吴组缃充分体现出一个中国作家的良心和热情,其表现和我们熟悉的作家老舍是一样的。如我们所知,《山洪》是“奉命写作”,进行抗战宣传自是题中应有之意,作者乐意为之;但另一方面也毋须讳言,作为有着丰富小说创作经验和艺术追求的作者,对文学艺术性的坚守也是其本分所在。也许,写作《山洪》时的吴组缃,就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夹缝中,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他写写停停,停停写写,写得“实在艰难”——他不得不游走在历史写真与文学想象的纠缠之中。但若荡开其中艺术瑕疵不说,作品还是以其极具指向性的皖南地域抗战书写,客观上为安徽的抗战传播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 吴组缃.吴组缃日记摘抄(1942年6月—1946年5月)[J].新文学史料,2008(1):1138.
[2]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 吴组缃.赘言[M]//吴组缃.山洪.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4] 陈思广.《山洪》:抗战初期民众觉醒的心灵史诗[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2(3):3135.
[5] 谢力哲.历史困境中的乡绅与佃农困境——“民国”情境下的《一千八百担》[J].文学评论,2018(2):145153.
[6] 舒乙.祥子的“路”[J].新华航空,2010(5):134.
[7] 吴组缃.答美国进修生彭佳玲问[M]//吴组缃.苑外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8] 方锡德.吴组缃生平年表[J].新文学史料,1995(1):4153.
[9] 吴组缃.后记[M]//吴组缃.山洪.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0] 黄书泉.抗战文学的独特叙事文本——吴组缃长篇小说《山洪》阐释[J].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4(1):3344.
[11] 吴组缃.一味颂扬是不够的[M]//吴组缃.苑外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12] 吴组缃.我对于全国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几点管见[M]//吴组缃.苑外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凤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