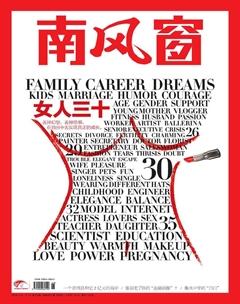几米的阳光
李少威

那一天,在东莞。
签名会,几十米的长队在等着几米。他快速走向签名桌,我跟在他后面,很难追上他。
小个子脚步如风,“seize the day”,几米一直如此。他总是想,要抓紧时间,说不定哪天就死去了。
他的眼睛已經老花,但等着签名的人们都慨叹他的年轻。正如他的书,对生命的忧思和对童趣的捕捉,一直矛盾着。
他是内向而害羞的。这样的人往往有更纯粹的心灵,少一些杂念。所以,你要他解释他的书,它们的深刻含义,他似乎一时语塞,停顿了一下就说“我读给你听吧”,然后把它朗诵一遍,反正一本书也不过寥寥数百字。
那声音达不到播音员的要求,柔软而有一点哀愁,但你会发现,他自己读自己的书,最是合适。
一种不可形容的美,令人屏息。
2018年到2019年,“几米创作20周年原画展”首次于大陆、台湾、香港举办跨地联展,蓦然回首,人们发现,这个玻璃般脆弱的画家,原来曾与自己有过这样多的心灵交流。
自卑的小孩
许多没读过几米的书的人们知道几米,是因为10年前(2009年)的夏俊峰刺杀城管案。
夏俊峰13岁的儿子夏健强擅长画画,然而人们发现,不少画作的构图、立意,和几米的作品太像。风闻几米或要维权,夏健强的妈妈出来道歉。
“那就是一个小朋友喜欢一个画家的画,对着画出来而已,哪有那么严重,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啊。”几米说,“没事的。”
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几米或许想起了他自己的童年?
几米生于1958年,有一个很传统的中国名字:廖福彬。他儿时也喜欢画画,但并未获得父母的支持。
有太多的故事告诉人们,画家落魄,上吊自杀;音乐家落魄,孤病而终。当时的台湾社会认为,对孩子可以培养艺术气质,但不能培养创作能力,按部就班地念书是最好的选择。
几米的童年一直在自卑中度过,才艺上他比有条件接受专业训练的同龄人相差太远,他画画,只是一种心情的表达。初中的时候他参加绘画比赛,初一拿了第一名,初二第二名,初三第三名,然而这些成绩并未告诉他,这是他的天赋。
高中念的是文学班,美育课程都被挪去上英语、数学了,离画画更远。直到高三下学期,一个同学从医学转到文学,因为想考美术系。
几米这才知道,噢,原来台湾也有美术系。
想上美术系,须考国画、书法、水彩和素描,任何一科,几米都不曾专门学习过,然而他决定:我也要考美术系。
作决定时,离考试仅剩三四个月。父亲帮他找到一位老师帮忙补习素描,每天放学后,几米就买个馒头,坐很久的车去老师家。
考试那天,几米惊奇地发现,考试用的石膏像,就是自己天天在老师家对着画的那一尊,顿时下笔如有神。其它三科全是凭感觉去画,谈不上任何技法,国画科甚至是临进考场才借了一支毛笔。
成绩出来却让人大跌眼镜:国画、书法和水彩都挺好,素描最差。
“看啊,考试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情。”
于是,几米进了中国文化大学美术系,看上去,梦想破门了。然而他在大二时却决定放弃绘画,改读设计组。“我的程度太差了,和同学的落差非常非常大,他们都是从小立志搞创作,经过长期专业训练的,待在美术系,让我越来越自卑。”
而在设计组,他的成绩相当好。
广告人
几米毕业的时候,台湾的广告业正十分繁荣,他顺理成章进了广告行业,4年一跳槽,跳一次升一次职、涨一次薪,几米过上了普通的白领生活。
业余时间,他还是想画。
去日本出差,几米看到了许多用个性化的插画呈现的广告,他想学。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自己的画也能刊登出来让人看,即便是登在广告上。
“他抓了一把米,往桌子上一撒,拔拉几下,就跟我娓娓道来,说你不要再寄人篱下了,你1995年开始就会平步青云,独当一面,你会有一份喜欢的职业,而且可以做得很长久。”
没有人教,他就自己乱画,随时都拿着一支笔、一本本子,逮住任何看到的东西都画下来。
他用相当软绵的台湾腔说道:“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这反而变成了一件很棒的事情。”
画得多了,就希望被人看到、被人关注,于是就拿出来跟同事们分享。“这跟现在人们喜欢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的东西差不多,等着别人点‘赞。”
某天,有个同事说要把本子借走一个下午。这位同事悄悄将本子送到了《皇冠》杂志的美术主任手中,说,“我这位朋友很希望能在你们这里发表作品,能不能给他个机会?”
对方居然说:“好。”
从那以后,几米获得了给杂志、图书画插画的机会,在内容需要的地方,配上一些黑白的小图。他说:“那时候,很多我很景仰的作家,像刘墉、司马中原、小野的书,都让我配插画,所以我画得很认真,很虔诚。”
然而拿到稿费他就泄气了,像一个气球被快捷地用针戳破,“啵”的一声。一张图只有一两百元新台币,太低了。对于收入丰厚的广告业者,这样的润笔标准,不是可怜,而是可笑。
做画家,没活路,几米打消了做专职画家的念头。回首当时,几米看到的是自己内心的功利,梦想在现实生活面前,并不一定会被坚持。
不过,传媒业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会画画的年轻人,许多编辑找他配插图,机会越来越多,工作量也越来越大。
回忆起来,几米说这是“被迫在画”,在现实与梦想之间挣扎着画。这是一种功底的训练,创作初期,每个人都必须花很多时间不断去练习,这是无法挣脱的必经之路。这种“被迫”,事实上正在帮助几米完成积累过程,只是当时并不知晓。
在广告业工作12年后,几米人到中年,退意顿生。“感觉越做越吃力,而且你的心漂得越来越远。我是如此地痛恨拿着一份策划案,去和客户介绍广告策略、市场营销设想,通常情况下,我其实都是在撒谎。”
然而,毕竟已经12年,有自己的办公室,有自己的下属,还有一份不错的薪水,几米难以抉择。
那时候流行算命,同事说,“要不你也去算算?”
1993年的一个晚上,雨一直下。几米情绪沮丧地下班回家,不知不觉走进了台北松江路的行天宮。那里有一个画着高挑眉毛的术师,入夜了,依然有许多人排队等着算命。几米鬼使神差地到来,又鬼使神差地排到了队伍后面。
“他抓了一把米,往桌子上一撒,拔拉几下,就跟我娓娓道来,说你不要再寄人篱下了,你1995年开始就会平步青云,独当一面,你会有一份喜欢的职业,而且可以做得很长久。”
几米心花怒放,“天意啊”。
他想到了朱德庸,想到了自己渴望的画家生活。“难道我也可以像他那样,画很多专栏,有很多工作机会?”
于是,这一年领了年终奖,他怯懦又坚决地对老板说:老子要辞职了。
当年的辞职,看上去是一种梦想激励之下的慷慨选择,但回忆起来,几米说,其实自己是被淘汰的。
在职场,他没有企图心,他是如此地不敬业,他痛恨客户、讨厌下属、不喜欢老板,事实上这些因素决定了他注定被一个社会所需要的形式所淘汰。
“只是我自己以为自己在辞职。”
濒死者
1994年,这一年,几米什么也不干,每天等着1995年的到来。“到那时,我就不一样了,平步青云,独当一面……”
焉知,等来的是一阵剧痛。
1995年农历春节刚过去2周,他被早晨袭来的疼痛叫醒。大腿内侧,无法忍受的痛。两天后痛感消失,却不能走路了。看医生,有的说是坐骨神经痛,有的说是骨刺,莫衷一是。中医、西医、密医,3个月里能看的都看过,但剧痛依然周期性发作,2周正常,2周剧痛。
疼痛让这个瘦弱的中年人不成人形,朋友们在街上见到他,脸上的表情都是“惊骇”。
5月份的第一周,妻子扶着他去看一个没有牌照的中医,在路上几乎痛昏过去。他被送进了台北荣总医院,挂了急诊,被安排住进了血液科病房。
第二天一早,接受脊椎穿刺。
“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两个医生站在面前,脸色很不好。其中一人说,廖先生,我们在你骨髓里发现了很不好的东西。”
“我是得了癌症吗?”看多了琼瑶小说的几米,用主人公的语气问道。
对方点头。
血癌,几米崩溃了。
于是,本该“独当一面”的1995年,几米却大部分时间在化疗中度过,掉头发、浮肿、发高烧,还要不断注射各种抗生素。
他说,到后来,自己曾一度濒死。看到各种妖魔鬼怪,还看到了已经去世多年的偶像三毛—一个就在荣总医院自杀、有着让他一直回味的好听的声音的女作家。
他说,到后来,自己曾一度濒死。看到各种妖魔鬼怪,还看到了已经去世多年的偶像三毛—一个就在荣总医院自杀、有着让他一直回味的好听的声音的女作家。
他挣扎着,收拾东西,说,“我要离开这里。”他感觉再不离开,自己会死在医院。并没有强烈的求生意志,他只是不想死在这里。
他回家了。家里并不温暖,经历更为可怕。
“在医院有很多人照顾你,发烧了就有人来打针,痛了有人止痛,回到家里之后这一切都不可能。更可怕的是,我身上一毛钱都没有了。”在家里,他开始吃素,练气功,期盼最后一丝希望。
“我成为了一个在死亡阴影之下颤抖着的、苟活着的可怜人。”
重 生
几米的书,总把最简单的故事讲得很传奇,或许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本身也相信奇迹?
因为1996年,几米竟慢慢康复。
某天,来探望他的朋友问道:“要不你重新开始画画?”几米说:“好。”
再次拿起了纸笔。原来一天能画5张,现在一天只能画1张。效率低了,但至少他已重新开始去生活。
他不知道画得怎样,朋友看了说:“你现在画得好棒啊!”
几米想,怎么可能呢?一两年没有拿画笔了,都要生锈了。
或许这就叫蜕变。被死亡拥抱了1年多之后,几米的画变了。华丽的画面不见了,浓墨重彩的意象消失了。纸上,场景空旷,人物渺小,并都毫无表情,但其中蕴藏着一种哲学般的开阔度。
他从电脑里调出一张当时的画作。远处是灯火辉煌的城,近处是萧瑟枯黄的草,一条小路在草丛蜿蜒,一个没有勾勒面部的人提着一盏小灯,孤独地走在夜晚的小路上。那画里,有一种力量能够逼近生命本身。
几米重生了。
“你也出本书吧。”1997年,对这些画爱不释手的朋友建议说。
几米一直很钦佩那些能出书的作者,于是他说:“好。”
出书的创作者,大多会说,我是因为对理想的追寻,对创作的热爱,对表达的执着。而几米的理由却十分悲伤:“我快死了,出本书,将来我的女儿长大也能看到。”
半辈子都梦想出书,最后,竟是因为这种“天杀的理由”。
他回头去找以前的作品,以便结集。然而他发现,那些作品都已无法表达当下的心情。脆弱、敏感而无助,同时有太多话想说,对成年人说。他想,出一本给成年人看的图画书吧。这在当时的台湾,还没有人做过。
他重新画。1998年开始,每天非常安静地坐在窗前一笔一划地画。充满激情的投入,让对死亡的恐惧渐行渐远。
这一年书出来了,很多人看。这就是他的创作元年。
朋友问:“为什么你的书这么忧伤?”
几米说:“因为我确实很忧伤。”
天生的内向、害羞,加上后天的忧伤,几米很少远行。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但一直“固定上班”。家和工作室相距20分钟步行路程,他每天这样往复。他希望生活简单,不要有任何波动,也少点被打扰。他不习惯面对闪光灯,他会怯生生地从镜头下快步逃脱。
大陆有那么多喜欢他的读者,他却几乎不来。2013年他来过一次,还是因为作家杨照的动员。几米被说动,是因为杨照说,在大陆你能找到你喜欢的读者。
你喜欢,而不是喜欢你。于是他来了。
然而那忧伤,让几米看上去很脆弱。杨照说,“我是把他请动了,但对于怎么把他运过来一直很伤脑筋,担心‘一不小心他就碎了。”
微笑的鱼
几米的画面很美,文字也像诗一般。他力求让文字最直白、最简洁,写出来后反复诵读,寻找一种乐感。
然而忧伤一以贯之。
《森林里的秘密》,讲述一个从疾病中慢慢站起来的小女孩,跟着一只毛毛兔体验天马行空的美丽生活,然后戛然而止;《微笑的鱼》,说一个生活无趣的白领,每天经过一个水族箱,“看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寂寞”,其中有一条鱼总是对他微笑。


这些故事里,都浸染着几米的影子。
那个小女孩,抱着一只毛毛兔,像鸟儿一样站在瘦削的树枝顶端。那树枝明显承受不了她的重量,几米说,那就是生命的脆弱。
而那条微笑的鱼待在鱼缸里的感受,源自几米住在无菌病房时的经历。“每天躺在那里,有人来看你就拉开窗帘,隔着玻璃挥挥手,微笑一下。”他说,一个健康的世界和一个患病的空间,无法互相理解。
“几米”这个开合度很大的名字,后面可以跟着很多意象:寒潭?冰层?愁丝?白发?
然而这些都是潜意识的感受,并非主动的表达,几米说,“我画的时候也搞不清楚我想传达什么”。
“创作就是生活的反映,只是每个创作者用不同的方法去重新看待他的生活,然后呈现给读者。很多事情当下在做的时候并不明了怎么回事,不晓得读者是谁,有没有传播的对象,只是觉得自己有好多好多的故事要讲,所以就一张一张不停地画。”
这或许正是几米作品的动人之处。
那些画变成了书,全世界都在看,几米的忧伤就跟着飞到了每个人的心头。香港作家马家辉只比几米小5岁,他也说,自己是“看着几米的书长大”。
几米的書看似童真,却包含着一种长大的力量。
2008年,《微笑的鱼》被改编成一部没有对白只有音乐的9分钟动画片,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评审团大奖。几米认为技术上没有可观之处,但全场2000多个小朋友,给了他最热烈的掌声。
《森林里的秘密》,毛毛兔给了许多人说不出的温暖,但故事结束得太快,读者总在问,后来毛毛兔怎么样了?小女孩怎么样了?几米想,是不是应该给毛毛兔一个续集,于是他在2003年画出了《谢谢你毛毛兔,这个下午真好玩》,那时非典蔓延,几米就以瘟疫为背景,塑造了一个空城。城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和一只老去的毛毛兔,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老太婆就是原来的小女孩。
看完,人们更难过了,又再问,毛毛兔还会回来吗?读者总希望看到毛毛兔有一个美丽的结局,但几米说,不会回来了。
尽管如此,几米给人更多的仍然是温暖。“几米”这个开合度很大的名字,本身就像作品一样总是戛然而止,后面可以跟着很多意象:寒潭?冰层?愁丝?白发?
而读者会说,是“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