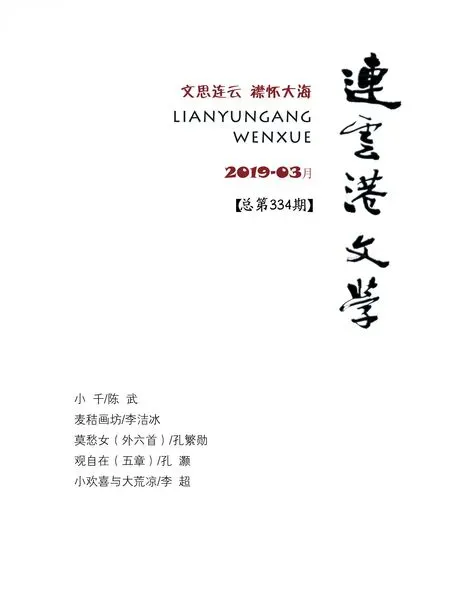麦秸画坊
李洁冰
一
陈士铎昨晚在青浦人家饭馆的酒桌上,凭空听到屋顶上劈下一个闷雷,手中的酒盏下意识地撩翻在地上。随着碎玻璃碴的爆裂声,耳朵亦嗡嗡哄哄地唱起柳子腔,呛踩呛,呛踩踩……单等着时来运转,脱蓝衫换上大红,可调子却是不着四六的,锣鼓点子、弦子全然不在板眼上。山神爷,这铁树开花驴长角了,自己怎么就主事了?陈士铎嘟囔着,立时头懵,眼晕,两股筛糠也似,只是抖个不住。特别是堂侄大齐伸出的那两根指头,更让他隐约生出某种不祥的感觉。“前头带走俩,周边都在讲,雁窝村里无好人,切!哪的话,俺堂叔就是。这不没多久,乡里就在酒桌上发话了……若论服众,除却陈士铎,再无有了。”堂侄还讲了许多。眼下头等大事,是搬家。区里已刷了黑漆的木头牌,候着带翻兜的铲车三日后开进来,村西打麦场还有画坊那片地,都得铲的铲,牵的牵,捋净弄光。
陈士铎看着,听着,口内像含了棵青杏,酸水从舌根底下滋滋缕缕冒了出来。由不得上下牙辗磨着,眼前浮起十几个麦秸垛。那是收割后堆在打麦场上的,傍晚看上去黑黢黢的,像塬间拢起的坟包。往年每抵此时,沟垅里腾起的雾霾就像飞起落下的乌鸦翅膀,抖开了,又阖上了,直遮得日头也不见,云也不见。高速路边铁丝网罩着的柳树,都被烧秸秆的烤焦了,棵棵顶着黄盖头。十二道金牌亦唬不住的。入秋时,上头下了死命令,组了侦缉队,但凡瞅着冒烟的,将管事的一撸到底。那日,陈士铎正赶着牛在水库边的稻茬地上打盹,忽被拽了去,膀子稀里糊涂套上了袖箍,让跟几个老嫚子去沟垅里守着。说壮劳力外出打工了,能喘气的都得顶上。陈士铎嗜赌,口讷,半生没吐过一句囫囵话。早年跟着柳琴班子跑坡,单等着人家唱到紧要处,咣地抹下锣子,算是糊口的生计。浮生闲度,转眼逾六旬了,老伴过世早,领养的闺女又远嫁黑泥湖。平日里,一人一牛一蓑衣,在水库边上逛个东南撂晌,只将柳子腔作了由头。不妨竟被抓了差,自是心中暗暗叫苦。戴了几日袖箍,终以哮喘病发作辞了。
摁倒葫芦瓢又起,越想修仙,越给个笼头罩着。堂侄话音才落地,这边厢脑袋嗡地大了。
喝着,聊着,陈士铎耳朵里的锣鼓家伙一阵阵敲得紧,尽管不在节奏上,左右仍是不歇。好歹趁着锣声换点,嘴巴里才嗫喏着,挤了句,没人上门说叨。堂侄诡异地笑笑,委任状?快了,等开过会……你侄就是村主任的侄子。言毕,又端着酒盏灌上了,好赖有了带火亮的叔,喝酒不用愁了。陈士铎没接话,半晌,又咕哝仨字,搬哪去……上游的造纸厂,不是也迁啦?对面吐瓜子壳似的,蹦出一句粗话,两手撸,两手都得硬。
半生在戏班子里抹锣子,陈士铎肚子里多的是伦理纲常。且看人家《丝鸾记》里的候美蓉跟龙官宝谈情,公子说话切留意,如若叫外人听了去,羞煞人呀咿嗯哎~最看不惯今天的年轻人,头发染得像鸭屁股,整天将鸡巴毛子挂在嘴上。揣着无奈,听得泼烦,只想草草终了饭局,躲个耳根子清净。大齐却没眼色,又聒噪上了,叔,人家都说村主任好,村村都有丈母娘。正抱着筒子骨啃得起劲,忽觉脑门上钻心的疼,原来被兜头摔了筷子。睡个鬼,堂叔呛了句,圣人……蛋哪个,滚家待着去。
没说嘛,是让您老先打场子,倘扶不上墙……大齐揉着脑壳,又抛出一句不着四六的话,三天后另派人。
二
苗翠岫的麦秸画坊,就在村西头的菜地里,距桐三高速不远,说是画坊,实则是挨着打麦场的两间半草屋。陈士铎过去的时候,苗翠岫正跟几个女人忙着给泡好的麦秸上色。陈士铎看到修剪过的麦秸都浸在盆子里,旁边有几位姑娘拿着篾刀灵活地给麦秸开片。靠屋子的北山墙上,撂着大大小小的画框。其中有两幅只做到半拉,靠在墙边上。上面写着《春朝鸣喜》,是两只喜鹊,蹲在树枝上剔毛。其中一幅嘴巴上的颜色还没涂好。有位小媳妇很细心地用篾刀夹起一片麦秸膜,像剔眉毛那样,一点点粘到上面。喜鹊的神气就出来了,再粘一下,陈士铎耳朵边咕噜噜的,好像听到鸟鸣声。又看一幅《猫戏蝶》,那猫的爪子半扣着,一只蝴蝶在鼻子那里翻上织下,眼瞅就要从画框里飞出去。再看那虎、那鹤,那花、那叶,一毛一翎,无不鲜灵活闪的。陈士铎拈起一幅,腆着面皮说,屋里的,俺那幅……弄好没?苗翠岫撩了下眼皮,等着八抬大轿来请。
眼前的这个婆娘,满头的小碎卷堆在脑袋上,通身缠红裹绿,大调门,见人笑吟吟的,体态像极后河里凫水的母鸭。早年间跑坡,陈士铎抹锣子,苗翠岫扮女角,人称“水上漂”。唱蓝瑞莲打水,七劝,双生赶船,至小散板,急急风,那锣声裹着小碎步跑圆场,直筛得人耳鸣,眼晕。打了个鬏髻朝南海,鱼鳞辫子脑后缠,八幅子罗裙腰中系,只盖着丁丁香香小金莲。整晚上,陈士铎瞄着那场子上的绣球鞋,罗裙一绽点点红,心里就怦怦跳得紧。只恨自家是一抹锣的,左右搭讪不上,空留下半生的失落。后来,柳子戏没人看了,苗翠岫的老情人也下海的下海,捞金的捞金,作鸟兽散了。无奈废了身段和唱功,办起了麦秸画坊,照例忙得风车般乱转。
陈士铎却从此走动得勤,跟得紧。平素里有事没事,总是哼着柳子腔过来凑几句,屋檐高,屋檐低,屋檐底下两只鸡。苗翠岫忙得不耐烦,就拿话掖他,或打打趣。陈士铎不以为意,自封了新晋的老相好。认准了家鸡打鸣不入耳,野鸡打鸣唱小曲,听着那骂声,如闻得满耳朵百鸟朝凤,心中自是别样的舒坦。
今天不同了,寻话的人,揣着很重的心事。
陈士铎看了看远处,高速路豁口的地方,又竖起几簇钢筋,新堆起的土像被刀劈过豆腐,四正四方地堆着。平时那个柔耐耐,水灵灵,嘎生生的声音,今天不知为什么,句句都是催命的锣。堂侄说了,只有三天时间。这三日,自己脱蓝衫换大红,总得办成点事体,让老相好高看自己一眼才是。
昨晚坊子四壁还空着,这太阳才升起来,就张榜了,说让三天内搬空,你看坛坛罐罐能撂哪?苗翠岫眼眶底下俩尬旯乌青着,正僵着指头鼓捣蝈蝈笼子。再说了,外贸那边催货,三日也得交割不是……雁窝村人都说村西那片叫“鬼画”了,不晓得这鬼早不画,晚不画,偏赶着农忙时凑热闹。总之新名词上墙,就得有大动静了。陈士铎揣着鬼胎,蹭到苗翠岫的耳朵边,小声说,不妨事,就算带个头……又待如何。苗翠岫愣了下,看着陈士铎的鼻眼都有些陌生,不明白发了甚呓症。却听得对方继续说,总得有人,先,先走。当即冷了脸,说陈结巴,你打梁山上才下来,蹬鼻子上脸的,招安了?便不再搭理,又紧着捣鼓帼帼笼子去了。陈士铎平素被挟枪带棒的奚落,只当是打情骂俏,话到狠处方显亲。哪晓得时下是军情急,天昏地暗,眼瞅着水漫金山。暗叫声婆娘,还当俺是那抹锣的?横耍些娘娘的脾气,到时候让你道万福,跪大堂,做香油葱花蛋的面叶都不灵了。却捱抑不住,将堂侄的话如此这般地讲了,口中竟奇迹般的没拌蒜。
苗翠岫放下手中的蝈蝈笼子,狐疑地盯着陈士铎的眉眼,定定地看了三回。然后张着满月脸,悠悠然,忽开口唱道,赵美蓉这边厢闪目观看,观一盏万岁灯一朝之主,有一些大臣灯列在两边……那一声转腔,逶迤连绵,直拽着陈士铎的头魂,袅袅荡荡,随着一溜云彩飞走了。陈士铎一拍腿,娘呼哉,多少年没听这口来!呶,那你去跟上头人说说,能否宽限几天?拿准了老倌子的心思,苗翠岫却不唱了。说无论如何,得让外贸的货脱了手,也就三两天的工夫,委实不济,一天也行呵,画坊招呼人再加下夜班……俺这就上你家,唱那个,陈士铎急问,唱甚来?苗翠岫纤纤巧巧,又抻出一句,唱堂会呀,咿呀啊哈哎~最后一个哎字,挤到鼻腔里,似捏非捏,只余一根细丝丝,眼见得抻扯着,游弋着不见了。这边厢,正愣怔着,又见那妙人儿翘起兰花指,左摘花,右理鬓,再系颔下龙凤扣的盘纽,随后冲自己嫣然一笑。
陈士铎的脑袋轰然大响,当年满场水上漂的小碎步又来了。八幅罗裙腰中系,只盖着丁丁香香小金莲……暗叫一声前世的冤家,就冲你这句话,也不枉从冬到夏,踏碎了画坊的门槛多少回,有也无有,死都值了。
三
往日里喧闹的乡间终于寂静下来。路上、田间沟垅到处都散落着麦秸屑子,空气里弥漫了粮食破壳后清新,又甜腻的味道。一种含混不明的声音因着某种惯性,仍在耳朵里似有似无,浮浮漾漾着。这样的季节,走在路上的农人,肩扛手拎,全身披挂,几乎没有闲着的。仿佛一夜之间,成片的金色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收割后排着麦捆子的褚色的农田,还有一个个巨大的麦秸垛。那是农人用木杈一下下垒起来的。远远看上去,衬着天宇,像一幅泼了油彩的画幅。
现在,这个叫陈士铎的男人,脚底发飘地在田埂上走着。立马要去办一件官差,平素想都不敢想的要紧事,去大白楼找有纱帽翅的说叨说叨。
那天从麦秸画坊出来,陈士铎闻着耳朵里的柳子腔愈来愈响,眼看着捏成了女花腔。尾音的尽处,却是大齐的念白,叔,甭稀泥巴糊不上墙……天爷,这屋芭上落下的,哪里是馅饼,分明就是一根系着活扣的绳子哇,鬼晓得怎么套到自己脖子上的。陈士铎三分受用,七分忐忑,拎着剩下的半瓶葫芦烧,出门后被风一击,脊梁立马冷飕飕的,醒了。这麦秸不让烧,只能垛着。如今垛着也不行了,让挪走。可麦秸不收了,青壮年打工去了,谁家动得半根指头,人家回来还不把他这口老棺材瓢子活扯了?话又说回来,雁窝村的天下咋就给了抹锣子呢,再不济,也不能让老相好苗翠岫看低了。
一宿辗转,锣声、鼓声交替响着,又敲了个失心疯。
天明的时候,陈士铎忽然想起要去找一个人。这人在村西高速路下面的瓜棚里住着,曾是甩着鼻涕穿开裆裤时的玩伴。从前闲溜达,总要到瓜棚里转转,说些个三皇五帝逗鸡走狗王小赶脚。近半年多,整日瞟着麦秸画坊使劲了,竟然疏落了走动。现在,陈士铎觉得自己发达了,请位军师琢磨定盘星,也在谱子上。
顶着乌青眼,去找瓜棚老伙计潘发讨主意。没承想,才进门就被骂了。抹锣子,你这是走路被大雁屎砸上,不是也是了。潘发摘来两个熟透的歪把子瓜,俗称骚罐插子,极甜。打头划开三角口,将籽掏了,留种。然后老哥俩一人一个,吃得汁水淋漓。村主任的远房外甥,可听说过?几年间包了鱼塘,方圆百里都拖着冰车去网鱼,白花花的鱼换成白花花的银子,转眼家里就起楼了。潘发吃得快,很快又裹了烟叶囱子,然后鼻孔里丝丝缠缠,又腾起了烟雾。前阵子,去喝满月酒,硬是让人分不清南北,就觉得高堂大户的,过去扛长活也没见过的阵式!你就猴子学样先拢着。熬过岁余,村西槐树林那边,能帮着弄块阖眼的地窝子,也不枉哥俩好过一回了。言毕,眵沫里挤下半颗浊泪。
陈士铎一言听罢,犹如醍醐灌顶!这自古官分七品,人归九流。我抹了半生锣子,没看过皇帝老儿下扬州,还没演过王朝马汉董超薛霸抡水火棍嘛,谁不晓得给个蜻蜓翅子就能抖,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事理?
夜阑,俩老倌子唠完了山海经,又喀苗翠岫。聊着聊着,潘发的老眼就萦萦有光了。随口哼了句,俺本是女娇娃,梳油头,带鲜花~然后问,到几分光了?陈士铎支吾道,还没底,只说家去……唱堂会了。潘发诡魅地笑了笑,不消说,是七分光了。哥俩遂揣摩着,需得先找个底细的人递话。一则宽限几天,让村里人,特别是苗翠岫那边把坛坛罐罐、针头线脑拾掇净了,交割了外贸的货再搬;二则讨了盖大印的委任状,这悬着的心方能放肚子里。
陈士铎一路思忖,额头上又禁不住碎汗涔涔。
这几日,村头那排白房子门前的路都跑得起狼烟了,可始终没找着人。几间屋子的门户闭得蹊跷,似乎从来就没敲开过。本想找大齐盘个底细,但那天在青浦饭馆喝了酒,堂侄又外出打工了,听说是去了新加坡。村里搬迁的事,问谁都成了掩口的葫芦。眼看着墙上的告示摞到了第五张,陈士铎吃不住劲,便试着去乡邻家里做说客。每次都是赚顿奚落,几乎被轰了出来。只好又找人探究竟。可一趟一趟,都白磨了脚指头。陈士铎就奇怪了,房子还是那排房子,风景还是那个风景,往年朝日里觥筹交错,推麻将的声音能传出几十里开外,连狗都偱着上风头打喷嚏。怎么眼下这么大操心的事,反倒见不着公家人了?哼柳子腔看夕阳的日子横竖是无有了,沟垅里每晚仍在打游击。天气也跟着凑热闹,喇叭头子里说了,近些日子还要刮台风。越拖,心里的锣鼓点子敲得越凌乱,有几段,分明是找不着板眼了。
苗翠岫也是凑热闹,次日主动上了门。云鬓散乱,花容失色,水上漂的步点也踉跄了。说陈锣子,有批货路上淋了雨,脱色了,外贸上让重换。眼下连老嫚子都上了……倘迟了单,画坊卖了都不够赔钱的。搬迁的事得顶着,到时别说唱堂会,过了这坎,就是拜花堂也成来!看着老相好婆娑着泪眼,身上的裤子满是皱迹,分明是几日未换了。唉,想当年,穿罗裙,袖带飘飘,红绫汗巾扎在腰……眼前立马浮上了画坊的蝈蝈笼子,柳笛哨儿,猫戏蝶图,耳朵里呛才呛又起了音,一桩桩,一件件,桩桩件件风雨满城……不知俺这里,也是熬夜三更。
当晚,陈士铎急火攻心,嘴巴上蹿起了燎浆泡。
雁窝村的那两层小楼,依旧在村前矗立着。白瓷砖贴墙,梳璃瓦的滴水檐,像一块橡皮膏药贴在村庄的肋巴撑上。远远看过去,黑漆的门户,旁边有俩石狮子蹲踞着,俱各张了嘴巴,风动时,有石珠子在口中滚来滚去。陈士铎早年串四乡,惯就了一副跑江湖的脾气。也曾拳打三皇脚踢五帝,说话嘴里没个把门的,见了村干部自是不放在眼里。吃过几次亏后,自感不是对手,就知趣地躲着走了。这多半生,跟牛说的话比跟人的多,压根不知官家大门朝哪开。无奈,眼下是乌鸦叫枝声声催,也只好梗着脖颈闯堂了。门,仍旧是阖着的,院内似有牲灵气咻咻的鼻息,压抑着,正欲嘶吼出来。陈士铎咽了口唾沫,再度壮着胆子走过去,拽着上面的铜环啪啪拍了半晌,少顷,终于听到里面风吹落叶,有动静传了出来。心下立马跳得急。就听咿哑一响,里面探出半个脑袋。
张眼看时,却是冬瓜嬾的面,细胡茬的唇。开口问,找哪位?天爷,总算有人理会了。陈士铎朝后挪了一下,讷讷地说,土地爷二……槐侄。亦不知言语上岔了辈分。对方愣怔着,一副懵懂的模样,明眼看上去是新来的。大名呢?后生操着外地口音问。顺字辈,叫那个,顺生吧?陈士铎像问别人,又像是在问自己。忽想起人已被带走了,忙改口道,副的,找唱副角的。都忙去了,有事两天后来。后生表情很活泛,很标准,却又例行公事。这边意欲再问,就听哐的一响,门又掩上了。陈士铎揣着百样的心事,还未升堂,又吃了一碗闭门羹。从门缝里分明瞅见院笼子里黑乎乎的,有东西貌似要蹿出来,只当是狼狗。自是十分的窝火,就想这提笼养畜的,哪里还是土地爷,倒惯成八王爷了,怪不得连着铐了俩。再下了死力敲,门复开了。大白天闭着门户,连着几日不接见,这边求升堂找不到擂鼓的。都去了哪!忙大事体了?
对方笑眯眯的,从墙上取下酱皮壳的簿子,张口念道:钱主任,陪领导去库区小水利验收了,金会计跟妇联的去白坎头慰问,吴助理上培训班,村副主任连夜赶到乡里开规划会……陈士铎听个仔细,串了几个小名对大号,俱各不认得,就泄了气。问及鬼画弧的事,新来的后生摇了摇头;再问委任状,对方突然像金鱼喝水似的,嘬着嘴巴,吐出一串无形的气泡。随后噤了口,目光里飘过一丝揶揄。
陈士铎看不懂那眼神,遂在门槛上坐下来。任后生拽也罢,劝也罢,硬是长坐不起。保不准这雁窝村叫鬼划符了,大小二鬼就都忙得转尬旯?左找不见,右找也不见,整日颠着屁股冒烟开大头会,可这麦垛,这画坊,这堆喘气的,三天就能弄清爽了?吃喝撒拉驴喊马嘶的,哪样不得人操持。这边厢一天不搬,叫你神气去。找不到和尚还找不到庙,罢罢罢,跟小孽障们省了口舌,直奔大白楼去了。
四
秋天的月亮挂在槐树梢上,就像柳子腔里的铜锣,黄澄澄的,镶着朦胧的金边。再远些,是一个更大的晕圈,在云彩里环衬着,若隐若现。偶尔有风掠过的时候,细细碎碎的动静伴着远处的鸡鸣、狗吠就又起了。
麦秸画坊里的灯火依旧亮着。退回来的货堆放在地上,一箱箱贴好的封条又扯开了。姑娘和小媳妇用忙完收割的手,一根根地拆着编织好的画板。只一下,喜鹊的嘴巴就掉了,再一下,梅花瓣就散了,纷纷扬扬地落下来。画坊里堆红砌绿,到处乱糟糟的。搁不下,只好拖到院子里放着,盖上了防雨布。有位女子眼见得自己熬夜编的双猫戏牡丹一瞬间被拆,指爪凌落,梗折花残,柳笛哨子也不发音了,心疼地落了泪。眼下,所有的画幅都得重新打理,能用的补色,不能用的,就作了烧灶锅的柴草。需得重选上好的麦秸,再开片,浸泡,染色,一切从头另来。苗翠岫柳子腔也不哼了,满月面上净是汗渍。两抹在鼻子上,半抹在下颔上。酷似憨闺女见婆婆里的傻妹子,总归顾不上头面了。正围着一堆残花败柳紧忙活,陈士铎来了。大踏步,急急风,满场子追着苗翠岫要说话。后者却风车般乱转,拆箱,搭箱,装箱,横竖只是不搭理。一屋子的人都揣着明白,看得清爽,抹锣的追着水上漂,那腿脚,那身段,何以能搭到拍子上?空落得一干不买票的戏迷饱了眼福。
陈士铎左转转,右转转,也是急了,脚一跺,开口唱道,万般处到无可奈,俺到北国去搬救兵。苗翠岫头也不抬,肿着眼泡问,搬来了?木牛流马还是七星阵?陈士铎跺了跺脚,接着唱,摘个苕瓜当大炮,拿根蒜薹当火绳……这回轮到苗翠岫急了,抹锣子,别学猪哼哼了,到底宽了几天也无有?陈士铎强扮了欢颜,说接见了,两拨。苗翠岫眼里倏地放出光来,谈拢了?陈士铎说,快了,说是明早回话!手脚却不听使唤,搔了搔脑袋,两手抱着膝盖蹲下了。翠岫不易察觉地叹了声,唉,看来是没戏了。又仿佛,要往地上蹲的那人胸口再扎一刀,幽幽捏了一句,满腹愁肠我难入眠……士铎呀,枉费了~俺翠岫一片真心。
陈士铎脸上挂不住,想接口,肚子里的唱谱子却一句也想不起来了。只好没趣地站起身来,像喝醉了酒似的,歪着身子朝门外蹩去。深一脚,浅一脚,既无章法,亦无路数。从背影看上去,完全不像在柳子戏班厮混了大半生的戏痴子。边走,边骂。骂完了自己,再骂苗翠岫。走着,咒着,脑袋渐渐有些疼,末了訇地一炸,像是要裂开来,恍惚着,一阵锣声又起了,敲完了小散板,再敲急急风。直敲得马蹄声碎,喇叭声咽。只剩一缕头魂牵着,悠悠荡荡,直冲着一干戴纱帽翅的驻地,一径去了。
青浦镇的大白楼自打落成,就成了当地的谈资。一个尖椎似的圆顶,直戳到漫天云里,主楼却似一把扇面,弯曲着打开来。有说像白宫的,有说像冬宫的,有说像扑克牌的,横竖是四六不搭。最出奇的是九十九级台阶,一级比一级陡,有说一百二十级的。总归给人的感觉,是进去办点事,难了。
现在,老鳏夫陈士铎正吃力地,一蹬一蹬地朝上爬着。过午的阳光,毒辣辣地挂在天上。他的神色看上去有点犹豫。脚下已登过三十多级了,抬头朝上看看,似乎仍旧无尽头。这时候,陈士铎就有一种感觉,觉得正站在一把倒立的梯子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只有云彩在身边浮浮游游,两腿忍不住有些打战,汗又禁不住淌下来。唉,这哪里是主事的料,分明是《报花》里的孙起高哇,火烤胸前暖,风吹着背后寒……张口告艰难……一个难字,陈士铎见左右无人,索性在腔子里吼了个痛快。直吼得酣畅畅,淋漓漓,到了后来,亦不知是吆牛的号子,还是拉魂的柳子腔了。这办桩官差,咋像是去登天!何妨给俺一把槌子一面鼓,左右擂将起来,升堂……玉皇大帝,土地奶奶。嘴巴里又咕哝着,不断给自己壮着胆。至半途,已是豪壮全无了。恐惧却像一张大网,铺着天,盖着地捂了下来,仿佛一念之悬,随时软了腿脚,像一只蚂蚁似的被风掠了去,摔个七荤八素。脚底下,已数到七七四十九级,再退回去,总归无任何可能了。
无奈,脑子里只好再琢磨些平时不敢想的美事乃至腌臜之念,以便分心壮胆。正编排着,苗翠岫就钻到怀里来了,自己亦变成了《罗鞋记》里的读书公,灯光下,念五经,念罢上孟念下孟……又见那水上漂苗翠岫,甩着一对长长的水袖,水桶腰变成一掐掐,扭捏着,开口唱道,织金裤褪扎一对,凤头的花鞋一小拃……随后,是一段叶里藏花,有音无字,夹嗔带韵,再跟一曲《大书房》,刘大仙窗棂外独立站,舍秋波,瞪杏眼,呆呆看你,读死书一眼不看俺,你那里不开门等到多咱……要的就是末了这句!这等了半辈,守了余生,苗翠岫总算人老珠黄了,水上漂不复当年了。可只有俺抹锣的知道,半老的徐娘赛香菱,木桶身堪比小蛮腰。俺这就去,开门去来。
太阳依旧毒热地挂在天上。这种炽热,俗称秋狗子,打到身上搓几搓,就能褪掉半层皮。陈士铎歇了数回,抽了七八管自卷的旱烟叶。终于在日头偏西的时候,爬完九十九级台阶,最终来到了青浦镇的那座高居云端的大白楼。
现在,这个叫陈士铎的男人,身子晃了几晃,用手指头揉着被日光映得发花的眼睛,勉力站稳了。定睛一看,发现自己正立在两扇大玻璃门前,张着蛤蟆脸,探着蜈蚣腰,汗褟子像粘鱼皮似的缠在身上,一把芭蕉扇插在脖梗后,活脱脱的济癫样。还没回过神,一堆男女说笑着走过来,眼前的圆筒门一转,又一转,轻轻巧巧,将他们送了进去。旁边两位驴桩样的后生,啪地敬了礼。陈士铎踌躇着,朝后退了半步,将汗褟子从腰间解下,捋顺了,又重新套上。顾不得刺鼻的汗酸气直冲脑门,也朝着入口,迈着柳子腔的台步子,稳当当地走了过去。奇怪的是,近前时,玻璃筒子门竟纹丝没动,好像停下了。不惟停下,那两根拴驴桩,也像使了定身法。一动不动。陈士铎遍搜唱本,脑子里蹦出了王朝马汉。只见王朝把手一伸,口中吐出仨字,请留步!马汉挤出俩字,证件。
陈士铎脑袋里锣声一响!自盘古开天,没听说进大堂还要掏本本的,过去大官都是在自家炕头上盘着腿,喝着小米粥,就把事情谈了。遂上下胡乱摸了一回,只掏出两根自卷的烟叶囱子。它们难看地弯曲着,已被汗渍浸得皱巴巴的了。陈士铎张着手递过去,正欲再开口,旁边袅袅婷婷,走过来一位挂牌牌的女子。大爷,你是赶集走错了门,对吧?跟我来。陈士铎方寸已乱,一时全无了主意。看着那女子眉眼还算和善,才稍稍定下心来。遂跟她一路绕着,最后被引到大白楼旁边一排刷着绿漆的平房里。刚进去的时候,误以为到了骡马市。各路人等俱各排着长趟子,到处挤挤挨挨的,却又没见着牲灵。女子耐心极好地盘了情况,又让陈士铎签了字,画了押。然后说,很快就有答复,先吃饭。
那天中午,陈士铎吃了自入秋以来最开胃的一顿饭。酸菜熬白肉,尖椒爆蛋,炸馒头片,大米山芋粥,管够。
五
东方渐渐露出了鱼肚白。
阳光探上窗棂的时候上。陈士铎伸了个长长的懒腰,醒了。昨晚,他很踏实地睡了个足觉,又重温了当年柳子戏班的跑坡生涯。只可惜回得迟,要不苗翠岫那里,当晚就过去了。就这样,一夜锣声骤起,又歇了,起了,又歇了。翻来覆去,只是自家在床上穷折腾。咣才咣,小丁香,入怀来,摇摇摆摆女裙衩。如此生煎活熬,好不容易盼到了东方既白,这才爬起来,换了件压箱底的对襟绸褂,蹬上养女从外地专程捎来的瑞蚨祥庄的布鞋。然后梳头,抹脸,一身全新的行头,昂昂然,直奔着画坊去了。
正兴冲冲地走着。蓦地觉得脚底下有些不稳。低头细瞅,有几道很深的车辙,一路交错着,从雁窝村的街巷里划着道道,径直去了村外。陈士铎有点奇怪了,就觉得自己睡得够沉,怎么不晓得昨晚村里过车?从深沟的宽度,这车决然不是装麦子的手推车,或胶皮轱辘车。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走着,看着,不知怎么,忽然有一股子憋尿的感觉。随后走走,停停,疑疑惑惑,一路来到了打麦场。那里,十几个草垛依旧在天空底下堆着,静静的,没有任何变化。一颗尚未消遁的寒星,还影影绰绰在天边上挂着。但麦秸垛旁边,却赫然停着一排黑咕隆咚的大家伙。它们一律张着带锯齿的爪子,将手臂霸气地伸向了天空。陈士铎打个激灵,胸口蓦然作疼起来。却原来,翻兜车还是开进来了!正愣着,就听到一种平时走正步的乐曲,伴着尖厉的噪音在空中炸开来,有个女音在高声说话。大意是马上要开工啦,请村民给予全力配合,云云。微露的晨光中,有几个人拿着纸夹子,指点着,跟在那位拿喇叭的人身后嘁嘁嘈嘈地吆喝着,接下去,翻兜车的轮子真的转动起来,巨大的泥浆被齿轮裹挟着,溅得到处都是,而且越转越快,轰鸣着,随后朝麦秸画坊的方向开了过去。陈士铎大梦方醒!拼力喊了一声,不能呀……下意识地摇晃着身子,朝前方迎了上去。与此同时,他感到有个东西不经意地刮在腿肚子上,新穿的布鞋噌地飞出老远。旋即倒扣在泥浆里。耳畔有人在急吼吼地大喊,快赶开,什么乱人都能进工地?!
陈士铎歪在那里,就像一只深陷泥淖的蛤蟆,嘴巴一张一阖地吐着气,隐约间,似听到一阵锣声渐来渐近,节奏细密,急骤,几乎耗尽了敲锣人平生的力气。尾音歇处,有种奇怪的动静又起了,萧萧瑟瑟,内含金石之声,心下正疑惑着,忽闻訇然一声巨响,有股子大风突然呼啦啦刮了起来,裹着天,搅着地,宛若缠着黑烟的黄龙飞速旋转着,将一条尾巴甩打着,围着麦秸垛盘上了,越刮越猛,越旋越急,最后咣的一声,将整个草垛旋上了天空!满天的麦秸立刻像乌鸦一般飞翔起来!它们黑压压的,扑闪着翅膀,盘旋着,然后抬着麦秸画坊,朝着八里路以外的城区倏然飞去!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望着那些开过片的麦秸编成的鱼、蝴蝶、残花败柳飞着,飞着,又箭矢一般掉下了……不能呀!铲兜车仍旧蜗牛似的自顾自爬行着,巨大的泥块再度被掘起,又重重地砸到车兜里。在即将失去知觉的瞬间,陈士铎抱着脑袋遑急地一滚,便轱辘辘跌到路沟里去了。
八幅罗裙腰间扎,小金莲就在那裙边下,走一步温柔典雅,行二步人人可夸……苗翠岫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来。随着麦秸画一片片,一根根飘舞着,宛如天女散花,朝着天边越飞越远,直至伴着漫天的麦扬,被一阵飓风呜地裹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