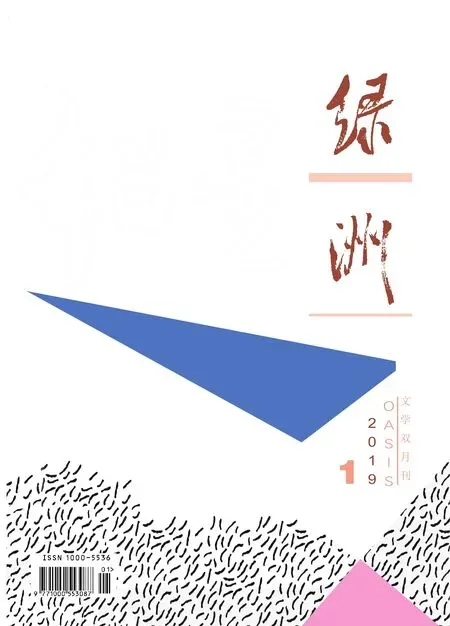我不是来参加葬礼的
方晓
下周马麦要去首尔做半年的交换生,他一个月前就告诉了马尚,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周五夜里,他问,钱准备好了吗,这次再浪费名额我就没机会了。马尚已拒绝过他两次;学校不会总把机会给不珍惜的人,下午,马麦的班主任在电话里说,有点类似最后通牒。他不反对马麦去,可是钱的问题无法解决。昨天,他找到厂里工头,刚露出想预支工资的意思,矮壮的工头用凶巴巴的一句话就打发了他:眼下经济形势这么糟,正打算裁员,你要想走人我倒能马上批准。他也找过偶有来往的几个人,结果在开口之前就知道了,他也不觉得别人有理由借给他两万块。他没打算告诉马麦这些,难题仍旧没能解决,马麦反而会觉得他在自我开脱。在相顾无言很久之后,他没料到马麦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这辈子我只求你这一件事了。而他才十一岁。
第二天清晨,马尚起床做好早饭,叫醒马麦。我要出趟远门,他说。他看见马麦眼里有光闪了一下又熄灭了。他等着马麦询问,但没有等到,他也就没有再说下去。何况他对此行能否成功一点也不确定。去客车站的路上,他想起昨夜模糊的梦境,在城市背后的原野上,他和林谷拉着马麦的手随风奔跑。他能感觉到李洁就站在角落里看着,在梦里,他也许想寻找她,但终究没有找到。
马尚还是第一次去往林谷的城市,浙江西南部一个叫云和的小县城。客车启动时,马尚又捏了捏口袋里的那张纸,上面是林谷写下的地址。林谷八年没出现了,他不知道如果她更换了地址该如何是好,但现在好像只剩下这一条路好走了。车窗外,春天的朝阳在城市楼宇间浮浮沉沉。十九年前,他在青蝉酒店里当传菜工,也是一个春天的上午,他注意到一个穿着火红风衣的女人,在透窗进来的阳光里,她微侧的脸看上去娇羞动人。她在接听电话。她突然向马尚招手让他过去,捂住话筒说,现在,我是在成都。她又告诉电话那边的人,如果非不信,我证明给你看。马尚帮她圆了谎,没有问为什么。几天后,马尚又对电话里的同一个男人说,这里是重庆。他感觉对方并不相信,但林谷说,无所谓,这只是一种需要。
客车在村庄小道上穿行,不时停上片刻。这让马尚担心今天无法回程,李洁去世以后,他还从未让马麦独自一人过夜。或许林谷留下地址时,就设想好了如果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门前,要如何向家人介绍他,他无须考虑。两次电话事件过去很久,他都快把她忘了,但夏天过半时,她又出现了。她送给他一个公文包:这是回报,请务必收下。他看不懂英文但知道价格不菲。不过我有个要求,她又说,我想去你常去的地方玩玩。他们去的地方不仅迎合了她的好奇,还赢得了她的惊叹。原始山洞,地下拳击场,废弃的村落,干枯的河床,这些地方他也是第一次去,但她的快乐证明他的猜想是正确的。看来你了解我,她兴奋地说。在青蝉酒店门口道别时,她指着不远处山边露出的屋尖——是栋别墅,打电话的人就住在那,她说,我父亲,他想让我继承他的事业,在全国开连锁酒店。那天夜里,林谷向前走去,又突然回过头来,在路灯下,她眼里有种梦幻般的亮彩,她说,我喜欢今天每一秒的感觉。此后十一年,马尚在附近干过四份工作,但一次也没去过那里。
十一点,客车到达云和县城,比预想要迟一个小时。“在南边,有点远,富人区。”出租车司机回答马尚的询问。马尚紧盯着马路边闪退的风物,尽力不去想将要到来的遭遇。玉兰花和红叶李正在盛开,垂柳倒映在污浊的河水上。他记得林谷说,玉兰花期很短,像古代青楼中的花魁,无子,很快殒败。
“来谈生意?”他听到司机在问。
“借钱,”他如实回答。
“那关系不一般。”
“我不知道,”他想了想,才说。
“我是说,这年头还愿意借钱的。”
“我们有几年没见了。”
“也不事先打个电话,让他来车站接你,那里住的都不止一辆车,还有人雇了专职司机。”
“没有。”马尚说,他感觉有种并不新鲜的挫败感在逼他坦白,“我没她的号码。”
司机从后视镜看了他一眼,咬住了即将出口的话。车停在一幢藏青色外墙的三层小楼前。没有任何标志证明林谷在这里生活;她曾说,二楼阳台上悬挂着紫色风铃,卧室窗帘是天蓝色的,在夜里看着它会想到宁静的海。大门紧闭——这也是一种不错的结局;他完成任务了,尽管回去无法向马麦交代。现在,他仍然没想好要从何说起,他更担心直到离开自己什么也没说。十八年前,是他亲手关闭了通向富足生活的罅口。她父亲应该知道一个传菜工的存在,他没有问过,在她与父亲的较量中,他有没有成为一个砝码,如果父亲逼迫她继承家族事业,她就义无反顾地嫁给一个传菜工。那年春天,她生日,他用一个月工资买了条丝巾送她。后来他认为,这是个提前来临的错误,而且是由他掀下爆破的按钮。庆祝我们相识一周年,两天后她回赠礼物时找了这样的理由,给他的感觉轻忽而牵强。是一只手表;三年前他用它抵偿了半年房租。他送她一只翡翠手镯,不过两千,然后他被带到杭州大厦,必须在一辆山地车和一架单反相机之间做出选择。他愤怒之下全要了。它们在去年被他扔进旧货市场,换来马麦渴望已久的电脑。她从来不会意识到这是对一个男人的伤害吗?他想问但没有问,因为他也明白她绝非故意。她本来就是那种临时得知新加坡有场演唱会,会连夜坐高价飞机去现场看演出的人。富足,原本是他在梦中都渴求的,但现实中真的来临时,他不知为何竟无法消除内心里恐惧的细密阴影。只要他在昂贵的价牌前表现出犹豫,她必然会说:不用担心钱的问题,我付。她付,这正是他担心的。我们不是一类人,有次他近乎赌气地说。她先是一脸愕然,然后也情绪失控了:我不理解更受不了你这渺小的无事生非的痛苦。他想过,但无法向自己求证,在与她形成亲密关系的原因中,富足究竟占有多大的比重。或许,人总是容易倾心于自己无法拥有的东西——与其说是他吸引了她,还不如说是贫穷,她希望过上一种与日日厌烦的富足完全不同的生活;也许不是这样。面对她,他开始感到怯懦,有时甚至不敢开口说话,最初和她在一起时的那种徐缓自如、快乐会随时自然来临的状态从他身体里慢慢消失了。他们的关系在他又一次断然拒绝礼物时戛然断裂,然后从此不再联系。并非因为感情不合而分手,马尚觉得这是命运给他留的唯一情面。
“你是来参加葬礼的吗?”背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马尚转过身,是个四十左右的女人,丰厚的嘴唇上涂着粉色口红,脸上是那种瞬间就可能转变为冷漠的肃穆神情,现在正被悲伤缓慢而艰难地覆盖。她也许只有三十来岁。
“请问,这家现在有人吗?”
她没有回答,示意马尚跟着自己往前走。她抱着一床毯子,边走边回头说:“他两天两夜没合眼了,殡仪馆那鬼地方连个铺盖都不提供。”
马尚不知该如何回应,只好努力摒除正从心里涌出来的某种寒意。
“我是他邻居。”女人又说,“你幸亏遇到我了,是从外地赶过来的吧?”
“我只是路过,我是林谷生意上的一个朋友,顺道来看她,”马尚希望对方听清了他说出的姓名,也许存在误会,他找错了地方。他感觉自己有些结巴,又补充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女人停下脚步,认真地看了他一眼,又点点头,但仍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指着左前方的一家酒店:“等会,就在这里答谢亲友。”
酒店紫黑色的玻璃墙显得雍容华贵,里面映出马尚的影子。头发纷乱,身形疲倦,还有生活馈赠给他的怯懦——也许在今天都可以被人当成悲伤。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像个生意人:“我是林谷的同学。这里挺高档。”
“附近最好的。他们家境这几年已经说不上好,他却非要选择这里,让人羡慕。呃,我不该这么说。”女人说。
马尚看见自己做了个手势,但一时并不明白究竟是想表达不介意,还是驱赶心头的惶惑。
“我是说他们感情一直不错。他投资亏了些钱,”她瞄过来的目光仿佛在判断马尚是不是个债主。他们已走到公交站,女人接着说,“我就从来没看见他们红过一次脸,据我所知其他人也没有看到。每个节日他都送花给她。”
车来了。她推搡他上车,似乎早已洞悉了他要逃走的念头:“有时候就是这么凑巧,可能注定你要来送她最后一程。底站就是殡仪馆。”然后,她终于沉默了。
马尚对殡仪馆并不陌生。他害怕它的任何气味。八年前,他送走李洁。路过营业部,他问:“我是不是应该买个花圈。”
“要我说,最好是这样。”女人立即回答。
“谁?”售货员手按在电脑键盘上问。要在花圈上祭奠谁。马尚突然发不出声音。林谷,女人说。他猜到了。似乎他早已知道,不然他不会出现在云和。他似乎对这个消息并不震惊。谁,他听见售货员又在问,这次是落款上的名字。他迟疑着,“李麦。”他说,“我,李麦。”
终于又见到她了。她躺在遗像后的灵床上。她在遗像里看着他。他也凝视着她,还是她,那略显苍老的脸庞上依然藏着一种娇羞。他奇怪自己在这一刻为何没有感到悲伤。他朝遗像三鞠躬,有几个早就等在一旁的人,也向他鞠躬致谢。他没有去看他们的脸,他们彼此没说一句话。他走到一个角落里,在长凳上坐下来,从这儿能瞥见她的身体,她应该了无生气了吧,他闭上眼睛,不敢去看。
十分钟过去了;或许已经过去一个小时。有人在摇晃他的胳膊。他抬起头,是那个女人,“走吧,悲伤是没用的。”她的声音里盈满安慰的气息,但在他听来又近乎命令,“现在我们去酒店。”他不想去,但也不想呆在这里,他顺从地起身。
他们到时很多人已经就座。似乎寥廓无边的酒店大厅里布设了七十多桌。他跟随女人在其间穿梭,她似乎在寻找两个紧挨的座位。他和很多人迎面而过,他担心突然遇见一个熟识的面孔,又立即觉得这种担心太过多余。他和林谷的所有交往都只属于一个隐秘、封闭、如今随着她的死亡而被埋葬了的世界。女人的心愿终于得到满足,拉着他坐下来,他不理解她为何要如此,但没有反对。他还没离开可能只是觉得这样做并不合适;自下出租车以来,他第一次想到了此行的目的。他意识到自己正在为徒劳无功而懊恼。
“林谷的同学。”他听见女人在说话。她带领他出现,似乎就有了介绍的责任。
他朝同桌的人点头致意。他依然不去看他们的脸,他不打算记住今天的任何场景和任何人,他已经暗自决定要把今天经历的所有细节统统忘记。他觉得女人看出来了他不是林谷的同学,但不明白她为何不揭穿却还要帮他隐瞒。
突然,所有声息都停止了。一个男人从门口慢慢走进来。
“喏,那就是他。”女人对马尚说。可能是因为他脸上迟钝的表情,她又说:“他就是唐森。”
“我知道。”他只是说。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唐森正向大厅中央搭建好的T台走去。尽管步伐缓慢而沉重,但马尚远在二十米开外也能感觉到他整个人都表现出那种极度悲伤之后的极度亢奋。然后唐森站在T台上开始说话。马尚要求自己不去听他在说什么。他厌恶唐森那贯穿在嘶哑声音里的夸张的沉痛。他接受不了这种表演,如果它是。唐森用双掌合十和谢谢大家结束了发言,竟然爆发了掌声。马尚有站起来呵斥什么的冲动,但按捺住了,他感觉到身边的女人正在观察他;她舀来一勺花生米放进他的碗里,细嚼慢咽有助于平复情绪,她说。人们都已经埋头吃起来,异乎寻常的肃穆与宁静。但忧伤的主题只维持了三分钟,然后就渐渐嘈杂了,很快——几近于狂欢。
“这只是一个形式。”女人对他说。“每个人都需要。不用过多久,所有人都会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包括你我,还有唐森。”
他不喜欢她话里的解释甚至劝慰的气息,似乎她已然了解一切。他盯着酒瓶。女人转动桌盘,拿过酒瓶,没有征得他的同意,给他倒满:“喝点吧,会好受一些。”
他确定了,是从已对她有所依赖感觉出来的:女人和李洁有些相像。他似乎一直想让李洁的形象在脑海中明朗起来,从昨晚的梦里开始,来的路上,凝视林谷的遗像时,他就尽力回想,现在终于做到了。那年,林谷突然不见了之后,他对身边的任何女人都再难有好感。有几个女人对他表现出善意。他在租房里每天看见一个女人抱着孩子上下楼梯,她应该就住在上面一层,他从未见过她丈夫,她给他送来烧好的菜。小卖部肥胖的女店主,有口白森森的牙齿,总朝他露出暧昧的笑容。隔壁花店的女服务员,右眼有残疾,但手很美,身上总带着清淡的香味,她送给他散落的花叶。送报纸的邮政快递员,一年四季都穿着一身藏青色的工装,有次给他带来一篮自家种的花生,她的腿脚看上去不太灵便。他想过和她们在一起,但又知道这只会永远停留在想象里。他从来没有碰过女人。一天,他站在街头橱窗前,中午他喝了点酒,他发现玻璃里的那个男人憔悴、瘦弱,每一寸肌肤都在往外倾泻着失魂落魄的挫败感。左边是一家洗头房。他在它门前徘徊。不要进去,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是青蝉南面傣妹火锅店的服务员,里面很脏,她说。他知道她叫李洁,偶尔,他会在火锅店里坐到打烊。你来店里吧,我十一点下班,她说,她的眼里流动着理解又同情的气息。凌晨,他们在火锅店相对而坐时,他觉得这种气息在她眼里有增无减。你中午喝酒了,她说,像在为一个孩子的错误寻找开脱的借口。他点点头;为什么要反对呢,如果她需要他承认。她的手伸过桌面,按压在他的手腕上,别去那种地方,她说,在他听来温慰的语气多于劝诫——只要一次,性情就会变化,你看待世界的眼光就不一样了。他倒觉得说成女人更合适,因为对这个世界他从来就没有好感过。
你们看上去真般配啊,他总听到别人这样评价。李洁大他四岁。他并不以结婚为目的和她交往,但半年后他们结了婚。门当户对,简单得有些潦草的婚礼上,证婚人的祝福里也有这句话。那么,这就是他选择与李洁在一起的理由了。因为知道他最初的秘密,李洁从来不真心信任他。在你心里我就是一个潜在的淫棍,有次李洁盘诘他的去向时他怒不可遏地说。他自我惩罚或者说释放内疚的方式,是剥夺了孤独生活养成的最后一份消遣,不再一个人沉默地喝上几杯。仿佛真如她说的,是酒让他在洗头房门前徘徊。而贫穷,婚后不仅没有改观,反而叠加上了李洁也从未逃脱的困窘,但毕竟,它也被李洁分担了一半。这个很多时刻表现得理性而克制的女人,精打细算地挡在贫穷面前,遮蔽了此前它时时刻刻投向他的阴影。然后,马麦猝不及防地来了。他还没准备好,还从未想象过一个父亲的角色,但孩子似乎是个水到渠成的东西。他没有任何反对的意思表露出来;不抗争,是面对这个糟糕世界最好的自我保护;夜里,他听着身边还谈不上多熟悉的女人的呼噜声时,就是这样想的。他偶尔会想起林谷,但次数越来越少,时间越来越短,她越来越像他眼前一道不可捉摸的阴翳。李洁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她的存在。
他离开青蝉酒店,去呆蝉咖啡吧当服务生,然后去凌睿酒店管理公司做仓库管理员,接着又在黄金影视公司干勤杂工,它们距离很近,在同一条街道上。十一年,他没有离开过那条街道。
“以前他是个小公务员。”马尚半天才反应过来女人是在向他介绍唐森。她凭什么认为他对唐森一点都不了解呢。唐森正在挨桌向客人敬酒,他神色依然亢奋,但脚步已有点虚浮。“后来下海了,”女人还在说着。
“呃。”马尚希望传达出了就此终结这个话题的意味。他不想了解唐森,一点也不想。他后悔没有带马麦来,满桌的菜至少有一半没动过,他们可以一起饱餐一顿,有些是马麦从未吃过的。他寻思等会让服务员打包合不合适;他决定就这么干。
“他开了家文化公司。”女人又说,“还没自我介绍,我是个图书管理员。所以我知道文化这东西可以装点门面,但当成生意做就不太靠谱了。”他不明白她为什么没有介绍姓名,又暗自庆幸她没有这样做。女人换上了一种强调又神秘的口吻,“对这个,林谷也是反对的。”
她是在暗示什么吗,林谷的死是一起悲剧?不仅关乎情感,还有更多恶劣的东西,却又并非疾病或者意外事件,而是和新闻里的那些犯罪有雷同之处?他觉得这一切都和自己无关,没必要深究。
“林谷的同学。”女人在向唐森介绍他。
他站起来,唐森向他伸出手。“谢谢你能来,”唐森说,声音干枯、颤抖,眼角还残留着泪痕。他们碰了杯,都喝干了。唐森又伸出双臂,马尚略微犹疑,然后也紧紧拥抱了他。
“等会你送他回家吧,再聊聊,多安慰他。”唐森走后,女人说。刚才,他恍惚能捕捉到唐森和女人之间有种只能意会的亲密,而且他们在遮掩这种感觉。
在酒店门口,他搀扶着摇摇欲倒的唐森,女人向他道别。他想说再见,但吞了回去。
“什么病?”马尚不想这样问,但还是说出了口。
窝在沙发里的唐森好像睡着了。室内光线幽暗,浅棕色的窗帘只拉开半扇,外面天已转阴。一如从屋外看来,目光所及的每一处都没有林谷曾经存在过的迹象,他无法判断那年她描述的家居环境是谎言或者只是想象,还是在后来的某一天被谁彻底清除了。
“心肌梗塞。医生是这么说的。”唐森缓慢睁开眼,没有掩饰语气中的厌烦。马尚说对不起,不该再问这个他几天来一直回答的问题。唐森摇摇头,目光移向窗外灰蒙蒙的楼房,春天的第一场雨已在下落,“但我想并不是因为这个。”
“真可惜,她还这么年轻。”马尚说。
“是啊。”
“她走得不痛苦吧。”
“差不多有一年半。”唐森说,“从她卧床开始,我就感觉有些对不住她了。”
然后沉默来临。很长时间过去,没有人说出一个字来解救眼下的困境。唐森突然起身,去了另外一个房间。似乎应该离开了,但马尚还是决定再等一会儿,马麦的问题依然没能解决。八年前一个春天的上午,就像在一条圆形跑道上背向而行的两个人势必再次遭遇,林谷出现在呆蝉咖啡吧。他一时无法分辨她的到来是计划还只是命运的巧合或者捉弄。你还好吧,她问。嗯,还好,你呢。我,我也不错。好像重新见面只为了看看对方是否还活着。然后,尴尬密布在他们之间的空气中,他想努力找随便一个话题来打破,但没有做到。很意外又见到你,他终于说出话来,李洁死了。她显然花了一点时间才明白他说的是谁。来,喊阿姨,他招呼在角落里独自玩耍的马麦。那年,马麦三岁。李洁半个月前迅速地死于一次怪异的流感。脏兮兮的马麦就像个流浪街头的孤儿——林谷震惊又同情的眼光透露了她的看法。一个女人用死亡给另一个女人腾出了位置,马尚不知为何会这样想,也许这是个全新的机会。但那天什么也没有发生。下午,他们带马麦去植物园,他们一左一右牵着马麦的手随风奔跑。在风中,他恍惚听到她问,当年我们做错了吗?只此一次。她好像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不仅有疑问,还有遗憾。她脸上已经初显岁月赋予的沧桑痕迹,嘴边露出的不再是明晃晃的俏皮笑容,而是不经意就敷上了一层酸楚,但神态又显得平和、安稳、泰然,仿佛什么都能接受,甚至相信了命运。她在生活中一定遭遇了什么,但他不想问。
你父亲……,他问。
在养老院,他坚持要去的,她打断他,语气快速而清淡,仿佛在讲一个不相干的人的故事,我们还是很难适应对方。他不愿和我生活在一起,他中风两次了。
他没有问她的婚姻情况。毕竟,她也没有主动说起。
身上只有这么多,她递给他钱时说。他觉得她的意思是下次会多带点——他希望是这样,会有下次,她再出现。他没有拒绝,接受得那般理所当然;她似乎为此有些吃惊。他还不知道一个无一技之长又卑怯到自闭的男人,带着一个幼儿该如何生活下去。他已经在承受,而且预感到只会越来越糟。他并不为此感激她,是她出现了又离开,才让他把生活过成了如今这个样子。他甚至觉得她递钱时小心的动作有些可笑;她早就应该知道,在不可改变的现实面前,没有什么是不会改变的。
后来她却再没有出现。这些年他要求自己不去想这是为什么。那时,疾病的阴霾还没有盘桓在她和唐森的生活里,所以那本不该成为最后一次诀别。现在她死了。如果李洁不是和他、如果林谷是和他生活在一起,她们或许都不会早亡吧。选择和这个人而不是和那个人一起生活,其实就是选择了另外一种命运,在今天,在这个陌生、阴冷、他早就可以离开却仍然被迫等待一个男人出现的房间里,他无法不这样想:甚至还选择了生和死。
唐森回来了,手中拿着两只酒杯和一瓶酒。马尚知道是米卡莎红酒杯和花庄葡萄酒。那年,她每次都带着它们进餐馆,如果不是米卡莎盛着花庄,她就宁可喝白开水。她经常说,来,马尚,陪我喝点。看来他们已深受彼此影响,有些甚至成了习惯。
唐森坐下来,斟上酒,把一只杯子推到他面前。
“她父亲生意败了。”唐森再次开口时声音低沉,但马尚不认为其间注满了忧伤。“我们,我和她从来都不属于一个阶层。已经固化,你应该知道的,两个阶层的人很难真正交流,情感并不能克服障碍,相反,我能这么说吗,情感在它面前表现得无比脆弱。”
马尚在心里为这个说法击节赞叹——仿佛唐森替代他生活在了某种宿命里,他想立即表达赞同,话到嘴边却又变成,“我不太能明白你的意思。”
“很多隔膜磨合不了,习惯难以容忍。”唐森说,然后笑起来。
马尚点点头。
唐森的目光在马尚的脸上逐渐聚焦,“她曾经和一个叫马尚的男人,对了,我还没有请教你的名字。”
林谷曾经告诉过他什么,如何向他形容那个叫马尚的男人;我是否像一根楔子嵌入了他们的心脏,阻断了情感血液的流动,我是否成为一次又一次家庭纷争的肇端或借口,让原本看上去静好的一切变成了怀疑、痛苦和夜不成眠。马尚想承认,那就是我,那样或许一种他眼下正急切需要的解脱感会立即到来。李麦,他说。
“抱歉,我对这个名字一点都不熟悉。”
“那就好。”
唐森或许更在乎她曾经的背叛——哪怕是在遭遇他之前,相比她已经到来的死亡。
“我们是同学,”马尚说,决定还是用这个词。“有几年没见了。我们毕业后就没有见过。”
“那么,你能跟我说说她吗?”唐森脸上布满了真诚的期待。
这让马尚对他有了一丝同情。旁人的叙述可以冲淡、弥补或修正记忆,她的或许已被遗忘的美好会重新呈现在他面前。他需要。
“她很好,人们都喜欢她。”马尚忽然哽咽住了,“对不起,我还是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呃,没关系。”唐森用理解的眼光看着他,仿佛该得到同情的是他。“你们以前关系很好?”
“一般,我是说,还行。毕业后我们再没见过。我走投无路了,被放高利贷的追杀,但我能盘活,如果……”
唐森伸手过来碰杯,止住了他。然后沉默再次降临,两个男人似乎都在倾听外面的雨声。室内光线更幽暗了。又过了一会儿,唐森说,“也许你愿意带走她的什么东西。请原谅我这么说,有些东西我不想保留。我简直认为是全部。”
“我不需要。”马尚听出自己的语气硬邦邦的,甚至带着宣誓的愤怒。“她所有的东西对你都是有意义的。你会害怕自己忘记她,只有它们才能让她存在得更久些。”几乎是为了阻止什么,他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
唐森脸上露出苦笑,几次欲言又止。
“我来,原本只是想向她借钱。”马尚说。
“我设想了很多种可能,”唐森没有掩饰自嘲又嘲弄的语气,“唯独没想到是这样。”
这样说并没什么,马尚安慰自己。怀念她,会成为以后生活中再也无法清除的情感,会成为我的生活本身。他不需要也不应该在这一刻坦白,哪怕痛苦的悸动已让他无法安坐。
唐森起身走向角落,在一堆杂物中翻捡着,然后又慢慢走回马尚身边,递过来一张银行卡片。“我还剩下一点钱,但不想借给你。这是她的,算是遗产,这意义不一样,我想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唐森说出密码,马尚跟着默念了一遍,确定那六个数字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马尚接过来,没有回答唐森的问题,甚至也没有说谢谢。这也没什么不可以,曾经的爱情——它的遗产,再次解救了当下的困窘。
“明天她下葬。如果可以,我想留你在这住一夜。”唐森说。
“不了。”马尚说。他和这个新丧妻子的男人,他们都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只能各自解决。事情不能再复杂下去了。而且,生活中的很多问题,它们的使命只是作为问题来到你的生命中,无法解决,也无须解决。他还记得,多年前,在突然消失的前一夜,林谷评价他们的关系时曾经这样说过。
“我还有个请求。对不起,能不能让你的司机送我去车站。”马尚声音里透着害怕遭到拒绝的焦灼和不安。我儿子一个人在家,必须连夜赶回去,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