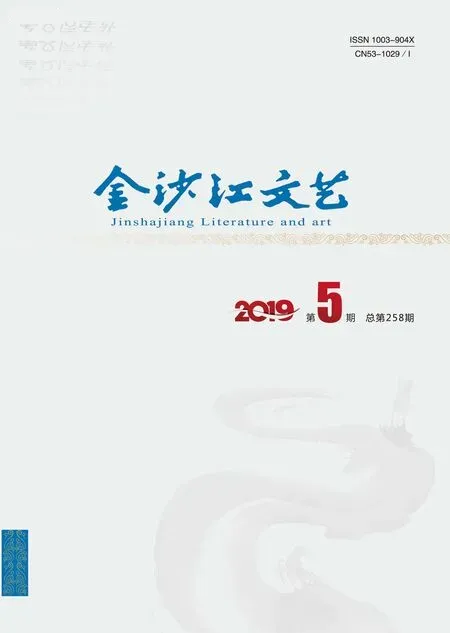感受生命律动 倾听大地心跳
——评米切若张长篇报告文学《大地根系》
◎纳张元
云南彝族作家米切若张既是一位诗人,著有诗集《痴情》,也是一位散文作家,著有散文集《情感高原》《三潭日月》《雾里阳光》,更是一位报告文学作家,著有长篇报告文学《攻坚》《大地根系》等。因此诗歌艺术的抒情性及语言的节奏感、跳跃性,散文艺术的灵活性及结构的开放性、自由性,细节刻画的传神性都在他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彰显。
米切若张善于把报告对象置于历史与现实、社会与文化、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坐标上,既有对新闻事件的纪实性报道,也有对重点工程、重大举措、重要突破的全景扫描。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性、多层面、多角度、历史感的书写和思考。作为一位少数民族作家,他常将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在共同的生活中建立起来的血浓于水的骨肉情感,以及无法割断的深情厚谊以叙议结合的方式书写出来,凸显了云南各民族之间的大爱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事实,谱写了各民族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的动人篇章。情理相融,感人至深,使报告文学写作具有强烈的时代、地域和人文色彩,打上了民族文化的深刻烙印。视角灵活多样,内容生动饱满,不尚温婉含蓄,唯求通达明快。其作品闪烁着历史理性的光芒,也洋溢着浓郁的人文关怀气息,使命意识、担当态度显得尤其突出。堪称大叙事、大写意与大抒情,有“大国气象”。
长篇报告文学《大地根系》是他对云南乃至中国 “三农问题”最真实与切近的见证。作家说: “祖国的根系在农村,我的个人根系,更在农村……回归大地的写作,我渴望,接通地气的大地根系,在泥土里生根,成活。”作家以敏锐的判断能力和捕捉能力,注重写实,以秉笔直书的史家之笔,对 “三农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 “事实演绎”。作家本着真切的人道主义同情,直面云南农村的 “物质贫困触目惊心,精神贫困瞩目揪心”,写出了 “山区、民族、宗教、贫困四位一体。”展现了这一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所蕴含的社会历史价值和作为报告文学创作题材的艺术价值。他关注弱势群体,揭露残酷现实,维护弱者权益,为我们徐徐展开了一幅由历史和现实、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组成的云南多民族聚居区农民生存真相的画卷。并深刻反思老、少、边、穷地区农村贫弱原因及未来发展方向,积极谋求农民的现实出路。既具有 “报告”的真实性、现实感,也具有 “文学”的吸引力和穿透力。发人所未见,写人所未及,在结构设置、人物刻画、细节描写、情景再现等方面所显示出来的语言功底、艺术视野和艺术表现力,均达到一定高度。
报告文学堪称最直率、最简洁、最本真的文学体式。真实性是其最基本的特性。它只能是历史真实、判断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报告文学不说真话,那将是死路一条。米切若张明确提出:“这是生活真实,任何削足适履的轻浮修饰,都不能解读它的严谨。”对于报告文学作家而言,说真话,说自己想说的话,做到真切、真实、真诚,是最起码的要求。面对这种非虚构、写实性文体,作家所 “报告”的内容必须真实可信、确凿无误,绝对不能虚构、编造和杜撰,不能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妄自揣度。
报告文学的创作常被认为是用脚走出来的,创作成本高、难度大。作家以置身其间的切身体验者身份,深入基层一线,实地考察,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心去感受。武定、会泽、插甸、禄劝、楚雄、牟定等地都留下了作家深深浅浅的脚印,积累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记录下一个个真实的案例。摆事实,讲道理,用数字来说话,用典型说话,用细节说话,迅速、及时地报告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关注百姓生活的喜与忧,聚焦社会发展的明与暗。既有感人的故事,也有丰富的细节。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严格遵循史实、现实、事实。以对历史性现场的触摸与近距离的摄照,观察、审视、记录了转型期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的大事件、小问题,努力探寻事物表象背后的真相、真理和规律,它所具有的历史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农民最中国”。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对 “三农”问题的关注与探讨,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广度还是深度,也无论影响还是地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形成了空前的创作热潮。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报告文学的再度繁荣与发展,而且对中国文坛和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千百年来,在传统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村落社会,人们聚族而居,安土重迁。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农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连系,胶著而不能移,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无论老一辈还是新一代农民,他们都对土地有一种难以割舍之爱和企图拥有更多土地的愿望。作家对故土有着一份深沉的爱,一份炽热的情。他深情宣告: “情之所倚,桑梓情深,讲究乡谊地缘的中华民族,出门在外,乡里乡亲血浓于水,最是他乡游子的温暖依靠。”作家怀抱着一种博大而深沉的家园之爱向外界,向世人昭示着责任心和使命感,豪情万丈地歌颂、吟咏脚下这片生我育我的神奇土地,以及千百年来扎根于这里的人们所创造的辉煌历史和伟大现实。
作家说: “每一个有天良的领导和作家,都是老百姓的贴心人。”透过文本,我们看到的是作家站在尊重农民、体恤农民的底层叙事立场,来关注农民的真实生存境况和情感诉求。没有居高临下的贵族式的悲天悯人,倒像是讲述自己父老兄弟的遭遇一样,在毫不雕饰的直白语言中流露出真诚的感受,为社会转型期农民的命运抒写出真正的心灵史。作家把我们带到一个个家庭、村庄,以及田间地头,让农民侃侃而谈,娓娓道出自己的辛酸、苦痛、劳作、无奈与挣扎。在客观的叙述当中,呈现一个个口述者的生活现场和精神世界,他们的希望和绝望,都一一晾晒在读者面前,构成了云南边地农民的立体群像。作家的叙述语言与农民的口语结合在一起,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读来感到亲切、自然。我们仿佛亲眼看到了这些生活在底层老百姓的真实生活以及他们的丰富的内心世界。这种平民色彩的个人化写作视角,在满含个性体验的同时,别开生面,并由此衍化出别具一格的新感知、新面貌。
文学的终极目标是要把写作回归到人物命运本身。作家善于选取最有代表性、典型性的题材内容,围绕人物形象展开。注意运用丰富生动的情节、细节来刻画人物,写活了“彝山袁隆平——超级水稻功臣李开斌”、 “刘爱明:实干出来的优秀工作队长”、 “豆玮:从城市法官转身为新农村建设工作队队长”等丰满、立体、富有个性的典型人物形象,提炼人物精神,展现人物个性,把个体人物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和一定的时间长度上进行考量、观照,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报告对象,赋予个别性的书写以普泛性的价值及意义。通过作家的思考、判断与爱憎,传递给读者真实的感动、感悟与感念,写出了一定的厚度、深度与力度。
报告文学被称为 “微观政治学”,也称为 “国家战略的文学”,它与现实政治形势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一种具有强烈政治意识的文体,报告文学写作必须与政治同构。报告文学作家不必是政治家,但必须具有敏锐的政治意识。《谋福云南》《会泽足迹》《楚雄散章》《禄劝情怀》等篇章正是以其敏锐的时代前瞻性和社会责任感,深刻反映社会焦点和事关国家生存发展命脉的重大课题,有效传达现实政治的诉求,体现报告文学可贵的社会担当与时代使命。作家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将多民族和谐共生关系、军民关系、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在云南这块红土地上演绎得如此真切、动人。他不满足于事实呈现和情景翻拍,为寻求事实真相、揭示真谛,深入现场,深度报道,深刻反思,自觉反映当下社会,刻画鲜活的人物,主动介入生活,关注大众生存与命运,审视文明的进程与缺失。对 “三农问题”这一“国家战略”进行综合性分析和锐意思考,并将精辟的见解贯穿于真实可靠的叙述之中。从内容到形式求新求变,力求书尽其形,穷尽其理,揭示了 “生活本身比文学更悲壮”的事实真相。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报告文学是非虚构的,现实的,批判的,同时也应该是文学的,审美的,创新的。报告文学家应具备记者的敏锐、思想家的深邃和文学家的创作技巧。单是依靠观察问题的敏锐和激情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与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相适应的 “思考力”和 “判断力”,善于从整体上把握社会生活的脉搏和发展的总体规律,并辅以艺术创作手法,唯此,作品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报告文学的写作不应仅仅立足于某个事件,而应立足于某种思想。这部作品还存在写作模式单调僵化,语言简单粗砺,有失精纯,塑造形象表象化,政论性、新闻性太强,文学性、艺术性不足等问题。如《引言:说不尽的农业中国和七彩云南》中写“俞正声的武定之行,低调而务实。”《第三章 先行者表率》中写 “令狐安书记在武定贫困山区出入频繁但行踪不定。”《第四章 会泽足迹》中写李纪恒省长在曲靖待补镇扶贫,《第五章 插甸经验 云南样板》中写丹增、刘维佳在武定县插甸乡扶贫……不一样的领导下基层,却是一样的写法。一种笔法一个腔调,一个角度一种语言,缺少变化。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多立足于正面宣传而缺乏有深度的独立思考与理性批判。缺乏鲜明的史诗意识与 “宏大叙事”,部分内容则重复、贫乏甚至空洞。有 “网”一样地铺排却缺乏牢实的 “结点”, “心似双丝网,却无千千结。”什么都想串联在自己的文章中,难免挂一漏万,散漫无章,出现了一些结构漏洞。
毫无疑问,《大地根系》是还原历史真实、揭示历史真相的主旋律书写,让我们感受到文字后面丰富而鲜活的灵魂,感动于他的真知灼见和赤子之心。体现了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求大同的道德判断、价值判断和情感判断。具有浓厚的平民意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性批判精神,写得厚重、神圣、庄严、大气。作家借用了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视角,运用口述实录、田野调查等方法,试图摆脱政治文学的某些俗套,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吟唱、讲述自己所熟知的民族、故乡和土地,增加了乡土色彩、田园情调和边地气息,使作品变得更加耐读,更有味道。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作品的学术含量和思想深度。对报告题材的深度开掘、报告对象的人文关怀、文体意识的自觉回归成为这部作品独特的审美诉求。
坚持意味着一切。米切若张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扎根大地根系,延伸心灵触角。使得报告文学作品接地气、显灵气、扬正气,既表现为深厚的民族性与本土性,也表现为鲜明的开放性与思辨性。每一步都如此坚毅、从容,其思想的穿透力、艺术的驾驭力和审美的表现力也必将越来越强劲、越来越娴熟、越来越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