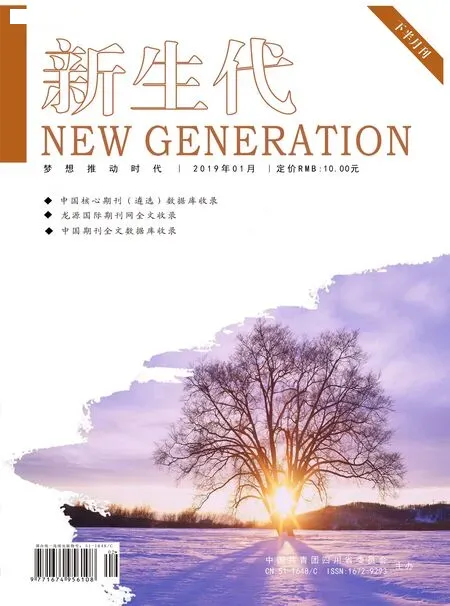文化实践者的多重逻辑
——以大理莲池会为例
张艳飞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081
大理洱海周边的村落中分布着众多以本主信仰为基础的老年妇女组织,除了莲池会还有诸如妈妈会、弥陀会、拜佛会等。这些组织在一村一本主的信仰体系下形成一村一会的组织结构,这种以村落为中心的信仰体系以及相应的组织结构在日常生活中虽然各自为政,但作为本主文化体系下的实践者或者说仪式组织,她们的共性远大于差异性,莲池会便是这类民间组织的典型。在白族村落当中,不同的村落自主成立各自的仪式团体,团体的成员构成以本主庙为中心,以地域单位为边界。作为民间信仰团体的莲池会,成员一般来自村落范围当中的老年妇女群体,团体规模与相应自然村落的大小成正比,规模较小的七八人成会,规模大的一会上百人。此外,在结构特征上,婆媳相传入会的情况让这一民间组织实现了非生育性的代际传承,使其成为一个有“历史”的地方文化活体。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莲池会的信仰体系在国家背景下,是一个大传统与小传统相互磨合的过程,而这一结果与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edfield·Robert)所认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二元对立的状态不同,它所反映的不是“小传统”被“大传统”取代的强权逻辑。对莲池会文化实践的历史主体性分析,是对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一分析框架的回应与反思,研究具有一定的学理意义。
莲池会以老年妇女为主体,在看似断裂的村落自治格局之外有一套统合的文化逻辑。首先,莲池会有一套自己的信仰体系,会内成员按班排位操持仪式,各村生活中的大小祭祀几乎都要仰仗莲池会的成员来操持。其次,念经祈福作为莲池会的重要集体仪式,每逢会期成员都要在本主庙一起举办诵经仪式,在一年当中,平均每月都有两个或以上的会期,除了不同神袛的诞辰日外,还与传统农业生产及节令有所叠合。总体而言,无论是在分布广度还是活动的频繁度上,莲池会与村落社会相得益彰,作为地方民族文化的实践者,它是研究洱海流域文化整体观难以逾越的鸿沟。
一、早期相关研究的梳理与讨论
在有关“白族学”的研究当中,对于莲池会的起源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它由“朵兮薄教”发展而来的。朵希薄教的性质是“幻想借助超自然能力对客体施加影响和控制,以达到现实目的”。莲池会的宗旨在于“行善、修行”,尽管二者都有祈福禳灾的功能,但各自使用的方式不同,前者更为主动,而莲池会则是通过诵经这一“善行”而获得福报,具有典型的佛教因果思想。此外,朵希薄教中的巫师之间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虽然新入会的莲池会成员存在拜师学经的现象,但经文知识对所有会员都是共享的。第三点不同的是,朵希薄教以鬼和本主为崇拜对象,但莲池会的信仰体系则超越鬼和本主而囊括本主外的一些佛、道神袛。
关于起源的第二种观点多根据王崧本《南诏野史》记载:“丁未太和元年,王(封祐)母出家,法名惠海(又云师摩矣)。太和二年,用银五千,铸佛一堂,废道教”,认为“师摩矣”是经母的白语称法,进而推测劝封祐的母亲是莲池会的“第一位有文字可寻的‘经母’”,这同时也间接阐明了莲池会的佛教源流。张宽寿和李东红也认为莲池会来源于佛教,不过是来源于佛教密宗的阿吒力教派,张宽寿从阿吒力教的节日与莲池会的会期作对比认为莲池会就是阿吒力教组织;李东红认为莲池会是大理地区阿吒力世家被统治阶级打击后流入民间形成的宗教团体之一。而从经文内容的角度,根据张明增整理的《白族民间祭祀经文钞》可知其中关于观音的经文占一半以上,莲池会的各种名称与佛教具有渊源关系,在实际调查中,莲池会成员也普遍认为自己信仰的是佛教。
第三种争论的焦点在于莲池会的形成时期,有的说法认为它开始于楚汉时期,有的认为它出现于南诏、大理国时期,有的推断它兴起于明清时期,也有观点认为它出现于民国时期,是近代佛教复兴的标志。鉴于对莲池会明确记载的历史文献的缺乏,关于莲池会的形成问题只能做一个可能性的推测。就今天普遍分布于洱海流域的莲池会来说,他与佛教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莲池会成员自称是信佛的人,会员以诵经为主要的修行渠道,每次开坛念经都有一个迎佛、送佛的过程,诵经中普遍使用的器物如小木鱼、念珠,分别在整体造型与数量上的尊崇都与佛教有一定的关联性;第二,在饮食结构上承认佛徒的饮食禁忌,个人也有一定的茹素规范;第三,每年的会期中,很大一部分与佛教的神袛直接相关,如二月十九观音会、四月初八太子会等;此外,对人类终极问题的解释上,相信存在佛教倡导的“西方极乐”。
综合以上的各种说法及调查材料,莲池会至今的佛教元素是显而易见的。具有佛教性的组织的产生与佛教的兴盛时期之间极可能有密切的关系。个人认为,从佛教在大理地区的发展史来看,莲池会的产生时间很可能在南诏大理国时期。
通过莲池会历史源流的讨论,我们看到社会与文化都不是静止不变的,莲池会作为一个佛教性组织产生之后,其延续和发展在社会发展的模式中继续发生变化,但在社会性的结构变迁之外,实践者的主体性仍然具有积极的一面。
二、主体性逻辑之文化的实践与传承
文化的实践与传承包括被动接受与主体创造两个方面,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传统与再造往往交织在一起,这种特征在莲池会的经文当中可见一斑。首先,现存莲池会的经文中包含有许多历史叙事和神话故事,如“把谁遇着老观音,手背石头房子大。背了石头走三村,把人来吓煞。处处立起观音塘,初一十五把家看。每日香火不见天,把观音报答。”这是对观音负石阻兵故事的描写;历史叙事的经文如“我是唐朝邓赕诏,丰咩就是我本名。吃水要吃白王水,立王立在德源城……邓赕诏六道神灵,西山皇帝万万岁”是对南诏国历史传说“火烧松明楼”的记述。此外,“我敬本主一盏灯,有常蜡烛亮真真。本主娘娘左边坐,本主太子右边生。我敬本主中间坐,做禄位高升”等经文对本主庙格局的描述构成了本主庙重修的依据。这类经文以集体记忆的方式呈现了地方社会、文化的历时性。其次,从形式上看,莲池会经文多为七言和五言的押韵句式,还有部分“三七一五”式的白族山花体民歌形式。关于山花体的形成,有的学者认为其始于唐王朝,有的认为源于洱海区域古老的民谣俚曲,是长期以来受到外来文化的渗透和影响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民歌体式。换句话说,山花体是实践者在外来文化基础上的一种主体性创造。再者,山花体出现的时间与儒学在云南的广泛传播及西南边疆纳入王朝统治的时间不谋而合,虽然山花体仅是作为一种宗教经文的文学表现形式,但却可从中看出中原文化及中央王朝对边疆的影响力。陈寅恪先生曾言,“世人或谓宗教与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参互合论,然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山花体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展现的是地方文化的发展,而作为莲池会文化实践的产物,却表现着中央与地方的互动。
此外,地方文化的实践与传承还表现在众多宗教仪式当中。莲池会是本主祭祀仪式的重要参与者,也是白族文化的传承者。不同的村落因为信奉的本主不同,所以大多数莲池会的本主会期存在时间差异。而与本主会期对应的“本主节”是村民在社会交往中宴请村外亲朋的高峰期,莲池会在地方性“全民参与”的本主会期中,通过各种仪式所传达的关于本主的系列文化,让年轻一代不断强化对本主的认知,实践了地方文化的代际传承。 在村落之外,像“绕三灵”这类的外出祭拜活动同时附和着民间艺术展演,莲池会在这个过程中既是参与者也是评判者,哪个地方的人跳得好、调子唱得好各自都有一个评判标准和口碑,正是在这样的宗教实践当中,白族歌舞和民间曲调以会期展演的方式得到了传承。
“民间宗教不是‘自然而然’的形成的,而是在国家力量的大力推进下形成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具有多元信仰元素的莲池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文化融合的结果。明王朝将洱海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统治后推行同化政策,致使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汉文化在洱海周边地区广为传播。莲池会接收儒家思想,并结合原本的佛、道、巫等宗教思想的源流,最终形成在外界看来多元的宗教信仰体系。但同时,就莲池会成员而言,她们并无意愿深究信仰体系内各种神灵到底属于学者所列的宗教派别中的哪一个,从主位的角度来讲,她们的信仰是一体的:以佛教元素为主,这是佛教在洱海流域兴盛的遗迹,辅以儒家伦理是中原文化和大一统的历史影响;而杂糅其中的道家、巫教等宗教元素更多的是对自身传统的创造性保留。不以类聚,是莲池会作为文化实践者的包容性发展观,而无法忽视的历史事实是儒学的扩张及中央与地方的文化交融。在历史的长河中动态的演绎着文化传承的戏码,这正是民间信仰作为主体性的逻辑。
三、文化实践与性别逻辑——白族社会的性别结社与莲池会的社会性别边界
社会性别是社会化过程中,社会对个人性别角色的期望,从一个人出生便已开始。在儒家思想主导下,“男女有别的界限,使中国传统的感情定向偏于向同性方面去发展。”在洱海地区,社会期望的性别角色与同性情感的培养通过“打老友”的习俗可见一斑。但“打老友”是基于两家人父母之间的友好关系,为了使两家人的关系更近一步,于是让各自的孩子结成老友,前提是互结老友的孩子性别相同。老友相互之间没有长幼尊卑的区别。同性子女结为老友表达了白族人家中“男女授受不亲”的儒家思想。家庭是孩子社会化的第一个场所,同性“打老友”同时体现了洱海地区来自家庭教育的社会性别分野 。对于成年人来说,除了各自的老友,还存在很多同性社群,如大理茈碧湖周边的“十兄弟、十姐妹”组织,但这样的组织只留存于洱海流域的部分地区。作为老年妇女组织的莲池会也是这种社会性别区隔的体现。按理说,同为老年宗教组织的洞经会与莲池会均以信仰作为入会的标志,没有明确规定说男女不可交错参加莲池会或洞经会。但同时,人们又都普遍认为洞经会是男性组织,而莲池会是女性组织。
透过莲池会在历史中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传统父权制在白族社会中一度成为主流,男尊女卑的思想在一些仪式场域中仍然存在,如具有神圣性的祭祀仪式中只采用公鸡作为牺牲;耍龙活动中,女性成员主要承担龙身部分的舞动或在一旁打跳,男性成员负责耍龙头或担任引导者的角色;洞经会与莲池会共用仪式场所时,通常洞经会占用寺庙的主殿,莲池会则使用偏殿或院落;丧葬仪式中棺木、守孝期长短等也存在男女性别差异。在整体的社会文化系统中,莲池会成员作为个人的性别边界是与生理性别对应的女性群体,但是作为信仰团体,莲池会的社会性别是介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可以说是一种无性别的状态。这主要表现在成员的入会资格上,首先,入会者必须是月经终止的中老年女性,这在生理上是作为女性标志的生育力量丧失的表现;其次,只有当子女均完成婚姻大事的妇女才会考虑加入莲池会,这在社会角色上是女性作为母亲抚育子女任务的终结。这种反结构的状态促成了莲池会作为仪式成员的非女性状态,它不在二元对立的性别结构中,是一种无性别、结构外的存在,这支撑了作为女性在与神沟通的过程中摆脱父权框架的束缚,同时在体制上保证了父系制度的权威。
作为当地最大的女性性别结社,莲池会在各自的村落内部构筑了一个女性的生活空间,老年妇女在家庭中失去劳力优势的时候使其得以转换角色,进入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空间,以另外的方式为家庭谋求福祉,并保证自身在家庭中的地位;作为一个独立的信仰团体,它在宗教仪式方面不依附于以男性为主体的洞经会,管理上独立于洞经会与老年协会。虽然它不具备“法律合法性”,但却通过作为传统的仪式操作者身份获得了“社会合法性”。通过莲池会组织,妇女可以参与更多的社会活动,并在村落内部结成一个关系友好的女性社交网络,仪式外的莲池会在一定意义上打破了传统文化中父权制的垄断地位。
在结构与反结构之间,莲池会构筑了一条不同的社会性别边界。这是莲池会作为性别组织不同于白族社会中其它性别结社的地方即作为宗教实践者的性别逻辑。
四、文化实践与空间逻辑——作为组织的地域边界
在大理地区,莲池会的信仰体系具有两个面向,即本主信仰与非本主信仰。本主信仰相对来说是一种边界性较强的信仰系统,但这种边界不是对外来宗教或其他神袛的排斥,本主信仰的边界是一种仪式边界。洱海流域的村落有各自的本主,相关的本主仪式各自为营,嫁到村外的女儿或上门女婿通过婚姻关系脱离与本主的关系;同时,通过婚姻关系进入村落的男女与本主产生勾连,这一进一出的关键在于家户的地域范围。莲池会的地域性主要基于其成员的在家性。简单的说,每位莲池会成员都是某一家庭的代表。
家的核心观念使莲池会成员拒绝摆脱世俗生活而彻底投身到佛教中去追寻“西方极乐”,家庭的发展使她诉求于地方保护神,所以本主神在莲池会的信仰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观音在净土宗经典中被描绘成了‘西方三圣’之一,成了引导众生进入极乐世界的接引佛”,这在宗旨上解释了莲池会信奉观音的原因,在所有莲池会关于佛教神袛的经文中,观音经的数量最多,由此不排除莲池会的佛教源流是基于对观音崇拜的可能性。对会员而言,除去自身修行的考虑,观音在家庭福祉方面的照应更加贴近俗世生活。就社会整体而言,家庭可作为莲池会由佛教性组织转化为多元信仰组织的能动性因素。家与个人的纠葛促成了莲池会多元混生的神灵体系,这是莲池会发展过程中寻找的平衡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虽然也有对人类终极问题的解释,但这两个宗教各自认定只有唯一的神,个人认为这种排斥性并不符合莲池会的运行逻辑,因此他们没能融合到莲池会的信仰体系中,成为洱海地区唯一两个与莲池会没有交集的宗教体系。莲池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基于家与个人的综合考量,虽然会员作为个体加入莲池会组织,但家庭仍然是莲池会成员信仰的基本单位和空间。
在仪式行为上,尽管莲池会之间非本主信仰体系几乎等同,但在诸如观音诞、绕三灵等跨越村界的仪式场域下,他们并未形成连接。这种群体之间的边界构成了共同仪式场域下数以百计的仪式空间。梁永佳在对喜州的仪式空间论述的过程中,主张仪式空间较之政治、市场等空间形成机制更为稳定,他在喜州“复合文化”的基础上将仪式空间划分为本主与非本主的二元社会空间,最后通过等级结构来阐释这种“复合文化”。但就莲池会而言,无论本主与非本主,一个莲池会就是一个仪式空间。在组织内部,入会的先后决定会员在会中的地位,一般入会早的老会员念经的位置在大经母旁边,而大经母是最接近贡桌的,贡桌的背后就是神像,与贡桌的距离被等同于与菩萨的距离,修行好是靠近菩萨的途径,但“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入会的时间长短就被作为对菩萨虔诚度的一个评判,所以入会早的会员念经的位置更接近贡桌,这也是大家默认的规矩。另一个评判的标准即对经文的熟悉程度,这也是选取下任大经母的重要条件,莲池会的大经母不全是入会最早的会员,但一定是熟练掌握经文,虔诚礼佛并获得大家一致认可的。大经母与会首不同,他是终身制的,不会因会期的不同而改变,只有经母身体不好或年龄太大无力主持完成仪式的情况下才找人代职,代职者一般是经母候选人,但只有当上任去世才会正式接任。
总的来说,莲池会是一个信仰组织,同时也是基于性别、年龄、文化的共同体,它由仪式组织形成,其中本主信仰的地域性造成了仪式组织之间的区隔,而家户之间的地域性构成了组织内部的统一性,这构成了仪式组织的独立性与仪式空间多元共存的特征,这也是莲池会作为文化实践者的空间逻辑。
五、结语
莲池会作为一个地方的信仰结社,组织本身具有当地文化的特征,然而,作为一个独立组织,它与主流文化存在一种离合关系,这也正是莲池会作为文化实践者的多重逻辑结构:在组织内部,会友作为老年妇女重新组建的社会关系消解了老年人在家庭中交流失衡的境况;在家庭内部,做了奶奶的老妇人加入莲池会的潜在原因是一种为子孙发展求得庇佑的努力;此外,她们在失去劳动力优势的情况下,通过入会的功修为家庭谋得一份福气可以稳固其在家庭结构中的地位。作为一个仪式组织的整体,莲池会是一个地域的代表,它的存在不是受到外来文化碰撞之后的文化自觉,而是当地人生活化的需要,是当地社会文化的重要元素。相对于体制内的老年协会而言,莲池会的自发性一方面体现了当地老年妇女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反映的是它在地方文化中的合法性。作为依托于本主信仰的民间团体,对以本主信仰为主的地方群体而言,莲池会在处理村内的宗教事务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他在各种人生礼仪和仪式中是不可或缺的一角。
文化的流转逻辑是复杂的,只有从文化实践者的角度去探寻这些内在关联才能更好的把握其内核与演变逻辑。在现代化的文化实践过程中,民族主体的自主性是趋向改变传统还是维持传统,旁人无权干涉。然而作为文化研究者,既要避免东方主义的中心视角,也要看到新时代一些“内部东方主义”的现象与文化实践者的主体逻辑。在这个问题上,路易莎·沙因(Louisa Schein)所看到的“内部东方主义”打破了以往的文化主体在萨义德所述的东方主义中沉默的他者形象,他们自身也在强调自己的不同。但是,就路易莎描述的主体而言,这种“自我他者化”的前提是旅游开发与市场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消费所致,倘若排除市场与旅游又会是怎样的呢?莲池会的例子正是对这种主体性最好的回应。在文化的演变逻辑面前,我们不能停留在记录文化变迁过程中的片段化印象,而是要积极思考和把握这种动态变化的内在逻辑。往常客观主义观点所固有的逻辑主义往往忽视主体的创造性而着重于社会性的分析,这在本质上脱离了实践的主体性,缺乏主体的客观可能并不客观,对于文化实践的研究有必要回到具体的情景中讨论多元的主体性阐释,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把握文化发展的动态逻辑,形成更为客观的文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