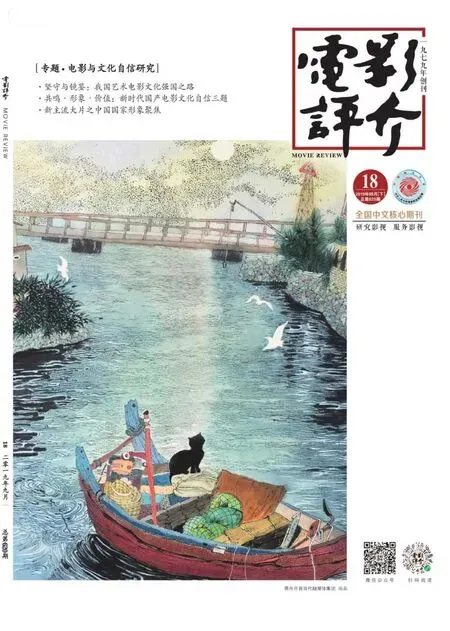少数民族题材电影70年:以守正促创新,倚融合增团结
李 静
电影艺术理论家陈剑雨曾指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应具有的三种属性:“一是少数民族导演拍摄的反映本民族生活的影片;二是少数民族导演拍摄的反映其他少数民族生活的影片;三是汉族导演拍摄的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影片。”[1]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即是以展现除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的电影。
中国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在这一时期,李萍倩执导的《花木兰从军》、侯曜导演的《木兰从军》、管海峰执导的《昭君出塞》,由于都涉及到塞外题材,成为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最初的探索。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正规的发展主要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可以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国家大局同行,随时代发展共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事业蓬勃发展的70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也以影像的方式记录着国家在这70年间走过的历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经历了“新中国”“新时期”“新世纪”三个阶段,全面展现了中华儿女共建伟大祖国的历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展现形式,是民族文化的记载者,承载着传播少数民族自然风貌、历史文化、性格特征的重要使命。它以独特的影像风格记录着中国历史,折射出我国社会发展走过的辉煌历程。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70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历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但不同阶段又有着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回顾其发展历程,本文从“历史与美学”的视角出发,从“新中国”“新时期”“新世纪”对其发展脉络和演进规律进行总结,以此聚焦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的发展特征,勾绘其以守正促创新、融民族增团结的别样景观。
一、新中国(1949-1966年):以文化自觉呈少数民族之生活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1997年对文化自觉进行了界定。在他看来:“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2]从中可以看出,文化自觉是指对于文化的自知与自省。在1949-1966的“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更多的就是在展现对于民族文化的认识。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6%,但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域却占全国总面积的60%。不同民族在宗教信仰、文化经济、传统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巨大,由此导致的民族问题错综复杂,加之反动势力未能完全消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任务仍然艰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成为极为重要的主流意识形态载体。展现少数民族文化,增强民族之间的了解、团结成为该时期的重中之重。
据统计,1949-1966年间,全国共拍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47部,涉及18个少数民族。[3]从内容主题来看,有表现农奴解放,歌颂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如《内蒙人民的胜利》(蒙古族,1950)、《山间铃响马帮来》(苗族,1954)、《边塞烽火》(景颇族,1957)、《达吉和她的父亲》(彝族,1961)、《阿娜尔罕》(维吾尔族,1961)、《冰山上的来客》(维吾尔族,1963)等;有歌颂追求解放进步、自由生活、美好爱情的,如《芦笙恋歌》(拉祜族,1957)、《五朵金花》(白族,1959)、《刘三姐》(壮族,1961)、《阿诗玛》(彝族,1964)、《草原雄鹰》(维吾尔族,1964)等;有展现英雄品格的,如《回民支队》(回族,1959)、《远方星火》(维吾尔族,1961)、《从奴隶到将军》(彝族,1979)等。在以深刻主题思想传达的过程中,这些影片还以影像的方式将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风情与文化展现出来,为各族观众推开一扇扇了解多民族文化的窗口。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部描绘中国少数民族生活的电影是《内蒙人民的胜利》。影片讲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蒙汉联军击溃反动派的武装进攻过程,展现了内蒙古人民解放的道路。该片内蒙风味浓郁,人物性格鲜明,节奏紧凑,故事情节完整。尤其在叙事技巧方面,更是奠定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叙事策略,“以阶级分析的二分法形成叙事类型上的最基本的二元对立结构,来阐释产生于国家意识形态体系中的基本主题,并在不同题材的不同主题中,形成各种万变不离其宗的叙事变形”[4]。但该时期内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一是猎奇感明显。许多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都将展现少数民族风貌作为影片重点;二是叙事情节雷同。《太阳照亮了红石沟》(回族,1953)、《金银滩》(藏族,1953)、《哈森与加米拉》(哈萨克族,1955)、《猛河的黎明》(藏族,1955)都沿用了《内蒙人民的胜利》的叙事模式;三是人物形象扁平化。无论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存在脸谱化的问题。
“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仍是以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具有“文艺工具论”属性。在这一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革命历史为背景,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自治等内容融入创作,主要展现少数民族的自然风貌、文化习俗等。该时期即是以这种深深扎根于少数民族文化深厚沃土之中的文化自觉,对我国的多民族融合进行了自我确认、自我阐释和自我表述。
二、新时期(1977-1999年):以文化自信现少数民族之风貌
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的表现。唯有在正确的文化自觉下,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对于所处的文化客体蕴含的文化价值、文化生命力的确信和肯定的心理特征。这种自信不是一种主观上的自满,而是在理性思索之下形成的自觉的心理认同、坚定的信心和正确的文化心态。在1977-1999的“新时期”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更多的就是展现对于民族文化的认识。该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开始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展现多民族的历史风貌和对改革开放的时代关注,展现出了可贵的民族文化自信。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定,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历程。随着文化事业的大繁荣,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也跨入全新的新时期。《五朵金花》《阿诗玛》相继解禁,广西电影制片厂、新疆电影制片厂(后改为天山电影制片厂)、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云南电影制片厂(后改为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四大少数民族地区电影制片厂相继成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开始依据自身特色,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
在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开始关注少数民族自身的命运与民族发展,以民族本体的文化内涵,以文化自信为原则,影片的风格、样式、类型更加丰富。除了《孔雀开阿佤山》(佤族,1978)、《奴隶的女儿》(彝族,1978)等延续了新中国时期的革命题材,更多的作品则展现了全新的文化内涵和叙事方式。《青春祭》(彝族,1985)、《黑骏马》(蒙古族,1995)、《红河谷》(藏族,1996)等影片都以“他者”视角来反映民族认同问题。“他者”是构建民族认同的重要视角。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表示:“他者的显现对构成我的‘自我意识’是必不可少的。”[5]民族认同感的建构也需要他者的参与。《青春祭》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之一。影片讲述了知青李纯在傣族村寨中找回自我的故事。该片以“他者”身份,凝视少数民族文化,以陌生化的手法展现了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内涵,从而让民族情感找到了归属。视听语言也成为该时期的探索对象。《骑士风云》(蒙古族,1990)、《东归英雄传》(蒙古族,1993)、《悲情布鲁克》(蒙古族,1995)以“马上动作片”将蒙古族勇士在马上追击、搏斗、枪战的镜头进行放大处理,给观众带来震撼的视听感受。纪实性传记类题材也是该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拔哥的故事》(壮族,1978)、《傲蕾·一兰》(达斡尔族,1979)、《从奴隶到将军》(彝族,1979)、《阿凡提》(维吾尔族,1980)、《森吉德玛》(蒙古族,1985)、《成吉思汗》(蒙古族,1986)、《松赞干布》(藏族,1988)《阿凡提二世》(维吾尔族,1991)等。
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去政治化”的语境中,电影娱乐化、商业化风潮兴起。“娱乐”也成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关键词。《幽谷恋歌》(壮族,1981)、《奇异的婚配》(彝族,1981)等影片将严肃性内容进行了娱乐化处理,过度追求戏剧冲突,弱化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应有的文化内涵。
文化自信是少数民族文化创新的动力之一。在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成为我国民族文化创新性基础与发扬的先锋。在该时期中,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开始从中国视角出发,在传承多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探讨民族的文化与记忆、生存状态、身份认同等深刻命题,探索独具中华美学特点的民族电影。可以说,在新时代的电影探索期内,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新人物展新风貌、以新生活展新时代。
三、新世纪(2000年至今):以文化多元展少数民族之魂魄
进入新世纪,全球化浪潮掀起。随着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电影市场也进入了全球化产业体制。伴随着“走出去”工程的实施,国产电影更加注重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交流。少数民族电影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体现,在全球化视域中的文化传播责任日趋重要。2011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可为构建全球共同文化价值体系作出贡献。”在2000年进入的“新世纪”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多元的文化思想于世界民族之林展示着中国民族文化的魂魄。
经历过改革开放的市场磨合,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进入新世纪后专业化、产业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在“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主题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愈发多元。有关注时代英雄的《索道医生》(僳僳族,2012)、《门巴将军》(藏族,2013)、《德吉的诉讼》(藏族,2013)、《天上的菊美》(藏族,2014)《真爱》(藏族,2014)、《德吉德》(蒙古族,2014)、《塔克拉玛干的鼓声》(维吾尔族,2017)、《金珠玛米》(藏族,2017)、《十八洞村》(苗族,2017)、《马骏》(回族,2019),也有聚焦少数民族普通生活、展现朴实小人物的《婼玛的十七岁》(哈尼族,2003)、《绿草地》(蒙古族,2005)、《马背上的法庭》(滇西地区少数民族,2006)、《香巴拉信使》(彝族,2007)、《冈拉梅朵》(藏族,2008)、《滚拉拉的枪》(苗族,2008)、《斯琴杭茹》(蒙古族,2009)、《鲜花》(哈萨克族,2009)、《乌鲁木齐的天空》(维吾尔族,2010)、《伊犁河》(维吾尔族,2012)、《童年的稻田》(侗族,2012),亦有展现历史光辉革命历程的《遥远的毡房》(内蒙古,2001)、《石月亮》(傈僳族,2003)、《狼袭草原》(蒙古族,2004)、《月圆凉州》(藏族,2005)、《血战千顷洼》(回族,2012);有表现传统与现代矛盾的《美丽的家园》(2004)、《花腰新娘》(彝族,2005)、《阿佤山》(西盟佤族,2012)、《唐卡》(藏族,2012),也有展现人与自然矛盾的《珠拉的故事》(蒙古族,2000)、《嘎达梅林》(蒙古族,2002)、《季风中的马》(蒙古族,2003)、《索蜜娅的抉择》(2003)、《可可西里》(藏族,2004),还有呈现世俗与宗教矛盾的《静静的嘛呢石》(藏族,2006)等。该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不同的方式,弘扬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民族之魂。值得一提的是,进入新世纪,少数民族电影也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开始进行国际合作,如费利普·弥勒执导的《夜莺》(中法合拍,2014)、让·雅克·阿诺执导的《狼图腾》(中法合拍,2015)等。合拍的模式一方面有助于拓展国内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从业者的视野,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走出去”。
少数民族电影的多元发展却未能在市场化道路中探索出一条成功的路径。多数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难以进入院线,困于无法融入主流市场的困境中。《花腰姑娘》《婼妈的十七岁》《静静的嘛呢石》《图雅的婚事》等影片都遭遇叫好不叫座的境遇。饶曙光先生也指出过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遭遇的此类问题,并提出了相应解决途径:“少数民族电影创作必须调整自己的思路和策略,在坚守本民族的文化立场和文化视角的前提下,借助于类型电影的创作手法和商业化营销手段实现自身的市场化生存。”[6]
新世纪以来,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艺术性、创新性显著提升,优秀作品大量涌现。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多样的形式、题材、内容,展现了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更应以多元包容之势,讲好有底蕴、有内涵的民族故事,探索市场化道路,让其成为国家形象的建构者、传声者。
结语
我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可以说,民族团结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的隐喻性、文化认同性,使其成为促进民族团结、展现国家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70年来,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记录着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文化历史印记。未来,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更应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多元为使命,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不断提升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以守正促创新、倚融合增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