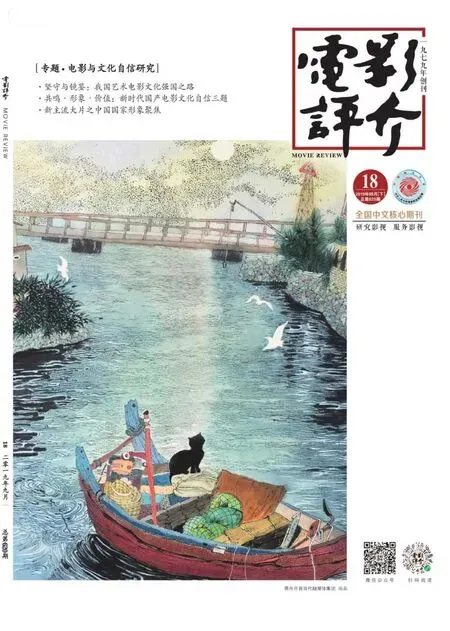从自觉到沉滞:“她时代”中国女性电影之思
赵自云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纪念100周年,这意味着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至今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让中国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艰难地浮出历史地表。新世纪初,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预言,21 世纪将步入“她”时代。2001年美国方言学会举办的“世纪之字”评选中,“她”字以绝对优势成为21世纪的关键字。[1]2007年“她经济”与“剩女”同时成为汉语新词,这一时间上的同步性正可以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为高学历、高收入、高龄的“剩女”群体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控制和影响中国消费市场的重要力量,有学者将这种围绕着女性消费和理财等而形成的特有的经济圈和经济现象,称为“她经济”。[2]依据电影资本逐利的原则,我们发现在“她时代”境遇下,贴近女性生活、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婚姻与情感等问题的电影作品数量在不断攀升,尤其催生了“小妞电影”等新的电影类型。值得深味的是,这些影片中却充斥着陈旧、落后的性别叙事观念和叙事话语,有些台词甚至带有鲜明的反女性色彩,这不仅遮蔽和扭曲了新世纪真实的女性形象,而且也完全背离了女性电影的创作主旨。基于此,我们需要反思和探讨:中国女性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创作已经趋于自觉的情况下,何以在“她时代”不但没有蓬勃发展的迹象,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种沉滞的态势?
一、西方女性电影创作主旨的提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女性在获得政治和经济权利的基础上争取在文化领域中和男性享有平等的权利,因此,批判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成为西方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的核心目标。正是基于女性这种强烈的文化权利诉求,英国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对经典好莱坞电影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专门研究。她在1975年《银幕》第16卷第3期发的表论文《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中指出,大多数好莱坞经典影片中,男性是观看的主体,女性是被看的客体,尽管是女人的故事,但仍是通过男性在讲述,以男性的眼光在打量和界定女人,女性是沉默的、没有说话权力的,甚至是不该有欲望及其自主个性的。对此,英国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克莱尔·强斯顿发表《作为反电影的女性电影》一文,她在文章中指出:女性形象始终在电影里充当着神话学意义上的符号。[3]“她们”不是作为女性的能指而存在,而是作为父权意识形态体系的符号。男人可以通过对语言的掌握把自己的幻想和迷狂强加到沉默的女性身上,女性只是意义的承担者而不是创造者。
在传统叙事电影中,女性不仅是片中男性角色的色欲对象,而且也是电影院里男性观众的色欲对象。比如,在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中,张曼玉的服装造型旗袍多达50多套,影片镜头特别喜欢捕捉张曼玉慵懒状缓缓爬楼梯的细节,不断扭动的水蛇似的腰肢将她烘托得性感十足。可见,在男性视角控制的电影中,“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4]
以劳拉·穆尔维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家正是在研究和批判好莱坞电影中与现实女性相去甚远的银幕女性基础上,提出了创作“女性电影”的实践主张。即由女性导演执导,以女性作为叙事主体,深入女性内心,关怀女性的生存状态与生活环境,探寻女性的成长与发展特点的电影类型,影片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性别意识。[5]
二、中国女性电影的创作态势:从自觉到沉滞
依据西方女性电影的创作主旨与创作实践,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女性电影作品屈指可数。学者戴锦华不无悲观地指出,在当代中国影坛,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女性电影”的唯一作品是女导演黄蜀芹的《人·鬼·情》(1987)。[6]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一个名叫秋芸的艺术家如何在京剧舞台上通过扮演钟馗、林冲等男性角色来逃避自身的女性身份。从艺术上来说,她确实通过“易装”成功地融入了男权社会,但她在现实世界中却陷入了一个“父不父、师不师、夫不夫”的尴尬境遇中,这也就意味着她最终也没有逃脱掉女性这个性别身份带给自己的悲剧命运。这个时期还出现过一批中年女性导演执导的电影,如王君正的《山林中头一个女人》(1987),鲍芝芳的《金色的指甲》(1988)、《女人·TAXT·女人》(1990)等,这些影片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体现出女性对男权文化与男权话语秩序的突破与对抗。
21世纪初出现了一批较为优秀的女性电影作品,如黄蜀芹的《嗨,弗兰克》(2001),李少红的《恋爱中的宝贝》(2004)、《生死劫》(2005)等。尤其是在2005年,同时出现了宁瀛的《无穷动》、马俪文的《我们俩》和李玉的《红颜》三部相当出色的女性电影。其中,又以宁瀛的《无穷动》女性意识彰显最为自觉和激进。片名寄寓为在女人内心深处,有着一股“无穷涌动的欲望的情绪”。
影片《无穷动》开篇即用特写镜头聚焦一个狭小鱼缸里来回游动的几条鱼,“鱼”谐音“欲”,这里显然是用来照应片名,作为表达女人欲望的一个意象,同时隐喻着女人的生存空间和生活境遇犹如生在褊狭鱼缸之内的鱼。电影整个故事就发生在一个四合院里,通过四位女主各自回忆的童年生活,表明她们从小就生活在四合院里,生活空间的极度促狭显然对她们的肉体和精神带来了双重压抑。因此,在一个男人缺席的时空中,她们不再化妆和装扮,任由布满毛孔的脸、涂了艳丽口红的嘴、下垂的眼袋、臃肿的身材和不再娇嫩的手,暴露在银幕世界上,她们不再为博得淑女、贤妻或者良母的名头而隐忍内在的各种本能欲望,大爆粗口、讲性、谈男人,歇斯底里地大哭大笑大闹,毫无顾忌地撕扯、硬拽、大嚼鸡爪……这种完全颠覆主流电影女性三观形象的镜像传达方式让坐在影院中的男性观众视听神经遭受着强烈的刺激,甚至让习惯于在银幕上观看青春靓丽女演员的男性观众发出尖刻的吐槽:“太恶心了,这部电影怎么把女人拍得这么丑?!”对此,集影片编、导、摄影、剪辑于一身的宁瀛认为,女性的欲望其实是非常有魅力的,男人不应该无视甚至藐视。
与影片《无穷动》通过极力宣泄中年女性内在欲望以彰显女性意识不同,马俪文在影片《我们俩》中通过讲述房东老太太和少女小马一起生活的故事,用带有纪实风格的镜头向观众呈现了在一个男性缺席的时空中,女性之间如何建构起超越血缘纽带的情感关系。影片开篇将故事场景设置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冬日,接着用大远景镜头缓缓地呈现冰雪覆盖、人迹罕至的远山,随着镜头慢慢推近,一个手推自行车的女孩气喘吁吁地闯进了画面;紧接着,又是全景镜头,女孩在无边荒凉的山路上踽踽独行,身影愈发显得孤单、渺小。随着女孩闯入一家四合院的老人家中,镜头又多次用全景方式呈现这位独居老人只身坐在庭院,老人往往被挤到画框边缘位置……这些镜头显然极富于隐喻意味,外部生存空间的萧条、寂寥与冰冷显然是两位女主内在孤独、凄凉与无助精神世界的映射。如此同处于精神荒原的她们,注定初次遭遇时会相互嫌弃、争吵和谩骂。但女性内在的情感世界往往极其细腻和微妙,马俪文用质朴的镜头和温情的画面向观众真诚地呈现了两位女性之间日渐形成的一种奇妙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基于女性自身的,完全超脱于血亲关系和外在的功利世界,这种无关乎任何男性的女性特殊情感建构显然是马俪文电影女性意识的自觉凸显。
相较而言,刚出道的李玉既缺乏宁瀛在影片《无穷动》中大胆宣泄女性欲望的勇气,又没有马俪文表现女性之间那分细腻温软又无限美好情感的乐观,这可能与李玉对女性身份带给自身的困扰与悲剧境遇有着深刻的认知有关。她说:“自己天生是一个女人,然后才是一个导演。我的视角自然是与男性导演不一样的。”[7]影片《红颜》采用女性叙述视角讲述了一个名叫小云的女孩由于青春期的骚动而意外怀孕生子,尽管她后来通过个人努力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艺术成功,但她却永远洗刷不掉她“狐狸精”的污名,最后只能选择孤独离开故乡才有可能开启新的人生。这种对女性身份的悲观认同和女性悲剧命运的书写,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黄蜀芹的创作状态:对于强势的男权文化秩序不自觉地认同与妥协,这显然制约了李玉电影中女性意识的凸显与张扬。
事实上,和李玉一样,宁瀛和马俪文的电影创作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商业化转型。影片《无穷动》虽然在当时赢得了不错的票房收入,但口碑评价却呈现两极分化趋势。中国电影市场日渐商业化的现实,让宁瀛觉得属于带有作者色彩的个性电影生存空间愈发狭小,她只有选择转型拍摄几部商业片才能重获市场话语权,“我要学会让我的想象力不要太偏离主流,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要以我的视角去看问题。我一定要有这个置换能力,只做我能做的那部分。”[8]马俪文的两部电影《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和《我们俩》虽然给她带来了较大声誉,但这两部电影的票房收入却非常低,《我们俩》的票房仅仅只有5万元。为此,马俪文在2007-2008年,接连推出了影片《我叫刘跃进》和《桃花运》,她灵活地采用了快节奏的剪辑、搞笑的对白、荒诞的情节,不惜重金聘用颜值超高、妆容精致、服饰时尚华丽、拥有众多粉丝团体的女演员,将镜头不时地捕捉影片中美女丰满的胸部和性感的大腿、令人着迷的脸蛋,最大程度上满足影院中男性观众的观看欲望,明显的商业意识取代了原先影片中日益觉醒的女性意识。这两部影片果然赢来了高票房收入。
也许,正是基于票房崇拜时代中国院线放映基本是大片、商业片“一边倒”的形势,近几年来虽然女性题材电影作品不断涌现,但大多数影片还是基于男性的叙述视角讲述女人的故事,女性的自我意识与主体精神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凸显与张扬。如冯小刚的《我不是潘金莲》(2016),虽然以李雪莲作为故事的叙事主体,讲述她如何不断反抗男权社会带给自身的不公平遭遇过程,但事实上,李雪莲的反抗只是一种男权话语规约下的徒劳挣扎罢了。恰是作为男性话语体系中“不正经女人”的符号能指——“潘金莲”,她是一位敢于正视并尊重自身本能欲望的女人,她不惜以生命换得自身权益的行为正是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萌动与觉醒。这就意味着李雪莲否认与拒绝自己是“潘金莲”的努力就是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否定与反叛。这样的电影叙事表意机制显然强化了传统的性别观念和性别秩序,不利于建构“她时代”女性观众的自我意识和主体精神。
再如张艺谋的女儿张末在影片《28岁未成年》(2016)开篇中,镜头犹如男性的目光通过凝视年轻女性精致妆扮的过程窥视她们的身体,从苗条婀娜的身材到性感红艳的嘴唇……将女性身体作为电影商业化的叙事符号,一直是主流商业电影的惯用技法。就这点来看,作为年轻女性导演的张末,并没有挑战和突破男性观众传统的性别观念和审美情趣。可以称得上是女性电影的作品是文晏的《嘉年华》(2017)。这部聚焦于少女性侵题材的影片,剧情重点并没有放在少女遭受性侵的过程,而是着力于家庭、学校、社会执法机构对被性侵少女心灵的二次伤害。影片不仅采取女性的叙事视角和叙事立场,而且将镜头集中呈现女性外在的生存空间和内在的心理世界,尤其通过小米和小文留恋于玛丽莲·梦露的雕塑隐喻她们性意识的萌动和对女性特质的身份认同。影片中的男性形象都是灰色的,对于他们带给女性的身心伤害,电影镜头给予了淋漓尽致地披露和呈现。由此可见,21世纪20年以来,中国女性电影创作虽然没有消弭但是却几乎陷入了沉滞的尴尬局面。
三、中国女性电影在“她时代”创作沉滞的思考
女性电影创作是激进的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倡导的特定产物,它的出现意义在于强化和凸显女性在电影艺术领域内的性别立场和性别特质,挑战和颠覆传统电影基于男权文化视角对女性形象的主观臆造,还原和再现现实生活女性的本真面目。如此鲜明的性别意识和性别立场决定女性电影在创作各个方面都是极具个性化色彩的,而这显然与电影从生产到消费过程都是集体性的艺术特质格格不入。因此,以马俪文为代表的女性电影导演在“她时代”创作发生市场化转型可能是女性电影发展的必然选择。作为大众文化的电影艺术,只有获得大众的关注和认可,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思想传递和艺术表达。吊诡的是,如果女性电影一旦舍弃自身挑战,打破观众传统性别观念和审美情趣的精英化叙事策略,必然会改变它旨在突破和颠覆传统电影中的性别建构和男权文化表意机制,重新建置女性电影语言和结构的创作初衷,这也就意味着它消解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意义,女性在文化领域内试图对抗男权中心制的内在诉求就无法得到满足。由此可见,即便在由女性观众主导和控制的电影消费领域的“她经济”时代,女性电影导演仍然无法克服和逾越创作中的两难困境,这可以说是中国女性电影创作在“她时代”出现沉滞状态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在男性一统天下的电影王国里,女性想凭借自身努力跻身其间担当起导演、编剧、制片人、摄影、剪辑等和男性一样的角色和身份,并能够拍摄出和男性一样“叫好又叫座”的电影,甚至要在男性话语主导的各类电影节中频频获奖以赢得自身的荣誉和价值,实属艰辛和不易。这自然也是中国女性电影创作在“她时代”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
此外,中国绵延几千年以来的家庭父权制、夫权制思想观念影响深远,这在女性意识色彩浓烈的影片《无穷动》中有着深刻的印迹。影片中虽然没有一位男性形象,但故事发生的动机却与男人有关。妞妞在发现老公出轨自己闺蜜的事实之后,决定以一场鸿门宴找出第三者,这才建构了整个故事。她们对童年生活记忆最为深刻的也是关于各自父亲的故事,在她们的记忆和讲述中,父亲对于一个家庭的建置和解构起着核心的作用。可见,家庭父权制、夫权制正是禁锢女性从身体到主体精神解放的牢笼和枷锁,女性要想获得身心的全面解放,必须勇敢地走出家庭或者让传统家庭结构全面解体。基于此,宁瀛在影片结尾设计了让女人们走出四合院,而马俪文和李玉则在各自的影片中用死亡的方式让男人在家庭中缺席……然而,女导演这种近乎偏执的电影叙事策略很难得到普通观众的理解和认同,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中心观念和性别秩序正是中国女性电影发展举步维艰的深层内因。
结语
在中国电影诞生之初,电影无论是片名还是期刊封面都是以女性形象为主,影片故事内容也大多与女性有关。然而,这些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数都是基于男性视角塑造的,她们是一群“不可见”的女性。以劳拉·穆尔维为代表的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通过揭示传统好莱坞电影对现实生活女性形象的遮蔽与扭曲,提倡女性导演基于女性视角和女性立场讲述女性真实内心的故事,同时建构女性电影叙事结构和叙事话语。遗憾的是,女性电影这种极具个性色彩的创作主张与电影的大众文化艺术品质难以相互兼容,加之中国女性导演数量不多,能够主动秉承女性电影创作主旨和精神的女导演则更少。此外,中国社会男权文化中心观念和性别秩序根深蒂固,这些都决定女性电影在“她时代”的中国立足与发展是相当艰难的。这也意味着中国女性意图通过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建构和表达女性自我意识和女性主体话语是深具难度的,女性在经济领域的崛起并未给自身迎来文化地位上的真正跃升。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