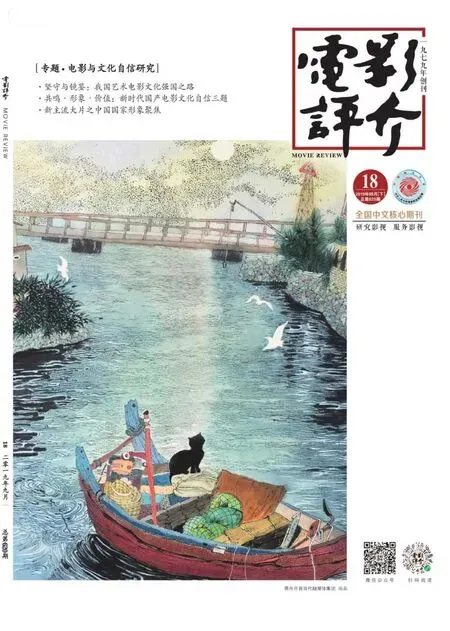解构、重塑与新生:电影中的中国经典文学IP
贾延龙 张 皙
多年以来,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因其多元的内容和思想而成为经典,其丰富的故事情节和多样化的个性角色更是让读者反复揣摩和研究。这些经典文学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成为众多文学作品进行再创作的基础和灵感来源。回顾电影史,可以看到不少中国经典文学名著被以各种方式进行解构和重塑。通过对比和研究,可以从中得出现代主义文化对于经典文本的影响,并从中窥见大众心理在时间流中的变化。
一、中国经典文学IP改编历程
了解现代电影作品对中国经典IP的解构与重塑,就不得不先从具体作品谈起,最先需要被提起的非《西游记》莫属。作为一部经典神魔小说,《西游记》以其丰富的神魔世界和经典的人物形象以及多年来被层层解读的复杂内涵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最早的一部《西游记》改编作品可以追溯到1927年上映的无声电影《盘丝洞》,此后又有1953年由叶一声导演的电影《猪八戒招亲》。此后十几年间,《西游记》的改编热度一直居高不下,从1995年的《大话西游》系列到此后2013年的《西游降魔篇》、2014年的《西游记之大闹天宫》,再到2015年大火的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6年的《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2017年的《西游伏妖篇》和《悟空传》,以及2018年的《西游记之女儿国》,我们可以看到,从2013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有一到两部《西游记》的衍生作品上映,这些作品质量有优有劣,虽然已经经历了90多年的改编,但仍有不减反增的势头。
除《西游记》之外,改编量也居高不下的经典文学IP还有《聊斋志异》。经由《聊斋志异》改编而成的电影作品非常之多,今年暑假上映的《画皮前传》就是其中的一部。而早在1927年,就已经有根据《聊斋志异》改编而成的电影《田七郎》。据笔者初步统计,历史上的聊斋题材电影不下60部,更不要提数量众多的电视剧作品,其数量之多令人咋舌。在《田七郎》之后,1954年的《人鬼恋》改编自《连锁》,1960年的《倩女幽魂》改编自《聂小倩》,1962年的《湖山盟》也改编自《连锁》;1987年同名经典电影《倩女幽魂》在2011年又被翻拍,由香港导演叶伟信指导。等等。进入21世纪,又有大量聊斋题材电影面世,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画皮》系列。除此之外,还有2011年上映的由陈嘉上指导的《画壁》,以及今年上映的《神探蒲松龄》,都算是聊斋题材中比较有名的改编作品。
除了《西游记》和《聊斋志异》外,还非常受欢迎的经典文学IP便是由白蛇故事改编的众多电影。同前两者不同的是,白蛇故事底本有很多,并非有单一经典文本,其电影故事改编来源有《雷峰塔传奇》《白蛇精记》《白蛇全传》等。由白蛇传说改编的电影中最具代表性的为1993年由徐克导演执导的《青蛇》。此外还有1980年的《白蛇传》、2011年的《白蛇传说》;今年还上映了一部由白蛇故事改编而成的动画电影《白蛇:缘起》,算得上白蛇相关电影中的中上之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已经过数十年的拍摄大潮,但这些经典文学IP的改编却依旧势头迅猛,且在人物和内容上不断创新。那么,是什么让这些经典文学IP得以在数十年的时间中长盛不衰呢?这是文章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
二、中国经典文学IP的解构、重塑与新生
总结《西游记》《聊斋志异》和《白蛇传》,不难看到两个经典元素,那就是神魔(妖怪)元素和爱情元素。爱情元素自不必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长盛不衰的故事元素。从《西厢记》中的张生和崔莺莺,到《长生殿》的唐玄宗和杨贵妃,再到《白蛇》中的白素贞和许仙,还有《红楼梦》中的宝黛爱情等等。而此外就是神魔元素,作为与现实结合,却有与现实截然不同的奇幻境界的故事,那种动辄可以上天入地、腾云驾雾的高超神力以及神秘莫测的神魔世界总能激起观众的想象力,尤其是在影像技术大发展的今天,各种瑰丽、神秘又或幽深黑暗的神魔世界都可以在大银幕上被展现出来。这种东方神魔故事备受青睐的现象其实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如近年来大火的阴阳师的形象及其代表人物安倍晴明,就是神魔元素受到欢迎的典型代表,其形象来源出自《今昔物语集》《古今著闻集》《续古事谈》等古代日本经典作品,此后由梦枕貘将这些内容进行取材,创作了《阴阳师》这部作品。阴阳师这个形象大火至全球,继而成为东亚神密文化圈的一种典型代表,而阴阳师的代表人物安倍晴明正是一个能够操控高深术法,沟通阴阳两界、驱使恶鬼的形象。其形象在此后的各种改编作品中又不断被解构,在正派、反派和中间派之间游走。而这些故事的共同点就是,在这些神怪故事世界里,鬼怪和人类是共存在同一个世界中的,好奇心驱使读者或观众不断关注此类故事。而在西方,也有与之类似的驱魔师题材,如2005年上映的《地狱神探》和1973年的《驱魔人》等,都是对怪诞未知的世界及其生物的想象构建。那么,体现在具体的创作上,这些电影作品对经典文学IP进行了哪些创新呢?
首先,是对主要人物经历空白的填补。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这些经典文学IP原作所呈现的主人公经历是有时限的,观众能看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之后的创作者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在空白的时间里对人物经历进行大胆想象。如《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就是将故事设定在了唐僧十世轮回的第一世,这一世唐僧不再是个大人,而是个有点儿唠叨、有点儿熊、年仅7岁的小和尚形象。观众虽然熟悉《西游记》正文中的取经故事,却不知道十世轮回第一世时的取经故事,因此这里就形成了一个能够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却又不被过分局限的创作基础。又如《白蛇:缘起》讲述的就是五百年前的白蛇和许仙的前世阿宣之间的爱情故事,同样是一个填补人物前世经历的文本。此外改编自《射雕英雄传》的《东邪西毒》讲述的是原著中一众德高望重的前辈们年轻时代的故事,也是一种对原著空白的增补和再创造。
其次,是对主要人物性格和角色定位的颠覆。这一点如《大话西游》《西游记降魔篇》和《画皮》。我们可以看到,《西游记》原著中的孙悟空形象在《大话西游》和《西游记降魔篇》中有了极大改变。在《大话西游》中,孙悟空成了一个落魄草根的形象,他会像普通人一样为生活所迫,也会为了求生而跪地求饶,同时,这个人物还会为情所困、爱而不得。如果说《大话西游》完成了一个将英雄人物大众化的过程,那么在《西游降魔篇》中则完成了对英雄人物妖魔化或者说恶人化的过程。在《西游降魔篇》中,孙悟空成了一个妖性十足、性情暴虐的恶妖,他不仅花言巧语,骗得唐玄奘将他的封印解开,在封印解开之后,还干掉了前来降服他的捉妖人,“美猴王”的形象在这个故事中变得丑陋、暴虐、嗜杀且残酷无情,满口獠牙、猥琐污秽的孙悟空与正气凛然的美猴王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给予观众既成印象上的巨大冲击。与前者的英雄人物大众化或者反派化相对,《画皮》和《青蛇》所采用的是反派人物中间化的手段。在《画皮》原始的故事文本中,《画皮》中的妖怪是个彻底的反派,恶鬼掏走了男主人公的心,男主人公最终是在妻子的努力下才复活。而在《画皮》的电影剧情中,画皮的妖怪有了妖狐的身份,而这个妖狐又有了一个牺牲自己救活大家的结局,这个形象与原作中那个单薄的画皮妖怪相比有了很大的丰富,同时妖狐小唯靠吃人心来维持美貌和她对男主人公的深情都成为这个人物复杂多面形象的组成部分。与之相对的,在电影《青蛇》中,反派人物法海不再是冷漠不讲人情的反派形象,他开始中间化,开始有了作为普通人的欲念,同时也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
现代学说中的解构主义认为,解构是对非正当的教条、霸权和权威的对抗,它需要打破已有的秩序,这种秩序体现在很多地方,而解构主义是对这些已有习惯或者说秩序的反叛。像前文的孙悟空就是一种典型代表——“吴承恩塑造的孙悟空形象本身便是解构主义的代表,大闹天空俨然是一次挑战世间规则、秩序,针对正统权威——天庭的解构。具体而言孙悟空形象本身具备德里达反逻各斯中心论的特点。”[1]这种解构和反叛的具体体现可以总结为以下两条:
一是对英雄人格的消解,即解构被神化的英雄人物。主要表现在对英雄人物英雄人格的消解上,即英雄正面人格的世俗化、草根化或者妖魔化。《大话西游》中的孙悟空和《西游降魔篇》中的孙悟空皆是代表,《大圣归来》也是这种类型的体现。在《大圣归来》中,孙悟空失去神力,不再拥有上天入地的能力,他变得像普通人一样,嘴硬心软,与原著中的孙悟空对比,这里的孙悟空更像一个时下的年轻人形象,虽然嘴上不饶人,但是心中却仍有英雄梦,希望能够坚持善良、惩奸除恶。
二是解构反面人物,重塑反面人物。具体体现在反派人格中“恶”的复杂化和多面化,即从单一、绝对的“恶”发展为复杂化的“恶”,“恶”聚焦在一个人物身上,开始有各种令人同情的理由,这个人物甚至会开始为善,因此不再是绝对的反派人物。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电影对经典文学IP的再创新即是对经典文学IP中的人物性格和经历的解构和重塑,也可以说是一种偏离原著但又以原著为基础的二次创作。经典的形象被推倒、打碎然后再糅以现代的精神去进行重组,故事也以现代的思想去重新组织,展现出与原来的文本有所不同的崭新生命力。
三、解构与重塑的背后:现代文化和大众心理
每个受青睐的故事人物的影像风格,从某种程度上讲都是大众心理的满足与展示。英雄式的角色可以体现大众心中的英雄情结,而更多的则是把自己代入主角的英雄式体验,即希望自己成为主角那样的英雄。而草根式的主角则能在经历上引起大众共鸣,如果草根逆袭,那么大众在这个过程中享受代入草根的角色,获得成功;而如果草根继续在泥潭中挣扎,则大众以情代入,展现对主人公的同情。
现代电影对于经典文学IP中人物和故事的解构和重塑,体现了现代文化的变迁和大众心理的变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商业化和娱乐化成为时代背景,面对快速发展的文化和时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背景所导致的迷惘在一代作家文本中的体现。而随着教育的不断普及和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精神诉求也不断提高,不同的社会群体开始寻找符合自己群体文化价值观的作品来填补内心。这些群体寻找的总体方向是:强调个性、追求新奇、反叛权威,拒绝一成不变,反英雄主义的同时强调人文主义关怀。于是,我们看到被神化的英雄走下神坛,反派开始拥有更丰富的内心。观众希望英雄更是一个普通人,而非仅仅是一个英雄。这种解构和重塑的背后所折射的大众心理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大众心中对于力量的渴望,包括对成为英雄的渴望和对正义的追求。每个人的心中都一个英雄梦,这个英雄可以呼风唤雨,且能力无边,因之可以惩奸除恶,打抱不平。这是大众心中对于英雄主义的长久渴望。但当今大众渴望的英雄形象是不必被神化或绝对化,而是在成为英雄的同时,还具有普通人的缺点,是一个大众化的英雄形象,这也是为什么近些年来逆袭类的作品会大受欢迎的原因。大众会在这种故事中感到安慰,同时也便于将自己代入主角的身份。这类英雄给大众一种鼓励:你就像这个主角一样,未来的某一天,也许就能从普通人成为一个英雄。这正如《哈利·波特》系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样,作者所构建的魔法世界是和普通人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而主人公原本是一个生活在普通世界的普通学生,但他却可以通过九又四分之三的站台前往神奇瑰丽的魔法世界。这些设定给了众多读者或者观众梦幻的想象和代入感。
第二,大众对于权威的反叛。追求个性化、反抗权威的时代潮流同样体现在对经典文学IP主人公的改造上。于是,我们看到好人可能会变成坏人,坏人可能会变成好人或者不再是个绝对化的坏人。对于经典形象的解构和重塑满足了大众对于权威解读和诠释的反叛。
第三,大众对于神秘主义的好奇心和对美好爱情的向往。神魔和爱情,是当今经典文学IP改编的两个热点,两者通常被结合起来进行再创作。无论是《西游记》《聊斋志异》还是白蛇的传说等,都包含这两个元素。影片的再创作,正是在寻找一种与大众潜意识的共鸣,而这类作品之所以受欢迎,就是从侧面反映了大众的心理渴求。大众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感受美好的爱情,同时还可以暂时忘却现实的烦恼,而专注于对神秘未知世界的探索,心灵得以放松和满足。
第四,大众对于爱情平等和自由的追求。几版经典的《倩女幽魂》电影和蒲松龄的原著《聂小倩》可以形成有效对比。在原著故事中,聂小倩是一个比较单薄的女鬼形象,而宁采臣其实也是有发妻的。宁采臣把聂小倩带回家后,聂小倩就开始在宁采臣家中操持家务并且任劳任怨,“即入厨下,代母尸饔。入房穿榻,似熟居者”[3],故事最终宁采臣在原配妻子去世后,将聂小倩纳为小妾。我们可以看到原作的故事其实是非常典型的男性中心主义且具有历史局限性。而在后来的电影作品中,发妻和小妾的情节都被删去了,故事最终也不再是团圆结局。此外,聂小倩也从一个单薄、任劳任怨的小妾形象摇身变为一个才女的形象,和宁采臣得以才华相匹配,成为一对现代意义上的才子佳人。以上这些改变正是大众思想随时代变迁的具体体现。
除以上之外,大众对于男性形象审美追求的转变也体现在影片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今年上映的电影《神探蒲松龄》。在这部电影中,宁采臣成了燕赤霞的化名,原著中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形象变成了能力战妖魔的大侠形象,从文弱书生到大侠的转变,体现了现今大众对男性形象的审美追求。
当然,当下对经典文学IP的解构和重塑也存在问题,因此,在创作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一是避免过于追求颠覆,失去剧情整体的逻辑性,无法说服观众;二是追求颠覆的同时却再次陷入刻板。如现在市场上大量出现的有关西游的电影,其中很多已经开始流于颠覆的刻板模式,反而再次陷入俗套。颠覆成功的本质在于能否让人耳目一新,在于是否有核心内涵,虽然传统的后现代主义被认为是强调无中心、无深度的,“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由于主体中心地位的丧失,使得文本审美意义的深度也随之消失,最终导致了作品的平面化。读者已无须去探求作品内在的深刻含义,因为作品本身就不隐含更深层次的意义,它仅仅提供给读者一种阅读的范式和体验。詹姆逊在给后现代主义的各种要素命名时把上述现象称之为‘无深度性’。”[4]但如《青蛇》《大话西游》等,它们对原著的颠覆都是建立在能被大众数十年来解说纷纭的深刻内涵上的。好作品不能空洞无物,嬉笑怒骂的内里一定要有能让人反复咀嚼的深度存在,当然,说教式的作品也不能称之为好作品,因此平衡内外极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