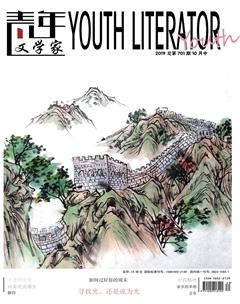《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
摘 要:叙事结构作为作品的骨架,对于整个作品的呈现效果发挥着重要作用。《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大致分为两条结构,即“现在”与“过去”并行,二者相互补充、对比与角逐。这一结构丰满了人物形象,揭示了尖锐的社会问题,表达了作者对传统乡村生活的向往,对当下社会颓靡现象的批判,对祖国未来发展前途的焦虑,以及对发展局势不可逆转的无奈。
关键词:叙事;现在;过去;平行;对比;角逐;《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
作者简介:赵秋玲,哈尔滨师范大学斯拉夫语学院2018级俄语语言文学在读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9--03
《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Дочь Ивана, мать Ивана? 2003)是瓦连京·拉斯普京(Валенти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Распутин,1937-2015)创作晚期的作品,讲述了一位母亲及整个家庭悲剧的故事。全书分为三部,分别以塔玛拉·伊万诺夫娜被捕前、被捕后及获释出狱三条线展开,小说以其富含哲理性的内容、巧妙的结构框架、细腻的情感深刻反映了当下社会面临的尖锐問题,引发读者的深思。作品看似简单的故事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正如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所说:“这是一部真诚的幽愤之作”。[1]
回顾以往的研究可见,学界从作品内容,作家经历等角度解读作品人物形象、现实社会问题及精神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已有成果。但是,针对该作品的叙事结构特色及艺术特征的研究还寥寥无几。作为一篇中短篇小说,《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的内容犹如人体肌肉组织一般充斥全文,而结构框架则作为骨架支撑全文。在这部作品中,作家打破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采用非线性叙事结构,即打破时间的次序,将“现在”与“过去”两个时空的叙事并列运行,借助该结构来搭建主人公塔玛拉·伊万诺夫娜的形象体系;其次,二者并列的同时产生强烈的对比,作者通过犀利的笔触映射出当代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最后,在二者的角逐中体现了社会未来必然的发展趋势,流露出作者内心无奈低沉的情感。
一、线性叙事与非线性叙事
何为线性叙事?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这样界定:“悲剧是对于一个完整而具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一件事物可能完整而缺乏长度)。所谓‘完整,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所谓‘头,指事之不必然上承他事,但自然引起他事者;所谓‘尾,恰与此相反,指事之按照必然律或常规自然的上承某事者,但无他事继其后……所以结构完美的布局不能随便起讫,而必须遵照此处所说的方式”[2](41),亚里斯多德的这段描述便是叙事结构的原型。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线性叙事是按照固定的先后顺序,严格遵守开头、中间、结尾的排列,对作品展开叙述。与线性叙事相对应的便是非线性叙事,它指的是“打乱了时间顺序的叙事方式。但从广义上来讲,可以将非线性叙事理解为一种反传统、多样化的叙事模式,不仅指叙述时间的错乱,也指叙述空间的混乱,以及叙述层的交替转换等有关叙事的各个方面”。[3](3)非线性叙事结构使作品看起来不如线性叙事那般工整,但也是展现作品艺术特征的手法之一,利用时空的错乱使情节跳动起来,不显得那么单调乏味。这种结构对于作品塑造人物形象、反映思想主题有着重要作用。本文从非线性叙事中的时间错乱的角度,讨论“现在”与“过去”的交锋对于阐释整个作品艺术特色及情感思想的重要意义。
“现在”与“过去”是相对于叙事时序而言的,叙事时序“也叫文本时间, 指叙述者叙述故事的时序,也就是文本展开叙事的先后次序,这种时序一般都会打乱故事的自然时序,变化不定”。[4](72)本文谈及的“现在”,是从现在作为母亲的塔玛拉·伊万诺夫娜、当今城市的发展以及新时代年轻人的角度提出的;而“过去”一词,则是从作为女儿的塔玛拉·伊万诺夫娜、以往的乡村生活以及老一辈人的角度提出的。《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的叙事便是将“现在”与“过去”错落相间,时而“现在”,时而“过去”,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使作品情节跌宕起伏,增强了艺术美感,作品背后的意义也得到完美诠释。
二、现在与过去平行:立体饱满的人物形象
《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的叙事者以一种全知全能的视角对事件展开描述,在以叙事“现在”为主的时间轴上,塔玛拉·伊万诺夫娜不仅是一位平凡的母亲,女儿出事后,心里倍感焦急与心疼;同时她又是一位沉着理智的“女超人”,她曾试图相信法律会还女儿一个公道,但呈现在她面前的却是政府官员的黑暗腐朽,因此她才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惩罚了罪犯。作品中各个环节此起彼伏,环环相扣,塑造了一个伟大勇敢的母亲形象。辅线是以回忆“过去”为主,作品在讲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同时,穿插女主人公以往的生活经历。俄国小说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在《散文理论》中指出:“人们是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的时间里结合在一起的”。[5](264)这样的双线并行结构不仅紧紧贴合作品标题“母亲”与“女儿”;同时,二者形象相互交错,各显不一,使得女主人公的人物形象被塑造得更加丰满立体。
作品以女儿斯韦特卡失踪开始,塔玛拉·伊万诺夫娜在到处寻访、起诉高加索人埃利达尔再到枪杀罪犯的过程中展现了一位可怜而伟大的母亲形象。寻访女儿朋友的过程中,母亲善于观察、冷静思考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得知女儿出事之后,前往检察院准备起诉高加索人的过程中,塔玛拉·伊万诺夫娜呈现的是一幅悲伤可怜的母亲的形象,面对佐科利的询问,母亲不仅“可怜斯韦特卡,而且也可怜自己。“逼问情况、索取细节——这无异于猛禽啄食女儿的心和自己的心”[1](75)但同时,听到女儿的回答,母亲“在极其痛苦中大叫一声”[1](81)之后立刻让自己的头脑恢复到清醒的状态,这一系列连续不断的过程描绘出一位具有高强度的忍耐力及超理智的母亲肖像。得知罪犯可能会被释放,塔玛拉·伊万诺夫娜计划自己动手惩罚罪犯,面对即将进行的杀人行为,她也流露出了一丝的胆怯惶恐,她在“走近那扇门的时候,她突然害怕起来,因为在她不在的时候,在那里,在那扇门里面,时间可能比这里,比在街上,过去得更快,那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1](108)尽管害怕,但面对检察长和罪犯的丑恶嘴脸,心中愤怒勇敢情绪上涨,最终选择射杀了罪犯。
另一方面,作品对塔玛拉·伊万诺夫娜从前的经历进行一番回顾,儿时纯真善良,原本母性性格经过父亲的雕琢,开始慢慢变得“坚如铁石”[1](35),她熟练使用枪支、拖拉机、拥有强烈的实践兴趣、对成长的奥秘产生好奇等一系列行为都在为人物形象塑造锦上添花。作品中谈道:“睡觉前,塔玛拉挂好门钩,站在昏暗的镜子前掀起睡衣,以一种极度的专注观察自己的身体……注视自己身体的每一处变化,而这些变化宣告着一个女人的步步临近”。[1](43)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作为“女儿”的形象出现时,作家将其塑造为一个充满青春活力,追求美丽的小女孩。对于女人的外表,她也有自身的审美观念,但从始至终,塔玛拉·伊万诺夫娜都是一个不赶时髦,信任旧东西的女人。她在“三十岁之前,她几乎一直梳着垂到背的淡褐色的长辫子——仅仅由于固执,由于反抗时髦”。[1](13)
在“过去”的时间轴线上,用母亲的人生回忆录,展现了母亲独特的成长历程,同时也是对后来母亲顽强冷静的性格成因作了一番解释——父亲的影响以及从小的生活经历。在辅线上,作者笔下的塔玛拉·伊万诺夫娜不仅是一位性格坚如磐石的“小伙子”,还是一位对女性奥秘激动迷惑的少女。正如杨爱华所言,塔玛拉·伊万诺夫娜的“形象一反拉斯普京笔下传统妇女的性格特点, 不再一味忍耐顺从, 而是充满了力量, 充满了行动力, 既具备了女性勤劳善良的特点, 又同时拥有男性果敢英明的一面”。[6](42)
作品利用非线性叙事结构,打破时间的顺序,“现在”与“过去”两条时间轴错落有致,“母亲”的形象与“女儿”的形象相互交叉,在这样的情节安排下,不仅使得整个故事情节更加丰满,内容朴实而内涵丰富,全面展现了人物的成长历程。同时,塔玛拉·伊万诺夫娜的个人形象更加鲜活立体,面对社会腐朽她勇敢果断,面对家庭她平凡细腻,人物形象塑造达到“去脸谱化”的效果。
三、现在与过去对比:深刻尖锐的社会问题
什克洛夫斯基指出:“艺术的各环节不相互重复,它们相互争论”。[5](398)在这部小说中两条叙事线并行的同时,避免不了二者之间产生强烈的对比。在“现在”这条轴线上,城市环境与“过去”时间线上的农村环境、现在的一代人与以伊万老父亲为代表的老一辈人之间的对比,揭示了尖锐的社会问题,传达了作者对时代变换、人心不古的批判,以及对祖国未来发展的焦虑。
拉斯普京是一个跨世纪的作家,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时代巨变,新时代的文化对旧文化的冲击更是力不可挡。这位西伯利亚作家看到了城市的快速发展,“如今,在各个方面都在进行这种外来的竞赛——从花花绿绿的服装到皮革……从性爱游戏产品到大众消遣产品,从随身带的小玩意到飞机发动机,从街道广告到国事演讲。所有这一切一拥而进,如入无人之境,把当地的东西挤到一旁”。[1](5)社会更新变化太快,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作家惊讶于此的同时又倍感苦涩,他心里产生巨大的落差。在拉斯普京笔下,当今的城市给人一种喧嚣繁杂之感,可这种喧嚣却把以往的朴实自然“挤到一旁”,作者以“镜子式”的手法直接将现实生活的发展变化呈现在读者面前,字里行间都明显透露了作家对这种“弃旧图新”的现象的不满与感慨。
小说中,作家对于老父亲伊万的故居安加拉河的草原美景是大加赞赏且向往的,塔马拉·伊万诺夫娜回忆道“安加拉河边的家乡,那长满白桦树和松树的广阔牧场,那路旁的白花繁盛的五月稠李,那在村子里四处飘散的甜甜的香气,那落花时节街道上如暴风雪过后的一片洁白,那将大地孕育在腹下的高远的天空,那位于西边的混浊而驯服的安加拉河的汛水,那荒凉的,却让人感到亲切的河岸……将你想要的任何东西清清楚楚送到你眼前……”[1](48)不得不说,拉斯普京以及其细腻的笔触将安加拉河的美景描绘得清新淡雅、和谐幽美,这与他自身的真实农村生活经历息息相关,唯有亲身感受过才能将其描摹得那么栩栩如生。而且,乡村的淳朴自然也与作家谦卑的性格互相呼应。我国学者任光宣在《我与拉斯普京》一文中谈道:“拉斯普京的这种谦虚和低调作风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7](71)万千美景融入了作家丰富细腻的感情,同时也交代了培育塔玛拉·伊万诺夫娜的生长环境。
“现在”与“过去”的对比,城市与乡村的对比,这样的描写这不仅只是简单的描绘环境。更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着作家的价值取向及浓厚的家国情怀,传达作家对过去乡村朴素自然生活的怀恋,以及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和担忧。可以说,“现在”主要是揭露社会问题,而“过去”则是作家的情感寄托。
在两种反差剧烈的环境下孕育着不同性格的人。在“现在”与“过去”的交错中,除了环境对比外,作家还将老一辈人与新时代人进行对比,老一辈人以伊万老父亲为代表,“他什么都会干,木工,钳工,造小船,摆弄各种机器,狩猎,在风雪交加的冬天去救援,在严寒中在雪地里过夜,会砌炉子,会唱歌。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多面手,他就像继承父亲的长相一样,自然而然地继承了父亲的灵巧能干”。[1](34)在安加拉河的哺育下,老一辈人身上形成了坚毅顽强的良好品质。并且,这种精神品质不仅在伊万老父亲身上得到传承,塔玛拉·伊万诺夫娜日后也成为一位能干、堅强的伟大母亲。
而时代的变换却歪曲了新一代年轻人的精神价值观,塔玛拉·伊万诺夫娜发现:“姑娘们在卫生间抽烟,弄得乌烟瘴气,人们在走廊里东拉西扯,无聊而虚伪,领班蛮横无理,操作间里弥漫着因电线短路而烧焦的气味”。[1](16)科技社会在不断进步,但人类的道德意识却在退化,作家在作品中多次谈及当代青年的精神面貌,在学校不再出现优秀生,“学习的愿望也消失了”。[1](61)新青年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领头人,却整日玩物丧志,不思进取,该现象引发作者与读者无限的思考及担忧,同时将现实直接暴露在大众面前,这也算是一种对社会发出的警醒。
在此,“现在”成为城市发展与当代人的象征,“过去”则是农村生活与老一辈的象征,二者的对比暴露了当代社会的尖锐问题,传达了作家对当代社会消极现象的批判,面对新时代年轻人的精神堕落,作家对未来俄罗斯的发展感到忧虑。
四、现在与过去角逐:时代发展的無可奈何
作品尾声以塔玛拉·伊万诺夫娜获释出狱结束,结局描写篇幅短小,寥寥数页却将作家的情感进一步升华。塔玛拉·伊万诺夫娜所在的监狱位于偏远乡村,她在这里的四年半时间,远离了城市的灯红酒绿,回归乡村,在这里获得心灵的救赎与宁静。从塔玛拉·伊万诺夫娜出狱到她进城回家的这段路程,作家放慢女主人公的脚步,进行了慢条斯理的细致描写,“已经是十月底了,天气还很干燥,还带着融融暖意。白蒙蒙的太阳疲惫地散发出微弱的略显色彩的光芒……林中一片寂静,没有生气;不知从什么地方随轻烟飘来一股好闻的气味”。[1](237)乡村的宁静和谐给刚出狱的女主人公带来些许轻松,让人有点流连忘返。但是,回家的公共汽车仍在慢慢驶来,以“山口”作为城市与乡村的界限,塔玛拉·伊万诺夫娜坐车路过山口,“广阔的城市一览无余,它像杂乱无章的废墟一样笼罩在灰色烟尘之中,闪烁着沉重金属的熔岩在废墟中流向四面八方”。[1](241)尽管城市拥挤压抑、消极颓靡,但是城镇生活却成了人们的梦想,城镇化趋势成为潮流,而乡村却成为了一座“空城”,这是大势所趋,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结尾作家又将城市与乡村进行了一番比较,虽然乡村生活令人向往,但是却不再是家所在的地方,城市成为人类前进的主要方向。进入城市,人类即将面临生活的无限压力,接触社会的黑暗腐朽,或许这便是塔玛拉·伊万诺夫娜一直“不急于回家”[1](242),发出无数声叹息,还唠叨:“时间太少了,只有这么点时间……”[1](244)的缘由所在。也正因如此,作家才会说:“我尽量不在城市里居住”。[10](21)既然无法阻挡这股潮流,拉斯普京就选择刻意回避,使心灵在浑浊的尘世中免受玷污。塔玛拉·伊万诺夫娜的结局与作家的追求存在反差,前者回归城市,后者留恋乡村,作家是以何种心情将女主人公的人生作此安排,内心的无可奈何溢于言表。
拉斯普京的无奈不仅表现在该作品中,仔细品味作家的其它作品,字里行间都蕴含着“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对即将面临的社会大灾难的忧患和反抗;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 即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科技的发展、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也使人类失去了一些不能复得的东西”。[9](31)作家不囿于慨叹社会发展潮流,还对人类精神品质退化产生无奈之感。淳朴的自然环境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失去了其本真之美,这种变化也在人类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自然的世界越来越走向了人为的、虚拟的世界,现在轮到它来摧毁人的世界了”。[10](21)简洁而精妙结局安排将作家内心深处的百般无奈表达得淋漓尽致,作者对过往乡村生活的向往被现实拖拽回来,对于当下的社会发展趋势无能为力,作家以其细腻的情感浸染读者,引发读者的深思:“在这迅疾变化和充满诱惑的时代,作为人是否应该固守一点什么?”[1]
结语:
巧妙的叙事安排有利于美化作品结构,揭示作品的深刻含义。在《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拉斯普京利用时空的错乱,打破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以双线并行的方式使内容更加丰富且具有跳跃性,作品的思想意义更加深刻。以“现在”作为叙事主线,小说整个的叙述环节都围绕主线展开,万变不离其宗。而辅线则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丰满了人物形象,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则传达了作品背后深刻的内涵底蕴及情感价值。“现在”与“过去”犹如交谊舞的双方,二者相互配合,相互切磋,使整部作品犹如一段完美和谐的舞蹈。
参考文献:
[1][俄]拉斯普京: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M].石南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古希腊]亚里斯多德:亚里斯多德《诗学》《修辞学》[M].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张秀娟:电影的非线性叙事[D].兰州大学,2010。
[4]李纾淇:论《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叙事时间特征[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5][苏] 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下)[M].刘宗次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
[6]杨爱华:塔马拉·伊万诺夫娜的“双性气质”——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伊万的女儿 ,伊万的母亲》[J].俄罗斯文艺,2008年第4期。
[7]任光宣:我与拉斯普京[J].俄罗斯文艺,2006年第3期。
[8]孙为:新媒体语境下的非线性叙事时间初探[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9]乔占元:拉斯普京小说的悲剧意识[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年第10期。
[10]林立:“文学的最大悲哀是失语”——瓦·拉斯普京访谈录[J].外国文学动态,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