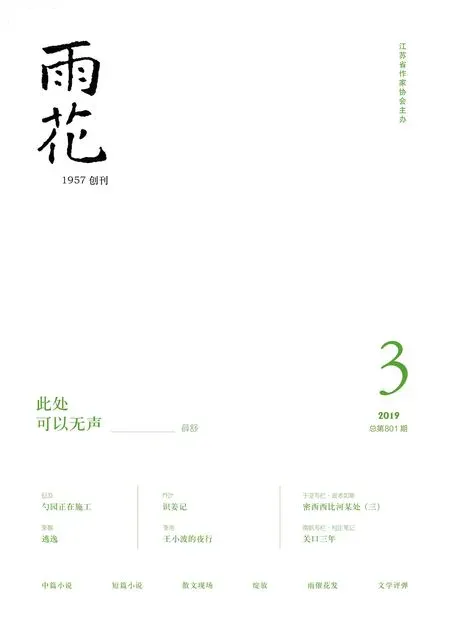王小波的夜行
1.重写的传奇
王小波《夜行记》写下的是“故”事,小说的第一句点明它的发生年代:“玄宗在世最后几年,行路不太平……”这篇小说可以说是“幻设为文”,属于“搜奇记逸”之类,极富传奇性。它最早收录于王小波在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小说集《唐人秘传故事》中,标明,它和“唐传奇”之间有着显见的联系,是对唐传奇“重新注入”式的改写。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丰沛的游戏性和想象力的驰骋,小说的趣味性魅力得到彰显——在我看来,这是贮含在小说中所谓的“稀薄的文学性”,值得重视的文学性。
我愿意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小波小说中的“传奇”。
艾柯说两类人“适合”当作家,一类是农民,一类是水手。所谓农民,它强调的是对“本地掌故的了如指掌”,是对本地生活的熟悉和熟知,它本质上可以看作是“现实主义”的;而水手,则代表的是传奇,是对你所不熟悉、不掌握和不了解的生活的构想和再造——水手离乡远走,他闯入的是一个你完全陌生的、具有冒险性和传奇性的世界。在那个你所不熟悉的世界里,水手具有“信口开河”的机会,他可以夸张、再造,甚至可以捕风捉影,“疑神疑鬼”:在聆听水手所带回的那些故事时,它的诉求不是你的确信,而是传奇性、紧张感和故事的魅力,在聆听这类故事的时候你很可能不那么在意“它是不是真的”,这一点变得不那么重要。大约没有人追问《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是不是真的发生过、在哪里能寻到发生时的遗迹;大约也没有人追问孟姜女是不是真的从葫芦里诞生,她哭倒了长城之后是不是化成了鱼,荷马《伊利亚特》的史诗中是否真的有神灵参与了战争,以及特洛伊的战争是否真的由金苹果而起。
在“人”没有居于问题和认知的核心的时代,在“神灵”或“上帝”参与着我们的生活和命运的时代,水手们讲述的故事更深入人心,在人们的心里面“外面的世界”才是更值得关注的,而“我们那么小,那么微不足道”。在整个人类的“童年时代”,传奇性的、搜奇记逸的故事充斥着我们的文学,幻觉和想象充斥着我们的生活,然而随着科学的前行,“人”慢慢地居于了认知的核心,问题的核心,人们习惯着上帝的死亡,同时习惯着“地球是平的”,习惯着实证,习惯着认为科学能够做到一切解释一切,那种所谓的“未知区域”经受着不断的挤压,“众神”也走向了他们的黄昏。在这一认知进程中,“现实”逐步进入到聚光灯下,我们开始愿意安静下来聆听和打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种种事件,愿意反思和追问人性的问题,社会生活的问题,在群体之间以及所谓的时代性……“现实”发展成为“现实主义”,更具有“农民”性的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一种普遍,而“水手”的传奇讲述则在一定时期内日渐式微,他们无法在科技发展到如此的时候再讲述新的、正发生着的关于“龙”和“怪兽”的故事,它遭遇到知识的侵蚀,人们和讲述者自己都开始“不信”。
“人类社会的童年时代早已过去,那时自然和非自然,事实与想象,好像几个亲兄妹,在一个家庭里玩耍吃喝,长大成人。今天,它们发生着巨大的家庭内讧,这是连做梦也没想到的。”泰戈尔在他的《历史小说》一文中发出感慨,在那篇文字里,他试图呼吁某种的“重新融合”,让现实的小说为想象、幻觉和非自然留出容身之地……这一吁求的声音是微弱的,突飞猛进的科学呈现出一种摧枯拉朽的强势,它让人确信(至少是部分地确信)未经科学检验的、认知的知识都是“伪知识”“伪经验”,科学挤占了宗教的神坛而成为一种更被知识界普遍认可的新宗教。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人类渴望一个善恶能够被清楚地区分的世界,因为他有一个天生的、不可扼制的愿望,就是要在他理解之前做出判断。”——这一天真是始终伴随着人类的,科学对它的改变远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巨大,反而增强了人类的傲慢。“在现代世纪的进程中,笛卡尔哲学的理性一个接着一个地腐蚀了所有从中世纪传承下来的价值。但是,正当理性记得了一个完全的胜利时,纯粹的非理性(力量决心实现它自己的意志)占领了世界舞台,因为已经不再有任何普遍接受的价值体系能阻塞它的道路了。”(米兰·昆德拉《被遗忘的塞万提斯的遗产》)
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或多或少使得人类的科学迷信发生着摇晃,科技的精进一方面加速着人的异化进程让个人的存在逐步成为“物”和“数字”,个人性的消弥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深渊;而另一方面,人类的某些愚蠢和荒蛮并没有随着科技的前行而发生根本的改变,恰恰相反,冷冰冰的科技可能和荒蛮联合而将人类拖向更为阔大的深渊……如果说“众神离去”曾带来过黄昏,“上帝之死”是人类信念的一次崩塌的话,那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的人类战争则让人们的信念又一次产生着崩塌的怀疑,科学和理性(或以理性之名)不再具有准宗教的力量,它在摇晃中出现的缝隙则几乎必然地塞入了另外的填充物。在这一境遇之下,泰戈尔所吁求的“重新融合”开始奇迹地、普遍地出现和被人接受,想象力、特别是具有传奇性的想象力得以重回这个大家庭并和现实同居一室,诞生出“梦和现实巧妙结合”的新生儿,像卡夫卡的《城堡》,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胡安·鲁尔福的《烈火平原》和《佩德罗·巴拉莫》,让·保尔·萨特的《苍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若泽·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卡达莱的《梦幻宫殿》……它几乎可以无限地枚举下去。
对于阅读者来说,我们可能接受一个建筑在我的理解限度之内的现实世界,也可能会接受一个超出我想象范畴的水手世界,我有时愿意在某种写作中“照见”我的生活、重新审视我的日常经验,有时却更愿意从日常的平常甚至平庸中短暂脱离而进入到想象和传奇的世界里。然而那种割裂依然强劲,习惯以知识替代了僧侣们的权威的知识者们或者威权人物更愿意将小说中的知识“翻译成”他们所能理解和懂得的语言,而某些被教育僵化着的头脑则更愿意接受那种“翻译成”的知识,并与流行思想保持一致。是故,在苏珊·桑塔格看来,“在现代大多数情形中,阐释无异于庸人们拒绝艺术作品的独立存在。真正的艺术能使我们感到紧张不安。通过把艺术作品消减为作品的内容,然后对内容予以阐释,人们就驯服了艺术作品。阐释使艺术变得可以控制,变得顺从。”——在这一驯服的过程中,只容留“农民”而抛弃“水手”,只容留现实而回绝幻觉和想象,把艺术作品中的丰富、歧意略去只剩下可怜的“社会学知识”,则是更为便捷有效的做法,当然也是使得文学更为贫瘠的做法。
“哲学理论,如果它们是重要的,通常总可以在其原来的叙述形式被驳斥之后又以新的形式复活。”罗素的这句话在我看来用在文学和文学形式的变化上也同样有效,当我们的“外在世界”过于庞大而我们又那么弱那么微不足道的时候我们更愿意依借“水手”们的冒险和传奇建立我们的世界想象、命运想象;而当我们身边充斥着种种构建地球是平的、我们的日常是平的的新闻纸,当我们的“农民”性写作被推至一个峰巅的时候,属于“水手”的、想象的和传奇的则得以复活。在这种螺旋上升中,传奇的、想象的当然不会是旧样貌,它会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同时具有了“现代”的可能。
谈及王小波的“唐人传奇”,我愿意将它和鲁迅的《故事新编》做某种比较。它们都立足于传奇性的“变异之谈”,是对中国旧有的传奇故事的改写,也都有属于自己的“重新注入”,正是这份“重新注入”让它们改变了原有面貌而具备了现代性。王小波和鲁迅的“故事新编”,都不是仅仅在原有构架下的肌肤的丰满,而属于再造,是完成的现代小说,具有现代意韵、现代意识和现代审美的小说,就像让·保尔·萨特的《苍蝇》重新改写了希腊神话中俄瑞斯忒斯的故事,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哈德良回忆录》以一种现代眼光改写了哈德良国王的故事那样。
鲁迅的《故事新编》有一种有意的系统性,它试图“串联”中国的神话和传说,有一种时间上的延续性;而王小波则专注于“唐传奇”,专注于“唐之传奇文”的故事提供,对它完成个人再造。鲁迅的《故事新编》依然有着某种凝重,他侧重于负载,而王小波的“唐传奇”系列则立足于轻逸,有趣,更注重腾跃之美。鲁迅的《故事新编》夸张感并不重,他甚至有意“落实”,为原有的故事增添着生活化的细节,而在王小波这里,则是在夸张处进行再度的夸张,在飘逸处进行进一步的飘逸……
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仿若是活的泉水,它总是为后来的写作提供原始支点,又允许作家们不断地注入新的阐释,成为一个个有深意、有启示的新故事,其中不乏经典。而中国的神话、传说在改造上则难度巨大,一是它们多是支离的、零散的,往往一个故事、一则神话只是“一件事”,缺少连续感,二是它们的内在贮含相对简单平面,和现代性的“兼容感”很弱,对它的注入很难达到某种精神高度。在我的理解中,鲁迅写作《故事新编》绝非单纯是什么“猎奇捕异”,他其实更希望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中国神话和中国传奇也具有和希腊、罗马神话传说同样的活力,让我们这个民族的神话与传奇“重新复活”,并成为河流……在我看来鲁迅的《故事新编》是“未完成”状态,大约和鲁迅自己的期许也距离甚远。他多少还有对原故事的拘泥,未敢走得太远,而中国传说多数只提供事件而没有对人性的、社会的描述勾勒,添加太多的丰富素材也确实会让它完全地失去原貌,起不到呼应。对于王小波来说,他大约也有让中国传奇“现代化”的诉求但绝不像鲁迅那样强力负重,他的个人趣味更让他着迷于“夸夸其谈”的奇诡,想象力的无拘伸展,或多或少确有“形式大于内容”之嫌。
2.故事讲述
在传统的传奇故事中,往往会有一个全知的讲述者,他告诉我们故事的来龙去脉,发展走向,致力于把故事讲得曲折起伏,波澜丛生;与此同时,这个讲述者往往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他所讲述的内容往往是“搜奇记逸”,似真似幻——你不能把它当真实的发生看待,因为它总有对日常的轻微溢出;但你也不能完全不把它当真实的发生看待,因为讲述者往往信誓旦旦地说他讲述的都是真的,他总想说服你让你相信。王小波的《夜行记》有意沿用着传奇故事的这一惯常,他充当着那个全知的讲述者。在这个全知的讲述中,我们看到王小波一方面全知地介绍故事,一方面将自己的身位和那个书生相互重叠:这个讲述者能够听得见、读得到“书生想”,反复的“书生想”,“书生气坏了,心说”……书生的心理波动是全被掌握的。而和尚的心理他则没有进入过,和尚在小说中有行为有动作有话语,但没有心理,除非他说出自己是怎么想的。全知的讲述视角为他建立了进入到和尚心里去的捷径,但王小波有意没用。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用?一,如果讲述者反复地进入“双方”的心理,向我们揭示他们的所思所想,就会把故事的紧张感和趣味性冲淡,等于是在猜谜的时候早早地公布了答案;二,它只进入书生,反复地强调书生想、书生想,其实也是把我们从旁观者拉入到故事里,和书生一起感受,让书生所想的与我们所想的联接起来,而这时一旦进入到“和尚想”就会造成混乱,破坏掉阅读者和书生之间建立的“视角契约”,也会冲淡故事的紧张感。三,不进入和尚的内心,他也因此获得了神秘感,而这神秘感是传奇所异常倚重的一点。所以在《夜行记》中,一个人(书生)一直心潮澎湃,而另一个人则口若悬河,却没有向阅读者展示他的内心。
在传统的传奇故事的讲述中,“奇”是重要的支撑点,它尽可能是奇闻奇人奇事,或有灵异,或有神怪,至少是某种常人难以达到的奇特……王小波的《夜行记》同样延用了这一惯常,这里的书生便是怀有绝技的奇人,而那位在前面摇头晃脑、一而再、再而三总是打不到的和尚则更是奇人中的奇人。而故事中支撑起“奇”来的,则是和尚的不断盘升着的讲述:“比如老僧在静室里参禅,飞蝇扰人,就随手取绿豆为丸弹之,百不失一,这就略得射艺的意思。夏夜蚊声可厌,信手撅下竹帘一条,绷上头发以松针射之,只听嗡嗡声一一终止,这就算稍窥射艺之奥妙。跳蚤扰人时,老僧以席蔑为弓……”“如果以剃刀在青竹面上剥下一缕竹皮,提在指间就是一柄好剑。拿它朝水上的蜉蝣一挥,那虫子犹不知死,还在飞。飞出一丈多远,忽然分成两半掉下来……”“有一位大盗以北海的云母为刀,那东西不在正午阳光下谁也看不见,砍起人来,就如人头自己往地上滚,真是好看!还有一位剑客以极细的银丝为剑,剑既无形,剑客的手法又快到无影……”也难怪书生觉得这和尚“吹得真是没谱了”,也的确是有些没谱——而这“大夸张”,这“没谱”,恰是王小波在小说中所要的,它展现的是想象力的奇诡,具有某种让人会心和意外的艳丽。在这里,他不要你信,但和尚所展现出的那部分“能力”又让你对自己的不信发生怀疑,就像《夜行记》中那个书生的怀疑那样。王小波用书生与和尚的“奇”,为和尚所说的内容做佐证,衬托它的“更奇”,将它继续地垫高。在书生、和尚与传说的大盗侠客之间,有一个层层向上的阶梯。
进入到故事。开头部分是介绍性文字,王小波将书生的出场放在夏日,关中,不太平的空旷。那句“见到路边躺着喂乌鸦的死人,还是免不了害怕”让我联想至伊塔洛·卡尔维诺《分成两半的子爵》的开头,他们都用一种轻质的、洗清了血色的平淡书写着死亡,不渲染,而且一掠而过。小说谈及书生“不想和车夫谈话,因为他们言语粗鄙,也不想和轿车里的女人谈话,因为她们太蠢了”——这句话说得政治很不正确,但在这里却是恰当的,它是那个书生的所思所想,而且“符合”那个年代的一般认识。
书生期待遇上同行的人——同行的人出现(和尚)——书生并不喜欢:几句话波澜就起了,它构成了叙事的张力。书生期待到和尚出现,这是顺接,而书生不喜欢这个同行者则又变成小小的逆向,它为故事性撑开空间。王小波从书生的角度,找出了两个不喜欢的理由,而第二个“和尚太肥,连脑后都堆满了一颤一颤的肥肉”则为之后书生用弹弓朝和尚后脑射击埋入伏笔。
故事行进很快,总体而言《夜行记》的故事行进是快的,它没有特别的渲染和停留,就是书生的所思所想、和尚的夸夸其谈也都没有粘滞感,它是“讲故事”的那种普遍方式。书生挑起话题,不太友好,但和尚却是顺接的,他卸掉了书生话语中的用力,这更增加了书生的不喜欢:“这和尚恁地没廉耻!”又一次的顺接和逆向,小波澜再起一层。接下来是纠缠性的环节,和尚非要和书生同行,这一次的波澜起在了书生的心里。在这时,波澜还都是微的小的,一些小摩擦或者小计较而已,何况和尚的态度又总是“化开的”,你无法表现出气恼和愤怒。
和尚开始滔滔不绝,这是故事中波澜推进的一个重要策略,这一点很不同于以往的传奇小说——在《夜行记》中,和尚的言说构成叙事的中心部分,它完成波澜的起伏与转换,影响着书生的行为和故事的走向。作为“话多的男人”,王小波有意安排他“旁若无人”,几乎是自己在言说,完全不顾及“听众”的感受——然而我们对作为听众的书生心理上的种种变化却一清二楚,王小波为书生的心理变化安排了一个极为有效的“外置话筒”。不肯回头、滔滔不绝的和尚其实也熟谙书生的心理变化,他所要的,就是这些。“你说东,我说西,你说鸡生蛋,我说蛋生鸡。说急了你打我我就露几手把你吓跑……”我们来看,和尚是如何将书生给“说急了”的,而他又都是如何去打他的。
和尚先谈女人,地域性给女人带来的差异等等:和尚为什么不谈天气和时事?不谈佛学?为什么不直接谈骑射引诱书生“心时发痒”以便让他出手?这里其实有一个阅读上的心理预期,和尚谈天气谈时事未必不会让书生觉得蠢,而谈佛学又未必让书生觉得有趣有共鸣,它会让话题僵住;而直接谈骑射则又突兀,书生的情绪和我们阅读者的情绪都不会随之调高,而谈女人,则会强化书生对和尚的某种反感,让他在后面合理地出手而不含太多愧疚——反正我打死的不过是一个花和尚,他本来该死,我杀他杀得心安……是故,我们看到小说中几次谈到书生“心里发痒”,随后是“心里痒得厉害”,再是“心里又发痒”,它其实含有情绪的波澜变化。书生谈射雁、射雕、射雉、射雀,和尚谈射苍蝇、射蚊子、射跳蚤——有了前面的情绪铺垫,这时书生心里已经是“奇痒难耐”。他的“奇痒难耐”是因为他也是个有技能的奇人,自恃有本领,当然“容不得”和尚胡吹。他的“痒”里面也含有“技痒”的意思。但这时时机依然未到,王小波知道书生心里的“奇痒难耐”也适用于我们,他偏偏不立即遂我们的愿,而是“耐心地”安排好书生和和尚的车仗家眷,“耐心地”让和尚和书生继续谈论剑术。和上次一模一样,“这也是书生心爱的话题”,在这里王小波有意让书生再次表现出行家的质地,接着让和尚否定:这不算什么,只能说是凡品……和尚话的“没谱”和里面带出的取笑意味让书生“心里又是一片麻痒”——在书生心里的“痒”发生了几次并变化了几次之后,他出手了。
当然需要夸一下书生的本领和他的弹弓,弹丸,这在小说中是惯常的做法,却也是暗含着“规定性”的做法。没有这个做法,后面和尚的轻易躲避就不具传奇性和惊艳感。
……略去二人之间的对话和书生的心理波动,小说中说得明白。王小波安排,书生又偷偷落后,拿出弓来,然后是第三次——在这里我想我要重审一般小说故事设计的叙事原则:一,“压低”主人公,让他的欲求变得强烈,成为不得不发;二,要有波澜上的设计,一般而言至少有三层或以上的波澜,波澜尽可能地多,要穷尽全部的可能;三,一般而言波澜设计应当由低到高,它要有顺序和层次感,个别设计会有小的调整,但大方向如此……《夜行记》中,书生心里几次“痒”的变化是铺垫性的,它让书生用弹弓打和尚后脑的欲求变得强烈,而后有了一共三次的弹弓使用。
第一次,一弹。在这里未做太多的交待,只说“书生悄悄落在后面去,偷手取出弹弓,照和尚脑后一弹弹去。”和尚通过晃脑躲过。
第二次,一弹,有了祝祷,同时书生咬紧牙——小说还强调“他放这一弹时格外的小心手稳”,书生的心理重视有了升级,暗含的力量和精心也随之升级。这次,和尚不是在月光的亮光里,而是“刚好走到阴影里”。再次安然。
第三次,连环弹。小说有意略掉在书生那里的波澜上升,但连环弹已说明问题。这次,黑暗又一次加重,由平常的月光之下到阴影中再到“周围伸手不见五指”,王小波还“帮助”书生把和尚的马勒住,而和尚的“喋喋不休”又恰好让他的位置有所暴露。似乎已万无一失,“就是神出鬼没的黄鼠狼,也逃不开黑暗中袭来的弹雨”——然而和尚却又逃开了。和尚的能力在三次“躲开”的过程中得到阶梯性的验证,它也是一次比一次更难。
埃德温·缪尔在谈论创作技巧时说过,对作家而言,“他可以不知道这些法则,关键是他应当遵守这些法则。”事实上有些基本的法则对于小说的设计是非常有效的,它不仅会在那些现实主义小说中得到运用,而且在现代主义小说、后现代主义的小说中也能见到它的存在。技巧可能已“改头换面”,但法则还在,它在后面进行着影响。在我看来影响小说的技巧法则的主要因素来自心理学——阅读者的心理期待、接受方式和接受程度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这些法则的形成与使用,优秀的作家一定也是一个优秀的心理学家,尽管他们未必能细细说出有关心理学的诸多名词,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可以不知道这些法则,关键是他应当遵守这些法则。”
继续回到小说的叙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打不中。书生“心里还在发痒,他真不乐意世界上有和尚这个人”——可是没有办法,他还在那里。和尚找个理由让书生下来看自己的马,然后“消失”,可偏偏书生是个“死心眼儿”,他又追了十里路才重新追上和尚。这一次,他们“各自想心事,再也不交谈。”走着,被小说忽略很久的书生的家眷和车辆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车夫在打瞌睡,而“老婆丫环在里面正在熟睡”——小说到这里主体的故事已经结束。但小说却不能结束在这个点上,因为它是下滑的,是叙述力量的“泻”,假设小说停在这个点上结束的话它会对整个故事构成“下拉”,之前的那些生动有趣、风生水起都会遭到部分的“消解”,不符合我们的阅读期待。没有作家敢于轻视小说的开头,同样没有作家敢于轻视小说的结尾,它是极其“较劲”的部分,要尽可能地盘向高点,尽可能地延宕起回声,尽可能地让阅读者感觉到回味。于是,《夜行记》安排死心眼儿的书生继续去追他打不死也打不过的和尚,一个夜晚在同行中过去,他们来到旭日东升的山顶。
想明白了。书生与和尚,都想明白了。
“这一僧一儒互诉心曲以后,就一起到和尚家里去。和尚要招待书生,把他当成最好的朋友。”
3.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和尚的车仗去了哪里?小说的开头部分,第二段即谈到“和尚骑着骡子,护送着一队车仗。轿车里传出女人的笑语”,后面又借和尚之口半真半假说道“老衲要出门云游,家眷放在寺里就不能放心,只得带了同行”——他的车仗是小说中一个支撑点,书生对他的“不喜欢”也由此而起,然而我们在阅读中却发现它在用过之后便遭到了“遗弃”。书生的家眷车辆在后半段被我们重新“看见”,但和尚的车仗去了哪儿?
王小波没有忽略。在小说中段,书生用弹弓射击和尚后脑之前王小波先做了一个安顿:和尚说“我们不如叫家眷车仗先行,自己在后面深谈”,这里虽然不尽合理(两个人都不再尽护卫之责)但也说得过去——传奇故事时常有对现实的“溢出”,有不被追究的部分,它甚至构成传奇小说的惯常——在书生打出第三弹之前,王小波再次安置了和尚的车仗,“相公,这是去我家的路,老僧一世也没有见过比你更有趣的人。所以要请相公到寒寺盘桓几天,宝眷和行李走了近路,现在已经到家了”……
小说中还有这样的叙述:车夫听见马蹄响抬头一看,见到这一僧一儒,吓得翻白眼,这一夜他经过不少惊吓,吓得再不敢说话,之后又说书生到轿车前撩开帘子一看,老婆丫环在里面正在熟睡。接下来还有一句妙语:“这些人可享福啦,车一进山就睡着,到现在还没有醒。”这里面有着丰富的暗示,它有着太多的“言外”了:车夫见到一僧一儒,本应是喜,在这里却是吓,它说明之前发生的事确有其“惊吓”之处,而且多少与这僧有关(僧不在场,那就与僧的家眷有关);车夫受到如此惊吓,而书生的老婆、丫环却睡得如此地熟则很不正常,联想我们在中国传统的传奇小说和武侠小说中的惯常,她们应是“着了道儿”,中了迷香或迷药之毒。谁下的毒?
和尚不在场。两个车仗是一起向前行的。它再次间接地暗示,和尚的所谓家眷更是“同伙”,她参与到过程中并让车夫受到了“不少惊吓”。这埋伏有些深,如果不停下来思量一下的话,它很容易被跳过。
在我看来王小波没有忽略但有疏漏——我觉得和尚的车仗是一个很重要也是很有意味的点,它应当被用足。如果是我来书写的话,我会让它更多地参与到故事中,形成另一条与一僧一儒的故事相呼应的线。他这样写,是“照顾”了和尚的车仗为它安排了去处,但属于一种差强人意的“减化”,有“招之即来、用过即弃”的小随意。它当然不能夺走一僧一儒这条线的光,也不会夺走,对它的加强只为增加丰富和层次,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任何一条线的出现都应尽可能地用到用足,而不应在轻描中淡淡抹去。这是我个人的“在我看来”,它包含着一个匠人的技术要求,也包含着一个有偏见的人的偏见。
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紧密相连,更多地,我是问向我自己的:《夜行记》中,和尚的那些夸夸其谈,射苍蝇、射蚊子、射跳蚤,云母为刀、银丝为剑,他对书生弓弹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躲过,这些夸张的甚至夸张到“没谱儿”的叙述我没想过“追究”,为什么在阅读中却对和尚的车仗“念念不忘”,非要追究它去了哪里?
这个问题大约和莱辛在《拉奥孔》里“为什么拉奥孔在雕刻里不哀号,而在诗里哀号?”“为什么造型艺术家要避免描绘激情顶点的顷刻而诗歌则不受这一局限?”的问题相类似。它完全来自于艺术的内部,其间的差异并不那么大,我不得不细致而审慎地对待它。
我为什么不追究和尚的夸夸其谈,难道仅仅是书生在小说中反复指责它“吹得真是没谱了”而让我放弃了追究的戒心,我就把它当成是“没谱”的戏言而不用认真对待了吗?有这个成分在,但不完全——因为它和“和尚的车仗”还是有所不同的。和尚的夸夸其谈是语词性的,它当然可真可假,可以容纳进一步的虚构与夸张,而“和尚的车仗”则在小说中属于实的部分,是建筑性的,它需要接受小说再造的真实里的“必然后果”。每一篇小说,无论它是荒诞的、魔幻的、梦魇的或传奇性的,只要它在小说中设定了真实和与它相关的限制词,那它就必须从一而终地遵守下去。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令人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那种甲虫性就必须紧跟着他,他就得拒绝属于人类的食物,就得用硬颚来笨拙地开门,无论是谁,一口牛奶也不能再让他(这时应当是“它”)喝到肚子里去;没有谁可以和戈耳工的女妖美杜沙对视,任何被她所“看见”的事物都会变成石头,那柏尔修斯也不会例外,他想要杀死美杜沙就必须想到回避与之对视的办法。在这里,在《夜行记》中,和尚可以精于武术身怀绝世武功但没被赋予“无中生有”“乾坤挪移”的本领,那,我就不得不追究“和尚的车仗”去向的问题,因为它的疏漏很可能会破坏掉文本的自洽。
第三个问题:小说最后,书生说他“想明白了”,这个想明白的是“杀人不是好游戏,无论如何,不要杀人。”而和尚也“想明白了”,这个想明白的是“抢劫不是好游戏,无论如何,不要抢劫”——我的疑问是:他们俩真的是依借二人在路上的“斗法”想明白的么?那个“斗法”真的会导致“杀人不是好游戏”“抢劫不是好游戏”的结论么?这里有没有牵强之处?
当然有它的牵强。不要杀人、不要抢劫是惯常的道理,根本不需要用什么“实证”来验证,这一僧一儒既然之前不顾及这样的道理,那杀人不死就悟到“杀人不是好游戏不要杀人”、把人吓不跑就得出“抢劫不是好游戏不要抢劫”的结论是立不住脚的。立不住脚,可王小波却利用着“逻辑漏洞”津津有味地得出了如此的结论——这也是他惯常的做法,他时常很“一本正经”地推断、证明某事发生或者不发生的种种条件,然而在他“严密”的推理之下我们发现这套由他使用的逻辑根本无法证明什么,并且常与我们所知的事实相悖。譬如在《黄金时代》中:“春天里,队长说我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眼,使它老是偏过头来看人,好像在跳芭蕾舞。从此后他总给我小鞋穿。我想证明我的清白无辜,只有以下三条途径:1、队长家不存在一只母狗;2、该母狗天生没有左眼;3、我是无手之人,不能持枪射击。结果是三条一条也不成立。”“陈清扬又从山上跑下来找我。原来又有了另一种传闻,说她在和我搞破鞋。她要我给出我们清白无辜的证明。我说,要证明我无辜,只有证明以下两点:1、陈清扬是处女;2、我是天阉之人,没有性交能力。这两点都难以证明。”在《夜行记》中,王小波也多次如此“一本正经”地推论着,直到最后。它是牵强的,转折得有些生硬,甚至有些特别“高调”。可王小波却让小说的结尾停在这个牵强带出的结论上。
且慢结论,或者我们应当且慢结论——在王小波的随笔中,我们随时可见这样的表述:“理学越兴盛,人也越虚伪”(《关于崇高》),“对于什么叫美好道德,什么叫善良,我有个最本份的考虑:认真的思索,真诚的明辨是非,有这种态度,大概就可算是善良吧。”(《知识分子的不幸》),同时他也对那种道德诉求作为文学的第一诉求的做法表示过反感,他认为这是“把马鞍子套在马头上”……让一个传奇故事在结尾处落在“拔高”的结论上,是中国传统笔记小说、传奇小说甚至世情小说的惯常作法,有些属于“狗尾续貂”,而有些不过是硬性地拔高,诸多本是格调俗下、有诲淫诲盗之嫌的小说也会“以阐明因果自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自己添置岸然道貌。王小波在自己的随笔中也提到过一个他从明清笔记中读来的《奸近杀》的故事,“寓意是好的,但有点太过离奇:癞蛤蟆吃蚂蚱,都扯到男女关系上去,未免有点牵强……”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解读,王小波故意“一本正经”地、按照旧有的传统样式为这一传奇“戏仿性地”安排了感慨和结论,故意“一本正经”地谈论“杀人不是好游戏,无论如何,不要杀人”“抢劫不是好游戏,无论如何,不要抢劫”,其实这里面暗含反讽,他要的更是这反讽的存在,就像塞万提斯在《唐·吉诃德》中所做的那样。他试图深入在这类叙事中,一本正经地跟随它们搭建,“从内部”拉动它未曾衔接的线头……
“这一僧一儒互诉心曲以后,就一起到和尚家里去。和尚要招待书生,把他当成最好的朋友。”也是戏仿性的,它戏仿的是那种大团圆的结局,“从此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游戏性和幽默感
“有必要记住的是,尽管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有他或她的风格,但只有这个或那个独特的天才作家所特有的风格才值得讨论。这种天才如果不存在于作家的灵魂中,便不可能表现于他的文学风格中。”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他的《文学讲稿》中如此强调。我非常非常认同这一说法,所谓“有风格”的写作也许并不那么少见,但真的是“只有这个或那个独特的天才作家所特有的风格才值得讨论。”
在我的有限视野中,王小波应是具有特有风格的独特的天才作家。那种强烈的游戏精神,以及同样强烈的幽默感让他的小说具有鲜明的风格,同时也具有独特的魅力。
“浪漫骑士”,这是一些阅读者对于写作中的王小波的命名。在王小波的小说中,我们看到它始终充溢着强烈的游戏精神,“游戏性”是王小波小说极为显见的特色之一,可以说游戏性笼罩了他的整个小说,而每个段落、每个句子也都可见那种游戏的构成。游戏性,把游戏性“放大”到如此,在我们这个习惯着“文以载道”、习惯着以一种正襟危坐的姿态“坐而论道”的国度其实是极为罕见的。他是林外的树,他是一个独特的、特有的存在。这篇传奇性的《夜行记》,我们当然可以读出“游戏”的丰盈,他甚至游戏性地让书生说出“杀人不是好游戏”、和尚说出“抢劫不是好游戏”这样的话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王小波的文本游戏中不乏严肃性,譬如他在《黄金时代》中谈论的是对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影响至深的“历史”和“时代”,而在“世界是银子做的”之《白银时代》,“我”出现在一家写作公司里面,反反复复地书写着一篇名为《师生恋》的小说,在这里他本质要谈论的依然是“威权”对人的影响以及施威者和受虐者双双出现的“迷恋”。《未来世界:我自己》中,第一章的开头即是游戏性的:“我被取消了身份,也就是说,取消了旧的身份证、信用卡、住房、汽车、两张学术执照。连我的两个博士学位也被取消了。我的一切文件、档案、记录都被销毁……”可以说王小波的小说里充满着荒谬、荒唐、信誓旦旦的胡言乱语,充满着“喜剧的恐惧”,也充满着对权力、时代、命运和个人性的严肃反思。然而王小波严肃言说的却始终是“满纸荒唐言”的喜剧面目,他游戏地对待着那些所谓的严肃话题,用一种陌生的、极有魅力和荒诞感的方式来呈现它。他的方式,就像是把药裹进糖衣里,我们可以在那种游戏性中、想象力的飞升中获得快感,进而引发思忖。
王小波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任何一种严肃话题,任何一种我们不得不直面的险峻话题,其实都可以以一种“游戏”的样式呈现,它“改头换面”,以一种有趣的、游戏的、卓有荒诞感的方式出现,它未必遵守这个世界和时代的所谓“真实相貌”,然而依然可以说出他“遮遮掩掩的真情”。
强烈的幽默感又是王小波风格的一大特色,他的幽默时常会让我这样的阅读者忍俊不禁,我感叹他无所不在的幽默感,感叹他幽默方式的多重多样。幽默,对王小波的小说写作具有结构性意义,它不仅是趣味和吸引,里面还包含着智慧、超越性和悲悯,它或许还像巴赫金所指出的那样,具有深刻的世界观意义,“这是关于整体世界、关于历史、关于人的真理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这是一种特殊的、包罗万象的看待世界的观点,以另外一种方式看世界,其重要程度比起严肃性来(如果不超过)那也不逊色。”也正是基于这一点,米兰·昆德拉才会笃定地说,缺乏幽默感、对流行思想的不思考和媚俗是小说的三大敌人。
在《夜行记》中,“幽默”几乎密布于小说的每个段落,如果需要摘抄的话我将不得不把三分之二的小说重新抄在这里。王小波的幽默更多是康德所说的理性的“妙语解颐”式的,他甚至创造性地“创造”了一种极有幽默感的推理方式,它貌似一本正经,貌似是逻辑性的,但我们顺着这条煞有介事的逻辑链推衍下来得到的却是喜剧性的荒谬,甚至有时是对常识明确的悖反:“别的不要说,捉个跳蚤来,怎么分辨它的牝牡?除非跳蚤会说话,自称它是生某某或者妾某某。纵然如此,你还不知道它是不是说了实话,因此你只能去查它的户籍——这又是很糟糕,跳蚤的户口本人怎能看见?就算能看见,人也不认识跳蚤文。所以只好再提一个跳蚤当翻译。你怎么能相信这样的翻译?跳蚤这种东西专吸人血,完全不可信。”“倘若云母、银丝都杀得了人,用一根头发就能把人脑袋勒了去。试问人身子是豆腐做的吗?原来女娲造人是这么一个过程:她老人家补天之余,在海边煮了一大锅豆浆,用海水一点,点出一锅豆腐来,这就是咱们的老祖宗。女娲娘娘不简单,一只锅里能煮出男豆腐和女豆腐,两块豆腐一就合,就生下一个小豆腐?真他妈的岂有此理。玉皇大帝坐在九天之上,阎罗大帝坐在冥罗地府,主管人的福禄生死,原来是两家合资开了个豆腐坊……”“强盗响马见了你不咳嗽,你是止咳丸吗?我读遍了药书没见有这么一条,秃和尚,性寒平,镇咳平喘,止痰生津,不须炮制,效力如神。是药王爷爷写漏了,还是你来冒充?就算你是止咳丸,吃了才能生效,怎么看一眼也管用?你不如去开诊所,让普天下的三期肺痨、哮喘症、气管炎、肺气肿的病号排着队去看你的秃脑袋。”在这里,王小波有意把“大前提”安放在一个极为荒谬、可笑的想法上,然后由此戏剧性推衍,结论自然可疑可笑。
强烈的游戏精神加上层出不穷的幽默感,使王小波的小说呈现出一种“轻逸”,它抵抗着重,同时抵抗着沉闷和一切僵化的可能,它让石头变成石头的对立面——王小波在他的小说中“再造”了一个和“这个世界”不太一样的世界,那是梦和现实相互交织并有了新的诞生的新世界,哪怕它不是《夜行记》这样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