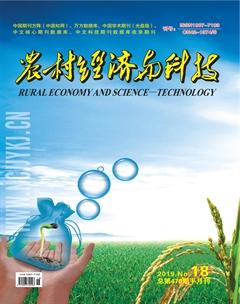甘肃民族地区民间资本参与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研究
王超 谢佳 蔡琪瑶
[摘 要]农村金融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的一个难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无法有效动员民间资本力量合法地参与农村金融活动。民族地区存在能够有效约束参与者违约行为的包括村庄信任在内的非正式制度,民间资本参与农村金融能够充分利用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效率,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成立的农村产业发展互助社,就是基于当地的“村庄信任”,把民间资本引入到农村金融而进行的制度创新,运行效果较好。本文基于对临夏农村产业互助社的实地调研,对该组织进行剖析,以为民族地区民间资本参与农村金融制度创新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
[关键词]民族地区;民间资本;农村金融
[中图分类号]D922.28 [文献标识码]A
长期以来,农村金融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理论界和政策设计者的一个重大难题。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传统的金融理论主要是基于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内,仅考虑利率、成本、风险等因素,从这些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往往较为悲观,认为农村金融风险大、成本高而收益较低,不符合金融的效率原则。因而,传统的金融理论既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各地的农村金融实践,也不能很好地指导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从而使得中国金融体系缺乏包容性,数量巨大的农村居民作为弱势群体被排斥在金融体系之外。不可否认,占据现代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建立了完整系统的分析框架和精密严谨的程式化话语体系。主流经济学对于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的善意回避,使其在对中国农村金融的分析中,忽略了各地农村源于传统“乡土社会”特有的信任结构及其作用路径,从而导致主流经济学无法对中国农村金融的现实作出正确的观察和解释。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在既定制度约束下的收益最大化问题,强调资源的配置效率而忽视经济发展的公平性与普惠性。因而,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下,农村金融由于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不利于金融资源的优惠配置,从而在“效率优先”的背景下农村金融受到较大的抑制,数量巨大的农村居民被排斥在金融体系之外,在抑制农村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拉大了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尝试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把农村地区的社会关系网络、村庄共同体、信任结构、社会资本、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等因素纳入到农村金融的理论分析中,并借以解释中国农村金融创新的实践。笔者借用胡必亮(2004)提出的村庄信任的概念,结合临夏州作为回族聚集区的特殊区情,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以下简称临夏州)产业发展互助社的实地调研为基础,来分析民族地区农村金融合作组织的创新实践。
1 临夏州农村产业发展互助社成立的基础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平均海拨在2000米以上,境内山谷多、平地少,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大部分地区气候属于温带半干旱气候,西南部山区高寒阴冷,东北部干旱,年均降雨量537毫米,蒸发量1198至1745毫米。临夏州东临定西市,西倚青海省,北濒兰州市,南靠甘南藏族自治州,是甘肃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汉藏贸易枢纽,在藏区与内地的经贸往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全州面积8169平方公里,人口215万人,有回、汉、东乡、保安、撒拉、土、藏等31个民族成分,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9.2%,信仰伊斯兰教的回、东乡、保安、撒拉等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57%。全州人均耕地仅为1.07亩,70%以上的耕地分布在干旱半干旱区和高寒阴潮区,农业生产条件较差,贫困人口92.02万人,贫困面达52.04%。
临夏州较差的农业生产条件,使得当地农村居民外出经商的比例较高,长期的外出经商传统,使得当地居民具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意识及市场经济的知识,也使得当地居民经常会遇到资金闲置或短缺的状况,因而在当地更容易形成资金的相互拆解关系。这种资金供、求状况,就成为在临夏农村成立产业发展互助社的经济基础。临夏州作为精确扶贫的重点地区,扶贫任务重,需要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以提高金融扶贫的效率,在此背景下,政府更有义务和积极性推动产业发展互助社来满足金融扶贫的需要。
2 临夏产业发展互助社的运行状况
临夏产业发展互助社成立于2013年初,2013年5月开始向社员发放贷款。互助社主要由政府牵头组建,目的是为了解决农村居民融资难、贷款难的问题,每个村级产业发展互助社政府注资50万元,本着入社自由、退社自由的原则,社员入社最低出资额为1000元,社员必须为本村长住居民,提交申请必须要经筹备小组审核批准后才能入社;并要求每个村级互助社吸引一个企业社员,企业社员的注资最低5万元,最高49万元,另外,精确扶贫的双联干部、双联单位也可注入一定金额的互助金。互助社运行中设理事会、监事会,并定期召开社员大会进行议事、监督。业务主要是向社员提供小额信贷,为了控制风险,借款原则上不超过5万元,期限多为一年,原则上不超过2年,借款农户要缴纳6%左右的占用费,其中3%作为入社资金的分红,剩余3%部分主要用于运行费用、提取坏账损失以及作为增值转作互助金本金。在借款时,要求有同社5户形成联保小组进行担保,借款农户违约后由担保农户承担偿还责任。
以临夏县调研的两个乡——安家坡乡与先锋乡为例,安家坡乡包括安家坡村、北小塬村、中寨村以及史娄村四个行政村,先锋乡主要包括前韩村、卢马村、张梁村等九个行政村,都建立了村级产业发展互助社。从表1中可以看出,各村社率都在60%以上,说明村民对于产业发展互助社的认可度较高;互助社的资金除了政府注资50万元外,主要由合作企业注资以及社员入社缴费构成,其中安家坡乡北小塬村还获得151万元的社会捐赠,为互助社的资金来源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从借款情况来看,各村产业发展互助社能夠较好地满足社员的信贷需求,运行三年来,累计借款额都已超过互助社资金总额,说明互助社的资金循环状况较好,能够有效地保障互助社财务的可持续性。
而根据笔者带领学生对于三个村子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随机走访的168户居民中,获得信贷支持的为88户,占调查户数的52.83%,其中获得互助社贷款的用户为36户,占受访农户的21.42%;贷款超过2万元的农户有36家,最高的为6.5万元(其中从信用社借款5万元,互助社借款为1.5万元),说明互助社已经成为农户重要的信贷途径;而未成立互助社的两个村子,获取贷款的农户为108户,占总数的34%,远低于上述成立互助社三个村子的比例,在考虑到广河县城关镇赵家村就在县城边缘,房产等资产的抵押功能较强的因素,更能看到互助社对于农户获取贷款支持的巨大作用。在对于信贷用途的问题中,有28家选择为“养殖、购买饲料”,有24家选择“做生意”,有16家选择“家中有病人、看病用”,有12户选择“孩子上学”,4家选择“孩子结婚”,8家选择“建造住房或购买住房”,还有8户用作生活费用。其中,生产性用途的农户为52户,占贷款农户总数的59%,说明临夏州农村居民从金融机构贷款的主要用途为生产性用途,其中,从互助社获取过贷款的农户为56户,全部用于生产性用途上,说明产业发展互助社对于农户的生产经营具有较好的支持作用。在80户没有贷款的农户中,有40户选择未贷款的原因为“不需要”,40户表示“怕到期无法偿还”,32户表示“不愿承担利息”,有8户表示“无法提供抵押品”, 4户选择“手续复杂、难申请到”,4户表示“要找关系”才能借到,说明在有产业发展互助社的地方,农户没有贷款的原因主要是来自农户自身需求方面的信贷约束有80户,而表示是供给端的信贷约束仅有16户,占总数的17%;而未成立互助社的两个村子,则仅有40户表示“不需要”,8户表示“所借金额小、划不来借贷款”,有52户表示“手续复杂、难申请到”,有60户表示“要走关系才能申请到”,有44户表示“怕到期无法偿还”,20户表示“不愿承担利息”,24户选择“无法提供抵押品”,其中原因在供给端的农户为136户,占总数的55%,远大于成立互助社的17%,说明产业发展互助社的成立能够有效克服农村信贷难的问题。
3 临夏州农村产业发展互助社的政策启示
在建设中国普惠金融的大背景下,基于临夏产业发展互助社的运行经验,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在民族地区的农村,由于市场经济发展滞后,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必要的金融制度创新很难在落后的农村地区自发地产生和演化。落后地区农村居民对于政府的超强信任,使得政府理应成为推动当地金融制度创新的最佳选择,通过合理的制度顶层设计,能够有效地推动当地金融制度创新。
(2)民族地区农村金融制度创新,要充分考虑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征,特别是要考虑“信任结构”、“社会资本”以及“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结合当地非正式制度的金融创新,不仅能够保障金融体系的“普惠性”,而且也能够发挥金融体系的“效率性”,保障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3)基于农村“信任结构”“社会资本”等非正式制度金融创新的核心是构建信任条件下无限次博弈关系,通过居民之间长期的信任关系来克服其短期“投机主义”倾向,充分发挥农村“闲言碎语”的信息传输功能和惩处功能,对于违约 农户的信息要及时在村落内部进行公示,加大违约农户的信誉损失。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 布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3] 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J].经济体制比较,2002(02).
[4] 王曙光.市场经济的伦理奠基与信任拓展——超越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3).
[5] 张维迎.法律制度的信誉基础[J].经济研究,2002(1).
[6] 周霞.传统与现代农村社会信任结构解读——基于布迪厄场域理论视角[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0(03).
[7] 胡必亮.村庄信任与标会[J].经济研究,2004(04).
[8] 刘峰,徐永辉,何田.农户联保贷款的制度缺陷与行为扭曲:黑龙江个案[J].金融研究,2006(09).
[9] 赵岩青,何广文.农户联保贷款有效性研究[J].金融研究,2007(07).
[10] 李涛.社会互动、信任与股市参与[J].经济研究,2006(01).
[收稿日期]2019-06-30
[基金项目]本文系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甘肃民族地区民间资本发展研究(编号:YB018)及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基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超(1979—),男,河南永城人,副教授,研究方向:金融經济学;谢佳(1995—),女,山东青州人,硕士;蔡琪瑶(1994—),女,河北承德人,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