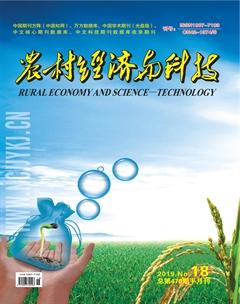“乡村软保护力”与国家强制力的博弈
赵中轩
[摘 要]本文试图运用博弈分析框架,以乡村政治秩序的建构为主线,探求以乡村文化网络的凝聚内力和以乡村精英领导的对抗张力为核心特征的“乡村软保护力”与国家强制力之间的互动逻辑,从而解释这一因素在乡村治理格局中的有效性,探寻在国家能力建设及乡村政治体系变迁过程中,村庄单元的自我保护能力的作用。
[关键词]乡村精英;乡村软保护力;国家强制力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根据传统的历史发展脉络,我国国家力量的建构有着向乡村社会渗透权力触角的因子,借助对基层乡村的严控,以保证对乡村治理的主动权以及社会资源的提取。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的场域整体呈现出“国家在上、相对分离”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下,国家强制力掌握着主动权。但与此同时,中国乡村长久以来在利益争取上和资源自卫上也探索出了特有的表达途径,形成了独特的自我保护力。这种自我保护力是以乡村文化网络为凝聚内力和以乡村精英为领导的对抗张力为核心,以保护自身生存利益而非攻击为目的,与国家力量的强制性有所区别,笔者认为称其为“软保护力”更为合适,以笔者实证调查为例:
家户制度调查期间,根据对笔者祖父的口述访谈得知,笔者曾祖父乃行武出身,闯关东至辽宁省阜新市韩家店定居以后,投身奉军帐下,在奉军中表现勇武,得到东北王张作霖的赏识,后被保送进入东三省讲武堂,即后来的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先后担任骑兵科排、营、团、旅、师参谋长,上校军衔,后任骑兵师长驻防内蒙通辽。康为民(曾祖父)驻军内蒙期间,每年只有过年才能回家,回到村里,地方政要都要设宴宴请,以表重视。康家作为当地其中一家大户,借助积累的财富、名望和权威,与商业地主刘家并驾齐驱,在村庄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在战争时期对当地村庄提供防卫功能。笔者将这种作用力概括为“乡村软保护力”,本文试图分析“乡村软保护力”与国家强制力的互动逻辑,探寻在国家能力建设及乡村政治体系变迁过程中,村庄单元的自我保护能力的作用。
1 精英治理理论
社会学家帕累托认为无论怎样的政体,都会被一小部分精英群体所治理,拉斯维尔则发展完善了早期政治精英理论,对该群体的统治方式进行了有益分析。在中国传统政治秩序中,所谓乡村精英就是在村庄治理格局中占有一席之位,在底层民众中拥有权威及决策影响力的领导人物,可通过各种治理单元实施行动与决策,从而实现治理目标、完成资源分配。本文所指的乡村精英其实是一种比较狭义的精英概念,仅指乡村政治精英。
士绅是本文所指乡村精英中的典型代表,这一群体在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治理中发挥着核心力量。在乡村阶层中,士绅作为乡村基层的一种特殊的精英群体,游走在国家政治与乡土社会的场域之间,发挥沟通媒介的作用,实现其治理功能。费孝通等人在《皇权与绅权》一书中总结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皇权—紳权的二元权力结构”,而这种绅权无疑就是一种长老统治方式,是地方权威的代表,承担着地方治理和教化等功能。秦晖笔下的“大共同体”社会在历代政治变迁过程中还带有某些精英治理的特征,伴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流动,这种治理模式在当前语境下又蕴含着新的意义。
经过长期的演变,乡村精英治理形成了一个鲜明的特点,即维护自身发展的独特性又要与国家保持协调一致,同时也会遭遇国家力量的管制。基于国家刺激的反应和谋求自身发展的需求,乡村精英往往依靠在草根群众中的地位和威望,以村庄为单位,增强辐射带动能力和权益保护能力,促进村庄内生性发展,作为基层社会对强国家治理的行为反应。
2 “乡村软保护力”
李怀印关注早期华北地区的国家政权建设,他以河北省获鹿县为例,揭示在这个建设时期,国家正式权威与这种地方草根辩护力一直进行互动。国家通常需要依赖具有凝聚力和归属感的农村共同体为工具,并配合以利益引诱等技术手段,来缓和国家制度力量与地方当权者的矛盾冲突。国家力量对于自身合法性的渴求给予了乡村自生保护力滋长的契机,可以从向内聚力和向外张力两个维度提炼探讨乡村社会对于国家强权统治的软保护力。
2.1 内向合力
我国农村社会整体来看,的确是相对比较封闭的,根据黄宗智对日本满铁村庄调查的研究可以论证这一特征,我国华北地区的乡村模式较为封闭、内聚、紧密。
因此如果从内部考察乡村的自生保护力,将会发现由点及线再到面的内向合力的产生线索。
2.1.1 点——个体宗族传承
从个体宗族传承的意义上讲,个体是任何一个社会或者群体的基点,中国人向来重视血脉传承,在各具特色的宗族文化仪式活动中强化宗族意识,并通过个人血缘纽带连接和传递宗族情感,这种从个体出发的对宗族的认同感是农村凝聚力的基础,可以促进农民行动力量的整合,产生集体行动。
2.1.2 线——礼俗准绳约束
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具有很深的传统性和文化保守性,在这个面对面的社群中,人们按照“无为而治”“礼治秩序”和“长老统治”的方式进行治理,在这个“无讼”社会中,礼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礼俗就像是一根看不见的准绳,维系着乡村的秩序,成为乡村凝聚力的内核。
2.1.3 面——文化网络保护
传统中国农村的文化网络是基于以本人为中心的血缘、乡缘、地缘、学缘、业缘等为基础的“关系式”文化网络结构。其中每一个个体可以通过其“关系网络”而搭载成集体,并借助内化于心的传统村落文化的指引产生行动力量。即使是集体化时期,人民公社制度虽然已经完成在农村地区的渗透,但各种传统文化因子仍然发挥着支配力量,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个性、传统的村落习俗仍然活跃在农民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刻影响着农民的生存和发展。
除了中国乡村传统的文化网络外,杜赞奇对文化与权力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他认为,“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政权建设往往伴随着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汲取能力的增强”。各种象征符号、思想观念等都具有政治性和权威性,并借助各种宗教、宗族组织和庇护、雇佣关系等网络对底层农民施展权力,这种“权力的文化网络”是地方士绅进行有效治理的合法性基础。